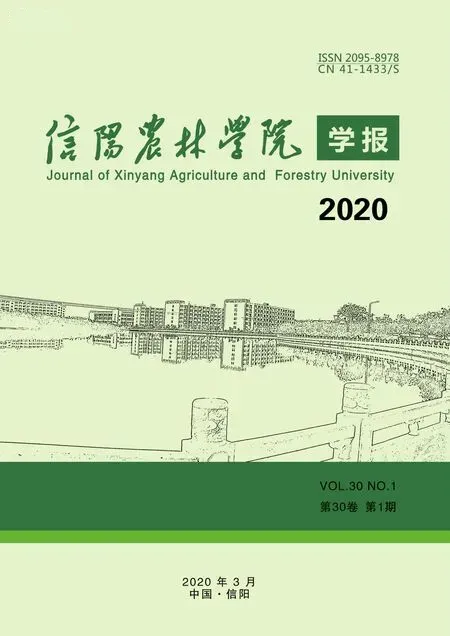身份、殖民與和解
——論《神秘的河流》的空間敘事
左佳
(安徽大學 外語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澳大利亞作家凱特·格倫維爾(Kate Grenville)發表于2005年的小說《神秘的河流》運用宏大的歷史敘事講述了英國底層人物索尼爾為了生存不得不犯罪偷竊,因此被流放到澳大利亞,重新開始人生和建立家園的故事,小說直面早期殖民歷史中白人殖民者對土著的血腥屠殺和暴力行為,公開承認白人殖民者所犯下的罪行。作者借助白人殖民者索尼爾個體的命運發展,重構了一段發生在“澳洲歷史上流血的秘河”[1]上的沉默已久的殖民歷史,希望通過本書向土著居民說一聲“對不起”[2]。該小說于2006年獲得英聯邦作家獎和邁爾斯·弗蘭克林獎提名。白人殖民者索尼爾從倫敦被流放至悉尼經歷了大幅度的空間位移,在重獲人身自由后占領“無主地”,與土著居民爭奪生存空間,導致最后白人與土著劃定界限,在空間上形成二元對立。然而土生土長于澳洲的白人殖民者后代與土著的和諧相處,打破了二元對立狀態,開創了第三空間。小說中空間場所的頻頻轉換,人物意識與小說空間的互動,使得小說充滿張力與空間藝術化效果。
20世紀下半葉,人文社會科學中出現了空間轉向,成為敘事學界關注的焦點。1945年約瑟夫·弗蘭克(Joseph Frank)在《現代文學的空間形式》一文中提出了“小說中空間形式”(spatial form)的概念,標志著空間敘事理論的產生。1974年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其著作《空間的生產》中對空間的社會屬性以及資本主義空間生產給予理論和政治重視。1984年加布里爾·佐倫在《走向敘事空間理論》中將敘事空間看作一個整體,在垂直維度上將文本空間結構劃分為三個不同的層次,文章對敘事文本中的空間結構論述復雜卻又完整,細致而又嚴謹。1996年愛德華·W·蘇賈(Edward W.Soja)的《第三空間:去往洛杉磯和其他真實和想象地方的旅程》將空間性的概念擴展到了權力關系以及階級、性別和種族的壓迫形式[3],拓寬了我們對空間概念的認識,其中“女性主義”和“后殖民主義”對“第三空間”的理論發展和批判實踐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為我們了解空間提供了多重選擇。本文從加布里爾·佐倫的地志空間,列斐伏爾的社會空間和愛德華·W·蘇賈的第三空間概念出發,解析小說《神秘的河流》中的空間敘事。
1 地志空間的移動:人物身份的重構
加布里爾·佐倫在《走向敘事空間理論》一文中劃分了文本空間結構的三個層次:地志學層次,即作為靜態實體的空間;時空體層次,即事件或行動的空間結構;文本層次,即符號文本的空間結構[4]。簡單而言,地志空間即我們通常所說的物質的或物理的空間。
空間是強有力的社會隱喻,空間的移動往往暗示著人物身份的轉變。索尼爾出生于倫敦,他的名字被姐姐辱罵成像污垢一樣庸俗,他的人生亦如名字一樣卑微渺小,童年過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生活。在寒冷的冬夜,只有等哥哥睡著后,他才能將毯子拉過來蓋在自己身上。因為肚子被餓得咕咕叫,而被母親和姐姐罵成貪婪又愚蠢的家伙。他羨慕住在斯萬大街并且有著豐衣足食的生活的薩爾一家,沒有兄弟姐妹的薩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擁有各種想要的玩具。在父母的關愛下成長的薩爾,天性善良單純,熱情開朗,如陽光般溫暖著寒夜里的索尼爾。為了謀生,索尼爾跟著薩爾的父親開始了長達七年的學徒生涯,最終娶到薩爾,住進了夢想中的斯萬大街,成為薩爾家中的一員。就在索尼爾以為可以靠著自己的勞動與智慧致富發家時,薩爾母親米德爾頓夫人的一場重病讓索尼爾一家花光所有的積蓄,再也無法負擔起昂貴的房租,從而被迫搬出斯萬大街,再次回到過去饑寒交迫的生活。索尼爾一家從溫暖寬敞的斯萬大街重回到簡陋逼仄的小巷中,居住地點的空間變化暗示著索尼爾從一個做生意的自由人再次淪為出賣體力的雇工,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中最底層的勞工階級。在倫敦,索尼爾忍受著冰涼的海水、關節腫脹的疼痛,為上層社會的紳士小姐服務。他預見到年老時的自己在巴洛養老院蜷縮著身體蹣跚而行,卻無力改變命運。作為典型的社會邊緣人物,在大英帝國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索尼爾始終無法靠自己的勞動和智慧實現夢想,只能被貧窮的生活所壓迫。“一個船夫所得的工錢是難以養活妻子和孩子的。大多數船夫都偷東西,盡管有人做得天衣無縫。”[5]為了養活家人,他和工友一起偷運船上的木材。“索尼爾感到身體里一陣空虛,他經常會有這種感覺,無論自己做過多少次違法的事情都是如此:恐懼和貧困交織在一起,讓他頭昏眼花。”[5]盡管他無法認同偷盜的行為,卻因為窘迫的生活不得不持續墮落下去,最后因為盜竊罪以大英帝國的“棄兒”身份被流放至澳大利亞。
索尼爾的人物身份也隨著大幅度的地志空間移動和空間轉換而發生改變。這不僅僅是從寒冷的泰晤士河邊到炎熱的悉尼,從人口密集的文明中心倫敦到荒無人煙的地理位置的移動,這是從舊世界到新世界,從一個既定的、熟悉的、由資本主義經濟塑造的階級固化的空間,向一個不確定的、邊緣陌生的、尚未被發展和構建的流動的空間的轉換,這種空間轉換的過程正是索尼爾身份重構的過程。“因為在霍克斯布里河,沒有誰比誰強。在那片隱秘的山谷里,他們大家都是刑滿釋放的犯人。在那里,只有在那里,人不需要拖著條死狗一樣,拖著自己那段不光彩的過去。”[5]盡管索尼爾與其他大多數殖民者一樣,都是被流放的囚犯,但是卻以“文明人”的身份在“光著身子,不知廉恥,到處亂跑的野蠻人”[6]土著黑人面前找到種族優越感,他甚至讓土著黑人疤子比爾赤裸著身體跳舞,從而為自己招攬生意。與此同時,索尼爾靠著自己的辛勤努力,在澳大利亞重新開始生活,“一點點運氣,再加上辛勤的勞動:有了這些,就沒有什么能夠阻止得了他們”[5]。他再次白手起家并實現了從一個重罪犯到自由人的轉變。他申請罪犯仆人給自己的運輸事業幫忙,作為主人對仆人有著生殺予奪的權力,再也不是泰晤士河上向貴族們卑躬屈膝的賤民了。他占據了霍克斯布里河岸邊的“無主地”作為自己的領地,驅逐和屠殺土著黑人,運輸事業也發展得蒸蒸日上,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將房子命名為“科巴姆大樓”以象征著紳士的居所,找回他曾經在倫敦丟失的尊嚴。他由一個在舊世界被壓迫和邊緣化的社會底層的勞工貧民,重構為一個在新世界享有權力和名譽的上層紳士和白人殖民者。
小說中格倫維爾用對比的手法表現出地志空間的差異,將英國與澳大利亞兩種地志空間并置,凸顯出兩地的文化和社會形態差異,為索尼爾的身份重構提供了可能性。從倫敦到悉尼的地志空間移動不僅僅是簡單的物理位移,它同時也象征著索尼爾以帝國使者的身份開始了帝國的海外擴張。
2 社會空間的形成:殖民體系的建立
法國思想家亨利·列斐伏爾在1974年出版的《空間的生產》中提出了“社會空間”的概念。列斐伏爾指出“社會空間是一種社會性的產品”[6],強調了空間的社會屬性,在他看來“社會空間”的母體是社會關系,認為空間不僅僅是社會關系發展演變的靜止的容器或者平臺,更是一個動態實踐過程[6],并總結出“社會性-歷史性-空間性”三元辯證法和三位一體的分析架構即“空間實踐”“空間表征”與“表征空間”。
列斐伏爾區分了“自然空間”與“社會空間”,認為空間性的實踐過程是“自然空間向社會空間轉化的過程”[7]。索尼爾一家離開悉尼來到霍克斯布里河岸邊的“無主地”生活,將這片無主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為“索尼爾岬”,以此來宣告占有權。為了讓自己的殖民夢想不被破滅,他否認這片土地早已是土著黑人居住的地方,把黑人種植好的雛菊連根拔起,并將自己帶來的種子摁進泥土中,試圖證明他是最先到達此地的人。同時按照自己的規劃改造原有的自然物,砍伐樹木,建造房屋,開墾荒地,辛勤耕種糧食,甚至在小說的最后建起了水力發電廠,他將“索尼爾岬”不斷擴大和延伸,把這片原始的自然空間改造為發展現代農業文明的社會空間。在標題為“劃定界限”的小說第五章,白人殖民者開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活動即劃界,通過劃界消除土地所有權的流動性和不穩定性,徹底將黑人居住的峽角地區納入殖民范圍。他們使用先進的槍支和彈藥血腥屠殺黑人,暴力霸占土地,通過征服、掠奪、占有、控制和改造土地,構建殖民空間和帝國的殖民統治,逼迫世世代代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土著撤退到保留地里,遭受被邊緣化、被他者化、被殖民的痛苦。
空間表征是構想的空間,是由規劃師、建筑師和政府官員構想出來的[7]。被流放至異國他鄉的索尼爾和薩爾多次構想和規劃他們重回倫敦后的生活空間,例如購買像斯萬大街一樣的住宅、沙發椅,置辦上好的駁船停在碼頭邊,在昂克飯店里悠閑地進餐等關于空間的構想成為激勵索尼爾不斷奮斗的動力,他渴望攢到足夠積蓄衣錦還鄉,在倫敦過上幸福的生活。在意識到回國無望后,發家致富后的索尼爾還原了自己印象中的倫敦,將其從圖紙上搬到現實中。無論是從倫敦訂購的石獅子,客廳里的紅色天鵝絨扶手椅,綠色的絲綢拖鞋等屋內種種裝飾,還是根據自己對柏孟塞的圣瑪麗妓女收容所的記憶而設計的半圓形石階都是對母國的文化和觀念的歸屬和認同。索尼爾一家來自舊世界的文明中心倫敦,作為已經“文明化”的個體,他的空間感知、空間意識以及他在新世界的空間構建,必定是以他在舊世界中形成的“文化代碼和慣例形成的對于世界的感知”為基本出發點的[8]。正如薩爾教育兒子迪克那樣,“他們是野蠻人,我們可是文明人啊,我們從不光著身子到處亂跑”[5]。這些來自文明世界的白人無法認同和接受原始的生活方式,將其視為野蠻和未開化的動物性的他者,為了防御土著侵襲而構造的帶鉸鏈的吊橋和清空周邊灌木叢的舉動,充分說明以索尼爾為代表的白人殖民者仍然生活在被土著威脅的焦慮和恐慌中,而土著黑人杰克依然堅守這片土地,這片土地是他最終的歸屬。小說最后提到的“俯瞰索尼爾的房子,眼前的景色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英格蘭”正是帝國殖民霸權的象征,暗示著白人殖民空間與土著空間的二元對立的社會空間已經形成,這種社會空間最終成為帝國殖民體系發展建立的平臺。
表征空間是藝術家、作家和哲學家視野中的想象和虛構空間、各種象征性的空間[7],通過意象和象征表現出來。在小說的最后,索尼爾建構出一個想象的空間,重新編造了自己的過去,將真實的人生經歷全部抹去。在這個想象空間中,他為英國君主效力向法國運送間諜,在月夜和有錢船主的女兒私奔,一系列虛幻故事樹立了一個帝國精英的高大形象,而這一形象充分體現了帝國優越感,更加有利于殖民霸權的統治和對殖民體系的維護。妻子薩拉一直未能實現重回倫敦的愿望,便將英國的白楊樹、玫瑰、水仙等種在自己的花園中,加以細心照料來緩解自己的思鄉之情,她對索尼爾說“如果我死了就把我埋在這里,那樣我就可以感覺到葉子落在我身上”[6]。她將這片花園想象成自己的家園倫敦,通過白楊、玫瑰和水仙等生長于倫敦的溫帶性植物意象表現出來,死后埋葬在這里滿足了薩爾想象中的葉落歸根,以彌補她此生未回倫敦的缺憾。被迫流落他鄉的生活經歷使薩爾無法獲得歸屬感,始終以“異鄉人”的身份寄居在澳大利亞。
3 第三空間的開創:種族和解的萌芽
美國后現代地理學家愛德華·W·蘇賈在1996年出版的《第三空間》受到了博爾赫斯的短篇小說《阿萊夫》的影響和啟發,提出了“第三空間”理論。同樣,后殖民理論家霍米·巴巴也是“第三空間”的創立者,在其著作《文化的定位》中他從后殖民文化批評的角度出發,在跨文化交流中基于“雜糅性”策略提出了“第三空間”的概念,“既非這個也非那個(自我或他者),而是之外的某物”[9]。霍米·巴巴同時提出的“間隙”、“疆界”等空間概念,是一種空間形式的思想在文化實踐中的“空間轉向”,超越種族差異、階級差異和文化傳統差異,他特別強調這個“間隙”是非傳統空間,而且這個“疆界”不是區隔彼此的鴻溝,而是彼此競相進入、糾纏不休、空間競爭的所在,原本清晰的自我在這里發生了改變,模糊了起來[10],宗主國文化和本土文化在這里相遇交織,產生文化間隙。
殖民者和土著之間由于語言的障礙以及膚色、種族的差異,形成了無法調和的矛盾。然而隨著索尼爾對土著居民的了解日益加深,以及目睹了其他白人殖民者對土著的殘忍折磨,索尼爾心中根深蒂固的歧視也開始慢慢動搖,索尼爾一家對土著居民的態度經歷了從敵視、排斥到同情、理解的過程。但是為了消除內心的恐懼和保護家人的安全,他不得不采取行動,驅逐土著黑人。他參與和見證了以斯邁舍為代表的西方中心主義者對黑人土著的虐待和屠殺,當他親眼看到白人殖民者對黑人女性的折磨和暴行,他們如對待牲畜般用鏈條將黑人女性鎖住后進行毒打和強奸,將其視為自己的泄欲工具,索尼爾心中的良知和平等意識被真正觸動和喚醒。趕走土著黑人之后,白人殖民者劃分了河岸邊的土地,這時候索尼爾的內心卻依然感到不安,無法享受到成就感和勝利的喜悅。為了贖罪,索尼爾給予大腦神智不清的黑人杰克生活上的幫助,卻一次又一次被拒絕。小說最后,索尼爾整日拿著望遠鏡觀看對面的山崖,“索尼爾讓他的身體緊緊地繃著,瞇著眼透過望遠鏡觀察,直到眼睛變得干澀難忍他才肯罷休”[5],“他只知道凝視著望遠鏡中的事物是唯一能給他內心帶來平靜的方法”[5]。殖民主體以一貫的霸權方式對土著加以掠奪和殺戮之后,卻渴望看到土著的身影,懷念最初二者相安無事的狀態,并對自己殖民的罪行感到內疚和不安,陷入焦慮之中。這足以說明殖民文化不再處于絕對的中心地位,以居高臨下的姿態界定土著文化,而是進入了影響和被影響的狀態,產生了“間隙”空間,殖民者與土著的關系從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絕對權威和統治逐漸演化為在“間隙”中動態變化與交織。
土生土長于澳洲的小兒子迪克的行為也同樣打破了殖民者和土著的二元對立,開拓了第三空間。“霍米·巴巴把兩個有著不同文化傳統和文化潛勢的社群的相遇看作是發生在第三空間的協商或轉化……這種協商不僅可能產生兩種文化傳統的播撒……而且可能帶來一種共同身份”。迪克出生于澳洲,沒有接受過西方文明的教化洗禮,因此避免了狹隘的種族歧視,他違背父母的叮囑,與土著孩子一起觀看如何鉆木取火,學習如何扔長矛,這樣的嬉戲玩耍讓他感受到了原始生活方式的樂趣和土著文明的神奇魅力。迪克身上毫無“白人至上”的種族偏見,他寧愿受父親的挨打,也不愿意否認土著生活的快樂與自由。這暗示著白人殖民者的后代被土著文化所吸引,兩種文化在迪克身上交匯產生了新的意義,超越了土著與白人空間上的二元對立,開拓了一個開放包容的第三空間。在聽聞到索尼爾等人的暴行后,他憤然離開了父親建構的殖民空間,從此拒絕與父親有任何來往,表示對帝國殖民霸權的拒絕,并跟一向與土著和睦相處的布萊克伍德先生相伴,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開拓了一種既非白人殖民者又非土著的第三空間。
4 結論
在小說的序言中,作者寫道《神秘的河流》是獻給土著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這段以白人視角還原的殖民歷史,將土著和白人之間的種族矛盾娓娓道來,直奔澳大利亞小說中最為敏感和爭議的話題,表達出對土著群體、土著文化傳統的尊重、同情和理解以及對殖民歷史的反思。在一次講座中,凱特·格倫維爾說道“我的祖先被置入一種環境,他不得不進行選擇”[2],她將索尼爾塑造為白人社會的邊緣化他者,以示弱的方式講述殖民者走投無路的無奈境地與犯下殖民暴行之罪后所經受的痛苦的煎熬和懺悔,以此促進土著和白人之間的互相理解和互相同情,并且以白人后代對待土著的友好表達出種族和解的希望。正如作者所說“我希望這部小說能夠跳脫二元對立的極端模式,抓住作為一個統一的民族我們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和歷史學家們不同,我要另辟蹊徑,創建一條互相理解、互相同情的道路”[11],《神秘的河流》為推動澳大利亞種族和解,共同建構澳大利亞的民族屬性作出了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