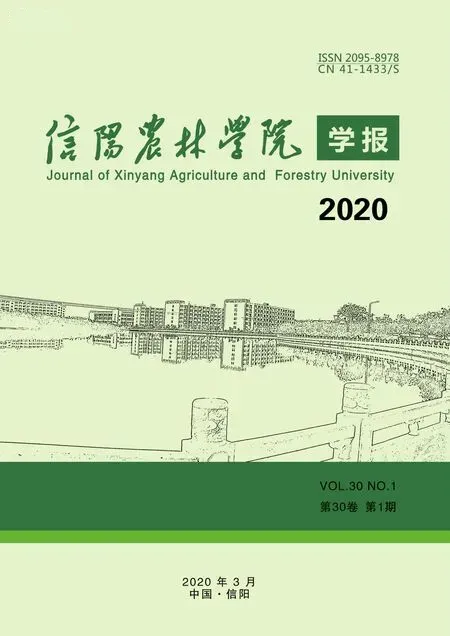“中國形象”與套話再造:《花木蘭》與《功夫熊貓》的敘述比較
強(qiáng)若蘭
(西華師范大學(xué) 文學(xué)院,四川 南充 637000)
為了豐富動(dòng)畫電影的素材種類、擴(kuò)大電影的市場(chǎng),挪用其它國家和民族的素材、講述異國他邦的故事,成為了當(dāng)前美國動(dòng)畫產(chǎn)業(yè)的必然選擇。1998年迪斯尼制作的動(dòng)畫電影《花木蘭》,在全球三十多個(gè)國家和地區(qū)上映,累計(jì)全球票房超過12億美元。由此,美國動(dòng)畫電影開始了一股挪用中國元素、講述中國故事、塑造中國形象的熱潮。但是,這并不是好萊塢動(dòng)畫產(chǎn)業(yè)對(duì)“東方故事”的第一次改編,甚至不是迪斯尼公司對(duì)“東方故事”的初次改編。1992年,迪斯尼根據(jù)阿拉伯神話故事《一千零一夜》制作的動(dòng)畫電影《阿拉丁》,收獲了5億美元的票房,并獲得了奧斯卡、金球獎(jiǎng)、安妮獎(jiǎng)等重要獎(jiǎng)項(xiàng)。1994年,迪斯尼制作的《獅子王》,又收獲了超過42億美元的全球累計(jì)票房,并得到了主流媒體的普遍認(rèn)同。
不難看出,好萊塢動(dòng)畫產(chǎn)業(yè)已經(jīng)擁有改編東方故事的嫻熟手法。但是,在歐美深受好評(píng)的《花木蘭》,進(jìn)入中國大陸卻“遇冷”,中國觀眾拒絕承認(rèn)其“中國血統(tǒng)”。而2008年美國動(dòng)畫電影《功夫熊貓》卷土重來,在中國卻收獲了高額票房,受到中國觀眾的普遍喜愛。“花木蘭”和“熊貓阿寶”形象,在美國電影中作為文化上的“他者”,但同樣是“中國形象”的挪用與再造,它反映出美國動(dòng)畫業(yè)塑造中國形象的過程中兩條相互重疊、又各有規(guī)律的線索。
1 美國動(dòng)畫中的“中國形象”
在1950—1966年的第一次繁榮之后,由于迪斯尼對(duì)行業(yè)的壟斷等原因,美國動(dòng)畫走向了長(zhǎng)達(dá)21年的蟄伏期。1989年,以迪斯尼動(dòng)畫《小美人魚》為標(biāo)志,美國動(dòng)畫業(yè)進(jìn)入第二次繁榮。迪斯尼公司開始講述東方故事,為復(fù)蘇的動(dòng)畫業(yè)注入新鮮血液。1992年,迪斯尼推出了幽默詼諧的東方故事劇《阿拉丁》,迅速開拓了廣闊的海外市場(chǎng)。此后,迪斯尼連續(xù)制作了《獅子王》《風(fēng)中奇緣》《花木蘭》等東方題材的動(dòng)畫電影。夢(mèng)工廠也在這一時(shí)期制作了動(dòng)畫電影《埃及王子》和《功夫熊貓》。通過這些影片,眾多“東方形象”迅速被全世界觀眾知曉。其中,“花木蘭”和“熊貓阿寶”,成為最具知名度和代表性的“中國形象”。
迪斯尼電影《阿拉丁》的主人公阿拉丁,在《一千零一夜》中是一位來自中國西部的年輕人。但在電影中,他被塑造為一位土生土長(zhǎng)的阿拉伯人,從而成為了被剝奪了原有身份的“中國形象”。對(duì)迪斯尼而言,這一改編不會(huì)對(duì)故事的發(fā)展造成任何影響,也不會(huì)使電影的異域風(fēng)情有所折扣。改變主人公的出生地,依然可以滿足美國主流社會(huì)對(duì)東方世界的綺麗幻想。事實(shí)上,1990年代初的美國動(dòng)畫業(yè),認(rèn)為“中國形象”沒有獨(dú)立于“伊斯蘭教”文化之外,沒有單獨(dú)言說的價(jià)值。直到《花木蘭》出現(xiàn),“中國形象”在美國動(dòng)畫電影中才有了第一次正式的亮相。緊隨其后的《功夫熊貓》,也著力刻畫了“熊貓阿寶”這一中國形象。此外,旖旎的中國風(fēng)景、多姿的中國人物,也在這兩個(gè)系列電影里集中亮相,從而呈現(xiàn)了美國動(dòng)畫中“中國形象”的典型類別。
在兩部電影中,“鬼神”化、“妖魔”化的中國鬼神,是挪用所謂文化“他者”的中國元素時(shí)首先追求的“東方奇觀”。《花木蘭》中,花家祖先和木須龍等被供奉在肅穆的花家祠堂里。作為“神靈”的花家祖先,在木蘭一家人心中具有庇護(hù)后代、實(shí)現(xiàn)心愿的力量。經(jīng)過電腦技術(shù)的處理,它們被美國動(dòng)畫公司制造成為一種中國形象的代表。除此之外,這些電影還將兇狠殘暴、詭計(jì)多端的反派角色納入了“中國形象”。正義與邪惡是好萊塢動(dòng)畫中最重要的矛盾關(guān)系,故事在正反沖突中才有講下去的可能。成功地塑造反派角色,也是講好一個(gè)故事的關(guān)鍵。《花木蘭》中詭計(jì)多端的匈奴單于,《功夫熊貓》中的大龍、沈王爺、天煞等,就是這樣的角色代表。他們野心勃勃,善于算計(jì),獲得強(qiáng)大能力后便開始作惡多端。
在被塑造的“中國形象”中,傳統(tǒng)中國文化得到的是“擬人化”的表現(xiàn)。《功夫熊貓》即直接以中國“五行拳”命名五位功夫大師:一身正氣、勇敢無畏的嬌虎,輕盈靈動(dòng)、富有同情心的仙鶴,熱心頑皮的金猴,行動(dòng)敏捷、性格善變的靈蛇,身軀瘦小卻力大無窮的螳螂。可以說,這一抽象事物具體化的手法,在美國動(dòng)畫面對(duì)如何塑造“中國形象”這一問題時(shí)得到了很好的利用。
擁有“典型”中國外貌,卻蘊(yùn)含著美國精神的人物形象,也是被挪用的“中國形象”的重要表現(xiàn)。美國精神的核心是個(gè)人主義,“相信個(gè)人主義就是通過一己之力改變自己和世界”[1],“追求自由、獨(dú)立、平等、民主是美國個(gè)人主義神話的誡命”[2]。因而在電影中木蘭拋棄了利用婚姻改變家庭命運(yùn)和個(gè)人命運(yùn)的傳統(tǒng)道路,毅然選擇了替父從軍。她在軍營(yíng)內(nèi)刻苦訓(xùn)練,期望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huì)里建功立業(yè),追求自由戀愛的權(quán)力。阿寶在影片中,則以中國國寶熊貓的形象出現(xiàn),他遲緩而笨拙,卻堅(jiān)信自己能夠練就絕世本領(lǐng),成為拯救世界的大俠。這一類形象是美國動(dòng)畫著力塑造的故事主人公,也是美國動(dòng)畫中飽受爭(zhēng)議、被中國觀眾認(rèn)為最不像“中國形象”的形象。
另一種代表形象,是智慧開明、高深莫測(cè)的長(zhǎng)者。不少研究者在“東方主義”視野下解構(gòu)美國動(dòng)畫中的中國形象時(shí),聚焦于被妖魔化、被閹割的異化形象或被賦予“美國精神”的故事主人公形象,而忽略了這類溫和慈愛的長(zhǎng)者。然而,這類長(zhǎng)者口中往往說出更加直接的“美國式”格言。例如《花木蘭》中,作為中國古代中央集權(quán)和封建專制象征的皇帝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決定勝負(fù)的或許就是那一人。”這種帶有個(gè)人英雄主義色彩的語句,成為“美國精神”的代言人。由此,花木蘭建功立業(yè)、追求自由戀愛,就取得了合法性、合理性。這一類長(zhǎng)者在動(dòng)畫故事中是“中國形象”的人生導(dǎo)師,他們往往擁有較高的社會(huì)地位和強(qiáng)大的力量,在主人公感到困惑、迷茫時(shí)及時(shí)相助,引導(dǎo)主人公克服困難、實(shí)現(xiàn)夢(mèng)想。顯然,美國文化利用這一類形象表明了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優(yōu)勢(shì)身份,中國則被視為了被“拯救的對(duì)象”。
2 《花木蘭》與東方形象的舊套話
迪士尼1998年改編的《花木蘭》,將木蘭的軍旅生活和利用智慧、克敵制勝的部分,做了大篇幅的詳盡的敘述,并增加了花木蘭與少將李翔的愛情故事。這使得傳統(tǒng)的“花木蘭替父從軍”故事的重心發(fā)生了偏移,忠于君王和孝敬長(zhǎng)輩的故事主題遭到了削弱,電影的主題轉(zhuǎn)向了追求真我、保持天性、反對(duì)傳統(tǒng)觀念對(duì)女性的束縛和壓迫。迪斯尼還添加了木蘭“相親”的橋段,并通過“美式幽默”的手法,將電影定位于以娛樂和消遣為優(yōu)先原則的喜劇,遠(yuǎn)遠(yuǎn)地背離了中國文學(xué)傳統(tǒng)“文以載道”的使命。
盡管中國的《木蘭詩》并沒有描繪出木蘭的外貌特征,但迪斯尼電影所塑造的褐色皮膚、丹鳳眼、厚嘴唇的木蘭形象,與中國讀者想象中的木蘭無疑存在著巨大的差別。回顧美國動(dòng)畫業(yè)對(duì)“東方元素”影視化的歷程,可以發(fā)現(xiàn)不少雷同于“木蘭”的形象。例如,1992年《阿拉丁》中的茉莉公主,1995年《風(fēng)中奇緣》中的寶嘉康蒂公主等,她們都擁有深色的皮膚、漆黑的大眼睛、花瓣?duì)畹呢S厚嘴唇,一頭烏黑亮麗的長(zhǎng)發(fā),以及舒展、健美的四肢。這些重復(fù)形象的塑造反映出,西方世界在認(rèn)識(shí)中國的過程中,存在以伊斯蘭教文化籠罩下的中東指代中國所處的遠(yuǎn)東的現(xiàn)象。
值得注意的是,關(guān)于異國形象的敘述,雖然出自不同的創(chuàng)作者,但這并不是一種個(gè)人行為,而是社會(huì)和群體的共同想象描繪的,是全體社會(huì)想象力參與創(chuàng)造的結(jié)果。木蘭在外貌上的阿拉伯化,即是相當(dāng)長(zhǎng)一段時(shí)期內(nèi)美國主流社會(huì)對(duì)東方形象的整體性想象。這一想象在動(dòng)畫創(chuàng)作者面對(duì)中國元素時(shí)被激活,從而潛移默化地引導(dǎo)著創(chuàng)作者以阿拉伯等地區(qū)的人物形象特征去塑造中國的人物形象。以中東概括整個(gè)東方,甚至是薩義德寫作《東方主義》時(shí)的做法。盡管《東方主義》旨在揭露西方對(duì)東方的文化殖民,反對(duì)一種文明對(duì)另一種文明的遮蔽,然而“薩義德的‘東方’是包括遠(yuǎn)東在內(nèi)的整個(gè)東方,但作為一個(gè)巴勒斯坦人,他對(duì)遠(yuǎn)東并不了解,故采用的材料和論述的重點(diǎn)皆是伊斯蘭文化籠罩下的中東(中國只是作為括弧中的注腳而出現(xiàn)的)”[3]。由此可見,忽略中國的獨(dú)特性、以中東指代遠(yuǎn)東,是諸多不了解中國事實(shí)的國家和民族的普遍做法。
在故事情節(jié)方面,《花木蘭》與《阿拉丁》《風(fēng)中奇緣》等電影擁有類似的結(jié)構(gòu)模式:主人公大方美麗、善良聰慧、崇尚自由,與生長(zhǎng)的社會(huì)環(huán)境格格不入,獨(dú)立追求自己的如意郎君……迪斯尼已經(jīng)形成了一套完備的“公主故事”敘述模式。《花木蘭》不過是“公主故事”的重復(fù)敘述,是美國動(dòng)畫關(guān)于“東方形象”的陳舊套話在中國形象上的生搬硬套。由此也就不難理解,迪斯尼2000年正式推出“迪斯尼公主”概念,將花木蘭與白雪公主、灰姑娘、海的女兒等并列為“迪斯尼八公主”,從而與中國讀者熟知的木蘭形象越走越遠(yuǎn)了。
1922年,美國學(xué)者瓦爾特·利普曼在社會(huì)科學(xué)領(lǐng)域首次使用“套話”時(shí),將它描述為“我們頭腦中已有的先入之見”[3]。《花木蘭》在美國上映創(chuàng)造了當(dāng)時(shí)的票房記錄,這也反映出套話中的中國形象對(duì)美國社會(huì)中的“先入之見”的契合。這種東方外貌、美國精神的人物形象,既符合美利堅(jiān)民族對(duì)中國人物外貌的預(yù)設(shè),又能實(shí)現(xiàn)借由影視作品向世界傳達(dá)國家意識(shí)形態(tài)的目的。但是,美國精神的外在表達(dá)與中國文化內(nèi)涵的矛盾和分裂,讓動(dòng)畫電影中的“中國形象”,在內(nèi)外兩個(gè)層面上與華人所熟悉的形象出現(xiàn)了斷裂,也使得中國觀眾產(chǎn)生了疏遠(yuǎn)感。這種疏遠(yuǎn)感源自中國觀眾的“文化自覺”,他們輕易地覺察出動(dòng)畫電影《花木蘭》對(duì)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顛覆和背叛。正如網(wǎng)易云新聞報(bào)道:“《花木蘭》在中國上映后,反響平平,大部分中國觀眾對(duì)該片不太買賬,在中國人看來,木蘭長(zhǎng)得像個(gè)外國人并且很丑,故事改編也太多,令人難以接受。”
3 《功夫熊貓》與新套話的形成
美國動(dòng)畫行業(yè)以文化他者的身份塑造“中國形象”,試圖阿拉伯化中國形象的做法,由《花木蘭Ⅱ》在中國市場(chǎng)的徹底失敗而宣告破產(chǎn)。美國動(dòng)畫的市場(chǎng)導(dǎo)向和中國觀眾的民族文化自覺意識(shí),迫使其尋找塑造中國形象的新方法。進(jìn)入二十一世紀(jì),中國電影市場(chǎng)的巨大潛力備受關(guān)注,以資本為主要導(dǎo)向的美國動(dòng)畫業(yè)不得不更多注重中國觀眾的審美要求,不得不去尋求塑造中國形象的新方法。事實(shí)上,作為一個(gè)幾度繁榮、成熟的行業(yè),美國動(dòng)畫迅速做出了調(diào)整。2008年6月,夢(mèng)工廠制作的《功夫熊貓》橫空出世,橫掃中國影院。該片在2008年北京奧運(yùn)會(huì)開幕前夕上映,在中國大陸上映3周,累計(jì)票房超過1.82億人民幣,成為內(nèi)地第一部票房過億的動(dòng)畫片。導(dǎo)演約翰·斯蒂文森表示,這是“一封寫給中國的情書”[4],大多數(shù)中國觀眾欣然接受了這一封“情書”。趙柯對(duì)此即有評(píng)論:“如夢(mèng)如幻的中國山水風(fēng)情,古老的武俠傳奇故事套路,再加上國寶級(jí)的超可愛胖熊貓出任男一號(hào),怪不得有人說,《功夫熊貓》簡(jiǎn)直比中國更中國。”[5]
《功夫熊貓》放棄了直接改編中國故事的做法,講述了一個(gè)全新的故事。與《花木蘭》隨意剪裁中國元素、嫁接其他民族元素的做法不一樣,《功夫熊貓》的制作團(tuán)隊(duì)不僅甄選了中國元素的典型代表,而且對(duì)這些典型元素做了符合中國人審美邏輯的整合。影片中的熊貓阿寶,頭戴斗笠、身背竹簍,在外貌上是一個(gè)完整、典型的中國形象。此外,制作團(tuán)隊(duì)還別出心裁地將中國功夫中的“五行拳”,具化為悍嬌虎、金猴、靈蛇、仙鶴、螳螂五種動(dòng)物。再加之,將音樂、美術(shù)、飲食等眾多中國元素整合在一個(gè)虛構(gòu)的世界里,構(gòu)建了能自圓其說的邏輯和完整的美學(xué)氛圍,從而使得中國觀眾認(rèn)為《功夫熊貓》比中國更中國。
事實(shí)上,《功夫熊貓》依然在敘述平凡小人物成長(zhǎng)為“神龍大俠”的“好萊塢式英雄”故事,但創(chuàng)作團(tuán)隊(duì)表達(dá)美國精神內(nèi)核的途徑更加中國化了。影片運(yùn)用香港電影中的“無厘頭”手法,制造喜劇笑料,增加了電影的娛樂性。同時(shí),在美國精神和中國傳統(tǒng)精神之間的選擇也更為慎重,電影努力將中西文化的交集作為了故事的文化內(nèi)蘊(yùn)。例如,阿寶在面對(duì)敵人雪豹時(shí),不再單純地依靠個(gè)人力量取勝,而是聯(lián)合熊貓村的大眾。雖然阿寶向同伴道明,人人都能成為英雄,但他在訓(xùn)練同伴時(shí)“因材施教”,布置人員時(shí)“因地制宜”,顯然是地道的中國方法。雖然影片對(duì)“道”和“俠”的理解還停留在淺顯的層面,但尚能被觀眾接受。
套話通常被認(rèn)為具有持久性和固定性,但并不是恒久不變的。“套話往往只存在于一定的歷史時(shí)期,并不具備那種無限、反復(fù)的可使用性。它們實(shí)際上都經(jīng)歷了一個(gè)產(chǎn)生、發(fā)展和消亡的過程,而這一過程往往與套話生產(chǎn)國對(duì)他者認(rèn)知的變化曲線相吻,也與國與國之間在經(jīng)濟(jì)、軍事、政治等關(guān)系方面的力量對(duì)比的曲線相吻。”[6]服從文化融合潮流和資本指向,以客觀甚至正面、積極的視角,來看待中國元素、講述中國故事,成為美國動(dòng)漫行業(yè)的必然選擇。2008年至2016年,借由三部《功夫熊貓》電影,阿寶的形象已經(jīng)深入包括中國觀眾在內(nèi)的世界影迷的內(nèi)心,美國動(dòng)畫行業(yè)關(guān)于塑造“中國形象”的新套話也開始形成。
美國文化塑造“中國形象”的套話,始終與中美兩國間的關(guān)系保持著高度一致。古代中國文化燦爛輝煌,以孔子、忽必烈等為代表的“哲人王”形象,在十三至十八世紀(jì)的西方各國擁有很高的聲望。至十九世紀(jì),中國國力衰退,被視為專制、貧困、腐朽、落后的代名詞,中國人在西方人眼中變得缺乏理性、陰險(xiǎn)邪惡、道德淪喪。由此,“中國佬約翰”的中國形象套話應(yīng)勢(shì)而生。清末民初,西方在種族歧視、排斥華人和義和團(tuán)運(yùn)動(dòng)的影響下,成吉思汗留給歐洲的恐懼情緒蘇醒,英國作家薩克斯·羅默筆下的“傅滿洲”形象成為這一時(shí)期美國社會(huì)對(duì)華人的刻板印象。此后,美國社會(huì)相繼形成了“紅色威脅”、陳查理、“功夫”等不斷更新的、關(guān)于中國形象的套話。
可以看出,在《功夫熊貓》中逐漸成型的新套話,不僅是美國社會(huì)對(duì)“以中東指代遠(yuǎn)東”錯(cuò)誤的更正,更是依據(jù)客觀現(xiàn)實(shí)的不二選擇。“(形象)既具有個(gè)性與豐富性,又具有原型的普遍性與一致性。”[7]“功夫熊貓”的確有二十世紀(jì)末“功夫”套話的影子,但也存在很大的區(qū)別。二十世紀(jì)功夫電影中的中國形象,往往只作為“中國功夫”的物質(zhì)載體,作為人的復(fù)雜性被“功夫”掩蓋。而以《功夫熊貓》為開端的新套話,則將“中國功夫”作為中國形象的特征之一,試圖塑造更富有人情味的中國形象。因此,《功夫熊貓》電影中所呈現(xiàn)的美國動(dòng)畫產(chǎn)業(yè)塑造中國形象的新套話,不僅僅是相對(duì)于《花木蘭》電影所呈現(xiàn)的好萊塢“公主故事”而言的“新”,也是相對(duì)于自“哲人王形象”“傅滿洲形象”和李小龍所代表的舊“功夫形象”的再次更“新”。美國動(dòng)畫在中國,甚至全球市場(chǎng)取得勝利時(shí),國內(nèi)出現(xiàn)了國產(chǎn)動(dòng)畫應(yīng)借鑒美國動(dòng)畫產(chǎn)業(yè)發(fā)展模式的聲音,提出了“在主題立意上探尋中國民族文化資源與人類共同終極命題的契合點(diǎn),以現(xiàn)代表達(dá)方式和產(chǎn)業(yè)化運(yùn)作思路開發(fā)能夠讓全球觀眾接受的中國元素”[8]之類的觀點(diǎn)。當(dāng)然,這的確是一條發(fā)揚(yáng)中華民族文化的途徑,但是在積極尋求中國文化和世界文明溝通方式的時(shí)候,我們還必須繞開“自我東方化”[9]的陷阱,去把握文化獨(dú)立與融合的度,真正實(shí)現(xiàn)世界文化融合大背景下不同文化間的平等交流和多元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