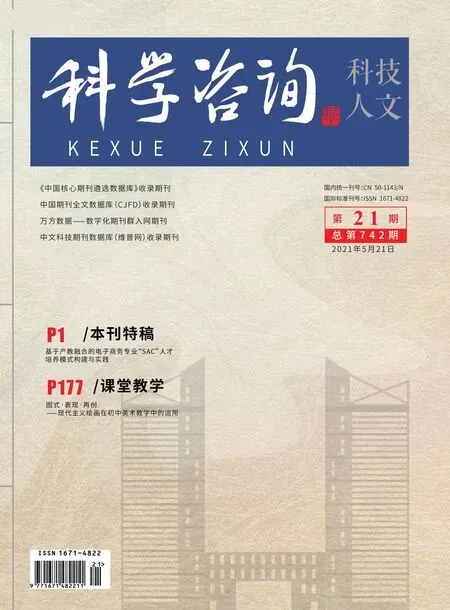對外漢語教學語法體系的歷史源頭與現狀思考
王小穹 王 佳
(重慶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 重慶 400054)
對外漢語教學語法體系的構建從1958年的《漢語教科書》算起,至今有60多年的歷史了。這個體系是在趙元任英文版《粵語入門》(1947年)改寫而成的《國語入門》(1948年)的基礎上,參照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1952年7月至1953年11月連載于《中國語文》的《現代漢語語法講話》,根據教育部1956年頒布的《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簡稱“暫擬系統”)構建起來的。這個語法體系吸收了漢語語法學家的研究成果,總結了語法教學的實踐經驗,因而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實用性和完整性,對后來的教材影響很大。
一、對外漢語語法體系的源頭說明
《暫擬系統》共16節:①詞和詞的構成;②詞類;③實詞;④虛詞;⑤助詞和嘆詞;⑥詞的組合——詞組;⑦句子;⑧句子成分;⑨復雜的謂語;⑩主謂結構作句子成分;?聯合結構作句子成分;?特殊的句子成分;?句子形式的倒裝和省略;?單部句;?復句;?復句的緊縮。《暫擬》的影響和作用是:漢語教材和語文課本的語法系統是根據《暫擬》編寫的,對普及漢語語法知識起到了很大作用;對高等學校的語法教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暫擬》的局限性是,由于考慮到教材應講定論,一些新見解沒有采用,同時由于綜合各家學說,不是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存在一些懸而未決的語法問題。
1958年,由北京大學外國留學生中國語文專修班鄧懿等根據《暫擬》編寫的《漢語教科書》由時代出版社出版。這部教科書包括緒論、語音、語法三部分,其中“語法”部分包括60課、170條語法解釋點。《漢語教科書》是建國以來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對外漢語教科書,是50年代漢語教學實踐的總結,是第一代對外漢語教師集體智慧的結晶。它的最大功績是:使對外漢語教學從對本族人的漢語教學中分離出來,現在使用的語法體系,雖然有了若干變化,但并沒有改變原來的體系。60多年來,《漢語教科書》所確立的語法體系不但影響了中國乃至全世界的漢語教學,而且也影響到今天[1]。
二、對外漢語教學語法的體系問題
半個多世紀前的《漢語教科書》第一次提出了較為實用的漢語教學語法體系。但是該書所確立的漢語語法體系,由于受歷史局限,缺乏對漢語事實與其他語種的深入比較,有不少問題已不再適應現在的對外漢語教學。
《暫擬系統》將“著”“了”“過”稱作“時態助詞”,《漢語教科書》叫做“詞尾”。我們知道,漢語不是形態語言,沒有嚴格意義上“時”的語法范疇;而“詞尾”在形態語言中特指-s、-ing、-ed等屈折詞綴,而且“詞尾”在字面上容易與后附在詞根后面的派生詞綴“-er”“-者”“-子”“-性”“-化”等混淆,現在基本不用“詞尾”這一稱呼了。現在語言學界也不再稱“著”“了”“過”為“時態助詞”或“詞尾”,而是改稱“動態助詞”了,但仍不乏有人維持著“時態助詞”“詞尾”的最初叫法,可見《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和《漢語教科書》對漢語語法教學的影響之深之遠。
1996年《漢語水平等級標準與語法等級大綱》的頒布,標志著漢語語法界已完全接受了結構主義的語法體系。以結構形式為主體的體系,顯得有些單薄和平面化,不能滿足學習者從句法到語義再到語用的主體化的要求。隨著對外漢語教學近半個世紀的發展,結構主義的語法觀越來越多地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對語言事實的無力感。
三、對外漢語語法體系的零存在
對外漢語有無語法體系?當前學界普遍認為,對外漢語教學語法并不表現為系統性,而更多地表現為菜單性。不存在“對外漢語教學語法系統”,僅存在“對外漢語教學語法項目表”。
李泉指出,現有對外漢語教材占絕對多數的是口語和書面語共用的“共核語法”,都缺乏語體意識。無論是詞匯、語匯,還是句法、格式、句式(包括單句句式和復句句式)等都沒有顯示語體屬性。也就是說,這種缺乏區別特征的亦此亦彼的共核語法更多體現的是模糊性而不是系統性[2]。
以上觀點與其說對外漢語沒有語法體系,不如說語言學家們認為這個體系不具備語法體系所應該具有的特性,現有對外漢語語法體系亟待改革。
四、對外漢語語法體系的構建思考
從《漢語教科書》至《對外漢語教學語法大綱》(1995年王還主編),都是在原有體系基礎上的修修補補。要求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新的對外漢語教學語法體系到底如何架構?早在2001年“首屆國際對外漢語教學語法討論會”的大會上,大多數人認為,目前的教學語法體系可以修訂,但最好是另立一個符合第二語言教學的語法體系[3]。
對外漢語語法體系的重建是一個宏大而具體的系統工程,無論是在現有體系三級單位(詞,詞組,句子)的基礎上,向兩頭擴展,增加語素和句群教學,還是建立一種“句型為體,字詞為翼”的對外漢語教學語法體系,或者構建一種以句子為中心,關注句子與短語、句子與句子、句子與語境三重關系的語法體系,或者建立一個由共核語法、口語語法和書面語語法三個方面內容構成的教學語法體系,都需要首先在漢語界形成共識,并在教學中經受得起實踐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