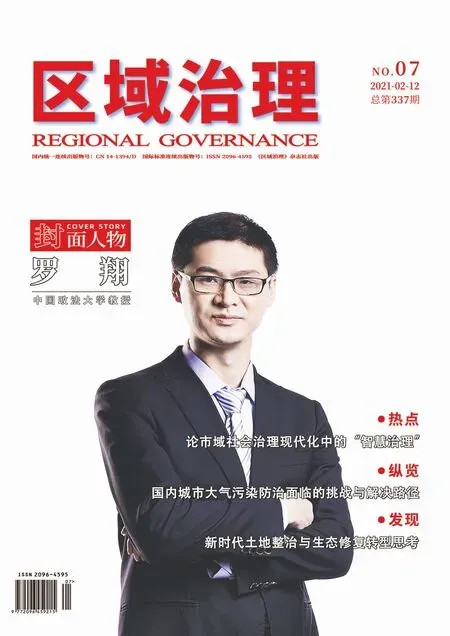國家治理觀的“法”之奧義及實踐啟示*
江蘇理工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劉小剛
它“以‘治道’為研究主題,圍繞治國理民的問題來開展關于‘內圣外王之道’的學問思辨,乃是中國傳統學術的本質特征。其治道的根本目的是為那些稱王的統治者欲成且能成名副其實的‘王者’提供有效治國理民所必需的政治智慧。”對韓非子而言,亦不例外,他繼承商鞅“任法為治”的思想,提出了國家治理“以法為本”的主張。
在韓非子的國家治理觀中,法是為達到治理目的而確立的標準,這種標準是治理過程中對所涉及的人的具體行為或工作情況進行衡量與評價而采取的適當矯正措施的依據。商君之法是韓非子法思想的主要來源。
商鞅主張君主應當通過制定公布統一的法令,“壹賞”“壹刑”“壹教”,最終達到“以刑去刑”,維護君主專制的目的。對于法的產生,他指出,法是適應制止爭奪和克服社會混亂的需要產生的。“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沒,以強勝弱,以眾暴寡,故黃帝作為君臣上下之義,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故時變也。由此觀之,神農非高于黃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適于時也。”
商鞅指出,法應嚴明,有統一的標準。“法者,國之權衡也。”法令如同稱輕重的衡器,量長短的尺寸一樣,是判斷是非功過和行賞施罰的公平標準。因此,圣明的君主要治理國家,使國家強盛,必須“緣法而治”,做到“言不中(合)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在行賞施罰上應公正無私,做到“不失疏遠,不避親近”。如果“授官予爵,不以其勞,則忠臣不進。行賞賦祿,不稱其功,則戰士不用”,而“世之為治者,多釋法而任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只有“立法分明,不以私害法”,國家才能得到治理。而對于民眾百臣來說,“中程者賞之,毀公者誅之。賞誅之法,不失其義,故民不爭”。即行為符合法令要求的就獎賞,破壞法令者就誅殺,賞罰以法令作為明確的統一標準,黎民百官也就不會起紛爭了。
商鞅提出法應公開,將法令公布于眾。主張吏民學法、知法,甚至“為法令置官吏”。他主張頒布成文法,認為“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力求做到家喻戶曉,使得“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這樣,才能使“萬民皆知所避就”。為了強調垂法而治的重要性,商鞅還批駁了儒家的“仁治”,提出仁義不足以治天下。“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于人,而不能使人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而好利惡害,避禍就福是人之天性,只有明法令才能使吏民皆知所避就,即知道什么是法今允許、鼓勵的,什么是法令所禁止的。
在商鞅看來,法是治理國家的根本,只有實行法治,國家才能安定,治理國家不可以一日無法。“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為治而去法令,猶欲無饑而去食也,欲無寒而去衣也,欲東西行也。”法律之所以如此重要,首先在于其能夠定分。“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商鞅認為制止社會動亂的根本途徑是確定人與人之間的財產分界,即定分,然而定分又必須通過法律才能實現。其次法律是實現富國強兵的保證。“立爵而民羞之,設刑而民樂之。”國家通過法律獎勵勤于農事,勇于參戰者;用刑罰懲罰那些惰于農事、不勇于參戰的人。在法律的驅使下,民眾不得不趨于田畝,國家也必然富強。
商鞅認為,為了實現法治,就必須使民眾對法律有所畏懼,其唯一的辦法就是輕罪重罰,嚴刑苛法。“立君之道,莫廣于勝法,勝法之務,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籍刑以去刑。”重刑的目的是以刑去刑。商鞅提出的刑無等級、一斷于法,以及重刑等主張都被后來的韓非子所汲取。
“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在韓非子對法的詮釋中可以發現:第一,法需詳明。“明主之法必詳事。”有了眾所周知的詳盡法律,舉國上下,諸事將一斷于法。第二,法要嚴峻。“峻其法而嚴其刑。”“嚴刑者,民所畏也,重罰者,民所惡也,故圣人陳其所畏,禁其所為,設其所惡,以防其奸,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第三,法不常易。韓非子在《忠孝》中言及:“法也者,常者也。”在《亡征》中也提到:“法禁易變,號令數下者,可亡也。”都說明法不能“朝令夕改”,而要保持“常”的姿態。第四,法必公開。《難三》有言:“法莫如顯。”“是境之民,其一談者必軌于法。”《五蠢》中強調“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第五,法不阿貴。《有度》中指出:“法之所加,知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法對臣民一律對待,不刻意偏袒地位高貴的人。
在韓非子的國家治理觀中,“法者,王之本也。”法是國家治理的根本原則和評判標準,實行治理而沒有法,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效的,猶如工匠造車,“夫棄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法的明晰性可從立法、明法、守法、執法等方面予以揭示。
立法。“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矯上之失,詁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他認為在當下,能夠去除奸私之行而實施國法的國家,百姓安寧,國家太平;能夠去除謀取私利的行為而實施國法的國家,就兵強馬壯。用法來治理國家,合法的就推行,不合法的就舍棄。君主不能放棄法治而隨心所欲。
明法。“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逾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謂之明法。”一個國家要想富強,必須“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宣明法令,治理國家就井然有序,有條不紊,則“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奸不生”,國君“雖暈弋馳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
守法。韓非子認為君主應該“據法而進賢”,“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迸,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故主讎法則可也。”“據法而進賢”,“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只要對國家和臣民有利,就要重用。“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縲紲漫索之中,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能、為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
執法。“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韓非子指出,君主過分仁慈,法制就難以建立;威嚴不足,就要受到臣下的侵害。因此刑罰執行得不堅決,禁令就無法推行。如果沒有公正執法的人,那么法律制定的再周全也無濟于事。韓非子認為執法者要有遠見和明察秋毫的能力,又要有強毅和剛直的性格。“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奸。”還要“大忠”,忠于君主和法律,因為“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于治民者也。”
黨中央強調:“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范社會行為、調節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在國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潤人心。”韓非子在國家治理觀中也注意到了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問題。
韓非子指出:“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圣王之仁義,無益于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治理國家要依靠嚴格的法律,而不是依賴動聽的言辭,只有嚴格的法律才能使國家達到大治。“夫圣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圣人治理國家,要使人們不可任意妄為做壞事。要采用多數人能做到的措施,摒棄只有少數人能做到的設想,應該致力于法治而不是德治。韓非子反對仁者、暴人在位的一些做法。“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仁愛之人為君,人民會放任自己并輕易觸犯法律禁令,以僥幸獲得獎賞或寬恕;殘暴之人為君,法令被其濫用,臣民會離心離德。對此,韋政通有言:“把權力和尊君思想結合起來,雖流弊極大,但對政治問題來說,他是切題的……是政治本身復雜的問題,突破價值之幕彰顯出來,確立政治哲學的獨立領域。”
韓非子理性分析了法在國家治理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再有:“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后窮。”在實行法的過程中,難免會產生一些副作用,但不能因噎廢食“而棄仁人之相憐也”。呂思勉指出:“法家宗旨,一在信賞必罰,一在重刑……重刑非臨時加重,乃重之于立法之先,使人畏而不敢犯,其意亦以求無刑也。法家之旨,凡事當一任法,如衡石度量之于短長輕重。然既設法,固不宜改輕,亦斷不容加重。世以嚴刑峻法為法家之本旨者,實大謬不然之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