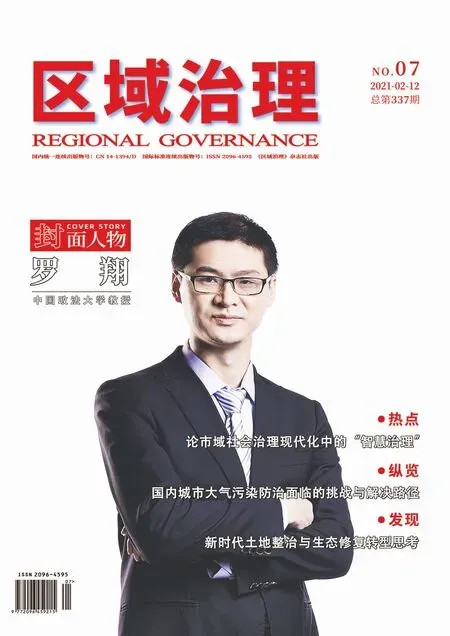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實效性的原因分析
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周笑
當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雖然被反復強調,但其實效性卻不盡如人意。盡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內容與形式的創新也一直處于進行時,但當今高校學子對思想政治教育之偏見與排斥卻始終存在,“強制性”“洗腦”“枯燥乏味”等負面評價似乎成了思想政治教育難以擺脫的標簽。為了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必須走出當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轉變受教育者對思想政治教育的認識。對中國教育學研究對象界定進行歷時性考察則不難發現,中國教育學研究的天平始終傾向認識論意義上的對象性研究,而人的主體性卻在這個過程中被遺忘了,即形成了“人”的缺失。
一、中國教育學研究對象的界定與“人”的缺失
學科的產生應當源于對“是什么”的發問,即對定義與本質的追問最終推動形成了學科的形成,而所謂對定義與本質的追問便是一種對象性意識。故而,對教育學的研究,便是從對“教育學的研究對象是什么”開始的。
1949年至今,對“教育學研究對象是什么”這一問題的回答一共經歷了四個階段。
最初,教育學的研究對象被定義為“教育”。新中國成立后至改革開放前,由于我國缺乏研究經驗,故而對教育學的研究主要是通過向蘇聯學習,全國掀起了向蘇聯學習的熱潮,尤其是凱洛夫主編的《教育學》,對當時教育學研究對象的界定有著深刻的影響。《教育學》中直接表述,教育學的對象就是青年一代的教育。改革開放后,蘇聯巴班斯基主編的《教育學》也被翻譯出版,其將教育學定義為“關于教育的科學”,認為蘇維埃教育學研究的領域是共產主義教育。
之后,教育學的研究對象被認為是“教育現象”或“教育現象及其規律”。在這一階段,我國的教育學有了一定的發展,除了繼續向蘇聯學習,借鑒蘇聯的經驗,我國學者也開始依靠自身的方式和經驗對教育學進行研究。這一階段,我國所編寫的教材中,教育現象及其規律被認為是新的教育學研究對象。
再者,“教育問題”是教育學研究對象這一觀點進入大眾視野。日本學者大河內一男、村井實等人認為將“教育現象”定義為教育學研究對象的提法模棱兩可,含義不清。教育學作為一門科學,其研究對象應當是“教育問題”,通過研究教育問題,揭示教育規律。
最終,以上三個觀點并存。“教育說”“現象說”“問題說”都不乏支持者。
對教育學研究對象的界定進行一個梳理,可得出,教育學研究對象界定的發展脈絡基本遵循“教育說”—“現象說”—“問題說”—多觀點并存。通過這樣一個脈絡,教育學研究“人”的缺失便清晰可見。首先,就“教育說”而言,不難看出,教育是為共產主義建設服務的,在教育過程中表達政治認同與政治訴求是第一要務,教育必須在思想意識面前保持高度的思想統一,這意味著,個性訴求在教育過程中會遭到忽略。其次,雖然“現象說”與“問題說”有所不同,有關兩者的爭論也未曾停止,但是這兩者的目的都是為了認識教育規律,這種規律可以對教育活動進行指導,教育活動也會受到教育規律的約束。但是,當我們默認這種恒教育規律現存時,“人”便從這個教育活動中消失了。因為當我們認為教育活動存在一個客觀的永恒的,足以指導一切教育活動的規律并竭力認識這一規律時,我們便默認教育研究即是一種認識論意義上的對象性研究。我們便只會以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看待教育活動,于是人與教育活動便會分站兩邊。我們無法真正處在教育活動之中領悟教育,而是一直處于教育活動之外,將教育當作單純的認識對象來研究教育。教育活動被視為一種認識活動,“人”便在教育活動中缺席了。
“人”在教育活動中的缺失,具體來說,即是人的主體性在教育活動過程中被忽略。人的主體性可以體現在人的實踐有其目的論設定,目的論設定則是社會過程的起點。目的論設定因人而異,千千萬萬個不同的目的論設定將激發千千萬萬個因果系列,而所有因果系列的綜合才形成了社會規律,這種社會規律是不以個人的目的論設定為轉移的,個人與社會如上所述的關系決定了社會規律完全不同于自然規律。教育作為一種實踐活動,其規律自然不同于萬有引力定律這一自然規律,教育的規律不是現存的,故而所謂的認識教育規律也就無從說起了。
二、思想政治教育三大問題
(一)思想政治教育對象化
思想政治教育作為實踐活動,應當區別于思想政治教育客體化知識的傳授。誠然,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需要客體知識的傳授,但不可將兩者等同。思想政治教育對象化便是將兩者等同的表現,其錯誤地默認思想政治教育規律如萬有引力規律一般現存于客觀世界當中,并認為教材文本是這一規律的載體,便將思想政治教育僅僅限定在教材文本當中,教育者所做的只是向學生正確陳述與傳達教材文本中既定的意義。故而,思想政治教育才會被貼上“枯燥乏味”等負面標簽。
(二)思想政治教育靜態化
思想政治教育也不應當是靜態的思想品德評判標準體系的知識教育。如果僅僅用對象性思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這一實踐活動,同時認為思想政治教育規律是和萬有引力規律一樣的客觀存在,便會理所當然地以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所要求的價值觀同樣是獨立于受教育者而存在的現存之物,那么思想政治教育便會成為靜態的思想品德評判標準體系。在這一過程中,受教育者都必須按照靜態的評判標準體系行事,從而失去自我選擇的自由。
(三)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化
思想政治教育所提出的思想政治層面的要求,如果不能使受教育者真正認同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最終便會淪為人們謀取利益的工具。受教育者會盡力做出符合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的行為,這種行為合乎道德卻并不是出于道德,而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是思想政治教育過程有時過度強調集體的需要而忽略了個人的需要,不得不指出的是,忽略了個人需求的教育是難以引起受教育者共鳴的,更無法使受教育者真正認同,那么人對于此類教育活動的接受只能是因為“不得不”,當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品德要求將個人的需求束之高閣,那么人對于這種思想品德的要求的滿足只能成為其獲得個人利益的手段,而無法化為其內心真正的“善”。
綜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缺乏實效性,是因為在此過程中人的主體性的缺失,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出現“人”的缺失,則是因為我們習慣于以對象性思維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對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應當與自然科學學科的研究區分開來,自然科學學科有著客觀存在的規律,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規律卻不是早已存在、留待發現的,更多的需要人的創造與發動。從對象性思維中走出來才能防止思想政治教育走向對象化、靜態化和手段化的困境。
而如何走出對象性思維呢?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應當開拓人的生活,豐富人的生活經驗,即釋放人的自我,引導人走向生活,充分感受和體驗真實的生活,與此同時,要促使個體觀察自身的思想與行為,關注自身的情緒與情感,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反思、內省。誠如海德格爾所說,對于自我存在的詢問,這本是人之為人的存在方式。推動受教育者走入生活并反思自身有利于推動思想政治教育走向詩意,走向動態化,獲得實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