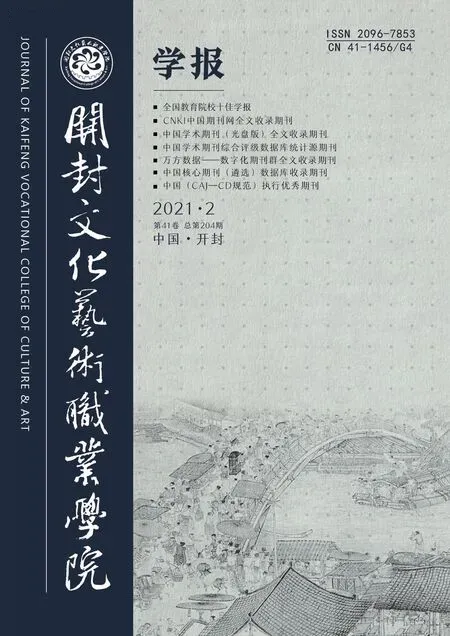失敗的自我救贖:空間批評(píng)視角下的《疾病解說者》
穆 歌
(大連外國(guó)語(yǔ)大學(xué) 英語(yǔ)學(xué)院,遼寧 大連 116044)
《疾病解說者》是美國(guó)印裔女作家裘帕·拉希莉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一經(jīng)出版就頗受好評(píng),并榮獲了2000 年的普利策獎(jiǎng)。小說集包含9 個(gè)故事,每一篇都堪稱精品,本文選取了其中的同名小說《疾病解說者》作為研究對(duì)象。這篇小說講述了達(dá)斯太太在旅行途中偶然得知導(dǎo)游卡帕西的工作是疾病譯解后,向其傾訴了不幸的生活以及隱藏多年的秘密的故事。
“空間就是產(chǎn)品”[1]26是列斐伏爾在其專著《空間的生產(chǎn)》一書中提出的觀點(diǎn),其強(qiáng)調(diào)了空間是可以被生產(chǎn)的以及空間具有極大的社會(huì)屬性。生產(chǎn)的空間“是思想和行動(dòng)的工具;除了作為生產(chǎn)手段之外,它也是一種控制的手段,因此也是一種支配權(quán)力的手段”[1]26。
自我在哲學(xué)中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亞里士多德的“體驗(yàn)說”。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自我是在個(gè)人體驗(yàn)基礎(chǔ)上的自我反思與自我救贖。隨著文藝復(fù)興的發(fā)展,人逐漸成為世界的中心。英國(guó)哲學(xué)家約翰·洛克將自我定義為會(huì)以意識(shí)思考的東西,能感覺到快樂或痛苦,是一種與物質(zhì)相對(duì)的精神實(shí)體。在心理學(xué)上,弗洛伊德提出自我(ego)是人格結(jié)構(gòu)中的行為主宰者“我”,由本我發(fā)展而來,受超我的監(jiān)督,具有協(xié)調(diào)人格結(jié)構(gòu)各部分關(guān)系的功能。但也有心理學(xué)家認(rèn)為,弗洛伊德的自我(ego)并非完全的自我(self)。榮格認(rèn)為,自我(self)是個(gè)性的全部,包含自我(ego)。威廉·詹姆斯認(rèn)為自我(self)包括“物質(zhì)我”“社會(huì)我”“精神我”以及“純粹的自我(ego)”[2]。綜上,自我(self)是包含所有個(gè)性在內(nèi)的精神實(shí)體。
本文將從空間理論切入,探究達(dá)斯太太在家庭空間中被壓抑的自我、文化空間中扭曲的自我以及社會(huì)空間中的自我救贖。
一、家庭空間中被壓抑的自我
“家庭首先總是以一種空間的形式出現(xiàn)”[3],是社會(huì)生活的基本單位。家庭空間與公共空間不同,是個(gè)人私人空間的一部分。因而家庭空間相對(duì)較為封閉,人在家庭中不斷接受著父母、伴侶和孩子帶來的幸福或痛苦。在拉希莉的作品中,“家庭既是與個(gè)人現(xiàn)實(shí)生活密切相關(guān)的社會(huì)單元,也是心理層面的歸屬感”[4]。家庭空間作為一種權(quán)力統(tǒng)治手段,控制著達(dá)斯太太的思想和行為。她在家庭空間中遭受著父母的權(quán)威話語(yǔ)、丈夫的精神壓迫以及生養(yǎng)孩子帶來的肉體負(fù)擔(dān)。
達(dá)斯太太是在父母從印度移民美國(guó)之后出生的,二代移民的身份使得父母成為其最信任和依賴的人,但她“從沒跟他們十分貼心過”[5]66。談到離世的父母,達(dá)斯太太并沒有多少懷念,反而在潛意識(shí)中強(qiáng)調(diào)父母的權(quán)威,如從年少起父母就為自己安排好了和拉茲的婚事,自己也從了父母,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了父母對(duì)子女在話語(yǔ)上的權(quán)威。
達(dá)斯太太在婚前被父母所束縛,在婚后則為兩性關(guān)系所統(tǒng)治。達(dá)斯太太和拉茲結(jié)婚時(shí)還不滿20歲,過早的婚姻生活讓她“整日疲累不堪”[5]66。婚前在大學(xué)里,她把時(shí)間都花在了拉茲身上,因此交心的朋友沒有多少;婚后的生活充滿了爭(zhēng)吵和矛盾,她找不到人傾訴,更不用說開導(dǎo)和安慰了。而拉茲卻只顧著教課,沒有多余的心思放在她身上,達(dá)斯太太陷入了婚后焦慮,“拉茲倒覺得沒什么”[5]66。八年來,她每天都承受著因丈夫的冷漠和無視而帶來的無盡的痛苦,掙扎著在家庭中存活,壓抑著內(nèi)心真實(shí)的感受。或許是想要逃離封閉的家庭空間的束縛,“仿佛她一生都在馬不停蹄地旅行著”[5]49,借此機(jī)會(huì)讓自己暫時(shí)得到一絲喘息。
此外,孩子也是在家庭空間中控制和束縛達(dá)斯太太的工具。羅尼出生后,玩具扔得亂七八糟,“走路須踮著腳尖,坐一坐都得小心扎著”[5]66;達(dá)斯太太耳邊從早到晚充斥著孩子“掙扎著想從學(xué)步車?yán)锱莱鰜淼目摁[聲”,每天照顧孩子忙得四腳朝天,她逐漸“變得煩躁、焦慮,人也長(zhǎng)胖了”[5]66。其間她還婉拒了大學(xué)同學(xué)約她去逛街的邀請(qǐng),“以至于后來人家再也不來找她了”[5]66。達(dá)斯太太的人際關(guān)系因?yàn)楹⒆訑嗟靡桓啥簦毂皇`在家庭中。拉茲“倒還是和從前一樣”,回到家“一邊看電視一邊把羅尼抱在腿上顛著玩”[5]67,沉浸在工作和孩子的喜悅中,卻從未給予達(dá)斯太太一絲關(guān)懷。
家庭空間“既是家庭的宅所,也是家庭的枷鎖。它既讓家庭成員陷入絕望的漫漫黑夜,也讓家庭成員被狂喜所洶涌地撞擊”[3]。達(dá)斯太太在家庭空間中遭受的疲累和煩躁沒有地方發(fā)泄,只能被壓抑著的痛苦所蠶食。父母去世,沒人幫忙分擔(dān)照看孩子的壓力;生活的無望沒有貼心的朋友可以傾訴;丈夫也沒有給予應(yīng)有的體貼和關(guān)注,導(dǎo)致夫妻之間越來越冷漠和疏遠(yuǎn)。對(duì)于達(dá)斯太太來說,家庭像是一個(gè)枷鎖,使之陷入絕望,但出于責(zé)任又不能拋棄家庭,只能在自我壓抑中等待救贖。
二、文化空間下扭曲的自我
文化空間是不同文化之間交流、沖突、融合的空間。米歇爾·福柯將其視為“多層次歷時(shí)性的積淀”;杰克·格林認(rèn)為文化空間是一種物質(zhì)空間或社會(huì)空間,由擁有這一空間的特定群體的一整套相關(guān)行為和生活模式來定義;羅伯特·楊認(rèn)為文化空間是一種文化能夠習(xí)得并得以傳承的框架[6]。文化作為人類特有的精神活動(dòng),其產(chǎn)品本身具有空間性,文化空間強(qiáng)調(diào)發(fā)展演變的歷時(shí)性。
達(dá)斯太太作為美國(guó)印裔的第二代移民,在美國(guó)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對(duì)抗沖突中掙扎,想融入美國(guó)主流文化卻始終未能逃離傳統(tǒng)的處于邊緣地位的印度文化。印度文化主導(dǎo)了達(dá)斯太太的前半生,等待救贖的自我逐漸變得扭曲。
卡帕西在旅行途中看到達(dá)斯夫婦間的不和,認(rèn)為他們可能是“很糟糕的一對(duì)兒”[5]56。卡帕西是土生土長(zhǎng)的印度人,其婚姻也是父母包辦的,兒子的意外去世使得夫妻間的感情日漸冷淡,“吵嘴、冷漠、長(zhǎng)時(shí)間無話可說”[5]56,種種跡象此時(shí)正發(fā)生在達(dá)斯夫婦身上。在印度,大多數(shù)婚姻都是父母一手包辦的,這是當(dāng)?shù)匾环N傳統(tǒng)的婚姻制度和風(fēng)俗習(xí)慣。但是,在美國(guó)出生、接受美國(guó)文化熏陶的達(dá)斯夫婦也未能建構(gòu)自由的婚戀觀,最終接受了父母對(duì)其婚姻的包辦。拉茲和達(dá)斯太太一樣,也是印裔美國(guó)人,相同的文化身份喚起了雙方父母強(qiáng)烈的文化認(rèn)同感,因此,有意撮合各自的孩子。達(dá)斯太太現(xiàn)在想來“總覺得多少是有點(diǎn)像是安排好的”[5]66。父母?jìng)鹘y(tǒng)的早婚觀念以及雙方相同的文化身份使得達(dá)斯太太過早地進(jìn)入婚姻生活,焦躁和不安籠罩著她,精神壓力無處發(fā)泄。
印裔美國(guó)人的文化身份在當(dāng)時(shí)美國(guó)主流文化中屬于由社會(huì)建構(gòu)起來的邊緣群體,地位較低,相互抱團(tuán)取暖是一種尋求自我以及群體安全感的最佳方式。因此,拉茲在得知一位來自旁遮普的朋友要到美國(guó)參加工作面試時(shí),跟達(dá)斯太太說想留他在家中暫住一周,而“她一下子肺都?xì)庹恕保?]67。達(dá)斯太太不僅忍受著因拉茲文化身份認(rèn)同帶來的不便,而且承受著男權(quán)主義對(duì)女性的壓迫。男尊女卑的文化環(huán)境剝奪了夫妻之間的平等交流,達(dá)斯太太也同時(shí)失去了拒絕的權(quán)力,只得默默接受拉茲的提議。也正是朋友的到來使得達(dá)斯太太在家庭空間的重壓下找到了發(fā)泄口,對(duì)家庭的失望使得達(dá)斯太太對(duì)于朋友的挑逗行為“沒有任何反抗,他們手腳利索、默然不語(yǔ)地做愛”[5]67。私生子波比的降生并未讓拉茲對(duì)孩子的身份有絲毫懷疑,達(dá)斯太太把這個(gè)秘密隱藏了整整八年。朋友后來結(jié)了婚,兩對(duì)夫婦每年都會(huì)互寄賀卡并附上一家人的照片。“他不知道自己是波比的父親,一輩子也不會(huì)知道的。”[5]67達(dá)斯太太獨(dú)自一人背負(fù)著秘密,“被它折磨得痛苦不堪”[5]68,逐漸產(chǎn)生了可怕的沖動(dòng)和想要“把一切都拋掉”[5]68的病態(tài)心理。旅途中,達(dá)斯太太在向卡帕西傾訴之后詢問自己是不是病態(tài),并希望他為自己診斷、治病,她內(nèi)心知道自己已經(jīng)接近崩潰的邊緣,并等待著某個(gè)人把自己拉入正常的生活軌道。
達(dá)斯太太的父母遵循傳統(tǒng)對(duì)其婚姻的包辦是導(dǎo)致其自我壓抑和扭曲的直接原因;而達(dá)斯夫婦移民的文化身份使得拉茲邀請(qǐng)朋友暫住家中,則直接導(dǎo)致了達(dá)斯太太和朋友的偶發(fā)性出軌行為,這使得其內(nèi)心的壓抑情感爆發(fā),并形成了想要把一切拋棄進(jìn)而獲得解脫的扭曲心理。印度的傳統(tǒng)文化禁錮、束縛著達(dá)斯太太,雖然其接受了美國(guó)的教育和主流思想,也沒能改變父輩和自己骨子里對(duì)印度文化的認(rèn)同感。
三、社會(huì)空間下的自我救贖
社會(huì)空間是指“社會(huì)的空間,社會(huì)生活的空間”[1]35。社會(huì)空間是由人的日常生活行動(dòng)建構(gòu)起來的,它的本質(zhì)是人與自然和人與人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空間的生產(chǎn)就是社會(huì)關(guān)系的生產(chǎn)與再生產(chǎn)[7]。
達(dá)斯太太和卡帕西的互動(dòng)與交流是其在社會(huì)空間中尋求救贖的表現(xiàn)。達(dá)斯太太在與卡帕西交流的過程中得知他除了導(dǎo)游外還有另一職業(yè),即疾病譯解,因?yàn)楫?dāng)?shù)氐尼t(yī)生不會(huì)講古加拉提語(yǔ),所以請(qǐng)他過去幫病人做翻譯。達(dá)斯太太對(duì)其做譯解的工作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認(rèn)為他可以治療自己的病態(tài)心理。一個(gè)“連三十歲都不到,就已經(jīng)不愛丈夫和孩子,失去了對(duì)生活的眷戀和熱愛”[5]68的女人向第一次見面的陌生人傾訴了自己痛苦的婚姻生活以及隱瞞多年的秘密——波比不是拉茲的親生兒子,而是她出軌后的私生子,并希望從卡帕西那里獲得理解和安慰,從而走向自我救贖。
“八年了,八年來我一直在忍受煎熬。我盼著你能讓我感覺好點(diǎn),講一些寬慰我的話。”[5]68當(dāng)達(dá)斯太太向卡帕西訴說深藏多年的秘密時(shí),卡帕西先生心情沉重,尤其是當(dāng)他想到拉茲時(shí),“這種沉重感就格外加重,壓得他喘不過氣來”[5]69。卡帕西的反應(yīng)表現(xiàn)出他對(duì)拉茲的深切同情而無視達(dá)斯太太的感受。他站在男性的立場(chǎng)上心疼拉茲,妻子出軌還生下了私生子,被蒙騙了八年,一無所知。他認(rèn)為達(dá)斯太太與其他來到診所就醫(yī)的患者不同,沒有“目光呆滯神情絕望”的樣子,她多年的煎熬只是“普普通通、雞毛蒜皮的小秘密”,為她疏解痛苦“像是受到了侮辱”[5]69。
在卡帕西聽到達(dá)斯太太用“浪漫”一詞來形容他的譯解工作時(shí),他感覺受到了從未有過的重視,獲得了巨大的存在感,并被達(dá)斯太太所吸引,一直尋找機(jī)會(huì)要和其獨(dú)處。但是,終究達(dá)斯太太對(duì)于卡帕西來說只是性的吸引而非心靈上的交流,像是利用達(dá)斯太太來疏解妻子對(duì)自己的冷淡,因此兩人溝通的失敗有其必然性。
達(dá)斯太太和卡帕西先生屬于社會(huì)性別中的兩個(gè)對(duì)立面。性別的不同導(dǎo)致雙方難以站到彼此的立場(chǎng)上考慮問題。因此,當(dāng)卡帕西聽到達(dá)斯太太的秘密時(shí),體會(huì)不到其多年的痛苦,只是從男性的視角上問達(dá)斯太太“所感到的,真的是痛苦嗎?還是心有愧疚?”[5]69卡帕西在其潛意識(shí)中認(rèn)為男性在社會(huì)中占據(jù)絕對(duì)統(tǒng)治地位,女性是男性的附屬物,女性做錯(cuò)事情之后只能對(duì)對(duì)方懷有愧疚感而不能有其他的想法。達(dá)斯太太聽到卡帕西的回答,“轉(zhuǎn)過頭來,眼含怒意”,之后卻“停嘴不說了,她打開車門,順著山路就往上走”[5]69。兩人交流的失敗意味著達(dá)斯太太尋求救贖的希望已然不復(fù)存在,她只得重新回歸家庭,繼續(xù)壓抑自我。
小說講述了兩對(duì)不幸的夫妻,而作者在小說結(jié)尾選擇讓兩對(duì)夫妻中的一男(卡帕西)一女(達(dá)斯太太)嘗試進(jìn)行交流,是想要把夫妻間的隔閡代入陌生關(guān)系,觀察是否隨著關(guān)系的改變,兩者之間的交流可以順利進(jìn)行,但最后溝通的失敗凸顯了男性和女性在社會(huì)中處于一種二元對(duì)立的狀態(tài),而男性總習(xí)慣于把女性看作附屬物,兩性關(guān)系的不對(duì)等是二者交流失敗的根源。
達(dá)斯太太自我救贖的失敗是其在家庭空間、文化空間以及社會(huì)空間中相互作用的結(jié)果。家庭空間中父母的話語(yǔ)權(quán)威、丈夫的冷漠以及生養(yǎng)孩子的艱難使得達(dá)斯太太產(chǎn)生了自我壓抑的心理狀態(tài);文化空間中二代移民的文化身份和強(qiáng)烈的文化認(rèn)同感讓達(dá)斯太太從自我壓抑走向自我扭曲的病態(tài)心理;社會(huì)空間中與卡帕西的溝通障礙導(dǎo)致了達(dá)斯太太渴望得到自我救贖的失敗,最后只得重新回歸家庭,繼續(xù)壓抑和隱忍。因此,女性如何消解心理疾病,尋求真我和自我救贖應(yīng)該重新成為值得關(guān)注的社會(huì)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