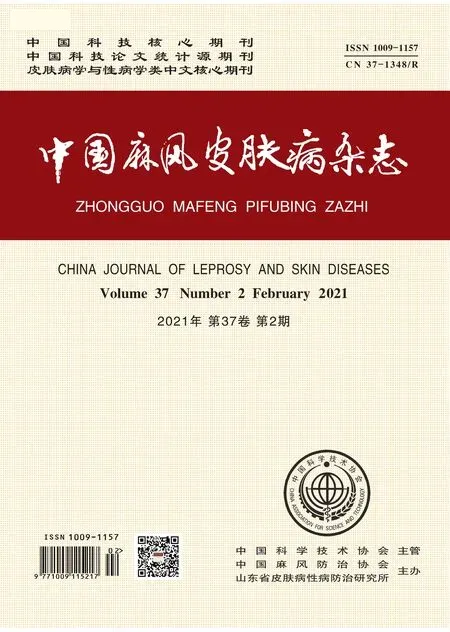化膿性汗腺炎與相關皮膚菌群的研究進展
張 敏 何艷艷,2 徐浩翔
1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 皮膚病醫院(研究所),南京,210042;2江蘇省皮膚性病學分子生物學重點實驗室,南京,210042
化膿性汗腺炎(hidradenitis suppurativa, HS),又稱反向性痤瘡,是一種慢性、炎癥性皮膚病,典型表現是皺褶部位反復發作的膿腫、竇道和瘢痕形成。本病多初發于青春期,國外數據顯示,女性患者居多。HS的病因和發病機制尚不明確,可能與遺傳、免疫、細菌感染、吸煙、肥胖等因素有關[1,2]。近年來,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在HS發病相關的重要皮膚菌群方面有不少新的發現,本文對這一方面的進展進行綜述。
1 正常皮膚菌群
皮膚微生物群是指定植在皮膚上的全部微生物,包括細菌、病毒、真菌、螨蟲、節肢動物等。皮膚是人體最大的器官,一方面作為物理屏障抵擋外界環境中病原的入侵,另一方面為多種微生物的定居提供了環境[3]。盡管皮膚表面呈弱酸性、干燥、缺乏豐富的營養物質,但仍有多種微生物定植,其中細菌的種類和含量最豐富,主要包括放線菌門、厚壁菌門、變形菌門和擬桿菌門[3]。皮膚菌群在門的水平上多樣性低,在種屬水平上呈現豐富的多樣性,且受部位的影響較大。眉間、背部、鼻翼等脂溢部位細菌種類較少,以丙酸桿菌屬為主;手掌、前臂、臀部等干燥部位,細菌種類較多,革蘭陰性菌占優勢;鼻孔、腋窩、指間等潮濕部位,主要是葡萄球菌屬和棒狀桿菌屬[4]。HS好發于大汗腺豐富的皺褶部位,如腋窩、腹股溝[5],這些部位由于多汗、潮濕、皮脂腺和毛囊豐富,更易導致某些細菌定植,它們可能參與HS的發生[6]。
2 細菌與化膿性汗腺炎
2.1 金黃色葡萄球菌與化膿性汗腺炎 金黃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 SA)是一種革蘭陽性球菌,可引起多種感染疾病。Brook等[7]對17例HS患者腋窩皮損研究發現,最常見的需氧菌為SA,占分離出的細菌總數的14%。Lapins等[8]對25例患者進行研究,發現14例患者皮損中存在著SA,其中6例來自深部皮損標本,在2例深部組織樣本中,SA是唯一可被檢測到的細菌。Jamalpour等[9]對26例患者皮損菌群進行分析,也發現SA是最常見的細菌,Matusiak等[10]和Hessam等[11]也有類似報道,患者皮損中SA是僅次于凝固酶陰性葡萄球菌的第二常見細菌。
SA在皮膚中的定植可能因皮脂腺減少,皮脂腺細胞產生的抗菌肽和抗菌脂缺乏[12];且HS患者皮損部位IL-26含量增高,但失去抗菌作用,IL-26抑制巨噬細胞對SA的吞噬[13]。同時,SA促進機體產生人β-防御素2和3,參與HS發展[14]。還有學者發現,攜帶SA的患者病程較短,推測SA可能通過炎癥機制引起毛囊結構改變,只在早期參與HS的發病[10,15]。
但是,Jahns等[16]和Ring等[17]分別對27例和30例患者皮損菌群研究均未發現SA;Sartorius等[18]研究了10例HS患者急性加重期的皮損,也未發現SA;Katoulis等[19]分析22例患者皮損,僅在1例患者皮損中分離到SA;Benzecry等[20]在60個Hurley I期皮損樣本中均未培養出SA,僅從16%患者Hurley II期和Hurley III期皮損中分離出SA。Nikolakis等[21]也發現Hurley I和II期患者皮損中SA極少,Hurley III期患者中分離出的SA比例較高,這提示SA參與了HS的慢性階段,是其他細菌已經形成的病變微環境的繼發感染。另外,Guet-Reville等[22]發現,與皮損區相比,皮損周圍正常皮膚中SA的數量更多、檢出率更高,提示SA可能不是HS的主要致病菌。
吸煙是HS的危險因素。Matusiak等[10]對68例HS患者研究發現,所有SA培養陽性的患者都是重度吸煙者。有學者提出吸煙者中SA定植的原因是煙草中的尼古丁通過增加cAMP水平,激活PKA通路,促進單核細胞產生IL-10,導致T細胞分泌IL-22減少,引起角質形成細胞分泌IL-20降低,IL-22和IL-20減少使角質形成細胞分泌抗菌肽(antimicrobial peptides, AMP)不足,引起細菌定植[23]。尼古丁能夠激活角質形成細胞煙堿型乙酰膽堿受體(nicotinic acetylcholine receptor,nAChR),抑制AMP的抗菌活性,并使AMP表達減少,促進SA定植[24];尼古丁還可以通過增強SA的黏附功能和誘導其生物膜的形成,增加細菌的毒力[25]。另外,吸煙產生的煙霧改變了葡萄球菌細胞壁的表面電荷和疏水性,使其對AMP具有抵抗力,促進SA定植[26],定植的SA刺激膽堿乙酰轉移酶表達,促進乙酰膽堿合成,進而激活角質形成細胞的nAChR,抑制AMP活性及表達,促進SA定植形成正反饋,參與HS發展[24,27]。
肥胖也與HS發病有關,Haskin等[28]對632例HS患者皮損菌群研究發現,與正常體重患者相比,肥胖患者皮損中SA的檢出率更高,但是,肥胖與HS皮膚菌群的關系尚需進一步研究。
2.2 凝固酶陰性葡萄球菌與化膿性汗腺炎 凝固酶陰性葡萄球菌(coagulase negative staphylococcus,CoNS),通常是非致病性的,它們會導致免疫缺陷者出現嚴重感染,而且CoNS感染導致的疾病多呈慢性或亞急性改變,這與HS病程相似。Lapins等[8]對25例HS患者進行研究,發現21例患者皮損中存在CoNS,16例來自皮損深部組織標本,在其中9例深部皮損標本中,CoNS是唯一被檢測到的細菌。還有學者發現,CoNS是HS患者皮損中最常見的細菌[10,11],Katoulis等[19]通過對22例HS患者的深部皮損進行針吸活檢,也分離出大量的CoNS,這提示CoNS可能與HS發病相關。Sartorius等[29]也有上述類似發現,并在9例Hurley II期患者的術前血樣中發現以CoNS為主細菌,部分患者可能存在持久的菌血癥。但是,Ring等[30]報道中重度HS患者外周血中細菌組成與健康對照組之間沒有顯著性差異,因此,HS患者菌群的變化可能僅限于皮膚,而與血液中細菌改變無關。
然而,部分學者在患者皮損中未檢測到CoNS[16]。Nikolakis等[21]對50例HS患者皮損菌群進行橫斷面研究,僅在26%患者皮損中分離到CoNS,在Hurley I期患者皮損中均未檢測到CoNS。Guet-Reville等[22]發現,與皮損組織相比,皮損周圍正常皮膚中分離到CoNS的數量更多、檢出率更高,皮損區CoNS中的表皮葡萄球菌豐度顯著降低[31]。2019年,Naik等[32]報道了CoNS等表皮共生的葡萄球菌相對豐度與HS嚴重程度負相關,提示CoNS作為皮膚正常菌群對HS的發病具有保護作用。同年,Ardon等[33]研究發現,與實驗室對照株相比,HS患者皮損中的表皮葡萄球菌的耐藥性和毒力增加,表現為對常用抗生素耐藥、生物膜產生增加,但是,表皮葡萄球菌等CoNS與HS發病的關系仍不明確,需進一步探討。
路鄧葡萄球菌是一種特殊的CoNS,可引起嚴重感染。Ardon等發現[34],HS患者皮損中的路鄧葡萄球菌株較健康者生長更快,故患者皮損中的菌株適應性更強。Guet-Revillet等[22]對82例HS患者皮損研究發現路鄧葡萄球菌大部分存在于Hurley I期皮損,說明路鄧葡萄球菌與輕度HS有關,Guet-Revillet等[31]的另一項研究結果也支持這一觀點。
2.3 其他細菌與化膿性汗腺炎 早在1999年,Brook等在HS患者腋窩膿腫中分離出卟啉單胞菌屬和梭桿菌屬。2012年,Sartorius等[18]在3例患者急性加重期結節中分離出普雷沃菌屬,在3例急性期皮損中分離出梭菌屬。2017年,Nikolakis等[21]研究并回顧文獻后提出,普雷沃菌屬是HS患者腹股溝皮損中最常見的、專性厭氧革蘭陰性桿菌。
Ring等[17]對30例HS患者和24名健康者皮膚菌群研究發現,在患者毛囊性皮損中,菌群主要由棒狀桿菌、卟啉單胞菌屬和嗜胨菌屬組成,在健康者皮膚中未檢測到卟啉單胞菌屬和嗜胨菌屬。最近,Schneider等[35]報道,HS患者皮膚中卟啉單胞菌屬和嗜胨菌屬較健康者皮膚更豐富。Guet-Revillet等[22]在HS皮損中鑒定出普雷沃菌屬、卟啉單胞菌屬、嗜胨菌屬和梭桿菌屬等厭氧菌,推測它們可能與HS慢性炎癥有關。在另一項研究中,Guet-Revillet等[31]發現,HS皮損區厭氧菌中梭桿菌屬和微單胞菌屬的相對豐度與HS嚴重程度有關。Naik等[32]進一步證實了普雷沃菌科、卟啉單胞菌科、梭菌目和梭桿菌門的細菌相對豐度與本病的嚴重程度正相關。Ring等[36]發現HS竇道中含量最多的細菌屬于普雷沃菌屬和卟啉單胞菌屬,認為它們可能通過形成生物膜,誘發機體異常免疫反應,參與HS的發生,也有學者提出[37]卟啉單胞菌屬和嗜胨菌屬的細菌可能通過激活C3a和C5a途徑在HS發病的初始階段發揮作用。
丙酸桿菌是皮膚表面的共生菌,對其他細菌具有抑制作用。Ring等[17]和Schneider等[35]發現HS患者皮損區丙酸桿菌較健康皮膚豐度下降,丙酸桿菌的減少可能是HS患者皮膚皺褶部位皮脂腺萎縮或數量減少引起的皮脂分泌降低所致[38],也可能是HS發病早期角質形成細胞分泌的AMP和炎癥介質,不利于丙酸桿菌定植[35]。丙酸桿菌減少,可以促進卟啉單胞菌屬和嗜胨菌屬等機會性致病菌的定植,并增加其生物膜的形成,激活異常的免疫反應,促進IL-17、TNF-α等炎癥介質釋放,參與HS發病[38]。Naik等研究發現,丙酸桿菌和棒狀桿菌等共生菌的相對豐度與HS的嚴重程度呈負相關[32],也支持上述觀點,但Guet-Reville等認為,與周圍正常皮膚相比,皮損中丙酸桿菌較少,丙酸桿菌與HS發病可能無關[22,31]。
米勒鏈球菌是人體口咽部、消化道及生殖道的共生菌,包括中間型鏈球菌、星座鏈球菌和咽峽炎鏈球菌3種,屬于兼性厭氧菌,常合并專性厭氧菌感染,米勒鏈球菌與膿腫的形成及嚴重的感染密切相關。Highet等分析了32例HS患者會陰部皮損菌群,發現米勒鏈球菌是最常見的細菌,米勒鏈球菌消失后,患者皮損好轉,說明米勒鏈球菌具有致病作用。Guet-Revillet等在32%(43/133)的HS皮損中分離出咽峽炎鏈球菌,僅在3%(5/175)的對照組檢測到該菌[31]。在另一項研究中,研究者也發現了與皮損周圍相比,HS皮損中檢出的米勒鏈球菌更多[22]。Sartorius等[18]在1例HS患者急性加重期的結節中分離出咽峽炎鏈球菌,Benzecry等[20]在Hurley III期HS患者皮損中分離出星座鏈球菌,但是,米勒鏈球菌與HS發病的關系仍有待進一步證實。
另外,Guet-Revillet等[31]在26%(34/133)HS皮損中檢測到厭氧放線菌,僅在2%(3/175)的對照組皮膚中檢測到厭氧放線菌,在另一項研究中,他們還發現放線菌與HS皮損有相關性[22],目前缺乏放線菌與HS發病機制方面的研究。
3 小結
HS的病因和發病機制仍不明確,但是,作為防護屏障的皮膚上寄居的多種菌群與HS的發病密切相關,菌群數量和(或)種類的改變能夠激活宿主的免疫系統出現異常的免疫反應,導致細胞因子表達改變,產生炎癥反應,影響著HS發病的不同階段。目前,不同研究者的報道結果并不一致,可能與采用的研究方法、樣本數量相對較少、選擇的皮損部位和類型等多種因素相關,同時,在HS發病相關的菌群代謝產物及代謝組學方面的相關研究仍然匱乏,隨著這一領域研究的不斷深入,未來有望揭示HS發病和皮膚菌群之間的關系,有助于發現HS患者特異性的菌群生物標志物,為干預皮膚菌群治療HS提供新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