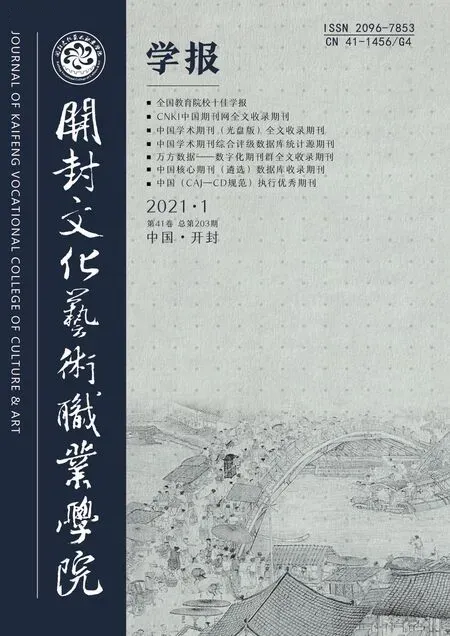“距離說”的中國聯結
孟易樺
(暨南大學 文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0)
一、研究背景
中國的傳統與外來的文化在中國近現代這個歷史時期產生了激烈的碰撞與交匯。王國維在《論近年之學術界》中感嘆:“外界之勢力之影響于學術,豈不大哉!”[1]96他認為,外來思想的輸入“非與我中國固有之思想相化,決不能保其勢力”[1]99。當西洋思想涌入中國之時,我們恰恰不能忽略的是中國傳統思想構成了其文化接受的歷史前提。
五四時期,中國學者對西方文化進行了大規模學習與接受。中國現代文人在西方堅船利炮的打擊下,在心灰意冷的痛苦中,用文學作為他們服務政治的上佳選擇,情感的“自然流露”在此時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梁實秋曾在《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中分析了這一現象,他認為:“中國人的生活在情感方面似乎有偏枯的趨勢。到了最近,因外來的影響而發生所謂新文學運動……到這時候,情感就如同鐵籠里猛虎一般,不但把禮教的桎梏重重打破,把監視情感的理性也撲倒了。”[2]在1925 年“五卅運動”之后,這種“熱情”便具有了革命的內涵。“情感的政治化”成為這個時期思想界的主要特色。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熱情”“浪漫”與“狂熱”似乎成為當時文學界流行的特質。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距離說”的引介和與之相關的“靜觀”的審美觀照方式與超然的審美胸襟的顯現,作為一股潛流,在王國維、朱光潛、周作人等一大批中國現代美學家心中流淌。“距離”“靜觀”“超然”等字眼似乎更符合中國人情感中“偏枯”的趨向。這種冷靜的觀世法與充分的透視距離正如一盆冷水,狂熱與浮躁為之洗滌后升華成為詩與美。
二、“距離說”在中國傳譯的可能性
新文化運動對學術界產生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當時,國內著名大學的校長與骨干力量大多有留學歐美的經歷,這就為西學的大面積引入與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提供了有利條件。羅鋼曾在《歷史匯流中的抉擇:中國現代文藝思想家與西方文學理論》中認為,“以文學理論而言,五四時期,幾乎沒有一個中國文藝思想家沒有受到一種乃至幾種西方文學思潮的影響,也幾乎沒有一個重要的西方近代文藝思想家沒有在中國得到相應的介紹。”[3]
首先,“距離說”能夠與中國古典美學中的某些范疇相化合。“遠”,作為古典美學的重要范疇,它拉開了審美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距離,表現出“超越有限,追求無限”的審美內涵。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有“三遠”之論。“三遠”即“高遠”“深遠”與“平遠”,郭熙尤其重視“平遠”。相比“高遠”與“深遠”中剛性與積極的一面,“平遠”具有的沖淡、放任與柔和之美更符合道家美學中“淡”“無”和“虛”的審美境界。徐復觀先生在《中國藝術精神》中指出:“遠是山水形質的延伸,此一延伸,是順著一個人的視覺,不期然而然地轉移到想象上面。由這一轉移,而使山水的形質,直接通向虛無,由有限直接通向無限。”[4]“遠”離不開“虛”和“空”,正如張晶在《超然之美》中說的那樣:“然而‘遠’更具深厚的哲學內蘊,其審美精神乃是哲學之‘道’在藝術上的延伸。”[5]
“遠”在體現道家美學的審美意蘊外,也是詩人與畫家內在心靈的折射。這種距離之“遠”有助于形成具有韻外之致的朦朧美,“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與“韻外之致”一直以來都是文人所追求的審美理想。距離之“遠”可以突破有限進入無限,從而產生“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境界。
其次,“距離說”的引入以王國維美學為背景。朱光潛對于詩論的研究正是在王國維美學的基礎上展開的。在《訪談錄:朱光潛教授談美學》中,當被問到那個時期美學界的近況時,朱光潛提到了三個人,即蔡元培、王國維和呂澄。他稱贊了王國維在學術方面的成就,同時談到了其著作《人間詞話》和“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的區別。
《詩論》是朱光潛自己認為比較有獨到見解的一部著作。在第三章《詩的境界——情趣與意象》中,朱光潛認為,情趣與意象是否契合是區別“隔”與“不隔”的關鍵。由此切入,他論述了詩的“顯”與“隱”和“同物之境”與“超物之境”的區別。
“隔”與“不隔”是王國維境界理論的關鍵所在。他在《人間詞話》中曾多次批評姜白石,認為他的詞“終隔一層”。這反映出王國維對其相反面——“不隔”與“真景物”“真感情”的贊許。王國維十分重視感情的真摯與觀物的真切。他認為:“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6]他肯定真摯動人,絕無矯揉造作的文風。因此,他推崇李后主,反對專門之文學家與“的文學”。他說:“吾寧聞征夫思婦之聲,而不屑使此等文學囂然污吾耳也。”[7]148
但是,“真感情”是否是激情?王攸欣在《選擇·接受與疏離》中認為:“隔與不隔的關鍵在于能不能靜觀到理念。”[8]在這里,“真感情”并不是指感情的自然發泄,其強調的是感情經過不動情的“靜觀”回味之后的境界。王國維在《文學小言》中有言:“則激烈之感情,亦得為直觀之對象、文學之材料。”[7]144可見,他強調觀照的客觀性。佛雛認為,在審美觀照中,王國維更加重視其中客觀性的成分[9]208。因此,“必須把此種激情轉為‘直觀之對象’,即須有‘寧靜的觀照’為之主宰”[9]224。
王國維對“不隔”與“真景物”“真感情”的追求是以“寧靜的觀照”為基礎的。朱光潛似乎繼承了這一方面,尤其關注“距離”與“隱”。
退休前曾是國企掌門人的陸長安副理事長,在印刷行業服務近50年,是業內資深的技術專家,頗受敬重。他親歷了技術變革帶給印刷行業的革命性變化,見證了行業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發展變遷,對這個自己奉獻一生的行業,充滿了感情。我們的對話,從聞名遐邇的印刷大展談起。
在《悲劇心理學》中,朱光潛把“距離”解釋為“審美對象脫離與日常實際生活聯系的一種比喻說法”[10]28。他認為,美的事物給人的感覺都有一點“遙遠”,而這種時空的距離在藝術創作和欣賞中非常重要。他贊賞華茲華斯曾說過的“詩起源于在平靜中回味起來的情感”這句話。與王國維由于“靜觀”而產生的審美觀照的客觀性相似,“距離”也能夠形成一定程度的客觀化。在引用德拉庫瓦教授關于“客觀化”的論述時,他說道:“‘客觀化’其實就是形成距離的另一種說法。”[10]32
簡而言之,“距離說”與王國維的境界理論有著很密切的關系。王國維既強調“不隔”與真感情、真景物,又反復論及“以物觀物”“靜觀”等理論。而朱光潛用“距離”二字便可將其概括。因為,只有把“距離”放遠,“出乎其外”,站在客位上于冷靜之中回味,才能產生“不隔”之“真感情”。
再次,“距離說”的引入有助于解決當時中國思想界的某些問題,具有啟蒙和教育青年知識分子的作用。在當時,上海立達學園的夏丏尊、葉圣陶等人有感于世人的急功近利與“超效率”,認為“學者和革命家們都太貪容易,太浮淺粗疏,太不能深入,太不耐苦”[11]2。為“勸青年眼光要深沉,要從根本上做功夫,要顧到自己,勿隨了世俗圖近利”[11]2,便邀請“青年導師”朱光潛寫些有關青年教育的稿子。
稿件發表于開明書店的刊物《一般》中。“開明”便有“啟蒙”的意思,其針對的讀者群體主要為青年。這些稿件其后被搜集起來輯為《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出版。這其中的一些篇章已經有了“距離說”的影子。在《談靜》中,朱光潛認為:“現代生活忙碌,而青年人又多浮躁。你站在這潮流里,自然也難免跟著旁人亂嚷。”[11]14他渴望與現世保持一點“距離”。在崇尚心境空靈的同時,于喧囂的塵世與忙碌紛擾中找出一點靜趣。在《談擺脫》中,他認為“‘擺脫不開’便是人生悲劇的起源”[11]50。在《談人生與我》中,他論述了“站在前臺”與“站在后臺”這兩種看待人生的方法。朱光潛顯然更喜歡有一點距離感的觀看方式。他喜歡做“袖手旁觀”狀,于閑靜寂寞之時尋思玩味,認為這樣“比抽煙飲茶還更有味”。在《談在盧佛爾宮所得的一個感想》中,他反對現代社會萬事都追求“效率”的做事方法。在《談十字街頭》中,他號召青年學生不要不假思索、盲目附和,不要陷入十字街頭的塵囂中,而要與其保持距離。
三、“距離說”在中國的傳播路徑
“距離說”的傳播離不開心理學在現代美學中的應用與風靡。它的傳播是在介紹西方心理學與“心理學美學”的潮流中展開的,其傳播過程與中國近現代心理學美學的發生與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首先,就研究層面看,從20 世紀20 年代到40年代,對心理學美學進行介紹與研究的論著有呂澄的《美學淺說》(商務印書館1923 年出版)、《美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23 年出版)、《晚近美學說和美的原理》(商務印書館1925年出版)。其中,《美學淺說》把現代美學分為“心理學的美學”和“非心理學的美學”。而美感全部是心理作用的結果,其來源于“感情移入”的心理現象。在談到“靜觀”時,呂澄認為美感同“靜觀”的態度不可分割,“用‘靜觀的態度’去感受時也能覺到美感”[12]。《美學概論》與《美學淺說》的主要觀點基本一致,重點分析了“美的感情移入”與“美的觀照”。而《晚近美學說和美的原理》除提到立普斯的“感情移入”說外,還涉及了哈曼以及克羅齊的“直覺說”。其次,范壽康對于心理學美學的普及也作出了很大貢獻。他將“美的態度”分為非功利的態度、分離與孤立、感情移入與藝術觀照的態度4 種。在“分離與孤立”這一部分中,他認同閔斯特堡的主張,認為“美的態度”就是將自己靜注在對象上,忘卻一切的心理狀態[13]。商務印書館1927 年出版的《美學概論》是范壽康在上海學藝大學授課時的講稿。此書對移情理論進行了重點論述。
這個時期出現的心理學美學著作還有李石岑等人著的《美育之原理》(商務印書館1925 年出版)、大玄等人著的《教育之美學的基礎》(商務印書館1925 年出版)與陳望道的《美學概論》(民智書局1927 年出版)。前兩者主要是將心理學的方法運用到藝術教育與美育中,對當時提倡美育有一定的積極作用。陳望道在《美學概論》中認為,人對世界的基本態度可以分為實行的態度、理論的態度與審美的態度三種。審美的態度和其他兩種不同,它是靜觀的、具象的、愉悅的、直接的[14]。
1933 年,朱光潛在結束了8 年的英、法留學之旅后順利回國。《談美》(開明書店1932 年出版)與《文藝心理學》(開明書店1936 年出版)都是從心理學角度對審美過程的心理現象進行系統的分析與介紹的著作。
“心理距離說”首次出現在大眾的視野中。朱光潛在《談美》中除介紹“距離說”與“移情”理論外,他還在“開場話”中號召青年要從“怡情養性”做起,美化心靈與人生[15]。《文藝心理學》的理論性較強。在介紹布洛的“心理距離說”時,朱光潛用“海上的霧”這個生動的例子來說明美感的態度就是將自己和實際生活之間插入一段“距離”,以“超脫”的胸襟,處之泰然地去感受美、欣賞美。這是一種美感的“距離”。
其次,就譯介層面來說,在20 世紀20 年代至40 年代,中國出版了一些與心理學相關的美學普及譯著,而對專門從事心理學美學研究的理論家的著作或文章翻譯較少。20 世紀20 年代初,中國現代美學受日本美學界的研究成果影響較大,這個時期有大量源自日本的心理學美學譯著問世。在當時,產生較大影響的美學普及譯著有商務印書館1920 年出版的《近世美學》(高山林次郎著,劉仁航譯)、開明書店1928年出版的《藝術概論》(黑田鵬信著,豐子愷譯)、中華書局1930 年出版的《文藝鑒賞論》(田中湖月著,孫俍工譯)等。
盡管“距離說”與“移情”理論曾在20 世紀二三十年代廣為流行,但對其倡導者里普斯與布洛的相關著述的翻譯卻開始的很晚。里普斯的《論移情作用》在1964 年才經朱光潛翻譯發表于《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第8 冊上。同樣,“距離說”雖在20世紀30 年代就已被大眾知曉,但牛耕在1982 年才將《作為藝術因素與審美原則的“心理距離說”》這篇譯作發表于《美學譯文》第二輯上。
這種現象的發生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國現代美學的發生與西方美學的進入幾乎同時進行。因此,中國早期的美學理論研究者往往也是譯介者,他們對西方文論的引介并不是機械性無目的進行的,而是為了回應中國的文學理論與中國社會的現實情況。這樣一來,就出現了研究者早在單篇文章或著述中就引用過的西方理論,在過了很多年之后才被翻譯的現象。另一方面,20 世紀50 年代開展了關于美學的大討論,心理學美學被蔡儀、呂熒等人批判。在《新美學》的第三章《美感論》里,蔡儀把矛頭指向了形象的直覺說、心理的距離說、感情的移入說等。他認為,美的根源在于客觀現實,由客觀現實去把握美的本質才是研究美感的正確途徑[16]。在20 世紀50 年代到70 年代,心理學美學的研究陷入了沉寂。這就必然會影響到心理學理論的翻譯。因此,當“距離說”在20 世紀80 年代隨著“方法熱”大潮被再次發現時,《作為藝術因素與審美原則的“心理距離說”》才被完整地翻譯并發表出來。
再次,就運用層面而言,朱光潛曾用“距離說”來為中國藝術做辯護。中國的畫藝、戲曲、詩歌等藝術也正因含有“距離”才顯得彌足珍貴。就戲劇藝術而言,出色的戲劇表演與演員獨一無二的唱腔、夸張的舞臺裝扮和與眾不同的肢體語言有密切關系。只有如此,才能與實際生活拉開“距離”,展現出與日常生活不一樣的舞臺情境。朱光潛更是用“距離”來探討悲劇。他認為,悲劇是通過以下6 種方式來使生活“距離化”的,即空間和時間的遙遠性、人物與情境的非常性質、藝術技巧與程式、抒情成分、超自然的氣氛、舞臺技巧和布景效果[10]36-44。悲劇的內容在經“距離化”的方式過濾后便成為理想的形式,其內容的粗鄙與人物的丑陋因此升華為壯麗和美。而古典詩歌的美很大一部分體現在韻律與節奏之中。五四新文化運動后,白話文被放到了重要位置。不論是出于何種原因,新詩與散文雖然可以毫無阻礙、自然而然地表達人們如洪水般的情感,卻總是缺乏“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含蓄與克制之美。究其原因,也在于缺少“距離”。
總之,“距離”具有詩化的意義與作用。只有在“距離”這個透視鏡下,意境、崇高與美才會出現。
四、“距離說”對中國美學的豐富與拓展
“距離說”不僅是作為一種西方理論而引入中國的,更是代表了大多數中國人的人生態度與處事風格,有著豐富的民族心理積淀。它與中國美學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
“距離說”不僅可以與中國古典美學中的“遠”范疇相互生發,與中國古典詩歌中含蓄的美學風格相符,而且它的引入也對中國現代美學的發展形成了回應。“距離說”不僅為王國維的境界理論與“靜觀”的審美觀照方式做了補充和引申,也為京派文學奠定了理論基石。
“距離說”雖強調對現實世界保持“距離”,但其“距離”是既“出乎其外”又“入乎其內”。它所強調的“空靈”和“心遠”其實并非真正的“空”和“遠”,而是在對現實與功利進行批判之后的超越。對“超然”“擺脫”與“心遠”等精神境界的追求便是反抗現實世界的另一種方式。
這種“超然物表”“獨享靜觀”與“恬淡自守”的“距離”之美與京派文學形成了千絲萬縷的聯系。“距離說”“靜觀”理論從形而上的層面規定了京派文學的發展方向。“距離說”的介紹者朱光潛十分推崇周作人,對其《雨天的書》尤為贊嘆。《雨天的書》中所具有的清、冷與簡潔的特質使他產生“似舊相識”的感覺。他認為,周作人之所以能寫出如此簡潔自然的文字,是由于心情清淡閑散的緣故[17]418。而“清淡閑散”也是他心向往之的境地。朱光潛在《文學雜志》中發表了《我對于本刊的意見》,這篇文章既是《文學雜志》的發刊辭,同時也是京派文學的理論綱領。他指出:“我們缺乏精神審視所必須的冷靜與透視距離。”[18]325他呼吁年輕的創作者要保持獨立自主的超然態度,注重修養、潛心創作。
“距離說”的引入是以中國古典美學為底色的,但同時它也豐富了中國現代美學理論,對中國現代美學的發展進行了回應。就這兩點來說,“距離說”是最傳統的,也是最現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