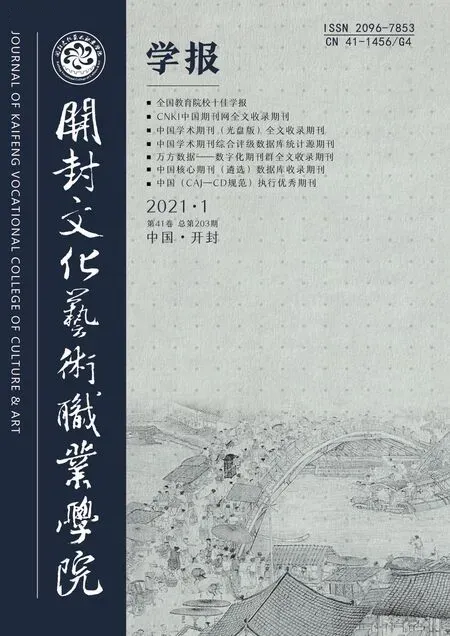應用型本科院校英語專業翻譯教育的生態譯學反思
冉海濤
(廣州理工學院 外國語學院,廣東 廣州 510540)
在翻譯學跨學科研究趨勢明顯的大環境下,翻譯研究經歷了語言學轉向、文化轉向、認知轉向之后,正迎來一次新的變革——“生態轉向”。胡庚申教授認為翻譯生態與自然生態屬“同構隱喻”[1]17,并以此為理據將生態學原理運用于翻譯研究,開創了翻譯學研究的“生態范式”。胡庚申提出了一系列構成生態翻譯核心體系的術語,如翻譯生態、文本生態、翻譯群落、適應/選擇、譯者中心、三維轉換、整合適應選擇度、譯有所為、事后追懲等,這些術語對翻譯的本質、原則、標準和策略進行了全面系統的闡釋。
翻譯教育生態系統是翻譯生態系統的一個重要子系統,它是“以翻譯教育為中心,對翻譯教育的產生、存在和發展起著制約和調控作用的多元生態環境體系”[1]146。生態系統存在多層次、多維度并相互交叉的特征,各種生態因子相互關聯,相互影響。要解決當前翻譯教育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提升翻譯教育質量,必須全面審視翻譯教育生態,調整教學生態環境中各因子(如學生、教師、教學策略、教學資料、教學軟硬件等)之間的關系,營造教學相長、師生共進的良好教育生態。目前,無論是教育管理者、教師還是學生,對翻譯教育生態的關注度還不夠,有關翻譯教育生態的研究嚴重不足。鑒于此,筆者將以自身所處的教育生態環境為研究背景,重點探討應用型本科院校的翻譯教育問題。
一、應用型本科院校英語專業的翻譯生態環境
應用型本科院校的辦學定位既有別于研究型大學,也有別于高職院校,應用型本科院校的人才培養目標是服務于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形成地方特色,培養高級應用型人才。應用型本科院校在專業設置、人才培養計劃上要廣泛、靈活地與地方生產生活緊密結合,在課程教學上要創新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把握好理論學習和實踐教學的關系,注重產學研結合[2]。因此,鑒于應用型本科院校翻譯教育生態的地方性和應用型特征,翻譯教育也必須在教學理念、教學模式、教學內容、教學評價等環節突出應用性、實踐性和靈活性。
(一)應用型本科院校翻譯教育的“生態位”
“生態位”(ecological niche)是生態學的一個主要術語,指的是物種在其生物群落中的時間、空間、地位、功能和作用,是生態群落內部和外部關系的基礎。在教育生態系統中,不同層次或水平的學校處于不同的教育生態位,處于不同生態位的學校所獲得的能量流和信息流也不同[3]。因此,學校教育活動的開展都必須以自身“生態位”為基礎,才能實現“適者生存”。
從宏觀角度看,普通高校、獨立學院、職業技術學院都設置了英語專業,開設了專業翻譯課。根據生態位法則,不同層次的高校辦學要適應不同的需求,努力做到特色翻譯教學,各層次的高校間應有恰當的能量分配比例,避開不合理的競爭與排斥,這樣才能維持整個生態翻譯系統的良性循環[4]。筆者任職的高校是一所獨立學院,位于珠三角經濟發達城市廣州,學生兼職、實習或進行社會實踐都非常便利。廣州的翻譯人才需求非常旺盛,一年兩次的廣交會以及平時各種博覽會和會展都需要大量的翻譯人員,還有各種翻譯公司外包的翻譯業務等,給學生提供了大量的實踐機會。李德鳳、胡牧指出,翻譯教學要通過市場調研了解社會對人才的需求,通過專業設置滿足學習者和社會的需求,通過專業教學使學習者和社會承認教學的實用性和前瞻性[5]。為了充分利用學校的區位優勢,結合市場應用翻譯需求,外國語學院在制定人才培養方案時適當增加了應用翻譯的課程,如商務翻譯、科技翻譯、政論文翻譯、法律翻譯、旅游翻譯等。教師會在翻譯課堂中引入真實翻譯任務,幫助提升學生的翻譯學習興趣和職業翻譯能力。另外,為鼓勵學生參與翻譯實踐,學校在上課考勤和期末評價上采用了靈活的管理制度。根據學生反饋,他們的翻譯以陪同翻譯為主,結合一些中等難度的筆譯任務,雖然他們目前無法勝任高難度的口筆譯任務,但是市場需要不同層次的翻譯人才,不同能力的譯者總能找到適合自我生存的“生態位”。
(二)應用型本科院校翻譯教育的“花盆效應”
“花盆效應”又稱“局部生境效應”。為促進植物生長,種植者給植物提供了盡可能“舒適”的生長環境,這種環境是人為營造的一種“局部生境”,長時間生長在局部環境的植物是很難適應嚴酷、苛刻的自然環境的。對于傳統翻譯教學來說,理論講得多,學生練得少,教學內容陳舊、單一,教學方式落后,真實翻譯任務、翻譯輔助技術和翻譯項目經驗缺乏等都是普遍問題,這對培養學生的翻譯實踐能力和職場適應力是非常不利的。對于應用型院校來說,必須加大產教融合力度,一方面,從事翻譯教學的教師要走出去,去了解翻譯行業現狀和市場動態,加強翻譯技術、翻譯項目管理的學習;另一方面,學校可以邀請行業專家、業內人士到學校開講座,分享從業經驗,教授實踐技巧,還可以邀請他們擔任校外專家,為翻譯教學與研究提供咨詢,協調校企合作,指導協助校內外翻譯實訓基地建設,積極提供校外實習場所等,打造有利于提升學生職業生存能力的翻譯教育環境。
二、應用型本科翻譯教學內容的選擇
教學內容是翻譯教學的基礎,傳統的翻譯教程突出文學翻譯,對獨立學院的學生來說內容陳舊艱深,不符合學生的學習需求。生態譯學認為譯者是整個翻譯活動的中心,譯者不僅直接參與翻譯操作,還要負責協調制約翻譯的各種間接因子。在教育生態體系中,學生又是學習活動的主體,因此,教師在選擇翻譯內容時要考慮學生的“雙重身份”,有條件的話可以讓學生參與教學內容的選擇,使教學內容盡可能適應學生的學習能力和翻譯水平。對于獨立學院的翻譯教學來說,教學內容以應用翻譯為主,以筆者所教的科技英語翻譯為例,為了找一本符合學生能力水平,滿足學生求職需要,同時有利于教學開展的教材,筆者幾乎翻閱了市場上所有的主流科技翻譯教材,有的翻譯理論過于艱深,與實踐脫節;有的譯例術語太多,話題太專業,學生望而生畏;有的體例太陳舊,沒有體現應用翻譯研究的最新成果,最后筆者只能博采眾長,自編講義供學生使用。方夢之把科技文體分成專業科技文體和普通科技文體兩個層次,再依據語場、語旨和語式的概念把兩個層次分成了六個等級。筆者按照這樣的劃分選擇適合學生學習的教學材料,再教授相應的翻譯標準、策略和方法,使教學目標更明確,教學過程更具操作性,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課堂參與度大大提高。
三、翻譯學習動機的保證
“譯有所為”在生態譯學中指的是譯者從事翻譯的內在或外在動機。通過強化譯者的主觀動機,并利用翻譯任務的客觀激勵功能,可以提升學生學習翻譯的興趣。對于應用型本科院校的學生來說,單純雞湯式的鼓勵他們熱愛翻譯,以翻譯為業往往效果不佳,但是優美動人的文學文本、現學現用的字幕翻譯和形式活潑的翻譯比賽卻是激發內部動機的有效方式,如果在完成翻譯任務的同時能夠收獲一定的精神和物質獎勵那就更完美了。隨著信息時代大數據、云計算技術的廣泛應用,翻譯技術和翻譯行業模式也在不斷創新。眾包翻譯模式,如社交網站上發起的字幕翻譯、新聞編譯、網頁本地化等為眾多翻譯愛好者提供了翻譯實踐平臺。翻譯任務委托者通過這些平臺發布翻譯任務,翻譯愛好者在完成翻譯任務的過程中可以探討問題、交流經驗,還能學習翻譯輔助技術,如語料庫、術語庫、翻譯軟件、網絡搜索及其他計算機基本操作技能。網絡眾包翻譯模式給師生都提供了非常廣闊的翻譯實踐平臺,相比傳統的校企合作翻譯實訓模式,該模式管理靈活,成本低廉,無須固定的時間地點,是教師和學生從事翻譯教學、翻譯實踐甚至翻譯研究的好幫手。鼓勵師生參與眾包翻譯,可以讓學生體驗到真實任務的挑戰、合作翻譯的樂趣以及看到翻譯成果的成就感。
四、“學生中心”“譯者中心”的確立
生態譯學提出的“譯者中心”,是指譯者是整個翻譯鏈的中心,在翻譯過程中不斷地對翻譯環境進行適應和對譯文進行選擇[1]207。在教育生態體系中,學生又是學習的主體,負責計劃、監控、調整和評估整個學習過程。翻譯課堂上的學生,同時又是譯者,應該形成自主翻譯學習的能力。鑒于此,我們提出了翻譯學習策略。可以借用O'Malley 和Chamot 的學習策略分類框架[6],根據翻譯思維的過程和特征,制定翻譯學習策略。適合翻譯學習的元認知策略有:確定翻譯學習目標,制訂翻譯學習計劃,監控翻譯學習過程,評價翻譯學習效果,調整翻譯學習方法。認知策略包括翻譯理論學習,文體與語篇分析,語言分析和理解,雙語對比和轉換,變譯技巧訓練,思維邏輯訓練,審美意識培養,翻譯職業與翻譯內容知識的擴展,翻譯輔助工具的運用,情感策略包括提升翻譯學習動機。社交策略包括:小組合作學習,向他人求助。
應用型本科院校的學生,特別是獨立學院的學生,專業基礎比較薄弱,自主學習意識和能力欠缺。現代翻譯課堂推崇以過程為導向的教學模式,如翻譯工作坊、翻譯任務教學法等,這些方法都非常注重學生的計劃、合作、監督、調控、評價和反思能力,對于很多獨立學院英語專業的學生來說,他們的英語語言基礎不扎實,漢語表達有時也不到位,在學習翻譯的同時還要花很大精力強化語言基礎,這就需要教師在教學中提供更多的“支架”。對翻譯任務中可以預計的重難點,如妨礙理解的疑難語法問題、背景知識問題等,教師可以給予必要的啟發和幫助。既不能完全放手,也不能越俎代庖,要運用“學生中心”“譯者中心”的理念,平衡好教師指導與學生自主的關系,循序漸進,幫助學生培養策略意識,形成翻譯自學能力。
五、翻譯教學的生態學理念
生態學范式的翻譯教育必須以翻譯活動的生態學本質為基礎,對翻譯教育的理念和過程進行整體觀照。生態譯學認為翻譯即生態平衡,即文本移植,即適應選擇[1]198。
(一)翻譯即生態平衡
“生態平衡”指在文本、語言、文化、翻譯群落等各種微觀、宏觀、內部、外部生態因子之間實現平衡[1]111。對于傳統的翻譯標準,如信、達、雅,忠實與通順,形似與神似,意美、形美、音美等;傳統的翻譯策略,如歸化與異化,直譯與意譯等,如果我們不考慮翻譯生態,如原文的交際目的、原語的文化地位、譯者的翻譯目的及譯文讀者的需求等,就容易把這些概念二元對立起來,造成翻譯操作中非此即彼的極端問題。
翻譯實踐中有很多“平衡”得較好的經典例子,如Coca-Cola(可口可樂),桂林山水甲天下(East or west, Guilin scenery is the best)就做到了意美、形美、音美結合。但是,由于英漢語言文化的差異,能否在語義、修辭、語篇、語用等各個層次實現譯文與原文的對等,考驗的是譯者的語言能力、雙語轉換能力、主題知識和策略能力,即生態翻譯中的“整合適應選擇能力”。生態譯學提出譯者中心,是對原文中心和譯文中心的解構,譯者的責任在于在翻譯生態、文本生態和翻譯群落中尋求平衡。
(二)翻譯即文本移植
文本移植就是將一種語言生態系統里的文本移植到另一種語言生態中去[1]200。原文生態是否可以在譯文生態中生存和長存取決于原語文本與目標語在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上轉換的程度。例如:
He had about as much chance of getting a job as of being chosen mayor of Chicago. (J. London)
譯文一:他找到工作的機會和當選芝加哥市長的機會幾乎差不多。
譯文二:他找到工作的機會簡直微乎其微。
譯文三:他要找到工作簡直跟要當選芝加哥市長同樣困難。[7]12
上述譯例中,譯文一采用直譯法,實現了語言維轉換,但忽視了文化維和交際維,容易造成譯文讀者的誤解,因為該譯文沒有明確交代“當選芝加哥市長的機會”到底是大還是小。譯文二采用意譯法,實現了交際維轉換,但是忽視了語言文化信息的傳遞,如美國人可能認為當選市長是很困難的。譯文三采用“直譯+補償”的方法,較好地實現了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的轉換。
生態譯學認為,翻譯是一個整合一體、和諧統一的系統。由于系統內各個組成成分之間相互作用,成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并且這個整體所表現出來的功能不等于各個組成成分功能的簡單相加,而是大于各個組成成分功能之和。字、詞、句、段、篇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各翻譯單位之間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從詞到篇的排列,反映的是語法結構由簡單到復雜,而這并不意味翻譯難度的逐步增加[8]。因此,簡單地按字、詞、句、段、篇的順序實施翻譯教學,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翻譯學習的心理規律。在實際操作層面,最合適的翻譯單位是句子,句子或段落給詞匯提供語境,而且句子又受到“銜接”“連貫”等語篇構成要素的制約,這也契合整體/關聯的生態理性。
以張培基的《英漢翻譯基礎》為例[9],該教材的譯例大部分選自文學作品且以句子為主,作者沒有給部分譯例注明出處,使句子缺乏語境支撐,導致翻譯講評缺乏理據。例如:They took a final look at Iron Mike, still intact in the darkness. 第一版譯文:“他們最后看了鐵麥克一眼,它依舊安然無恙地聳立在黑暗中。”讀者看到沒有上下文的“鐵麥克”時一定會感到莫名其妙。再看第二版修訂版譯文:“他們最后看了鐵麥克(雕像)一眼——它依舊安然無恙地聳立在黑暗中。”加了“雕像”后意思清楚多了。因此,每一級翻譯單位意義的確定都根據上下級關系進行整體判斷。翻譯與語篇關系密切,譯者一定要培養語篇意識,學習語篇結構與功能知識。翻譯教學要摒棄句比字櫛的操作方法,幫助學生利用語篇知識去理解原文和創作譯文。
(三)翻譯即適應與選擇
生態譯學認為,“適應與選擇”包括譯者對翻譯生態的適應和譯者對譯文的選擇,好的翻譯就是“整合適應選擇度”高的翻譯[1]239。
紐馬克根據語言的功能把語篇分成信息型、呼喚型和表達型三個層次[10]。表達型文本以文學類為主,而大部分非文學類的實用文體如科技、商務、法律等則屬于信息型和呼喚型,不同的文本類型有不同的翻譯標準、策略和方法。對于應用型本科翻譯教學來說,翻譯訓練就應該以信息型和呼喚型文本為主,以傳達信息、實現雙語交流為主要目的,注重信息傳遞的效果。在翻譯質量上,詞匯語法必須正確,但不必追求語言的完美,這讓語言基礎不太好的學生也有了嘗試翻譯的可能。
連淑能在《英漢翻譯教程》中談到翻譯評估標準時[7]3,在忠實、通順的基礎上提出了“速度”的要求,這其實是考慮到了翻譯的實際應用目的與環境,認為翻譯不僅僅是文本移植,而且是翻譯教育生態和翻譯市場生態中的一個環節,因此,譯者必須適應翻譯生態環境,整體考慮原文作者的意圖、譯文讀者的需求和譯事委托者等的要求,最后選擇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譯文。在以應用翻譯為主的當今翻譯市場中,不顧時間成本去追求文本完美的工作方式是無法適應市場生態的。傳統的翻譯訓練以全譯為主,不注重時效,不利于學生職業適應能力的培養,因此翻譯教育有必要向學生傳授節譯、摘譯、改譯、編譯等各種翻譯策略,結合限時課堂練習,增強學生時間觀念,提高翻譯效率。
結語
生態譯學把翻譯教育置于一個整體翻譯生態系統來進行統觀,拓展了傳統翻譯教學研究的視野,給翻譯教育理念、師生角色、教學內容、學習動機、教學策略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和有益啟示。應用型本科的翻譯教育要研究翻譯生態環境,明確自身的生態位,消除“花盆效應”,全面培養學生的翻譯能力和職業適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