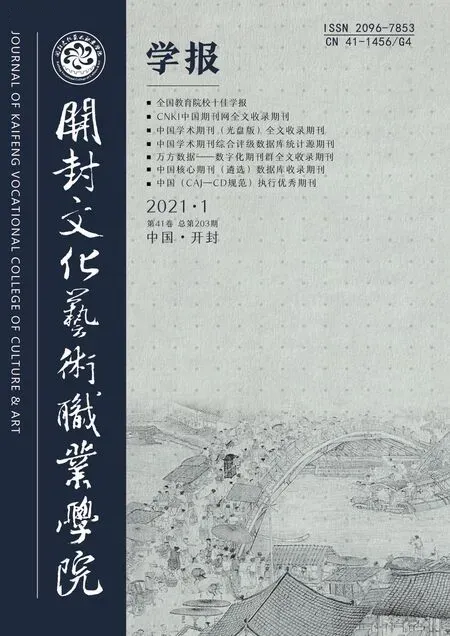商標侵權案件中市場調查報告的適用
張志遠 栗東升
(1.中央財經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081;2.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102)
市場調查報告,也有“問卷調查”“消費者問卷調查”等稱呼。在美國早期的司法實踐中,市場調查報告被視作傳聞證據,非經庭審宣誓和交叉訊問,不得作為定案依據。而后,在學界理論認識的推動下,開始作為傳聞證據的例外被廣泛應用[1]。《科學證據參考手冊》(Reference Manual on Scientific Evidence)中明確描述了調查報告作為證據使用的意義,法院開始逐步接受調查報告的價值,如有當事人訴稱商標侵權或存在混淆等問題時,可以通過調查報告獲知消費者是否發生混淆,這種方式可以大量節省法院時間,提高訴訟效率。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以下簡稱“《商標法》”)第57 條第一項和第二項規定的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內容,體現“混淆”標準作為判定商標侵權的第一標準,而是否發生“混淆”的判斷基礎正是消費者對相關商品及商標的主觀認識,只有相關公眾才是商品的使用者和商標的識別者,也只有相關公眾才是判斷商標“混淆”與否的關鍵因素。《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8 條規定:“商標法所稱相關公眾,是指與商標所標識的某類商品或者服務有關的消費者和與前述商品或者服務的營銷有密切關系的其他經營者。”而市場調查報告所具備的功能和特點,決定了它是商標侵權訴訟案件中獲取相關公眾主觀認識的最經濟方法[2]。
一、司法實踐現狀
筆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進行案例檢索,以“商標權權屬、侵權糾紛”為案由,選擇文書類型為“判決書”,共檢索得到裁判文書60 012 份(截至2020年8 月)。在此結果基礎上,再以“市場調查報告”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得到裁判文書44 份,在全部商標權權屬、侵權糾紛案件的占比僅為0.07%。在44份裁判文書中,篩選去掉未涉及市場調查報告作為證據主張的案件,得到16 份屬于商標侵權案件的裁判文書。其中,法院采納了當事人一方出具或者委托第三方出具的調查報告的有6 份裁判文書,法院不予采納涉案調查報告作為證據使用的有10 份裁判文書。法院不予采納的理由各有不同:有的以調查報告的內容設計不合格、認定缺乏科學性為由,不予認可。如在“古馳”案中,法院不予采納調查報告的理由是該調查問卷存在記錄錯誤等問題,報告結果不具有科學性和準確性。有的以調查報告系當事人單方委托出具,主觀性較強,缺乏證據的客觀性要求為由,不予認可。在“新百倫”案中,法院不予采納第三方出具的調查報告,理由是該調查報告系當事人單方委托,對方對該證據的客觀性存在異議,并且調查人員未出庭質證,故法院不予認可。也有的法官認定涉案調查報告所選取的調查對象狹窄,調查地域局限,不能客觀反映相關公眾認知的實際情況而不予采納。在四川滕王閣制藥有限公司訴四川保寧制藥有限公司侵犯商標專用權糾紛案中,法院認為調查報告系當事人自行設計,調查范圍小,對其證明力不予采納。可以看出,法官作為司法裁判者對于訴爭雙方當事人通過出具市場調查報告作為證據進行舉證持懷疑態度,即使個案中認可市場調查報告的證據能力,法官也更傾向于采用綜合其他證據認定的方式進行判斷。
二、我國商標市場調查報告的不足
(一)證據屬性未明確
目前,我國商標侵權糾紛案件中的市場調查報告適用率很低,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在商標侵權案件數量不斷增加的情況下,采用市場調查報告作為證據主張的案件數量占比極小,難以產生有效的司法影響力;另一方面,在涉及將市場調查報告作為證據舉證的商標侵權案件中,被法官采納的案件數量非常之少,可以看到司法實務對市場調查報告的證據屬性認識偏向保守[3]。從內部原因來看,我國現行法律并未明確規定市場調查報告的證據能力,法官裁判案件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司法裁判更傾向于謹慎的態度,采取結合其他證據綜合認定的方式。
(二)報告制作缺乏規范
目前,市場調查報告的成文方式主要是以市場中的商業機構為制作主體,以其工作人員為調查人員,以其實施調查工作得出的分析結論為最終的市場調查報告結果。在商標侵權案件中,市場調查報告的啟動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當事人自主進行的,通過自行實施或者付費請第三方機構進行市場調查,出具調查報告,作為支撐訴訟的證據呈貢法庭;另一種是法官依職權啟動調查,通過第三方機構進行操作,調查特定商品或商標的相關消費者,得出調查結論[4]。不論是當事人自行實施調查還是第三方機構操作,都可能出現調查過程存在瑕疵的問題。且不論舉證效力如何,法官都會以瑕疵調查報告不具有客觀性為由而不予采納。這樣的模糊處理也是目前市場調查報告適用率低的原因之一。
(三)多因素檢測的裁判困境
我國《商標法》堅持混淆可能性標準,法官通過多因素綜合判斷涉案行為是否侵權。多因素檢測法是指在對個案進行司法認定時,法官根據涉案商品性質、商標相似程度、銷售區域、消費者類型等因素綜合考慮,最終作出判斷[5]。商標侵權案件的性質決定了涉及相關公眾人數眾多,全部出庭不具有實操性,這種判斷方法就需要法官在個案中設身處地體會消費者心理,結合多種已知信息綜合進行侵權判定。因此,面對當事人提交市場調查報告作為證據主張時,法官囿于市場調查報告無法律依據而難以直接判斷,加之慣于采用多因素檢測形成的商標侵權裁判思維,促使法官在個案裁判時傾向弱化單一市場調查報告的證據作用。即使有少數案件認可調查報告的證據屬性,也因案件數量極少,難以形成裁判性指導。
三、我國商標市場調查報告的完善
(一)明確證據屬性
從立法上明確市場調查報告的證據屬性,肯定市場調查報告的證據合法性要件。近幾年我國司法實踐的探索表明,市場調查報告在商標侵權案件中有適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方面,市場調查報告以直面消費者的方式,通過科學問題設計,采集特定消費者對商品的顯著性、類似性等內容的客觀反映,以證明待證事實,符合證據的客觀性要件;另一方面,市場調查報告針對的對象為特定商品的實際消費者和潛在消費者,以及相關經營人員,報告結論與待證事實與特定消費者相關,符合證據的關聯性要件。目前,最容易被質疑的是市場調查報告的合法性要件。因此,應考慮在商標法律體系納入市場調查報告內容。具體而言,對證據種類的考慮,現階段不宜大規模修改證據法條文,可參照現有證據形式中的鑒定意見進行法律適用。同時,以司法解釋或部門規章的方式規定調查對象的選取、調查問卷的設計等事項,從立法上肯定其合法性要件,為市場調查報告的司法適用提供法律環境。
(二)規范調查機構
借鑒協會管理模式,制定市場調查報告中介機構管理制度,進行從業人員培訓管理。在涉及訴訟的市場調查報告業務中,調查機構及調查人員應履行注意義務,根據法院要求進行報告制作和內容設計,必要時由調查報告主要負責人員出庭闡釋調查報告的內容。同時,引入調查報告的審查機制。當事人在商標侵權案件中通過市場調查報告進行舉證時,同時應當提交調查報告機構的資質證明及其他證明材料,由法官對其進行司法審查,督促調查機構規范運作。此外,我國公證制度已經逐步完善,可考慮由公證機構參與市場調查報告的證據舉證過程,保證調查報告制作過程的透明、留痕,提高市場調查報告的司法適用率。
(三)引入技術輔助人員
引入技術輔助人員,建立商標侵權判斷技術支撐模式。具體是指,在商標侵權案件中,由技術輔助人員監督市場調查報告的形成過程。啟動市場調查報告前,可由法官與雙方當事人進行協商,由技術輔助人員協助確定調查報告的對象范圍及問卷內容設計。調查報告的過程由技術輔助人員監督,調查報告呈給法官時,技術輔助人員也應出庭,就調查報告的形成進行闡釋。同時,市場調查報告的證據主張作為商標侵權判斷司法審查的新型方式,多以抽樣調查方式運作,樣本選擇的差異影響最終調查結果。多因素檢測雖然考慮因素廣泛,但依托法官主觀經驗判斷,司法理性不足。因此,在司法適用中,二者應當結合使用,互相補充,逐步增加市場調查報告的司法適用,積累審判經驗,以應對不斷增多的商標侵權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