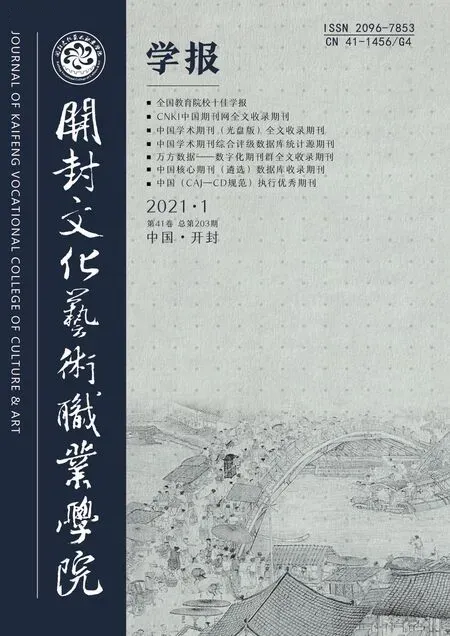曹禺話劇創作的本土元素探析
胡 芳
(福建師范大學 文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曹禺是現代杰出的話劇作家,觀其劇作,可以看出他對西方文化極強的消化能力,從古希臘的命運悲劇到莎士比亞的性格悲劇,從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到奧尼爾的現代主義戲劇,西方著名戲劇大師的思想內涵和作品都對他的話劇創作產生過影響。但曹禺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其話劇的主旨內涵、情節故事、人物塑造和寫作手法都有明顯的中國特色,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
以儒佛道三家思想為基礎的中國傳統文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文化立場和價值觀念。中國人對儒佛道思想是兼收并蓄、融會貫通的,不管是為人處世還是著書作文,都體現了儒佛道思想。曹禺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作家,其作品中體現的強烈的愛國主義、人道主義、理性精神等,與傳統文化一脈相承。
儒家思想以“仁”為核心,把“仁”視作道德規范的最高準則。孔子呼吁人們要以仁愛之心待人,要尊重、包容他人,并且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曹禺出生于湖北省潛江縣的一個大家族,祖父是私塾先生,父親是軍人出身的官僚。曹禺沒有上過小學,他的父親請老師教他學習孔孟之道,儒家思想深深地浸潤了曹禺的心靈。所以,曹禺在刻畫戲劇人物時,對“仁者”表現出明顯的敬仰,對“不仁者”抱以深深的同情。我們可以從愫方、瑞玨這些有著近乎完美道德形象的典型人物中領會儒家思想對曹禺的深刻影響。愫方是一位富有人情美和人性美的傳統女性,她愛戀著表哥曾文清,但曾文清遵從父母之命娶了家世相當的曾思懿。然而,愫方仍無怨無悔地照顧他的家人。瑞玨和覺新是包辦婚姻,雖然知道覺新愛慕著梅表姐,但她仍然對丈夫關懷備至,對梅表姐表現出深深的同情。愫方和瑞玨身上的溫柔善良、尊重他人、關愛他人、無私奉獻的美德與儒家以“仁”為核心的道德哲學不謀而合。擁有一顆“仁”心的曹禺對這些女性給予極大的肯定和贊美:“特別是像愫方這樣秉性高潔的女性,她們不僅引起我的同情,而且使我打內心里尊敬她們。中國婦女中那種為了他人而犧牲自己的高尚情操,我是愿意用最美好的言詞來贊美她們的,我覺得她們的內心世界太美了。”[1]對于“不仁者”,曹禺則為他們設計了“罪有應得”的結局,如周樸園最后家破人亡、獨自懺悔;仇虎最后選擇自殺;殘忍自私的曾思懿在曾家處境艱難,孤立無援,苦苦掙扎。
曹禺的父親在中風后研究起了《金剛經》,繼母也曾教曹禺背過往生咒,所以佛教思想在曹禺心中埋下了種子。曹禺對佛教思想的領悟吸收在于他的劇作中體現了世事無常、命運不公,話劇中的人物相信善惡因果論,最典型的是《雷雨》中的人物,周樸園和魯侍萍年輕時犯下的錯,以30 年后周萍和四鳳這一對有血緣關系的兄妹在不倫之戀的悲劇中雙雙慘死終結。周樸園作為封建大家長,嚴格管束家人的思想、生活,使得他的妻子和前妻之子亂倫;作為資本家,橫征暴斂,無所顧忌地犧牲他人的生命達到自己的目的,使得自己的親生兒子同自己作對。最后,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在懺悔中度過余生。而魯侍萍得知四鳳和周萍的“丑事”時,哀嘆“人犯了一次罪過,第二次也就自然地跟著來”[2]。魯侍萍認為是自己的“不規矩”,才讓自己的兒子和女兒產生了畸形的情感,兒女的死就是她的報應。
道家觀念對曹禺的話劇創作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老子主張清凈無為,回歸自然;莊子主張追求自由,掙脫物質束縛,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他們的思想在曹禺話劇創作中較為明顯的表現是,《日出》開頭引用了老子《道德經》七十七章“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等內容,奠定了話劇諷刺黑暗現實的基調。曹禺借《日出》批判“損不足以奉有余”的剝削制度,倡導建立一個平等自由的社會,這與道家的理念有契合之處。此外,曹禺還把道家的思想融入人物個性塑造。蘩漪是曹禺塑造的一個張揚灑脫、崇尚自由的女性形象,她熱情如火,美麗強悍,敢愛敢恨,極端而又尖銳。她愛上自己名義上的兒子——周萍,生命中原始的向往自由的力量給了她沖破封建禮教束縛的勇氣,她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愛情,即使這種畸形的愛情不符合人倫。當她被周萍拋棄時,她掙脫理智的束縛,抱著非生即死的心態毀滅周萍的生活。蘩漪是最具“雷雨”性格的角色,這是因為她真實,不掩飾自己的欲望,勇敢地暴露自己的內心,敢于付出全部的力量爭取自己的權利。蘩漪的形象受到曹禺的贊賞,表明了曹禺對回歸自然、追求個性與自由的道家觀念的認同。
曹禺身上有儒家以仁待人的責任意識,佛家自我覺悟、超脫現實的思想性格,道家順其自然、追求本真的精神境界,這些傳統文化思想真切表現在曹禺的劇作中。
二、古典戲曲藝術的借鑒
受家庭和環境的影響,曹禺對傳統戲曲十分熟悉,他曾回憶家里有一套《戲考》,讀得很熟。除了閱讀戲曲典籍,曹禺還有豐富的看戲、演戲經歷,中學時期他加入了南開新劇團,開始演戲。大學時,他認識了巴金,還和同學靳以去戲樓看京劇。他深知觀眾喜歡什么、想看什么。
民間小調有著漫長的歷史,用詞通俗、曲調柔和,適宜傳唱,在中國傳統戲曲中廣泛運用。曹禺把民間小調融入自己的劇作中,可謂是錦上添花。《原野》第一幕引入民間小調“正月里探妹正月正,我與那小妹妹去逛花燈”[3],這首情歌為花金子與仇虎相遇的情節埋下伏筆,使故事發展更為順暢。而后文中的《妓女告狀》等曲子對故事發展過程和人物命運的揭示更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據此可以看出,民間小調雖然通俗、直白,卻能增加話劇的內涵和趣味性。曹禺在話劇創作中融入民間小調這種傳統戲曲形式,有利于塑造豐滿的人物形象,增強語言表達效果,體現強烈的個性色彩。
傳統戲曲主要以語言、動作表現故事情節,戲劇場景往往集中于某一個或幾個固定的場所。曹禺對中國傳統戲曲十分熟捻,也熟知舞臺的虛擬性,因此,他在劇作中有意將有助于營造舞臺氛圍的場景集中起來。如《雷雨》中,將30 年間錯綜復雜的故事安排在周樸園家的客廳和魯侍萍家的房間兩個場景中展現;《日出》中以陳白露和翠喜的臥室為主要活動場所;《原野》則是在焦家和黑林子展開故事情節。除了舞臺的虛擬性,曹禺的劇作中還有人物的虛化。《日出》中,有一個人物沒有露面卻一直被人提及,他就是金八。他有錢有權,無所不能。在金八面前,顧八奶奶、李石清等所謂的“人上人”都得夾著尾巴賠笑臉。
三、詩意藝術手法的追求
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古典詩詞和中國傳統戲曲,講究抒發真情實感,追求“形而上”的藝術。曹禺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總是以詩人的心態捕捉畫面,運用詩化的語言表達情感。
曹禺的劇作中常引用古典詩詞,或巧用古典詩詞長短句結合的技巧,使戲劇語言帶有濃厚的詩化色彩。《家》中,覺慧時不時教鳴鳳讀古典詩詞,如蘇軾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當兩人吟唱千古絕句“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時,濃濃的愛意流淌其間;當鳴鳳深情訴說對覺慧的愛慕:“這臉只有小時候母親親過,現在您挨過……再有就是太陽曬過,月亮照過,風吹過了”[4],這些語言樸實無華,但采用長短句結合的方式,配上獨特的語言背景,動人的愛戀之情便隨境而生了。曹禺的文字流露出深情款款的意味,飽含著對鮮活生命的尊重和對詩意生活的向往與追求。
綜上,曹禺借鑒古典詩詞的抒情手法,寓情于景,創造了和諧統一的詩化意境。
結語
曹禺之所以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杰出的話劇作家,他的劇作廣泛流傳,是因為其作品恒久的歷史價值和雋永的藝術魅力。這種魅力的源泉在于,曹禺在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接受古典戲曲藝術的熏陶,形成了獨特的詩意戲劇風格。雖然曹禺受西方戲劇的思想觀念和藝術手法影響很大,但其話劇作品的載體依然是中國傳統文化。長期以來,學者對曹禺話劇的研究主要從西方文化角度分析其創作淵源,而忽視傳統文化對他的影響,這是一大遺憾。因而,探究本土元素對曹禺話劇創作的影響有重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