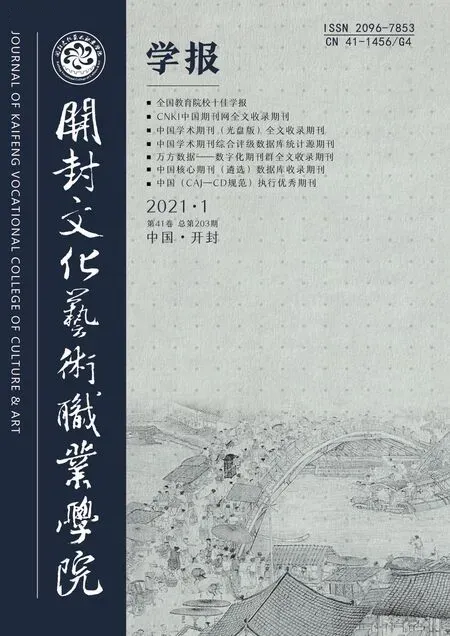托妮·莫里森《家》中主人公弗蘭克的抗爭之路
趙玉存
(河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00)
作為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第10 部作品,《家》以20 世紀50 年代的美國為背景,通過描寫黑人男性弗蘭克·莫尼(Frank Money)抗爭意識的覺醒,踏上南下旅途找尋自我身份,最終在洛特斯小鎮實現自我救贖三個階段展現了其艱難的抗爭歷程,體現了小說的成長主題。美國學者莫迪凱·馬科斯將成長小說定義為:“年輕主人公經歷了某種切膚之痛的事件之后,或改變了原有的世界觀,或改變了自己的性格,或兩者兼有;這種改變使他擺脫了童年的天真,并最終把他引向一個真實而復雜的成人世界。”[1]在他人的引導下,弗蘭克最終治愈了因戰爭引起的心理創傷,找到了自身的家庭和社會角色。
一、抗爭意識的覺醒
種族歧視和家庭環境的雙重折磨在弗蘭克的心中埋下了抗爭的種子,離鄉參軍體現了弗蘭克初步覺醒的抗爭意識,在北方的痛苦生活成為弗蘭克抗爭意識覺醒的加速器,而妹妹茜的求助信使弗蘭克的抗爭意識徹底覺醒。20 世紀50 年代的美國被認為是“一個道貌岸然的、假正經的、虛偽的和狹隘的世界”[2]。然而,對于弗蘭克而言,對家庭不聞不問的父母以及尖酸刻薄的祖母并沒有給他營造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不僅如此,煩悶枯燥的小鎮生活使弗蘭克忽視了小鎮黑人善良友好、陽光積極的一面,從而選擇參軍來逃離這個令人窒息的地方。冷漠的家庭環境以及乏味的小鎮生活為弗蘭克抗爭意識的覺醒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條件。
雖然參軍沒有帶給弗蘭克想要的生活,但弗蘭克的抗爭意識并沒有因此被磨滅,而是隨著戰爭帶來的精神創傷以及戰后在北方的痛苦生活逐漸強化。朝鮮戰爭結束后,美國政府沒有履行優待參軍者的諾言,所以弗蘭克退役后的境況變得愈發糟糕。恰如洛克牧師所言:“你們出去打仗了,回來了,他們卻把你們當成狗。不對,還不如狗呢。”[3]16那場駭人驚聞的戰爭不僅讓弗蘭克目睹了童年摯友的離世,而且成為他揮之不去的噩夢。受到種族隔離政策的影響,弗蘭克在乘坐公交車時只能蜷縮起六尺三寸的身軀,謹慎地坐在屬于黑人專座的最后一排。生活的壓力迫使弗蘭克和女友擠在條件惡劣的出租屋內,為了掙錢而四處奔波。盡管弗蘭克姓“錢”(Money),但是在白人的傾軋下,他卻掙不到錢。精神創傷、種族歧視、經濟貧困使退役歸來的弗蘭克在北方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熱的苦境,也成為弗蘭克抗爭意識覺醒的催化劑。
在成長過程中,他人的求助對自我的發展也會產生積極的影響。茜的求助信成了弗蘭克人生的轉折點,而帶領妹妹返回南方老家的決定體現了弗蘭克抗爭意識的徹底覺醒。在收到茜的求助信之前,弗蘭克一直在北方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妹妹作為弗蘭克心中唯一的家人,如他的影子一般重要:“如果不是聽說妹妹遇到了麻煩,我連回家的念頭都不會有。”[3]84兄妹之情徹底激起了弗蘭克的抗爭意識,令他決心離開使他委曲求全的北方城市,毅然踏上反抗命運、反抗壓迫、反抗種族主義的抗爭之旅。
二、自我身份的找尋
除擺脫不公正的生活外,找尋自我身份也是弗蘭克南下之旅的一個重要目的。美國黑人受到“美國主流文化的影響,很多人會不自覺地認同于美國文化,希望能更好地融入主流社會”[4],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他們對自身民族身份的認同感。在弗蘭克的成長道路上,親情的缺失使弗蘭克難以形成對自我身份的完整認知;對洛特斯小鎮的偏見使弗蘭克缺乏對黑人身份的認同感;朝鮮戰爭造成的精神創傷以及在北方的痛苦遭遇加劇了弗蘭克民族身份和“個體身份的游移和破碎”[5]。逃離醫院坐上開往亞特蘭大的火車,意味著弗蘭克對自我身份的追尋。在旅途中,眾多黑人同胞以及各類白人扮演著弗蘭克成長道路上的引路人的角色,幫助弗蘭克找尋自我身份,進一步刺激著弗蘭克去抗爭。
黑人同胞以正面引路人的形象,令弗蘭克感受到了來自同伴的愛與關懷,堅定了他回歸洛特斯小鎮的信心。被警察打斷右臂但依舊對生活保持樂觀的黑人男孩托馬斯,重燃了弗蘭克對生命的熱愛與自信。當弗蘭克詢問托馬斯長大之后想做什么時,托馬斯的回答是想要成為“一個男人”[3]32,體現了他想要獲得和白人一樣的平等權利,被人尊重的渴望,同時也激起了弗蘭克對人生的思考和對黑人身份的重新定位。坐在開往亞特蘭大的火車上,弗蘭克突然發現過往的記憶不僅“再也沒有碾壓他”,而且自己“可以清晰地憶起每一處細節、每一次痛苦”[3]100。在黑人同胞的幫助下,弗蘭克心靈上的創傷逐漸愈合,能正視曾經的痛苦回憶,而不再被其束縛。
弗蘭克的成長同樣受到了以大個頭男子和白人醫生為代表的反面引路人的影響。弗蘭克從大個頭男子挑釁的言語與行為中受到了刺激,由此,面對他人的欺辱,他不再沉默,而是勇敢還擊,找回了被壓抑的男子氣概。憑借著親情的力量以及從還擊大個頭男子中找回的勇氣,弗蘭克由內而外散發出的男人力量讓白人醫生棄槍而逃。經歷了所有的這一切,弗蘭克找到了自己作為黑人的身份。
三、實現自我的救贖
在外漂泊已久的弗蘭克最終在洛特斯小鎮找到了久違的歸屬感,實現了自我的救贖。20世紀50年代,麥卡錫主義的恐怖監控讓本就處于社會底端的美國黑人的境況愈發艱難,他們隨時會遭到白人的威脅。“孩子們仍然在大笑,奔跑,叫嚷著玩耍;后院把床單夾到晾衣繩上的女人們在唱歌。”[3]121歡快的小鎮生活讓弗蘭克感受到了真實的安全感和親切感,并最終決定留在這個帶有濃郁黑人文化傳統的小鎮,結束在外游蕩的生活,以積極的態度迎接嶄新的生活。
在理想和現實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重新認識過去的自我是實現救贖的途徑之一。作為“非裔種族最終的歸宿和家園”[6],洛特斯小鎮不僅友好地接納了弗蘭克兄妹,治療了茜的身體,而且為兄妹二人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支柱。黑人社區折射出積極陽光、堅韌不拔的黑人文化,使弗蘭克逐漸融入這個充滿活力的黑人群體,勇敢地正視曾經遭受的磨難,實現了精神上的救贖。因為茜清醒后告訴弗蘭克自己能看到一個小女孩的笑臉的幻覺,所以弗蘭克再次想起了朝鮮戰場上那個被自己親手打死的無辜的朝鮮女孩。此時的弗蘭克有了親口承認罪行、說出事情真相的勇氣,并像自己的名字(Frank)一般坦白了一切:“打爆那個朝鮮女孩腦袋的是我。”[3]139洛特斯小鎮強大的治愈功能以及歡樂祥和的氛圍,讓弗蘭克決定重新打掃和修理父母的房子,改變之前對下地勞作的看法,和大家一起等待著被雇傭。
做一件“真正有價值的事情”[3]141的決定是實現救贖的關鍵。當弗蘭克在洛特斯的生活逐漸走向正軌的時候,馬場埋尸正等著他去完成。弗蘭克從老人口中得知,十幾年前白人借“斗狗”之名,以殘害虐待無辜的黑人為樂。重埋尸體時,弗蘭克“小心翼翼”“抱在懷里”的舉動與他之前在北方四處漂泊、迷茫頹廢,并且隨時會發瘋的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體現了弗蘭克的蛻變。重新埋葬尸體后,弗蘭克在墳墓前豎起木制墓碑,寫上碑文“一人站立于此”[7],這不僅意味著弗蘭克“對自己個人罪行的救贖和面對與接受黑人集體屈辱歷史的一種超越”[8],而且預示著弗蘭克已與頹靡消沉的過去漸行漸遠,明日的弗蘭克將會以嶄新的姿態“站起來”迎接新的生活。
結語
在《家》中,莫里森講述了弗蘭克艱難的抗爭之旅,揭示了黑人在美國所遭到的歧視以及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抗爭路上的種種遭遇,不僅刺激并強化了弗蘭克的抗爭意識,而且促進了弗蘭克的成長。在秉承黑人文化傳統的洛特斯小鎮,弗蘭克最終找到了歸屬感,走出了精神困境,實現了自我救贖。作為一名黑人女作家,莫里森通過描寫弗蘭克的成長歷程,暗示了黑人應在堅守價值觀念,認清黑人身份,團結一致做斗爭的過程中,構建屬于自己的民族家園,實現民族的解放與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