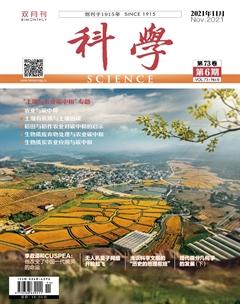土壤有機質與土壤固碳
鄭聚鋒 陳碩桐
全球地表以下至1米深的土層儲存碳約25 000億噸(15 500億噸有機碳和9500億噸的無機碳)[1]。其中有機碳庫為大氣碳庫(7500億噸)的2倍,接近陸地植被生物量碳的1.8倍。土壤有機碳庫是地球表層系統中最大、最具有活性的生態系統碳庫,其微小變化將對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產生巨大影響。據統計,全球每年因土壤呼吸(包括土壤生物呼吸和土壤中植物根系呼吸)釋放的二氧化碳為500億~760億噸,占陸地生態系統與大氣間碳交換總量的2/3,接近于大氣碳庫的1/10[2]。可見,土壤有機碳的保持與穩定對全球氣候變化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并影響著陸地生態系統的分布、組成、結構和功能。
土壤有機碳庫主要集中在植物根系分布的表層。由于氣候、植被和土壤類型等不同,土壤有機碳儲量地理差異較大。例如,干旱區農田土壤有機碳密度較低,僅為30噸/公頃,而在高緯度草原地區可高達80噸/公頃以上。據估算,全球土壤表層(20厘米以內)有機碳儲量約為6150億噸,占土壤剖面(1米)有機碳總儲量的40%。土壤表層碳密度易受到人為活動的強烈干擾,因而土壤碳管理在全球環境管控中具有重要地位。
土壤有機質與土壤碳庫
土壤有機質及其類型
一般來說,土壤有機質主要來源于植物殘體、根系及其分泌物,以及土壤微生物及其代謝產物,是不同分子大小和碳鏈結構的糖類、單寧、脂質、木質素、蛋白質和芳香族化合物等類群的有機物質的集合體。有機質組分在土壤中經歷不同的分解與轉化過程,同時與土壤礦物質和團聚體結合并受其保護作用。以閉蓄態或包被態等物理形式保護在土壤團聚體內和團聚體間的有機質,稱為顆粒態有機質,屬于潛在快速更新的碳庫;而主要以化學結合態固定存在于礦物質組分的有機質,稱為礦物結合態有機質,它們分解程度較高、分解較慢,屬于抗性有機質,為慢更新碳庫。因此,顆粒態有機質富集植物來源的較新鮮有機質,微生物利用性較高,而礦物結合態有機質,因植物源有機質組分基本分解,主要為微生物來源的有機組分。另外,微生物分解產物短期可能仍以分解中間狀態的小分子有機組分存在,環境中遷移性較強,這部分主要是可溶性有機質。土壤中微生物生物體,在測定土壤有機質時也被檢測到,且可以采用單獨的熏蒸提取而測出來,這部分活的和死亡的微生物成為微生物生物量碳。一般地,微生物生物量碳占土壤有機碳的1%~3%,特殊情形下可能占5%。有機質豐富的土壤,顆粒態有機碳可能占主導地位,反之,以微生物來源為主的礦物結合態碳占優勢。最近十多年氣候變化研究日益證明,土壤中有機質積累實際上是植物源有機質不斷被土壤/團聚體結合保護的結果,因此,土壤有機質與團聚體發育不可分割,土壤有機質的保持實際上是土壤團聚體的發育和穩定的過程,這將碳庫與土壤結構緊密地聯系起來。
土壤團聚體與土壤有機質連續體概念模型
土壤團聚體是礦物質—有機質—微生物相互作用形成的土壤基本顆粒,是土壤生物地球化學循環及土壤肥力和質量的基本反應單元,是土壤有機質儲存的重要場所。團聚體的建成可以理解為有機分子與礦物質顆粒的結合,先形成有機—無機復合體,后通過新有機質(顆粒態有機質)膠凝為更大的團聚體。大團聚體是土壤中有機質—微生物—生物活性的功能活躍區域[4],因為棲于其中的微生物往往選擇保持有可利用碳組分(如顆粒態有機碳)的微生境。土壤有機碳庫形態的多樣性分布和有機質分子組成的多樣化構成了土壤生物多樣性,并潛在影響土壤的生態系統功能多樣性。隨著團聚體保護與封存在土壤固碳中越來越得到重視,了解團聚體尺度有機碳的穩定與微生物活性的關系是理解土壤固碳與生態系統功能協調關系的核心問題。

美國土壤學家萊曼(J. Lehmann)等人提出的土壤有機質連續體概念模型[5],展現了土壤有機質理論應用的前景。該模型提出的觀點涉及兩個方面:一是土壤有機質分子的微生物分解與有機質分子在團聚體中的分布和空間隔離有關;二是有機質分子在團聚體中的存在與其和土壤礦物結合保護而避免微生物挖掘利用有關。因此,進入土壤的有機質的分解序列與其在團聚體中分布和結合穩定的序列存在契合關系。土壤中有機質是一系列既處于不同分解階段又結合或保護于不同粒徑團聚體的生命來源的有機分子集合。考慮到有機質的分解程度和微生物參與分解的區系序列,分解程度較低的生物大分子和主要參與初期分解的真菌及其殘體多存在于粒徑較大的團聚體中,而充分降解釋放的較小分子以及主要參與后期分解的細菌及其殘留物趨向于向較小團聚體集中。團聚體結構中土壤微生境多樣性,可能賦予了土壤有機質的分子多樣性與微生物區系及種群的多樣性。
土壤有機質的功能
土壤有機質的積累改善了土壤質量并促進土壤功能,這尤其體現在農業生產力和土壤管理的可持續性方面。作為土壤的關鍵組成部分,有機質通過對土壤結構發育和地球生物化學過程的雙重控制,對各種土壤過程起著調節作用,發揮著多種生態服務功能。這些功能主要表現在:①保障生物量生產和能源生產; ②維持土壤生物多樣性;③提供養分、保水和保肥的功能;④固碳和穩定氣候變化功能;⑤改善土壤物理結構的功能;⑥生物激活功能,即刺激土壤生物(包括根系)代謝活動的功能,也包括可礦化有機質對土壤微生物的激發效應。隨著對土壤有機質含量、組成、結構和功能研究的深入和有機分子分離、檢測和定量等有機化學分析及鑒定技術的提升,剖析土壤有機質的豐度、組成、結構及其生物活性的條件日益成熟,有機質研究終將由“黑箱”抵近“白箱”。
不同生態系統中的土壤有機碳庫
陸地生態系統主要包括森林生態系統、草原生態系統、濕地生態系統與農田生態系統等。其中全球森林、草原和農田生態系統碳儲量分別約占整個陸地生態系統碳儲量的46%~56%、29%~31%和5%~8%。這些生態系統中土壤有機碳儲量所占比例較大,其有機碳庫變化和調控是陸地生態系統碳循環與氣候變化反饋的核心機制。
森林生態系統 這是陸地生態系統中最大的碳儲庫和碳吸收匯。森林土壤按1米深估算,其有機碳儲量達7900億~9300億噸,是全球土壤有機碳儲庫的主要貢獻者[3]。按照生態系統的碳庫估算,全球森林土壤層持有的有機碳庫分布為:北方針葉林 4710億噸,熱帶亞熱帶森林4800億噸,溫帶森林1000億噸,可見在全球碳庫中,保護北方森林和熱帶森林具有優先地位。在中國,森林土壤有機碳主要儲存于東北黑土區和熱帶亞熱帶紅黃壤地區。北方苔原土壤碳庫對日益加劇的全球變化最為敏感,而熱帶森林土壤碳庫因植被退化最不穩定,所以溫帶森林土壤可能是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的主要調節者。
草原生態系統 這是世界上分布最廣的植被類型。據估算,世界草原面積約為35億公頃,有機碳儲量達到7600億噸,約占陸地生態系統總有機碳儲量的15%,其中近90%以有機碳的形態貯存在草原土壤層中。在草原生態系統中,土壤有機碳的來源主要是植物殘根和凋落物。草原中土壤有機碳主要集中于0~20厘米的表層土壤中,其中0~10厘米土壤有機碳含量是深層土壤(80~100厘米)的4~10倍。草原土壤隨著水分遞減,碳密度也在逐漸降低,其中黑鈣土、暗栗鈣土、栗鈣土與同緯度的森林土壤碳密度相當[6]。
農田生態系統 全球農田耕地面積約為13.7億公頃,其有機碳貯量約為1700億噸,超過全球陸地有機碳貯量的10%。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碳儲量存在較大差異。例如,水稻土作為長期水耕熟化下形成的人為土壤,固碳能力顯著高于其他農業土壤。在我國,近30萬公頃的水稻土碳庫為13億噸,碳密度46噸/公頃以上,而農業土壤的平均有機碳密度僅為36噸/公頃左右。從農田土壤有機碳在剖面的豐度分布來看,表層土壤由于容易受到農業固碳措施的影響,其含量大大高于深層土壤。

濕地生態系統 這也是陸地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之一,盡管全球濕地面積僅占陸地面積的4%~6%,但因濕地植物較高的生物量生產率和較低的分解率,濕地土壤能夠儲存大量的有機碳。全球濕地土壤總碳庫為5500億噸,占全球陸地土壤碳庫的1/3[7]。如果這些有機碳全部釋放到大氣中,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將增加約50%,全球平均氣溫將升高0.8~2.5℃。研究表明,濕地土壤有機碳密度,一般在150噸/公頃以上,很多沼澤和泥炭濕地的碳密度高達300噸/公頃。在一些泥炭沼澤濕地,表層土壤有機質含量高達50%以上。全球濕地碳絕大多數儲存在泥炭地中,主要分布于北半球溫帶及寒帶地區。濕地作為溫室氣體的儲存庫、排放源和吸收匯,對全球氣候變化具有重要的影響,濕地開發因造成溫室氣體排放而越來越受到詬病。
農業土壤固碳措施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四次評估報告指出,農業溫室氣體減排潛力90%是通過土壤固碳,因此,通過適當的農業管理措施,農業土壤可以發揮較大的固碳作用,從而減少農業生產引起的土壤溫室氣體排放。農業上主要的土壤固碳措施有以下幾種。
秸稈還田 它是常見的農業管理措施,也是重要的土壤固碳途徑之一。作物秸稈是農業生產過程中的主要副產品,含有豐富的氮、磷、鉀等營養元素和其他微量元素,是一種寶貴的可再生有機資源。秸稈還田不僅能改善土壤結構,增加土壤團聚體穩定性,提高土壤中養分含量,而且能促進作物生長,增加作物產量,尤其重要的是能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減少土壤溫室氣體排放[8]。據估計,秸稈約占生產性農作物總生物量的50%,全球范圍內每年農業生產約產生40億噸秸稈,具有巨大的固碳減排潛能。以中國江蘇為例,2014年未被利用的秸稈資源相當于170萬噸標煤,若將其全部還田,所返還的養分替代化肥可抵消36萬噸二氧化碳當量溫室氣體的排放;若將其全部進行熱裂解炭化,則可以生產近130萬噸生物質炭,發電9.19億千瓦時,所生產的生物質炭有機碳含量為77萬噸,施入土壤相當于固碳280萬噸二氧化碳當量。綜合土壤固碳和稻田甲烷減排,推廣秸稈“旱重水輕”還田技術(即主要還田于旱作季,盡量少還田于稻作季),中國農田每年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當量約2.1億噸,相當于2000年中國全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6.2%。

生物質炭 它是有機物質在完全或部分缺氧的條件下低溫熱裂解生成的固態混合物,原料可包括作物秸稈、樹木枝干、畜禽糞便和稻殼等,其在農業應用實現土壤固碳的技術近年來受到了廣泛關注。由于生物質炭較為穩定,難以被微生物降解,使得其成為土壤的惰性碳庫,只有5%的碳會通過土壤微生物的作用重新釋放到大氣,而土壤多固定了20%的碳。研究估計如果能將作物秸稈、樹木枝干等轉化為生物質炭施于土壤,而不是直接燃燒,全球尺度下碳排放將降低12%~84%。國際生物質炭組織估計,到2040年平均每年僅利用農林廢棄物就可以減少3.67億噸二氧化碳當量溫室氣體排放。就全球作物秸稈的利用情況來看,發展以及推廣應用低溫熱裂解生物質炭技術,對于農業應對氣候變化和實現糧食生產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保護性耕作 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保護性耕作已經為世界各國廣泛采用。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目前全球保護性耕作面積約為1.7億公頃,占總耕地面積的11%。隨著全球氣候變化加劇,人類逐漸認識到自身活動,特別是耕作對土壤溫室氣體排放的貢獻,保護性耕作作為一項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措施受到特別關注。最新的研究表明,土壤有機質分解的關鍵在于有機質在土壤中失去團聚體的保護而被微生物所分解,在常規耕作模式下,土壤結構的破壞以及頻繁的干濕交替作用,使原來受到團聚體保護的土壤有機碳暴露而被土壤微生物利用,導致土壤有機碳礦化速率提高,加速了土壤碳的釋放。實施保護性耕作后,減少了對土壤的擾動,一方面降低了土壤有機質的礦化分解,另一方面還能夠促進土壤團聚體的發育。研究表明,通過采用保護性耕作和其他農田管理措施,大約60%~70%的損失碳可被重新固定。全球范圍內,如果采用保護性耕作等碳管理措施,每年從大氣中吸收固定的碳量為 4億~12億噸,相當于全球每年排放量的5%~15%[9]。以美國為例,57%的耕地采用保護性耕作技術時,美國土壤的碳收集能力達到0.8億~1.3億噸;若有76%的耕地采用保護性耕作措施,美國土壤的碳收集能力將達到3億~5億噸,由此可見保護性耕作對于增加土壤碳匯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重要意義。
土壤固碳與可持續農業
土壤有機質是耕地地力最重要的性狀之一,是土壤質量和功能的核心。在農業生產中, 土壤有機質是至關重要的決定因子。對于我國一些糧食主產區來說, 年平均糧食單產水平與其耕地土壤的平均有機質水平密切相關。我國耕地面積約為1.3億公頃,約占我國國土面積的1/8。以占全球不到9%的耕地養活了全球1/5的人口,我國農業一直擔負著保障不斷增長人口的糧食安全的重任。然而,就碳密度來說,我國土壤總體上低于世界平均值。因此,提高我國農業土壤的碳密度對提升土壤肥力和保障糧食生產具有重要意義。
提升土壤固碳本質上看是從其量的平衡角度關注有機碳在土壤的封存,因而增加有機質儲存成為農業固碳減排的主要途徑。通過改善農業發展模式、發展可持續農業、提高農田土壤碳儲量,實現溫室氣體減排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必然要求,同時,也是提升土壤質量和作物產量的必然選擇。以生物質炭為例,因其具有良好的理化性質和高度穩定性,在農田應用中不僅實現短期土壤增碳的目標,而且還能改良土壤、降低土壤污染、改善作物的生長環境而提升產量和品質。
可持續農業要求實現生態環保、高效多元化發展。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只有將生產效益和生態效益相統一,探索固碳與保持土壤健康、提高作物產量協同的可持續發展農業道路,發展一種全新的以低能耗和低污染為基礎的綠色農業經濟,才能全面實現農產品優質化、營養化、功能化,從而達到農業生態系統的持續良性循環。
[1]方精云, 郭兆迪, 樸世龍, 等. 1981~ 2000年中國陸地植被碳匯的估算. 中國科學, 2007, 37(6): 804-812.
[2]Post W M, Emanuel W R, Zinke P J, et al. Soil carbon pools and world life zones. Nature, 1982, 298(8): 156-159.
[3]Dixon B R, Wisniewski E J, Houghton P J, et al. Carbon pools and flux of global forest ecosystems. Science, 1994. DOI: 10.1126/ science.263.5144.185
[4]Jastrow J D, Miller R M. Soil aggregate stabilization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Feedbacks through organomineral associations.// Rattan L, John M K, Ronald F F, et al. Soil processes and the carbon cycle. Washington: CRC Press, 1998: 207-223.
[5]Lehmann J, Kleber M. The contentious nature of soil organic matter. Nature, 2015, 528(7580): 60-68.
[6]王紹強, 周成虎, 李克讓, 等. 中國土壤有機碳庫及空間分布特征分析. 地理學報, 2000, 55(5): 533-544.
[7]Bridgham S D, Megoniga J P, Keller J K, et al. The carbon balance of North American Wetlands. Wetlands, 2006, 26 (4): 899-916.
[8]田慎重, 寧堂原, 王瑜, 等. 不同耕作方式和秸稈還田對麥田土壤有機碳含量的影響. 應用生態學報, 2010, 21(2): 373-378.
[9]Lal R. 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impacts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food security. Science, 2004, 304(11): 1623-1627.
關鍵詞:土壤有機質 土壤碳庫 土壤固碳 可持續農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