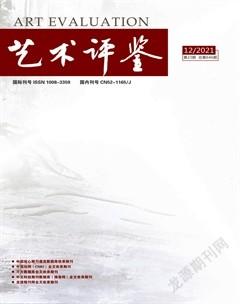泗州戲的繼承與發展探究
侯貝貝
摘要:泗州戲是安徽四大傳統戲曲之一,其音樂特色融合了南北風格,唱腔委婉與豪邁兼之,具有鮮明的地域性風格,作為國家級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泗州戲一直受到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視,人們從各種角度對泗州戲的傳承和發展提出建設性意見和建議。但是,發展泗州戲急需強根固本而非單純求新。改編傳統劇目,在表演中傳承民俗文化,加強完善理論研究,加強泗州戲演員隊伍建設,激活傳承動力,使傳承者明白其本質特征,明確泗州戲的本質意義,研究繼承什么、怎么發展泗州戲才是首要任務。
關鍵詞:泗州戲? 傳承? 發展
中圖分類號:J8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3359(2021)23-0158-04
一、改編傳統劇目
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與魂,作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組成部分的戲曲藝術,不僅記錄了隨著時代湮沒的社會歷史文化變遷,還在不同時代,以不同的表現形式反映民風、民俗與民情,是傳承和表現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泗州戲具有濃郁的地方文化特質,其演唱特點、伴奏形式、表演程式、發音技法等都具有原生態文化屬性,在那個群眾文化生活極度匱乏的年代,由于泗州戲拉的是家常,演的是身邊事,音樂唱腔簡單、樸實,所到之處都備受人們歡迎,人們常常翻山越嶺,趕場欣賞。聽戲是老百姓為數不多的精神生活,在這個精神世界里他們能夠學習歷史知識、禮教涵養,這對于塑造民眾的品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隨著泗州戲的流傳,一些劇目也能起到教育教化的社會作用。地方戲曲以演出劇目為載體進行移風易俗的教化活動,從而起到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戲曲的教化和中國儒家文化一樣都是中華民族文明的精神符號。泗州戲中的很多傳統劇目都取材于民間傳說、遺聞軼事等,和社會現實十分契合,鄉土氣息濃郁。劇目內容上沿襲傳統觀念,使廣大群眾產生了情感上的共鳴。它以當地人們所熟悉的正義或非正義的形象來說教,在戲曲表演方面用戲劇化的行為、表演程式來弘揚百姓公認的道德品格,諷刺甚至譴責生活中的假惡丑,老百姓在欣賞戲曲時,情不自禁的融入戲曲世界中,自然而然地接受戲曲中所體現的說理教化內容,這對人民遵守社會公序良俗起到積極作用。抗戰時期泗州戲藝人積極參與抗戰中,自編自演許多全民抗戰題材的劇目,在抗日救國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泗州戲以現實生活為例,形象而生動地訴說著人生至真至純的道理,對于普通民眾來說有很強的感染力,于是出現了將戲曲教化帶入生活的例子。富有哲理性且體現當時人民的愿望、思想和感情的戲曲形式受眾面逐漸寬廣,從而完成了戲曲藝術的精神使命。正是有了廣大群眾的喜愛與支持,泗州戲藝人才能在實現養家糊口重任的同時,使泗州戲得以頑強的流傳下來。
例如泗州戲傳統劇目《三蜷寒橋》,該劇講述宋代書生黨金龍進京應試得中,攀結權貴。其生身之母朱氏千里尋親至京城,黨金龍六親不認,竟然用腳將其母親踢下了寒橋。恰好得到官屠盧文進的救助,并且視其為娘。沒過多久,朱氏女兒黨風英來京尋找親人,母女二人得以相見,朱氏將其愛女許配給盧文進,并贈予祖傳之寶“四寶珠”,盧文進又把此寶物奉獻給皇上,因此圣上封盧文進為進寶狀元,獲封西臺御史。有一天,盧文進去拜東臺,黨金龍以“四寶珠”為他家的傳家寶,扭送盧文進到開封衙門,可是朱氏出堂作了證詞,并且痛斥逆子;包公判忤逆不孝之罪,用狗頭鍘將黨金龍鍘下。固然情節實屬虛構,但戲曲所表達的恩怨情仇、正義邪惡本質上是社會黑暗的折射,即人民痛苦的呻吟,也表現出人民對社會變革的美好愿望。他們質樸善良的品性在呼喚人間真善美的出現,他們希望現實生活不能完成的在戲曲里面做到,從而使審美回歸到精神層面,進而使得戲曲審美獲得意境美的境界。
泗州戲按題材來說十分廣泛:從生產生活、歷史風俗、談情說愛,到武林俠義、保家衛國等。泗州戲的演出很多出現在婚喪嫁娶、慶生、祭祀、開業典禮、廟會等活動中,這些傳統劇目大都來自民間,又走向民間。泗州戲除了有類似其他地方小戲的精彩內容、靈活表演、完整程式以外,還具有與地方文化風格意義一脈相連的戲曲內容。關于泗州戲,有許多民間普遍流傳的諺語:“從東莊到西莊,要聽還是拉魂腔”“女人聽了拉魂腔,面餅貼在鍋蓋上;男人聽了拉魂腔,丟掉了媳婦忘了娘”。可見大家對泗州戲的熱愛與迷戀。這種戲曲表演的道德教育不言而喻,道德說教要有靈活的形式體現才能潛移默化的深入人心,戲曲的形式說教就更容易達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泗州戲所呈現的道德觀念與歷史傳承、地域性有直接的關系,如仁義禮信、善惡相報、親情友情、家庭和睦等等。藝術以劇目為載體,得到百姓的情感共鳴。泗州戲所反映的都是老百姓的人生觀念,它所蘊含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念與意志,尤其會對建設美好鄉村發揮著積極作用。泗州戲作為地方文化的代表,它必然是具有地理特性的,也有文化圈的意義,且具有歷史意義,涵蓋了藝術審美、道德倫理、文化認知等一系列知識結構。近年來,隨著人們精神文化生活的豐富,大家有了更多的選擇機會,泗州戲在傳承方面出現了“斷代”的情況,面臨市場萎縮、幾近消亡的險境。因而,搜集、整理并編寫泗州戲劇傳統劇目,對于泗州戲的研究和傳承意義重大。
如何傳承發展泗州戲是個復雜社會性的問題,在保持傳統戲曲元素的基礎上要強化對傳統劇目的改革力度,唱腔、戲曲程式、曲式結構、伴奏等方面也是改革的主要方向。對泗州戲的藝術審美也要加以提煉,地方小戲永遠不能丟棄其“地方性”。地方性不僅僅包括一些民俗文化,它也是地域概念下人性的體現。就像世界地理中不同緯度、不同氣候、不同環境下對人的影響是不同的,那么,在我們戲曲改革的時候一定要從地方文化本質屬性出發,不能搞大統一。完成這樣龐雜的戲曲改革任務是十分困難的,不能僅靠政府投資,或者改頭換面的戲曲變化就能改變戲曲發展的歷史軌跡,需要集中社會各個方面理論認真的研究,主要是認識到戲曲這門藝術的規律,并且結合社會發展的現實情況,有針對性的取舍,有些劇目需要進入淘汰環節,有些劇目需要大刀闊斧的改革,主要還是與時代生活保持一致性,這樣更容易拉近與現代人的生活情感。劇目改革還要遵從“小”的概念,不適宜突破劇目格局,達到小而精。
二、表演中傳承民俗文化
文化傳承對于戲曲藝術的發展十分重要。戲曲營養主要是來自民俗,民俗不但具有民族文化特征,而且具有鮮明的地方性,在泗州戲流傳區域有一句俗語:“十里,八里改規矩”,這就是民俗地域性的形象描述,在相聚十幾里的地方就有不同語言發音的婚喪嫁娶規定。因此在內容和敘事等方面,戲曲藝術的表演都賦予不同的表演傳達,民俗文化正是在這樣特定的區域內繁榮發展,同時也對戲曲題材有了特定要求。隨著時代的進步,全世界開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重視起來了,因此戲曲藝術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典型代表也受到了政府、專家、研究機構的高度重視。戲曲藝術傳承民俗文化的功用性漸漸顯現出來。從民俗文化的基本特點來看,毫無疑問泗州戲所反映的民風民俗屬于俗文化,這就是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正是因為具有俗文化的特色,泗州戲才可以經久不衰。鄭振鐸說:“戲曲作為俗文學是中國文學史主要的成分,許多俗文學的作品卻總可以給我們一些東西,他們產生于大眾之中,為大眾而寫作……只有在這里,才能看出真正中國人民的發展、生活和情緒”。傳承是將民俗在演繹中留存。泗州戲綜合地反映了老百姓多層面的生活,從民俗學視野來看,泗州戲最大的藝術及社會價值就在于:通過戲曲表演,反映民生、再現民俗生活,并揭示了民俗文化傳承的價值內涵。
關于藝術起源眾說紛紜,有勞動說、游戲說、神話論。總之,在泗州戲中融合了各種藝術形象,吸收眾家所長,它的劇目凝練了黃淮地域百姓的生活與情感問題,具有文化圈屬性。民間風土人情、故事傳說在泗州戲中都有充分體現。綜合分析泗州戲題材在傳承民俗文化中包含了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農業生產。如《拾棉花》主人公玉蘭在夢想其婚后生活的一些情況,玉蘭說:“要把那玉米、秫秫收到家,要吃飯。食物出現在戲曲演出劇目里,更能夠體現地域的民俗特色,反映農民勞作的故事。二是地域風俗,老百姓對婚喪嫁娶等人生要事都極為重視,民間儀式在泗州戲中有十分突出的表現,地域性的各種儀式在泗州戲表演過程中都會以各種形式展現出來,如《拾棉花》中婚期的選擇,玉蘭“喜期日子臘月二十八”,翠娥“日子十月八”就是婚嫁風俗習慣。另外,老百姓對先祖祭祀十分重視,泗州戲小戲《打乾棒》是民俗的又一例證。此外,泗州戲還借鑒了姊妹藝術關于人們生產生活的表演。三是意識形態現象,泗州戲對于當地的道德理念、紀律約束等都反映著尋常百姓對真善美的至高追求。總之,泗州戲對民俗文化傳承是顯而易見的,并且有著歷史的積淀和審美地域性歸屬。因此,為了更進一步傳承好地方民俗文化,就需要以戲曲表演的影響力為向導,如在現代戲《秋月煌煌》中,無論是在劇本創作上,還是表演上,都有融傳統因素于現代性,情感淳樸,唱腔設計婉轉優美,內容情深意濃、引人思考。歌舞表演的有機融合,復雜的人物表演突出情節的對抗因素,民俗文化的戲曲化不僅給人們心靈上快樂,藝術審美價值上也是值得肯定的。同時,該劇以現代化視角發展了傳統泗州戲表演,堅持“新舊結合,大膽創新,固本強根,移步換形”,把優秀的民俗文化有機融合在泗州戲藝術表演中,這對泗州戲發展意蘊深遠。
三、加強完善理論研究和人才培養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帶來的保護效力之一就是傳承人相比較以前人數越來越多了,這些人是泗州戲發展的重要生力軍,泗州戲傳承人不僅僅要掌握泗州戲的理論知識,還要具有其他方面的藝術造詣,這就需要培養高專業、高素養的傳統戲曲人才,還要融合相關學科,如社會學、美學、哲學、心理學等理論知識,只有從一個宏觀的角度去審視泗州戲,才能把握泗州戲發展脈絡,以及未來發展總的思路,也只有具備這樣的專業素養才能進而談戲曲革新問題。
早期的泗州戲藝人都是來自社會最底層的農民,他們文化素養低,理論研究也是一片空白。自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泗州戲藝人的社會地位與生活環境得到了極大改變,他們有更多的機會學習文化知識,徹底改變了泗州戲藝人理論基礎薄弱的問題。他們結合自身對新社會、新生活的感受,學會了創新與改革,不斷總結了一些唱腔與表演的心得體會。隨著我國文化藝術的繁榮發展,一些學者、教師、戲劇演員先后在各類報紙、雜志以及其他學術刊物上發表了很多相關的研究性論文。這些關于泗州戲的論文和專著,填補了泗州戲理論研究的空白,直接推動了泗州戲的傳播與推廣。前期的泗州戲理論性研究多數以研究演員和曲目為主,具有深遠意義的學術性研究相對較少,多數是一些泛泛而談、概括性的文章。自從2012年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計劃實施以來,許多戲曲專家、民族音樂家、文化學者、民俗學家、高校教師等紛紛加入泗州戲理論研究行列,使泗州戲的學術性研究得到了加強。新時期,自從“文化強國”戰略目標確立以來,傳統文化建設隨之提升到了一個全民參與的新高度,與此同時,泗州戲理論研究又迎來一個新的機遇期。筆者認為,為了進一步提升泗州戲理論研究的廣度與深度,應該積極整合區域優勢資源,提高泗州戲理論研究層次,積極推動區域性學術研討會模式發展,大力挖掘泗州戲理論審美性和文化屬性。
泗州戲和其他地方小戲一樣都是一種寶貴的文化資源,要想使其得到很好的傳承發展,戲曲人才工程建設勢在必行,人才建設涵蓋面很廣泛,涉及到技術層面、政策層面、社會層面等等要素,應該說是一個涵蓋廣泛的建設體系。在這個體系建設中,我們需要做到:抓住要點,突出重點。其中,作為藝術骨干的青年演員首當其沖成為重點,他們是傳承和發展戲曲藝術的有生力量,承擔著弘揚和改革戲曲藝術的重任。為了激勵青年演員為傳承發展戲曲藝術提供不竭動力,就要想盡一切辦法提升他們的藝術表演能力、藝術審美素養,在新社會背景下,青年戲曲演員不可避免的摻雜了現代因素。因此,為了讓他們詳盡了解和掌握泗州戲的文化特質和藝術精華,一定要加大對他們的藝術審美教育和相關藝術知識培訓力度,從而使他們更好的勝任泗州戲的表演任務。其一,要著重培養演員的戲曲表演能力,使得他們將表演習慣和泗州戲藝術特點結合起來。根據不同曲目和劇情量身定制表演,具體到進行藝術的二度創作;其二,培訓演員的泗州戲演唱能力,使其演唱地域性風格更加鮮明,進而區分到泗州戲同其他地方戲劇之間的差異,同時還要注意演唱審美的創新性發展,從而全面提升他們的戲曲素養。
泗州戲作為皖北地區的傳統戲曲,墨守成規對于其傳承和發展是不利的,需要順勢而上、順勢而為,以一個全新的觀念對傳統戲曲進行改革,為了更好地傳承和發展泗州戲,首先,需要改變傳統劇目,即鞏固傳統知識結構,起到“強根固本”的作用;其次,在表演中傳承民俗文化,使傳承者溯其根源,知其本質;再者,著重加強理論研究和人才培養,這對于泗州戲藝術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欽媛.民俗文化傳承視角下泗州戲的社會功能變遷研究[J].淮南師范學院學報,2019(04):21-22.
[2]孔丹丹.泗洪泗州戲的傳承與發展[J].大舞臺,2015(04):35-36.
[3]王衍軍.中國民俗文化[M].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8:111-113.
[4]李洪.泗州戲的傳承與發展[J].戲劇之家,2017(04):41-42.
[5]王艷偉.論中國戲曲音樂的傳承和發展[J].東方藝術,2011(01):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