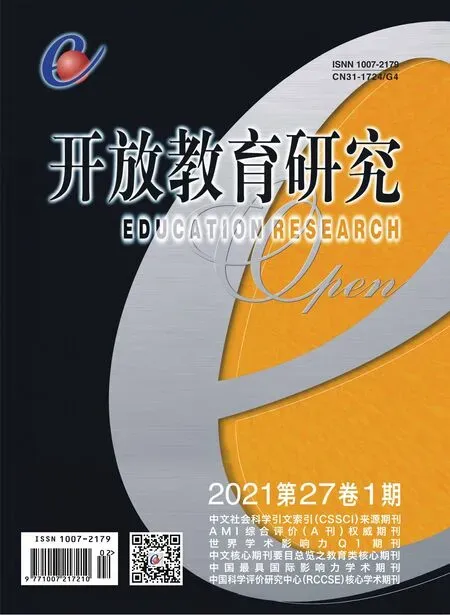遠(yuǎn)程在場的知識延展與存在收縮
——對在線教育的存在論闡釋
張敬威 蘇慧麗
(東北師范大學(xué) 教育學(xué)部,吉林長春 130024)
在線教育是基于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的教育模式,具有“非真實(shí)”與“遠(yuǎn)程在場”等特點(diǎn),它通過人工技術(shù)對人的自然身體進(jìn)行數(shù)據(jù)化的替代性復(fù)制,一方面為教育提供超越此在時空的可能,另一方面對現(xiàn)實(shí)教育全方位的擠占要求教育必須警惕學(xué)生面臨存在收縮的危機(jī)。
一、知識傳播的有條件延展:當(dāng)遠(yuǎn)程在場得以可能
隨著通信技術(shù)與在線教育的發(fā)展,教學(xué)與學(xué)習(xí)更具延展性,教學(xué)場域的遠(yuǎn)程在場得以可能。然而,伴隨著學(xué)生知識的延展,學(xué)生在虛擬情境中獲取的知識也呈現(xiàn)出片面而斷裂的特征。
(一)技術(shù)成為身體的延展性工具
在線教育中我們能夠通過網(wǎng)絡(luò)跨越地域的限制實(shí)現(xiàn)遠(yuǎn)程的視頻與音頻等多維交流,現(xiàn)代化的非自然技術(shù)重構(gòu)了教學(xué)的場域,也重新定義了學(xué)生在課堂中的身體構(gòu)成——技術(shù)成為身體延展的同時向?qū)W生提供著具身經(jīng)驗(yàn)。學(xué)生的身體本身是一種作為經(jīng)驗(yàn)存在的“活的身體”(corps vecu)①,而在線教育為經(jīng)驗(yàn)的身體提供了可被感知的延展性工具。工具自誕生伊始便承擔(dān)起作為身體延展的作用,比如當(dāng)猩猩想吃樹洞中的螞蟻而手臂又無法夠到時,便使用木棍插入洞中將螞蟻沾出來吃,此時木棍便成為猩猩身體的延展,承擔(dān)了猩猩手臂的作用。正如海德格爾提出的“錘子”與梅洛-龐蒂提出的“盲人的拐杖”,他們均作為身體的一部分,成為身體的延展。在線教育為身體提供了更大范圍的延展空間,使學(xué)生的“視覺”與“聽覺”得以延伸。
在線教育為學(xué)生提供了遠(yuǎn)程視聽課程內(nèi)容的可能,也為師生提供了遠(yuǎn)程在場的技術(shù)支持,但是遠(yuǎn)程在場的存在與交流形式自其出現(xiàn)伊始便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小孩的推斷和他的實(shí)踐思維首先具有實(shí)踐和感性的性質(zhì)。感性的稟賦是把小孩和世界連接起來的第一個紐帶。實(shí)踐的感覺器官,主要是鼻和口,是小孩用來評價世界的首要器官。”(馬克思,2016)當(dāng)人成為遠(yuǎn)程在場的存在,便限制了學(xué)生認(rèn)識世界的部分感官——“五官感覺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歷史的產(chǎn)物”(馬克思,2016),“人的對象性關(guān)系的全面生成,就是人通過與世界多式多樣的關(guān)系,全面地表現(xiàn)和確證自己的本質(zhì)的完滿性”(丁學(xué)良,1983)。當(dāng)人被局限在有限維度的虛擬環(huán)境中,就成為單一性關(guān)系中的一部分,人也不再是全面與完整的人,而成為碎片化世界所規(guī)定維度下的人。在這種規(guī)定的碎片化世界中,人的認(rèn)知能夠得到一定范圍的延展,卻導(dǎo)致了認(rèn)知的整體性與深刻性不足,從而使人知識內(nèi)化的過程被削弱,出現(xiàn)片面與斷裂的特征。
(二)片面而斷裂的知識內(nèi)化
知識的內(nèi)化往往源于自我的同一性,即我的意志與我的行為的同一性。動作對思想反饋,從而產(chǎn)生一種主客觀的互動關(guān)聯(lián),在認(rèn)知沖突與順應(yīng)中完成內(nèi)化。知識的內(nèi)化過程是多感官協(xié)同作用的結(jié)果,也是事物因果聯(lián)系的反饋性結(jié)果,因此其產(chǎn)生需要在一個實(shí)存完整的真實(shí)世界中得到全面且真實(shí)的因果性反饋。教學(xué)同樣適用這一規(guī)律。學(xué)生對知識的內(nèi)化需充分調(diào)動其官能及其所擁有的經(jīng)驗(yàn),在感知與沖突中再思考,在矛盾中完成經(jīng)驗(yàn)的修正與再認(rèn)識。
在線教育的弊端有兩項(xiàng):一為反饋的整全性缺失,二為反饋的因果關(guān)聯(lián)性的呈現(xiàn)缺失。在線教育提供了得以延展的界面化圖景,使得教育的可視、可聽的范圍更廣延,卻削弱了教育的一項(xiàng)重要環(huán)節(jié)——學(xué)生自我同一性的建構(gòu)。學(xué)生在界面化操作中獲取了少量的界面反饋,對五官與統(tǒng)覺的刺激僅僅來源于界面本身,這樣教學(xué)就出現(xiàn)了一種對象化的偏移——教學(xué)的對象從知識或事件偏移到了界面本身。學(xué)生從學(xué)習(xí)知識或事件轉(zhuǎn)為了對界面的關(guān)注,而界面作為知識與信息的載體與表現(xiàn)形態(tài),僅僅呈現(xiàn)了表象化與可視化的內(nèi)容,人與世界的關(guān)系被縮減成人與界面的關(guān)系——世界對人的因果性反饋被簡化為擬真程序的界面反饋,人開始在被削弱了整全性與因果性關(guān)聯(lián)反饋的界面世界中出現(xiàn)眩暈。
表象內(nèi)容的大量碎片化呈現(xiàn)使學(xué)生的知識掌握出現(xiàn)彌散狀態(tài),缺乏因果聯(lián)系的認(rèn)知與主客沖突的內(nèi)化過程使學(xué)生對知識的掌握僅僅停留在“名稱”的理解層面,而無法達(dá)到“概念”②的掌握程度,也無法形成內(nèi)在的邏輯掌握。遠(yuǎn)程在場的學(xué)習(xí)形態(tài)在使學(xué)生擁有了更為廣博的見識的同時削弱了學(xué)生對這種見識內(nèi)化的過程性訓(xùn)練,以及在思維層面的沖突性認(rèn)知步驟。碎片且彌散的知識成為學(xué)生存儲的對象,而非內(nèi)化理解與應(yīng)用的對象。
(三)缺乏應(yīng)用的知識存儲
當(dāng)教育成為一種界面化的存儲方式,學(xué)生所接觸到的知識淪為與經(jīng)驗(yàn)關(guān)聯(lián)更為遙遠(yuǎn)的符號,那么學(xué)習(xí)便成為一種以符號為對象的學(xué)習(xí),而符號與世界的聯(lián)系在學(xué)生的感官中消失了。喪失了內(nèi)涵的符號便淪為符號本身,“知識”也被削減為單純的“識”③,學(xué)生掌握符號對應(yīng)的概念,卻無法聯(lián)系符號所代表的世界,符號的意義與經(jīng)驗(yàn)脫節(jié),學(xué)生進(jìn)入符號世界卻脫離了現(xiàn)實(shí)世界與真實(shí)經(jīng)驗(yàn)。學(xué)生淪為了存儲的容器,其所掌握的符號關(guān)聯(lián)也成為僅存于虛擬世界呈現(xiàn)的經(jīng)過教育者篩選后的片面性關(guān)聯(lián),由此會出現(xiàn)這樣一種傾向:虛擬的世界成為學(xué)生的真實(shí)場景。學(xué)生通過教育者的訓(xùn)練適應(yīng)了虛擬的教育場景,而教育者卻忘卻了虛擬場景僅僅是為呈現(xiàn)現(xiàn)實(shí)中某一規(guī)律或特征而塑造的場域。虛擬場景的目的是培養(yǎng)學(xué)生掌握虛擬的因果聯(lián)系,從而對實(shí)存的因果聯(lián)系進(jìn)行分析,然而這種虛擬的因果聯(lián)系與真實(shí)世界的經(jīng)驗(yàn)脫節(jié)后,就不再具有對實(shí)存因果聯(lián)系的代表性,使這種虛擬的因果聯(lián)系喪失了其對真實(shí)世界指導(dǎo)的基礎(chǔ)。
當(dāng)學(xué)生對知識的存儲形式淪為脫節(jié)于真實(shí)經(jīng)驗(yàn)的存儲,那么知識對實(shí)踐的指導(dǎo)作用將會失效。當(dāng)“形而上”脫離了“形”,那么“上”就喪失了意義。存儲本身并不具備主體性價值,作為純粹的知識載體其僅僅是一種手段或工具。“人是生活在目的的王國中。人是自身目的,不是工具。人是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的自由人。人也是自然的立法者。”(康德,2003)真實(shí)經(jīng)驗(yàn)是人作為目的性存在的重要支撐,是人成為自然的立法者的前提。教育作為培養(yǎng)人成為人的實(shí)踐活動,保障人的知識與經(jīng)驗(yàn)的關(guān)聯(lián)性、尊重人的完整性與目的性是其基本要義。面對在線教育帶來的延展性便利,保障學(xué)生的真實(shí)體驗(yàn),是教育現(xiàn)代化過程中需要注意的。
二、存在的收縮:知識碎片化與彌散化溯因
以存在論視角進(jìn)行分析,在線教育產(chǎn)生的知識碎片化與彌散化問題、知識與真實(shí)經(jīng)驗(yàn)脫節(jié)問題,其內(nèi)在原因可歸結(jié)為“存在的收縮”。
(一)空間收縮導(dǎo)致的認(rèn)知局限
當(dāng)教育情境從一個可感知的真實(shí)場域被縮減為界面化的呈現(xiàn)時,其空間感便消失大半。“如果間隔(intervalle)在突然變?yōu)榻缑?interface)時,變得苗條,‘更加苗條’了,則事物,也就是被感覺到的客體,也同樣變得苗條,失去了它們的重量,它們的密度。”(維利里奧,2004)存在的收縮為教育帶來兩項(xiàng)挑戰(zhàn):一是學(xué)生可感知深度的確定,二是教師擬呈現(xiàn)的與學(xué)生重點(diǎn)感知的一致性對接。被電子界面分裂呈現(xiàn)的世界投影給予學(xué)生一種不能被察覺到的視覺緯,其中唯一的停止成為了當(dāng)前瞬間的一種類癲癇發(fā)作的缺席,電子界面化的呈現(xiàn)給予觀看者一種無休止的鏡頭造成的錯覺(維利里奧,2004)。學(xué)生在這種錯覺中逐漸習(xí)慣,將把不在場當(dāng)作在場,由而產(chǎn)生一種存在論的替代,這種電子界面化的擴(kuò)張隱匿了空間收縮的同時加劇了人的生存空間的收縮(張一兵,2018)。
當(dāng)電子化的遠(yuǎn)程界面承擔(dān)身體的工具性意義,延展了身體的同時也將身體的感知扁平化了。當(dāng)學(xué)生習(xí)慣了電子化學(xué)習(xí),將虛擬世界摻雜于真實(shí)生活時,相當(dāng)于被裝上了電子化的義肢——數(shù)字化世界成了健全的電子化殘疾。當(dāng)身體的延展變得輕而易舉,就會削弱主體到客體之間的路程(trajectivite)④,若沒有路程,則喪失了人在客觀世界中的交融過程,也就意味著感知與經(jīng)驗(yàn)在進(jìn)行與反思雙重層面的壓縮——線上技術(shù)帶來瞬時性的同時使可感與可思的區(qū)間減小,使思想習(xí)慣于無法跟隨通信的速率而變得麻木與機(jī)械,從而產(chǎn)生一場源于路途性喪失導(dǎo)致的人類環(huán)境的“景深”⑤的衰變(維利里奧,2004)。路途性的消失直接導(dǎo)致了空間存在的收縮,而空間存在的收縮則直接關(guān)涉教育環(huán)境的“景深”——學(xué)生的感知的深度。
這種精神的缺失正是胡塞爾(1988)所指的“已經(jīng)沒有活生生的體驗(yàn)了……已經(jīng)把意義抽空了”。而此類空洞卻在學(xué)生生活與學(xué)習(xí)中不斷重復(fù),成為學(xué)生的認(rèn)知習(xí)慣,不斷地壓縮學(xué)生的存在空間與對存在的認(rèn)知。這種存在認(rèn)知的壓縮在在線教育中變得更為突出,扁平化的內(nèi)容被快餐式地重復(fù),在教師擬呈現(xiàn)與技術(shù)可呈現(xiàn)的雙重制約下,學(xué)生知識掌握的碎片化與彌散化、認(rèn)知的空洞化正在加劇。
(二)身體缺席導(dǎo)致的主體沖突
遠(yuǎn)程在場意味著身體的缺場。盡管技術(shù)作為身體的延展,但身體仍然承擔(dān)作為交往效應(yīng)的載體。傳統(tǒng)教學(xué)常常借助非語言符號進(jìn)行完整與豐富的表達(dá)與交流,包括動作、表情、眼神等,并且這一系列符號在不同的時間、場合、人群背景下表露不同的含義。多維共存的交往方式呈現(xiàn)的是一種整體性信息,使人在多維度接受信號的同時對對方進(jìn)行綜合判斷。然而,身體的缺席使交流者的交流方式由多維度變成單一或有限維度,表達(dá)者盡管在遠(yuǎn)端仍保持著表情、神態(tài)、動作等信號的持續(xù)輸出,但是它們在傳輸中都被屏蔽掉了,而接收者僅僅收到了特定維度信息,從而出現(xiàn)教師擬呈現(xiàn)與學(xué)生重點(diǎn)感知對接的偏差。
由此學(xué)生所處空間出現(xiàn)了這樣一種沖突:教師的綜合形象消失了,學(xué)生的身體感卻持續(xù)在場。學(xué)生接收遠(yuǎn)程在場的虛擬信號時卻感受此在真實(shí)場域?qū)Ω泄賻淼拇碳ぁ€體在通信穿越中的碎片化呈現(xiàn)使多維的生物性與物理性存在變?yōu)榉栃源嬖冢栠M(jìn)行綜合情境表達(dá)帶來了通信雙方信息的不對稱交流,伴隨而至的是感知層面的虛擬與實(shí)在相交替的眩暈感(閆旭蕾,2009),此時對學(xué)生而言,存在著真實(shí)世界與再現(xiàn)世界、主動性與互動性、在場與遠(yuǎn)程在場之間的多維兩重性(維利里奧,2004)。由于主體接收信號的雙重性,導(dǎo)致的主體認(rèn)知判斷的雙重性,認(rèn)知的佐證材料由此在感受與接收此在信號的綜合變?yōu)榱舜嗽诟惺芘c遠(yuǎn)程信號的綜合,因而出現(xiàn)了直接經(jīng)驗(yàn)與上手世界的分裂,也衍生“分立出行動的當(dāng)下能動性和遠(yuǎn)程行動的互動特征”(張一兵,2018)。
在線教育的工具性意義在此維度中與梅洛-龐蒂所指的“盲人的拐杖”有別。“盲人的拐杖”作為身體的延伸,使盲人的觸覺由手延展到拐杖的盡頭,然而盲人所處的場域仍然是拐杖所在的真實(shí)空間,“此時此地”的條件致使拐杖所接觸的實(shí)體盲人仍可通過空間內(nèi)的其他信息加以佐證判斷,而在線教育則出現(xiàn)在近乎于“此時”而非“此地”的情況下。當(dāng)拐杖作為介質(zhì)承擔(dān)的作用是以“此地”的延伸綜合“此地”的統(tǒng)覺,而在線教育則無法達(dá)成這一狀態(tài)。
(三)情境殘缺導(dǎo)致的片面發(fā)展
在線教育呈現(xiàn)的是一種定向化的殘缺情境,其目的性呈現(xiàn)與教學(xué)目標(biāo)契合度越高,教育的有效度越高。在線教育的特定情境一方面受限于客觀載體的技術(shù)限制,一方面來自于施教者的片面化給予。當(dāng)學(xué)生僅僅接觸施教者所設(shè)定的情境,這種定向的殘缺情境就構(gòu)成了學(xué)生的全部學(xué)習(xí)范疇。這種取代了真實(shí)空間的虛擬情境設(shè)立的目的在于:通過虛擬呈現(xiàn)使學(xué)生掌握一種抽象認(rèn)知,并力圖使學(xué)生可以通過該認(rèn)知指導(dǎo)真實(shí)世界的實(shí)踐。若要達(dá)成這一目的,需要符合兩個基本條件:首先,學(xué)生對抽象認(rèn)知擁有真實(shí)的經(jīng)驗(yàn)基礎(chǔ),使該抽象呈現(xiàn)與現(xiàn)實(shí)世界產(chǎn)生確切的關(guān)聯(lián);其次,一系列虛擬呈現(xiàn)具有邏輯關(guān)聯(lián),能夠通過綜合得出具有邏輯性的抽象結(jié)論,而非直接呈現(xiàn)結(jié)論。
在線教育與人的認(rèn)知具有相向發(fā)展的趨勢:一方面,技術(shù)產(chǎn)生與改進(jìn)的目的在于為人服務(wù),所以其發(fā)展的核心基礎(chǔ)是人類信息交流的感官平衡;另一方面,學(xué)生接收在線教育會在不斷的認(rèn)識沖突中向已改進(jìn)的新環(huán)境順從和適應(yīng),即技術(shù)趨向人性化的同時人性順應(yīng)技術(shù)性,從而致使一個可預(yù)見的教育危機(jī)逐漸清晰化:學(xué)生在人與技術(shù)的特征更為趨近的環(huán)境中局限了對存在的認(rèn)知。在線教育為人提供了一種“物的尺度”——決定了人具有認(rèn)識活動的可能,而“人的尺度”則超出了“物的尺度”的局限,具有反思性、創(chuàng)造性和批判性特征(蘇慧麗等,2019)。定向的殘缺情境會加劇人的定向殘缺,人的片面化同樣會致使情境的定向殘缺。
由于在線教育所呈現(xiàn)的定向殘缺情境是現(xiàn)實(shí)的片面化映射,在線教育與現(xiàn)實(shí)世界具有有待于被充盈的擬真關(guān)系。這種擬真關(guān)系為教育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增大了可教、可呈現(xiàn)的范圍,同時也付出了真實(shí)性危機(jī)的代價,所以在線教育的價值取決于學(xué)生對真實(shí)世界的把握。實(shí)在世界是在線教育的基礎(chǔ)與支撐,如果在線教育妄圖拋棄在場教育獨(dú)立進(jìn)行,就會喪失其存在的合理性與前提性。
三、重述“在場”的意義:以此在真實(shí)引領(lǐng)彼在虛擬的教育
遠(yuǎn)程在場的在線教育使學(xué)生面臨經(jīng)驗(yàn)與認(rèn)知斷裂的危險,給學(xué)生帶來存在感知收縮的危機(jī),這就不得不對在線教育的適用情況與適用規(guī)定進(jìn)行批判性思考。在線教育的先天劣勢在于真實(shí)經(jīng)驗(yàn)的缺失,由此重述“在場”的意義尤為重要,應(yīng)以此在真實(shí)引領(lǐng)彼在虛擬的教育。
(一)區(qū)分現(xiàn)實(shí)與虛擬的課堂
在線教育為教師與學(xué)生都提供了現(xiàn)象學(xué)意義上的身體,這種現(xiàn)象學(xué)意義的身體以符號化的形式承擔(dān)起了主體功能與技術(shù)功能的雙重任務(wù)。施教者的意識在其所在場域生發(fā),其所處的知覺場決定了意識生發(fā)的重要源地,而受教者出現(xiàn)一種現(xiàn)象場或 “身勢圈”的差異性沖突——他者場域下形成的經(jīng)驗(yàn)性規(guī)律在本土場域中的接受性沖突,由此所傳遞的僅僅是信息符號本身,而在場域的變換中篩濾掉了體驗(yàn)性與感知性的傳遞。當(dāng)學(xué)生適應(yīng)于這種缺乏感知性的符號傳遞就會出現(xiàn)“可思”與“可感”一致性的削弱,而新的一致性的出現(xiàn)會使學(xué)生在虛擬與現(xiàn)實(shí)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當(dāng)學(xué)生習(xí)慣于將其知覺現(xiàn)象場中的因果聯(lián)系歸結(jié)為虛擬場域中的聯(lián)系時,其對現(xiàn)實(shí)世界的因果判斷就會出現(xiàn)偏差與斷裂。
當(dāng)學(xué)生將其主觀意志與遠(yuǎn)程在場的能動性反饋結(jié)合起來并作為意識指導(dǎo)實(shí)踐的主要依據(jù),那么學(xué)生就會脫離實(shí)存世界的因果規(guī)則,盡管虛擬條件下部分行為不在此在發(fā)生,卻仍然需以此在為基礎(chǔ)。遠(yuǎn)程在場是現(xiàn)實(shí)在場行為的延伸而非可以獨(dú)立存在的能動表現(xiàn),當(dāng)在線教育無法使學(xué)生區(qū)分遠(yuǎn)程在場與在場形成的能動性反饋,就會面臨將虛擬操持看作真實(shí)行動的危機(jī),進(jìn)而導(dǎo)致學(xué)生對經(jīng)驗(yàn)真實(shí)性的懷疑。
所以在線教育開展的前提是區(qū)分現(xiàn)實(shí)與虛擬課堂,使教師能夠清晰地區(qū)分真實(shí)與虛擬的教學(xué)手段,從而有目的地搭配虛擬與真實(shí)的教學(xué)手段;使學(xué)生能夠明晰地認(rèn)識在線教育的遠(yuǎn)程性與虛擬性,能夠區(qū)分虛擬情境的因果關(guān)系與真實(shí)情境的因果關(guān)系的差異,并且能夠根據(jù)不同的情境與場域進(jìn)行差異性應(yīng)用與實(shí)踐。這便要求課程設(shè)計(jì)對虛擬場域與真實(shí)場域教學(xué)手段的功能性區(qū)分與體系性設(shè)計(jì),明確區(qū)別性的同時挖掘關(guān)聯(lián)性,發(fā)揮兩種教學(xué)手段的比較優(yōu)勢,實(shí)現(xiàn)互補(bǔ)效果。
(二)明確虛擬是現(xiàn)實(shí)的輔助教學(xué)
學(xué)生意志與行為的同一性是其行為得以通過虛擬手段延展的基礎(chǔ),這種虛擬手段作為為目的服務(wù)的工具,其被關(guān)注的重心往往在于目的而非可接受性,僅僅作為目的而存在的數(shù)字化符號不具備傳播意義,因?yàn)槠鋯适Я私涣鞯闹薪楣δ堋_@也在根本上決定了在線教育的輔助地位,明確了在線教育的延展性作用與價值的同時規(guī)定了其指向與目的。
傳統(tǒng)教育早已出現(xiàn)了擬對象的教學(xué)方式,盡管受技術(shù)的限制缺乏一定的真實(shí)性,但仍然可以通過情景構(gòu)建等方式使學(xué)生擁有一定的“沉浸式”體驗(yàn),其自始至終都被定義為一種使學(xué)生獲取知識、能力或培養(yǎng)思維的輔助手段。而在線教育由于其沉浸性與真實(shí)性的提升,為教學(xué)帶來了便利性與高效性,使教師與學(xué)生在虛擬真實(shí)的意識迷思與經(jīng)驗(yàn)幻象中逐漸忽略了技術(shù)被創(chuàng)設(shè)伊始的目的。
人類接收的外部信息,約65%通過視覺通道,20%通過聽覺通道,10%通過觸覺通道,2%通過味覺通道(陳月華,2005)。人作為多感官綜合接受體,直接規(guī)定了真實(shí)環(huán)境與虛擬環(huán)境對人的價值。真實(shí)的外界是人的生存環(huán)境,人需要在實(shí)踐中同化、順應(yīng)并平衡于外界的客觀定在⑥,而虛擬世界作為外界實(shí)存的投射自產(chǎn)生伊始就被賦予了服務(wù)人類的技術(shù)目的。在線教育技術(shù)的價值在于能否更契合地反映技術(shù)使用者的預(yù)期目的,能否更完整、準(zhǔn)確地投射真實(shí)世界的實(shí)存狀態(tài),這也就規(guī)定了在線教育技術(shù)是以真實(shí)環(huán)境為基礎(chǔ)的,是真實(shí)世界的投影,其目的在于促進(jìn)人對實(shí)存世界的認(rèn)識。所以教學(xué)應(yīng)明確擬對象是作為把握真實(shí)對象的中介而存在的本質(zhì),在線教育是現(xiàn)實(shí)教學(xué)的輔助。
(三)以真實(shí)經(jīng)驗(yàn)引領(lǐng)虛擬感知
身體技術(shù)使我們的肉的形而上學(xué)結(jié)構(gòu)具象化并予以擴(kuò)大,其既是可見他者的又是他者可見的,每個人都是每個人的鏡子( Merleau-Ponty,2007)——即身體具有感知層面的反身性。所以,技術(shù)雖然可以設(shè)計(jì)或創(chuàng)造有利于學(xué)習(xí)的環(huán)境,但不能為學(xué)生創(chuàng)造學(xué)習(xí),因此不能將經(jīng)驗(yàn)(人與現(xiàn)象之間的關(guān)系)與現(xiàn)象本身混淆起來(拉斐爾·A·卡沃等,2020)。學(xué)生對世界的認(rèn)知源于其對周遭環(huán)境的真實(shí)感知,這就要求教學(xué)要有真實(shí)的根源與經(jīng)驗(yàn)的過程。教學(xué)應(yīng)尊重學(xué)生從個別到一般的歸納的認(rèn)識世界的過程,因而課堂教學(xué)要努力還原知識產(chǎn)生、發(fā)展的情境,從而使學(xué)生學(xué)習(xí)完成一種類似于探索與發(fā)現(xiàn)的過程性復(fù)演,在意識、思維與經(jīng)驗(yàn)層面完成具有因果關(guān)系的訓(xùn)練,只有擁有對真實(shí)世界經(jīng)驗(yàn)從個別到一般的歸納能力,才能真實(shí)地辨別虛擬的個別所代表的真實(shí)的一般。
教學(xué)應(yīng)突出真實(shí)經(jīng)驗(yàn)的歸納性教學(xué)與憑借虛擬感知技術(shù)的延展性教學(xué)的結(jié)構(gòu)性關(guān)聯(lián),通過真實(shí)體驗(yàn)——經(jīng)驗(yàn)歸納——技術(shù)延展等步驟引導(dǎo)學(xué)生。真實(shí)場域既要引導(dǎo)學(xué)生完成從個別到一般的認(rèn)識過程,在歸納中使學(xué)生認(rèn)識虛擬與現(xiàn)實(shí)、符號與實(shí)體、個別與一般的差別,同時加深從場域之定在到意識之運(yùn)動的因果性關(guān)聯(lián),核心是在虛擬場域中結(jié)合學(xué)生對真實(shí)經(jīng)驗(yàn)的歸納基礎(chǔ),使學(xué)生擁有更廣博的見識與更具延展性的深思。
在線教育有助于將抽象對象具象化、將模糊對象實(shí)例化,從而使教學(xué)更具情境性與具象性,使學(xué)生更易理解。但是,這種“擬對象”的呈現(xiàn)方式易于使學(xué)生養(yǎng)成一種僅適合于“擬對象”構(gòu)成的場域中的思考邏輯。當(dāng)學(xué)生帶著這套邏輯方法回歸到真實(shí)世界時容易出現(xiàn)迷幻與錯亂的異方法域問題。教學(xué)應(yīng)使學(xué)生在對真實(shí)對象的操作體驗(yàn)中,在真實(shí)情景的認(rèn)知沖突中堅(jiān)定其認(rèn)識論基礎(chǔ),夯實(shí)真實(shí)經(jīng)驗(yàn)在精神世界中的基礎(chǔ)性地位(于偉,2017),也就是說,要在保障對真實(shí)經(jīng)驗(yàn)正確把握的基礎(chǔ)上以在線教育增強(qiáng)學(xué)生的認(rèn)知,達(dá)到以真實(shí)經(jīng)驗(yàn)引領(lǐng)虛擬感知的目的。
[注釋]
①“活的身體”指作為身體的經(jīng)驗(yàn)存在,區(qū)別于政治、文化與社會構(gòu)建而存在的身體。
②2015年6月4日,孫正聿在“東師人文講壇”講座中從“名稱與概念”層面闡釋了人文社會科學(xué)研究應(yīng)有理論自覺,指出“概念”與“名稱”的內(nèi)涵區(qū)別:“概念”是深入的理解,“名稱”僅僅是對字面的認(rèn)識。
③“知識”的“知”字由“矢”和“口”構(gòu)成。“矢”指“射箭”,“口”指“說話”,“知”指說話像射箭一樣一語中的;“識”字從言從戠,“戠”字本指古代軍隊(duì)的方陣操練:“音”指教官口令聲,“戈”指參加操演軍人的武器,原指整齊劃一的動作,衍生為區(qū)別、辨別之意。當(dāng)學(xué)生缺失了基于經(jīng)驗(yàn)的主體性思考,所能夠掌握的便僅僅是認(rèn)識與辨別的能力。
④此處指存在論意義上的“路程性”的消失,并非常規(guī)所指的路程性,而是路程的存在論意義。
⑤“景深”原意是指在攝影機(jī)鏡頭或其他成像器前能夠取得清晰圖像的成像所測定的被攝物體前后距離范圍,維利里奧以此比喻一種存在論意義上的關(guān)聯(lián)性。
⑥ 定在,是黑格爾的哲學(xué)用語。黑格爾把存在作為第一個邏輯概念,但沒有任何規(guī)定性的存在是純粹的無。由存在過渡到空無是變異或生成,變易就成為第一個具有特定內(nèi)涵的概念,即具有質(zhì)的規(guī)定性。這樣,存在就成為有特定規(guī)定性的存在——定在(參看于黑格爾.小邏輯:商務(wù)印書館,198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