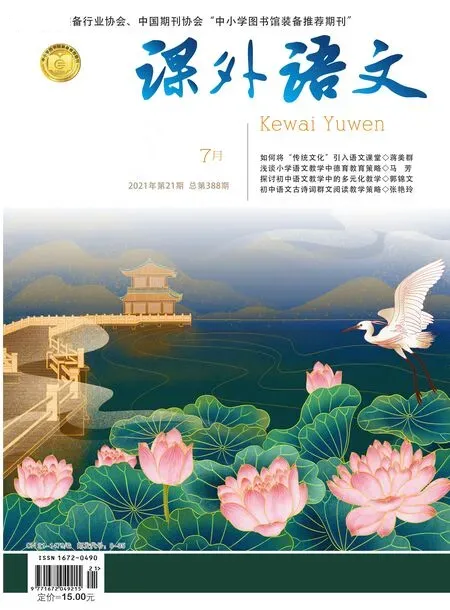《論語》的教學價值之我見
黃曉雯
(中山市桂山中學,廣東 中山 528400)
在孔子及其弟子的語錄世界《論語》中,他們或正襟危坐地談論著政治理想,救世之道;或懷著赤子般的熱忱審視著眼前禮崩樂壞、秩序紊亂的時代并致力于在追索歷史中尋找現世的出路;或將視角從歷史時代推進到個體的自我價值建設的層次,心懷天下之余仍然堅信“事在人為”,強調“人”的歷史主體地位,肯定“人”在改造社會推進歷史進程不斷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不管是縱向維度上的歷史視角,抑或是橫向維度上對個體人生發展的觀照,《論語》微言當中暗涌著的大義需要我們師者不斷地深入挖掘思考體味,并從中提取那些能夠助益于我們自身包括學生群體去解決現實人生困境的精神營養。
一、基于“仁”的人生觀及其對高中生的積極影響
《論語》中將“仁”視作人生的最高境界。子曰:“若圣與仁,則吾豈敢”,孔子將“仁”視作一種連古今眾多大圣大賢之人也無法企及的最高的人生境界,是一個絕對遙遠絕對理想化的狀態。孔子將“仁”絕對距離化高度化,并且自嘲這是一種自己也無法自居的狀態,那么這種遙遠到無法企及的目標對生活在現實中的人來說,意義何在?事實上孔子不吝口舌地贊許了那些朝著“仁”這一最高理想而不斷邁進的個人,贊許那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追逐理想的姿態。“面對其無法實現的理想之仁, 孔子‘罕言’其仁, 但他并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而是將理想放到現實的基礎上,希望通過方方面面、 點點滴滴的努力來接近、 實現其最高理想。于是在孔子心中,‘愛人’ ‘ 忠恕’ ‘孝悌’,一切具有仁性的道德都成了仁, 一切積極為仁的行為也成了仁。”這也就是說“仁”作為一種理想層次的目標,其意義卻恰恰是以一種燦若明星的光輝感召人們在現實世界中不忘對“仁”的追求。孔子在這里不僅強調了作為結果的“仁”這一人生狀態的最高性,同時將這種追求“仁”的過程,將為達到“仁”的境界而做出的種種努力也視作一種寶貴的姿態,鼓勵世人不畏艱難地在追逐理想的過程中實現自我成長。
立足當下社會,浮躁輕佻的急功近利主義盛行,這種心態成為快節奏生活中人們的普遍情態,追名逐利的氣氛中金錢權力被視作衡量一個人社會價值的重要標準,而人源自本心的對理想的渴望,人的本質信仰卻不被關注,由此造成了一種本末倒置的困境。高中生在成長過程中不免會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心境不夠沉穩,做事不夠踏實,長此以往,很難獲得可持續的成長。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回到《論語》,回到孔子及其弟子所處的時代,觀照他們在亂世之中為著治世濟世理想而不懈追求的姿態,是不是能夠放下心中的戾氣也去追逐理想呢?是不是能夠為了保持本心而做出一點努力呢?我們應該學習的不僅是蘊含在《論語》中深入淺出的思想,文本中散發出的著書立說的先賢古人對待人生的誠摯態度和姿態更值得高中生思考學習。
在《論語》中的“仁”的系統中, “孝悌”“愛人”“忠恕”是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孝悌的基本意義是對家庭結構中父母、兄弟的愛和遵從。然而《論語》當中對孝悌的認識并不只是停留在家庭結構的環境中,孔子及其弟子將這種基本的人倫精神拓寬至社會秩序的層面,闡發出“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在這里孝悌的內涵不僅僅局限于對父母兄弟的遵從,而是將這種愛及尊重進一步放大到社會環境中對他人的理解和尊重。基于血緣關系的愛和尊重是容易實現的,而將這種自然之愛的范圍主題,拓展至更加廣闊的社會層面卻是需要付出一定精力和心血的。然而穩定和諧的社會秩序必然是建立在理解尊重包容的人際關系之上,因為人是社會的主體,社會本身存在的種種禮崩樂壞的問題本質上是人心不古的問題。孔子在尋找現實的出路時尤其犀利深刻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認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途徑正在于人與人之間基于孝悌又超出孝悌的愛人與忠恕。
而這種根本性的認識雖然是為了解決孔子所處的時代社會秩序已然崩壞的問題而闡發出來的,但無疑它同樣適用于現代社會,同樣適用于啟發高中生應該以怎樣的姿態與他人、與世界相處。作為《論語》的思想精髓,“仁”在孔子所處的時代可以理解為統治者對臣民的仁愛慈悲,理解為每一層等級之中人與人的平等,由此打造出一種和諧的穩定的人際關系。將這種“仁”放在現代語境下考量,“仁”便意味著基于社會群體的一種心中有他人的博愛情懷,在樹立個人主義,尊重個體自我發展的自由時代,人的主體地位被充分地認可。然而人畢竟不是絕對孤立的存在,而是生活在社會中的個體,人無法避免與他人的交流、溝通、相處,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人與人的相處之道是什么?《論語》給我們的答案是“仁”,“克己復禮為仁”,“仁”就是在與他人交流的過程中自我要有所節制,不能夠只著眼于自我的利益需要,還需要觀照他人的需求和感受,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打造和諧的人際關系,以愛生愛。高中生正處于三觀塑形和成形的階段,以“仁”的思想啟發引導他們在這個時候顯得很有必要,通過“仁”的感染,可以讓他們修身養性,收斂張揚的個性,懂得尊重他人,培養悲憫之心,以積極善良的姿態看待和擁抱世界。
二、聯系“過去”“現在”及“未來”的歷史觀及其對高中生成長的啟發
《論語》不僅在具體的思想論述上具有澤被后世、引人深思的現代價值,《論語》當中著眼于當下時代,尊重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從歷史中尋找出路解決現實問題并展望未來的這樣一種看待問題的歷史觀也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
《論語》中孔子及其弟子在探討社會出路這一問題時的基準原則表現在“克己復禮為仁”這一理念上。孔子對周代井然的社會秩序一直以來都有著一種深深的感念情懷,生活在食不能飽、居無法安的亂世,懷念周朝的秩序井然和太平盛世無可厚非。孔子既是一個夢想家更是一個實干家,為了尋找現實的出路,他主張恢復周禮以重建已經崩壞的社會秩序。然而孔子主張恢復周禮是基于現實亂世的出路思考的基礎上。“《論語》中的‘禮’出現了七十五次,現代人一般把禮當成活動形式或思想理論來認識,其實它包含著規范社會秩序和體現政治導向的意義。”這也就是說《論語》中主張恢復周禮的觀點只是孔子及其弟子闡發的為了有效地規范社會秩序的一種形式和方法。孔子回到周禮的目的是為了整治當下混亂無序的社會,并且遙望著一個能夠媲美于西周的將來。
這一點也在提醒我們,傳統文化中認識外在世界的方式和方法并不是絕對稚嫩的,其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和縱橫古今的歷史觀對高中生如何解決自己的人生困境也具有很重要的啟發意義。我們在解決現實世界中的困境時也應有《論語》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氣概和姿態,不忘歷史的榮與辱,吸取歷史的成敗經驗為現實問題的解決提供可以借鑒的方案,從而遙望越來越理想的將來。
《論語》除了在人生觀和歷史觀兩個維度上給高中生以發人深省的啟發意義,在許多具體的思想點上也具有超越時代的性質,例如《論語》中體現的自省慎獨、積極入世等思想。深入到《論語》的文本中,深入到孔子及其弟子的赤子之心之中,我們一定能夠發現那些歷久彌新的思想光輝一直生生不息地照耀著中國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之路,以《論語》為基點立足當下,回顧歷史,去展望民族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