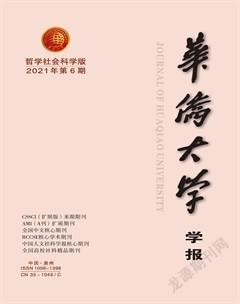法益路徑下合同詐騙罪中“合同”范圍
摘 要:涉合同的詐騙罪是指行為人利用合同實施普通詐騙犯罪的行為。司法實踐中,如何區分合同詐騙罪與涉合同的詐騙罪問題始終困擾著司法人員,導致案件處理結論不盡一致,量刑差異明顯,影響了司法的協調性、穩定性。該問題產生的根源在于,合同詐騙罪所保護的秩序性法益具有抽象性、模糊性,無法有效指導該罪中“合同”構成要件要素的解釋。故應當將合同詐騙罪所保護的合同管理秩序法益,實體性還原為經營性合同的信賴利益,由此出發將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限縮解釋為經營性合同。同時明確經營性合同包括經營者之間的商事合同及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消費者合同,將不具有營利目的或持續性特征的消費者之間的交易合同排除在經營性合同范圍之外;行政合同系行政機關履行行政職權的行為,不具有營利性,不屬于經營性合同。由此所確定的經營性合同的解釋結論不僅具有可操作性,也與目前實務中的處理方法相契合。
關鍵詞:合同詐騙罪;秩序性法益;實體性法益;合同信賴利益;經營性合同
作者簡介:劉健,吉林大學法學院刑法學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刑法(E-mail:cizhong2@163.com;吉林 長春 130022)。
基金項目:國家法治與法學理論研究項目“刑法中因果關系認定的類型化思考”(19SFB2020);吉林大學廉政建設專項研究課題“農村基層組織人員騙取涉農款物問題研究”(2021LZY002)
中圖分類號:D9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398(2021)06-0128-10
涉合同的詐騙罪是指行為人利用合同實施普通詐騙犯罪的行為。合同作為市場交易中明確權利義務的重要載體,在推動經濟持續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也容易被一些不法分子惡意利用實施犯罪。對于行為人利用合同實施詐騙行為的規制,我國《刑法》雖然單獨設置了合同詐騙罪,然而司法實踐中實務人員對于行為人利用某些特定類型的合同,如征地拆遷補償合同、個人借款合同等合同實施詐騙行為的,應當認定為合同詐騙罪還是詐騙罪,存在較大分歧,裁判結果混亂,既影響了司法的協調性、穩定性,也不利于實現罰當其罪的司法效果。因此,明確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范圍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現有研究主要從合同詐騙罪所保護的市場經濟秩序法益出發,將“合同”限縮解釋為體現市場交易性質的合同,以此與涉合同的詐騙罪進行區分。然而秩序性法益內容本身具有抽象性、模糊性,無法有效指導合同詐騙罪中合同要素的解釋,致使所謂的“體現市場交易性質的合同”仍然缺乏明確性、可操作性。本文嘗試對合同詐騙罪中的秩序性法益進行實體性還原,并通過實體性法益實質,有效地界定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范圍,為合同詐騙罪與涉合同的詐騙罪的區分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標準。
一 問題的提出
合同詐騙罪規定于我國《刑法》第224條,理論及實踐中通常將其作為詐騙罪的特殊類型加以理解、研究。與此同時,合同詐騙罪作為司法實務中出現頻率較高的經濟類犯罪,多年來也時常困擾著辦案人員,其復雜性集中體現在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尤其是涉合同的詐騙罪的區分認定上。所謂涉合同的詐騙罪,是指行為人在實施普通詐騙行為的過程中利用了合同。從概念的界定來看,涉合同的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在邏輯結構構造、手段方式上具有極強的相似性,容易混淆;在辦案過程中則體現在,行為人利用某些特定的合同詐騙他人財物時,應當認定為合同詐騙罪還是詐騙罪,處理結果混亂。例如,對于行為人利用與政府簽訂的征地拆遷補償合同,通過虛報土地面積、偽造虛假材料等方式詐騙拆遷補償款的案件,各地裁判結果不一。有的法院將其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如福州市倉山區人民法院辦理的齊某某合同詐騙案,河北省黃驊市人民法院辦理的劉生杰、張芳合同詐騙案;福州市倉山區人民法院(2017)閩0104刑初183號刑事判決書、河北省黃驊市人民法院(2019)冀0983刑初384號刑事判決書。也有最終定性為詐騙罪的案例,如福建省龍巖市新羅區人民法院辦理的張榮生詐騙案,上海市崇明區人民法院辦理的倪挺詐騙案。福建省龍巖市新羅區人民法院(2019)閩0802刑初36號刑事判決書、上海市崇明區人民法院(2016)滬0230刑初380號刑事判決書。除該類案件外,對于行為人編造事由、偽造權屬,利用個人借款合同、個人買賣合同詐騙相對人財物的案件,各地法院的處理意見同樣分歧嚴重。如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法院辦理的王新明合同詐騙案,甘肅省臨洮縣人民法院辦理的王燕子合同詐騙案,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法院(2013)石刑初字第239號刑事判決書、甘肅省臨洮縣人民法院(2017)甘1124刑初196號刑事判決書。均將此類行為認定為合同詐騙罪;但同時也有法院將此類行為定性為詐騙罪,如成都市成華區人民法院辦理的盧正坤詐騙案,遼寧省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辦理的羅翼辰詐騙案。成都市成華區人民法院(2018)川0108刑初122號刑事判決書、遼寧省鐵嶺市人民法院(2019)遼12刑終21號刑事判決書。
與此同時,定性分歧也引發了另一個突出問題,即對同類案件的定性差異所導致的量刑失衡的問題。由于合同詐騙罪相較于詐騙罪而言,其在“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設置上,明顯高于甚至數倍高于詐騙罪中相應的數額規定,雖然司法解釋僅對合同詐騙罪中“數額較大”的標準進行了規定,即為2萬元,并未明確“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具體標準。但從各地的司法實踐來看,諸多省份均以省級公、檢、法三機關聯席會議的方式予以明確。如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市檢察院、市公安局聯合印發的《關于如何處理當前刑事訴訟案件中亟待解決法律問題的會議紀要》中規定,合同詐騙罪“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按照該省詐騙罪相應標準的四倍數額予以掌握,即分別為28萬元、200萬元。又如浙江省相關會議紀要規定(出處為“刑事實務”公眾號2020年11月3日推送的《浙江省刑事立案量刑最新標準》一文,文章內并未列明詳細的紀要名稱),合同詐騙罪“數額巨大”的標準為20萬元,“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為100萬元,明顯高于該省詐騙罪“數額巨大”(10萬元)、“數額特別巨大”(50萬元)的標準。如此就導致在犯罪數額相同的情況下,本應被定性為合同詐騙罪的行為若被不當認定為詐騙罪,行為人所遭受的刑罰會不當加重;或者本應被定性為詐騙罪的行為在被不當認定為合同詐騙罪時,所產生的放縱犯罪的后果。例如,行為人利用拆遷補償合同詐騙60萬元補償款的行為,如若以詐騙罪的數額標準衡量,系“數額特別巨大”,對應的法定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但若以合同詐騙罪的數額標準衡量,則屬于“數額巨大”,對應的法定刑僅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兩罪的量刑結果差距明顯。正因如此,在諸多涉及合同的詐騙案件中,辯護人經常以“被告人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為辯護理由,為被告人爭取較輕的量刑結果。由此可見,合同詐騙罪與涉合同的詐騙罪的區分問題,在定性與量刑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現實研究意義。從實務中遇到的難題來看,司法人員關于合同詐騙罪與涉合同的詐騙罪區分問題的癥結在于,對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范圍的理解存在差異,即該罪中的合同是否包括行政合同、個人借款合同、個人買賣合同(如個人之間出售閑置物品的合同)等特定類型的合同。目前實務中的通行做法系以合同“是否具有市場性”為標準進行判斷。但關于此標準,理論上要么語焉不詳,未對“市場性的合同”的范圍進一步明確;要么以經濟合同、市場合同進行語意重復性的解釋,例如有學者認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宜限于經濟合同,即合同的文字內容是通過市場行為獲得利潤。”張明楷:《刑法學(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835頁。由此導致司法人員始終無法清晰明確地判斷某一合同是否屬于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
對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解釋,本質上系對合同詐騙罪構成要件要素的解釋,而法益所具有的解釋論機能客觀上要求以合同詐騙罪的法益指導構成要件要素的解釋。目前學界關于合同詐騙罪保護法益的主流觀點認為,該罪保護的是秩序性法益與財產法益雙重法益,并將其中的秩序性法益界定為市場秩序或合同管理秩序。張明楷:《刑法學(下)》,第833頁;桂亞勝:《論合同詐騙罪的取消》,《湖南警察學院學報》2018年第3期,第80—87頁;鞠佳佳:《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的雙層界分》,《中國刑事法雜志》2013年第6期,第102—106頁。但是,秩序性法益本身具有抽象性、模糊性,無法清晰有效地指導合同詐騙罪中“合同”要素的解釋。因此,本文擬對合同詐騙罪中的秩序性法益內容進行實體性權益還原,通過實體性的法益內容指導合同詐騙罪中合同要素的解釋,明確合同的范圍,為合同詐騙罪與涉合同詐騙罪的區分提供明確標準。
二 合同詐騙罪秩序性法益的解釋局限及其實體性還原
法益的解釋論機能,是指法益具有作為犯罪構成要件解釋目標的機能。張明楷:《法益初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16頁。《刑法》的重要目的在于保護法益,因此《刑法》對具體罪名的設置也必然遵從保護法益的目的,由此對構成要件的解釋應當以法益為指導。法益本身具有明確性、實體性,是法益有效發揮指導構成要件解釋機能的前提。換言之,如果法益本身表述模糊、內容抽象,不僅難以判斷法益是否被侵害,更難以對構成要件的解釋發揮實質性的指導作用。
(一)合同詐騙罪秩序性法益的解釋局限
目前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合同詐騙罪保護的法益內容不僅包括財產法益,更主要的是秩序性法益。關于秩序性法益的界定,總體來看有市場經濟秩序、市場秩序及合同管理秩序三種表述方式。然而現有理論對秩序性法益的界定均停留在秩序層面上,并未對秩序之下的內容進一步闡明。然而秩序本身具有抽象性、模糊性,如果僅在秩序層面對合同詐騙罪保護的法益內容進行界定,無疑會使此項法益極具“彈性”,使得合同詐騙罪淪為“口袋罪名”,容易成為司法者擅斷的工具。例如,在評價某一行為是否侵害了合同詐騙罪所保護的經濟秩序時,既可以認為違反任何一條經濟規范的行為,都對經濟秩序造成了侵害;也可以認為對某一經濟規范的違反,不足以對秩序整體造成實質性侵害,得出該秩序性法益未被侵害的結論。由此可見,法益本身的模糊性、抽象性,使得法益被虛置化、“工具化”,不僅無法征表犯罪行為對法益的侵害程度,更使得法益的解釋論機能被架空,無法對合同詐騙罪構成要件的解釋進行有效指導。因為無論是將秩序性法益界定為市場經濟秩序、市場秩序還是合同管理秩序,均無法對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的范圍進行明確有效框定,充其量僅能將合同限縮解釋為市場合同、經濟合同。且不說市場合同、經濟合同本身并不是學理上或者法定的合同類型,這些概念本身也依然難以擺脫內涵不明確的詬病。或許,市場合同、經濟合同的提法意在說明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應當是能夠體現交易關系的合同,從而將收養合同、贈與合同排除出去。但是,即便以“是否體現交易關系”作為合同的解釋標準,仍然無法對實踐中出現的利用個人借款合同詐騙、利用行政合同實施詐騙的情形,能否適用合同詐騙罪的規定進行合理說明。因此秩序性法益內容存在明顯的解釋局限,無法有效指導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解釋。究其原因,是由于經濟秩序并非是利益本身,正如學者所言,“經濟秩序是經濟系統內各要素正常運行的一種狀態,但這種有序狀態并非是利益本身,而是利益的前置性條件……對經濟秩序的損害未必會產生利益受損的結果……”魏昌東:《中國經濟刑法法益追問與立法選擇》,《政法論壇》2016年第6期,第156—165頁。因此需要將秩序性法益進一步還原為實體權益,通過具體的權益內容化解秩序性法益抽象化、模糊化的弊端,從而有效地指導構成要件進行實質性解釋。
(二)合同詐騙罪秩序性法益的實體性還原
1.合同詐騙罪秩序性法益表述的厘清
目前理論及實務中對合同詐騙罪保護的秩序性法益共有三種表述方式,分別為市場經濟秩序、市場秩序與合同管理秩序。要對秩序性法益進行實體性還原,首先需要對該法益的表述進行厘清,確定哪種表述更符合合同詐騙罪的設立本意。事實上,“市場經濟秩序”及“市場秩序”的表述均系根據合同詐騙罪在《刑法》中的章節位置而得出的結論。前者從合同詐騙罪所處的《刑法》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出發,認為該罪所保護的秩序性法益為市場經濟秩序;后者從合同詐騙罪所處的《刑法》第三章第八節——擾亂市場秩序罪出發,得出市場秩序的結論。然而這兩種結論,均適用于《刑法》中該章或該節內的所有罪名,缺乏合同詐騙罪所保護的法益的特殊性。相比而言,第三種表述“合同管理秩序”更為恰當,該秩序不僅是市場秩序中眾多內容的一項具體秩序,更與合同詐騙罪利用合同實施詐騙的行為方式緊密相關。因此,將合同詐騙罪的秩序性法益表述為合同管理秩序更為妥當。
2.合同管理秩序的實體性權益落腳點為合同信賴利益
秩序并非憑空產生,其確立需要依托一系列的規范,而規范設立的目的在于保護特定的、具體的法益。由此,秩序與實體性法益之間具有天然的聯系,將秩序性法益進行實體性權益還原具有方法論上的可行性。對于合同管理秩序而言,其建立依托于國家對合同的各類管理規范。具體而言,《民法典》總則及合同編、《合同違法行為監督處理辦法》分別體現國家對合同的民法規制與行政規制。其中,《民法典》相關規范所確立的平等、自由、公平、誠實信用等原則均體現對合同當事人實體性權利的保護。《合同違法行為監督處理辦法》更是在制定目的中明確,本規范系“為了維護市場經濟秩序,保護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當事人合法權益。”由此可見,合同當事人的實體權益是合同管理秩序的實體性落腳點。那么,合同詐騙行為除了對財產法益造成侵害之外,還侵害了合同當事人的何種具體權益,從而侵害了合同管理秩序?這與合同詐騙罪的行為方式密切相關。合同詐騙行為系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合同的簽訂、履行過程中騙取被害人的財物。行為人所實施的欺騙行為既是對誠實信用原則的違反,更是對合同關系的破壞。而從合同關系自身講,合同及其法律所保護的是當事人之間的信賴與期待,實現意思自治的理念。王澤鑒:《民法債編總論·基本理論·債之發生》(總第1冊),臺北:三民書局,1993年,第2頁。轉引自崔建遠主編:《合同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3頁。由此,行為人利用合同實施詐騙行為,不僅降低了當事人對誠信交易的期待,更使其對合同這種確定權利義務的方式失去信心,致使合同的信賴利益遭到破壞。因此合同詐騙罪通過合同管理秩序所保護的實體權益應當還原為合同當事人對合同的信賴利益。
3.合同詐騙罪所保護的信賴利益應限縮為經營性合同的信賴利益
設立合同詐騙罪的目的在于對合同信賴利益進行保護,是否意味著合同詐騙罪保護所有類型的合同的信賴利益?本文認為,從合同詐騙罪在《刑法》中所處的體系位置及市場的概念、內在規律綜合分析,合同詐騙罪所保護的合同信賴利益應當限縮解釋為經營性合同的信賴利益。
第一,從合同詐騙罪所處的章目位置來看,該罪位于《刑法》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之中,該章的內容主要涉及對經濟活動中各類犯罪行為的規制,且大都與經營活動及經營環境密切相關。如第一節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規制的是經營銷售偽劣商品的行為;第三節妨害對公司、企業的管理秩序罪,系圍繞經營活動的主體公司、企業而展開的;第四節、第五節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及金融詐騙罪中所涉及的金融活動更是經營行為的典型體現;第六節危害稅收征管罪中的稅收也與經營活動息息相關;第七節侵犯知識產權罪中的罪名更是與商標、專利、商品、商業秘密等經營要素直接相關。因此,合同詐騙罪作為設置在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一章中的罪名,其規制的行為也應與經營活動緊密相關,該罪中的合同也應系圍繞經營活動而展開的合同。
第二,合同詐騙罪具體設置于《刑法》第三章第八節擾亂市場秩序罪中,從該節內容來看,大都在罪名或罪狀的表述上涉及經營行為,更為直接地體現出對市場經營行為或市場經營環境規制的特征。如非法經營罪系為了保護合法的經營市場,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進行規制;又如虛假廣告罪中明確禁止廣告的經營者進行虛假宣傳,體現對經營者經營行為的規制;損害商業信譽罪禁止他人捏造虛偽事實,損害他人商業信譽,擾亂市場經營環境;再如在強迫交易罪中,不僅明確禁止實施強迫買賣商品、接受服務的行為,而且在兜底性規定中明確禁止強迫他人參與或退出特定的經營活動,足見該罪對經營活動的規制特點。值得注意的是,作為與合同詐騙罪并列規定于《刑法》中的罪名,即《刑法》第224條之一的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在罪狀的表述中亦明確強調了“經營活動”,系對以虛假經營活動為名的詐騙型傳銷活動進行打擊,本質上體現出對合法經營行為的保護。由此,合同詐騙罪在體系上亦應當體現對合法的市場經營行為的保護,由于合同詐騙罪中所涉及的經營活動系通過合同進行的,故而其所保護的合同信賴利益也應系對經營性合同的信賴利益的保護。
第三,從市場的概念及內在規律出發,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應具有規模性、重復性,從而體現出明顯的經營性特征。經濟學意義上的市場,是指整個商品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關系的總和。它是同商品、貨幣、價值、價格等相聯系的經濟范疇,是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王毅武、康星華編著:《現代市場經濟學——中國特色市場經濟釋要》,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17年,第7頁。從市場的概念來看,市場應具有明顯的規模性,個別的、偶發的交易行為不能稱之為市場行為。從市場的內在規律來看,市場的運行或市場對社會資源的配置是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的。楊干忠主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論》(第五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6頁。概括地說,市場機制就是在市場競爭中通過供求關系的變化觸發價格變動,又通過價格變動反過來帶動供求關系發生變化的調節機制,是價值規律的具體表現。王軍旗、劉旭青主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3頁。平時我們所強調的某種行為是否為市場行為,將某行為放到市場中去檢驗,本質上并非指市場的概念本身,而是指該行為是否受市場機制所調節。市場機制的內容主要包括競爭機制、價格機制和供求機制。王軍旗、劉旭青主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第14—15頁。就市場競爭機制而言,客觀上要求多個市場主體參與,體現出規模性的特征;而市場主體要想在競爭中獲得優勢,也需要重復性地實施市場行為。價格機制、供求機制亦是通過重復、大量的市場行為的實施,最終起到調節市場的作用。由此,市場的內在規律要求市場行為具有規模性、重復性。合同詐騙罪作為保護市場秩序的罪名,客觀上其所規制的行為也應系市場行為,應當具有規模性、重復性,故而該罪中的“合同”應具有明顯的經營性。
綜上所述,合同詐騙罪所保護的秩序性法益應當實體性還原為合同信賴利益。從合同詐騙罪在《刑法》中所處的章節位置來看,明顯體現出對市場經營行為或經營環境的規制;同時從市場概念及其內在規律出發,要求市場行為具有重復性、規模性的特征,因此,作為設置在擾亂市場秩序罪一節中的合同詐騙罪,其所保護的合同信賴利益應當具體限縮為對經營性合同信賴利益的保護。
三 基于經營性合同的信賴利益確定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范圍
前文已述,由于合同詐騙罪的秩序性法益內容具有抽象性、模糊性,使得法益被虛置化、“工具化”的同時,也無法有效地指導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的解釋。因此,本文將合同詐騙罪所保護的合同管理秩序實體化為經營性合同的信賴利益。由此出發,基于實體化的法益內容指導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解釋,從而合理劃定該罪的成立范圍,確定合同詐騙罪與涉合同詐騙罪的區分標準。
(一)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應限縮解釋為經營性合同
通過前文的分析可以明確,合同詐騙罪所保護的法益為經營性合同的信賴利益及財產法益,其中經營性合同的信賴利益系合同詐騙罪所保護的主要法益。由于法益具有指導構成要件解釋的機能,因此,從經營性合同的信賴利益出發,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應當限縮解釋為經營性合同。換言之,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經營性合同的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行為,屬于合同詐騙行為。如果行為人系在簽訂、履行非經營性合同,如行政合同、個人借款合同、個人租賃合同等,詐騙他人財物的,則不能適用合同詐騙罪的規定,而屬于涉合同的詐騙犯罪行為。由此可見,經營性合同是合同詐騙罪與涉合同詐騙罪的區分標準。需要說明的是,盡管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僅指經營性合同,但并不意味著只要實施涉及經營性合同的詐騙行為,就一律適用合同詐騙罪的規定。因為從合同詐騙罪的規范結構來看,《刑法》第224條明確要求行為人“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也即合同詐騙行為是以經營性合同的簽訂、履行為核心而展開的,經營性合同中所約定的利益內容及其保障性功能是使被害人陷入認識錯誤進而交付財物的原因,因此,經營性合同的簽訂、履行過程應當能夠涵蓋行為人實施的全部或者核心的詐騙行為,否則就不屬于合同詐騙罪所規制的行為類型。例如,行為人以簽訂經營性合同為誘餌,編造其他理由、借口詐騙被害人經營性合同約定之外的財物的(如為簽訂合同而繳納的人情費、手續費),此時則應當適用詐騙罪的規定。
(二)經營性合同范圍的明確
1.經營性合同應具有營利性、持續性
既然行為人是否利用經營性合同的簽訂、履行詐騙他人財物是合同詐騙罪與涉合同詐騙罪的區分標準,那么合理確定經營性合同的范圍是使區分標準具有可操作性的關鍵。所謂經營性是指,行為人的營利行為具有反復性、不間斷性和計劃性的特點,表明主體至少在一段時間內連續不斷地從事某種性質相同的營利性活動,具有職業性。趙旭東主編:《商法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3頁。經營性的民事合同系與非經營性民事合同相對應的概念,后者指一些經常發生的非經營性交易(如借用)、非經營者之間的交易(如民間借貸)或者不是主要表現為經營性的交易(雇傭)。朱廣新:《論合同法分則的再法典化》,《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9年第2期,第41—56頁。事實上,經營性這一概念是從“商事經營活動”的概念中提煉出來的。商事經營活動需具有主觀上的營利性和客觀上的營業性,也即主觀動機是為了獲利,客觀上表現為持續性的職業行為。施天濤:《商事法律行為初論》,《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21年第1期。第96—111頁。由此,經營性合同應同時具備兩個特征:一是簽訂合同的一方或雙方主觀上系為了營利,如果合同的雙方都不是為了獲取收益而簽訂合同,如簽訂單純的借用合同,則不是經營性合同;二是簽訂合同的一方或雙方,其交易行為需在一段時間內反復實施、具有持續性,如果雙方的行為均不具有持續性,如個人之間的借款合同,即便主觀上具有營利目的,也不屬于經營性合同。由此可見,在經營性合同的兩個特征中,持續性是其核心特征,營利性則為次要特征。正如學者所指出的,“在‘泛商業化’的時代中,任何人都可能從事營利活動,即是說一般的民事行為也可能具有營利性,僅有營利性不足以使商行為區別于一般的營利性民事行為,但營業性卻是商行為所獨有的。”徐喜榮:《營業:商法建構之脊梁——域外立法及學說對中國的啟示》,《政治與法律》2012年第11期,第106—117頁。這里的營業性,實質上系指持續性的特征。
2.經營性合同的判斷規則及與商事合同、民事合同的關系
如前所述,經營性合同是具有營利性、持續性的民事合同,而經營性這一概念又是從商事經營活動中提煉出來的,因此,經營性合同判斷規則的確定與民事合同、商事合同的概念及兩者的區分密切相關。所謂商事合同,即發生在生產經營領域內,服務于生產經營目的的交易行為;所謂民事合同,即發生在生活消費領域內,服務于生活消費目的的交易行為及發生在雇傭勞動領域內,以提供勞務為內容的交易行為。王軼:《民法原理與民法學方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253—254頁。從表面上看,商事合同與民事合同的區別在于發生領域的不同,前者發生在生產經營領域,后者發生在生活消費領域。但從實質上來看,正如學者所言,“所謂商事合同與民事合同之區辨,前者概念主要即系所謂B2B(business - to - business)合同,后者則為所謂B2C(business - to - customer)合同。”王文宇:《梳理商法與民法關系——兼論民法典與商法》,載王保樹主編:《中國商法年刊2015》,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81—82頁。換言之,在區分合同發生領域不同的同時,還需要通過合同主體來具體明確合同性質。若雙方均為經營者則系商事合同,而如果一方為經營者、一方為消費者則屬民事合同。所以有學者指出,“商事合同是一個相對性或比較性概念,其相對或比較的對象,一開始主要是民法典上的典型合同,現在進一步發展為民法或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消費者合同。”朱廣新:《論合同法分則的再法典化》,《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9年第2期,第41—56頁。此外,從合同主體的角度來看,民事合同除了包括B2C的消費者合同外,還應包括消費者與消費者之間合同,即C2C(customer - to - customer)合同,如家庭親友之間的生活借貸、“閑魚”買賣、自然人之間的住宅租賃。李志剛、張巍等:《民事合同與商事合同:學理、實務與立法期待》,《人民司法》2020年第1期,第103—111頁。由此可見,商事合同與民事合同的區分系依據合同主體實現的,這對經營性合同判斷規則的確定很有啟發。由于經營性合同需具有營業性、持續性,因此可以從合同主體的角度具體判斷合同是否具有營業性、持續性,以此確定經營性合同的范圍。
具體的判斷規則可以分為以下三種情形,第一,當合同交易的雙方均為經營者時,由于經營者之間的交易本身就具有明顯的營利性、持續性特征,因此屬于經營性合同沒有疑問;第二,當合同的一方為經營者、另一方為消費者時,由于經營者一方在簽訂合同時具有主觀上的營利性和客觀上的重復性,故而也屬于經營性合同;第三,當合同的雙方均為消費者時,盡管在一些情形下具有主觀上的營利性特征,但由于雙方均不是職業的經營者,不具有在一定時間內有計劃的、重復性的簽訂合同的性質,故而缺乏經營性合同所要求的持續性的核心特征,因而不屬于經營性合同。當然,上述依據合同主體所確定的經營性合同的判斷規則,系以合同具有交易性內容為前提的,如果合同本身不是對交易內容的約定(如借用合同),那么即便合同雙方均為經營者,也不屬于經營性合同。根據上述判斷規則,經營性合同與民事合同、商事合同的關系也能夠進一步確定,即經營性合同包括B2B(business - to - business)的商事合同及B2C(business - to - customer)的民事合同(消費者合同),但是不包括C2C(customer - to - customer)的民事合同。
3.經營性合同與行政主體簽訂的合同的關系
由于實務中時常出現行為人利用與政府簽訂的行政合同詐騙公共財物的情形,針對此類案件能否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存在較大爭議,因此有必要確定行政主體所簽訂的合同與經營性合同之間的關系。首先需要明確的是,行政主體所簽訂的合同是否均為行政合同?其實不然,根據我國《民法典》第97條規定,承擔行政職能的法定機構可以從事為履行職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動。由此,行政主體可以以法人的身份簽訂民事合同,例如為更好地履行行政職能而與其他法人、自然人簽訂的建筑施工合同、辦公設備修繕合同、物業服務合同等。而關于行政合同的界定,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年11月頒布的《關于審理行政協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后文簡稱《行政協議規定》)中進行了明確。《行政協議規定》第1條規定,“行政機關為了實現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務目標,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協商訂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權利義務內容的協議。”因此,行政主體所簽訂的合同分為行政協議與民事合同兩種類型,需要分別明確其與經營性合同的關系。
對于行政協議而言,《行政協議規定》第2條對協議的類型進行了列舉,具體包括:政府特許經營協議,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補償協議,礦業權等國有自然資源使用權出讓協議,政府投資的保障性住房的租賃、買賣等協議,符合該規定第1條規定的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協議及其他行政協議。從行政協議的概念及列舉的類型來看,行政協議系行政機關以公權力行使者的身份,與相對人訂立的合同,本質上不是一種市場交易行為,而是一種行政權的行使方式。王利明:《論行政協議的范圍——兼評<關于審理行政協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條、第2條》,《環球法律評論》2020年第1期,第5—22頁。換言之,行政機關通過行政協議與相對人建立的仍然是行政管理與被管理的權利義務關系,只不過相較于傳統的向行政相對人單方向發布行政命令而言,行政協議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公私合意的色彩,但本質上仍然是行政機關行使行政職權的行為。例如,在房屋征收補償協議中,雖然在形式上體現為行政機關與相對人簽訂了協議,但仍然是行政機關行使征收權力的行為,具體體現在征收補償的價格范圍由行政機關主導,其行政性大于協議性,更多地適用行政法律規范,是一種替代行政行為。因此,對于行政機關與相對人所訂立的行政協議而言,從內容上看并不具有營利目的的交易內容,從簽訂主體上看也并非是經營者與經營者或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簽訂的合同,不符合經營性合同判斷規則的要求,故而不屬于經營性合同。
對于行政主體所簽訂的民事合同而言,則需要從簽訂合同的主體出發,具體判斷其是否屬于經營性合同。如果合同的相對方為經營者,則屬于行政主體與經營者簽訂的消費者合同,即B2C合同,此時的行政主體作為法人與自然人消費者具有同等的身份地位。根據前文分析,B2C合同屬于經營性合同,故而由行政機關與經營者簽訂的消費者合同應當納入經營性合同的評價范圍。如果合同的相對方并非經營者,則屬于消費者與消費者之間簽訂的民事合同,即C2C合同,由于此類合同中雙方均不具有經營者身份,所簽訂的合同不具有持續性特征,因此不能納入經營性合同的評價范圍。
四 經營性合同解釋結論的實務印證
關于合同詐騙罪中合同范圍的界定問題,實務中出臺過相關的參考性案例和地方性規范文件,雖然在案例說理及文件中并未明確提出將該罪中的“合同”限縮解釋為經營性合同,但從具體的分析理由來看,系與經營性合同的判斷標準相一致,也即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應具有營利性、持續性的特征。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審判參考》中發布的第1056號案例陳景雷等合同詐騙案中,針對行為人以適格農民名義低價購買農機出售而騙取國家農機購置補貼款的行為的定性給出了意見,認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必須能夠體現一定的市場秩序,與市場秩序無關及主要不受市場調整的“合同”“協議”通常不應視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因此案件中的行為應當構成詐騙罪。雖然論者給出的理由為,國家農機購置補貼協議系不受市場調整的協議,但其實質意在強調國家農機購置補貼協議屬于行政協議,其給予適格農民補貼系行使行政職權,該行為并非是具有營利性的交易行為,因此,其與農民簽訂的協議不是經營性合同,故不構成合同詐騙罪。除了參考性案例,實務中也有地方性裁判體現了經營性合同的判斷思路。例如,福建省龍巖市新羅區人民法院辦理的張榮生詐騙案,對于被告人張榮生利用征地拆遷補償合同騙取拆遷款的行為,法院認為拆遷合同簽訂的雙方均非市場經營主體,所簽訂合同的行為亦非市場經營行為,故認定張榮生的行為并不構成合同詐騙罪,最終以詐騙罪對其定罪處罰。福建省龍巖市新羅區人民法院(2019)閩0802刑初36號刑事判決書。與此同時,以經營性合同區分合同詐騙罪與涉合同的詐騙罪的思路也得到了立法解釋上的佐證。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14年4月24日頒布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66條的解釋》中規定,“以欺詐、偽造證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騙取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等社會保險金或者其他社會保障待遇的,屬于《刑法》第266條規定的詐騙公私財物的行為。”事實上,行政機關在落實各類社會保障待遇的過程中,往往通過行政協議的方式與適格主體簽訂協議發放補貼,而行政協議如本文所述并不屬于經營性合同,故利用此類協議詐騙公共財物的行為僅能夠以詐騙罪評價,屬于涉合同的詐騙犯罪行為。
此外,多地司法部門也聯合出臺過關于合同詐騙罪的會議紀要,其中關于“合同”范圍的規定也體現出“經營性合同”的認定思路。例如,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省人民檢察院、省公安廳于2020年6月18日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合同詐騙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座談會紀要》中規定,“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應當體現一定的市場秩序,主要受行政法調整的行政合同通常情況下不應視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同時規定,“對于利用手續完備,充分體現市場經濟活動特征的借款合同詐騙的行為,應當認定為合同詐騙罪,但對于當事人之間基于親友、熟人關系等簽訂的普通借條、欠條等形式的借款協議以后出現的詐騙行為,沒有體現市場經濟活動,無市場交易特點的,一般不以合同詐騙罪處理。”該紀要以借款合同為例,著重強調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需充分體現市場經濟活動的特征,利用不體現市場交易特點的借款合同詐騙財物的,不構成合同詐騙罪。這里所強調的市場經濟活動特征,不僅僅指合同需體現財產交易的內容,更是從市場交易自身逐利性、持續性的特點出發,強調進行財產交易時主觀上的營利目的和客觀上交易行為的重復性。由此可見,紀要所強調的市場經濟活動特征本質上與經營性合同所具備的營利性、持續性相一致,故將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限縮解釋為經營性合同的解釋結論,與目前實務界的處理邏輯高度契合。無獨有偶,浙江省人民檢察院于2005年12月24日發布的《詐騙類犯罪案件專題研討會會議紀要》中也有類似規定,“合同詐騙罪的合同主要是體現市場交易行為的合同,如果行為人利用合同形式進行詐騙不致擾亂市場經濟秩序,則不應構成合同詐騙罪,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不屬于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的范圍。”該紀要中要求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具有能夠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的特點,而行為人只有利用以逐利為目的所簽訂的、可重復實施的合同詐騙他人財物,才會使合同當事人對市場交易的信賴落空,并對未來可能進行的合同交易喪失持續性的信賴,從而擾亂市場經濟秩序。因此,將具有營利性、持續性特征的經營性合同作為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解釋結論,能夠得到實務上的印證與支持。
實踐中關于合同詐騙罪與涉合同的詐騙罪的區分問題始終困擾著司法人員,集體表現為司法人員對合同詐騙罪中“合同”范圍的理解分歧嚴重,致使實踐中的案件處理結論不盡一致,量刑結果差異明顯。產生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合同詐騙罪所保護的合同管理秩序法益具有抽象性、模糊性,無法有效指導作為構成要件要素的“合同”的解釋,致使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范圍始終未能明確,因此需要對秩序性法益進行實體性還原。從合同詐騙罪所處的《刑法》中的章節位置及市場的概念、內在規律出發,合同管理秩序法益可以還原為經營性合同的信賴利益。由此出發,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應當限縮解釋為經營性合同。經營性合同應具有營利性、持續性的特征,它既包括經營者與經營者之間的商事合同,也包括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消費者合同,而消費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民事合同屬于非經營性合同。另外,行政協議本質上系行政機關履行行政職權的行為,不具有營利性,不屬于經營性合同;但行政機關以法人身份與經營者之間簽訂的民事合同則屬于經營性合同。由此,將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限縮解釋為經營性合同,不僅具有可操作性,更與目前實務中的處理思路高度契合。
Abstract: The crime of contract - related fraud refers to the act that a perpetrator uses contract to commit ordinary fraud.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problem of how to distinguish the crime of contract fraud from the crime of contract - related fraud has always plagued judicial personnel, resulting in inconsistent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of case handling, and obvious differences in sentencing, which affects the coordination and stability of justice. The root of this problem is that the orderly legal interests protected by the crime of contract fraud are abstract and vague, which can not effectively guid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contract” in the crime. Therefore, the legal interests of contract management order protected by the crime of contract fraud should be reduced to the trust interests of operating contracts, and the “contract” in the crime of contract fraud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operating contract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clear that the business contract includes the commercial contract between operators and the consumer contract between operators and consumers, and the transaction contract between consumers with non - profit purpose or sustainability should be excluded from the scope of operating contract; An administrative contract is an act of an administrative organ performing its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and powers. It is not profit - making and does not belong to an operating contract. The interpretation conclusion of the operating contract is not only operable, but also consistent with the current treatment methods in practice.
Keywords: crime of contract fraud; orderly legal interest; substantive legal interest; contract trust interest; operating contract
【責任編輯:龔桂明 陳西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