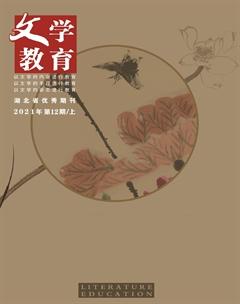沈從文筆下人物的矛盾與張力
陳方君
內容摘要:本文從《湘行散記》的三種對比來體現書中人物的矛盾與張力,并以此剖析沈從文的對湘西鄉民及其生命的體恤、關懷與贊美。
關鍵詞:沈從文 《湘行散記》 矛盾 張力
提及沈從文,大多數人浮現于腦海中的往往是《邊城》,那畫一般唯美的景色借由文字躍然于紙上,于是一座“希臘小廟”便被建造起來——它無暇而美麗,令人神往。比之于《邊城》,這本用山山水水和鄉間瑣事搭建起來的《湘行散記》則顯得瑣碎和簡短了些,似乎缺少了唯美的意境與純潔的愛情,但正是這本由沈從文在回鄉為母探病路途中斷斷續續記述的散文集成的冊子,讓我感受到了更為真實,不加掩飾的湘西鄉村世界——沒有那么唯美,存在著粗糙和無知的一面,卻又表露出動人的哲理和生命活力。《湘行散記》通過其人物的矛盾和張力,展現了比其他小說文本更為復雜的內容。
一.粗魯的行為方式與多彩的情感世界
在《湘行散記》中,出現最多的人物是水手。毫無疑問,帶著鄉間粗野氣的水手們會有著專屬于他們的“粗言粗語”。
十九句話中就說了十七個壞字眼兒。仿佛一世的怨憤,皆得從這些野話上發泄,方不至于生病似的。(水手們)[1]
便因為這樣,前后的水手就互相罵了六七十句野話。船上罵野話不作興生氣,這很有意思。并且他們那么天真爛熳的罵,也無什么猥褻處,真是古怪的事。(《過梢子鋪長潭》)[2]
在這類對話語的描寫中,我們不僅體會到了此間鄉人的一些言語特色,也能夠理解沈從文向往的那股“野性”和“蠻性”是什么。這是天地間孕育出來的一股子沖勁兒——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做了也不多計較得失和結果,好似什么都不忌諱似的,好似什么都不能將它徹底改變似的。
船夫分許多種,最活潑有趣勇敢耐勞的為麻陽籍水手,不多數皆會唱會鬧,做事一股勁兒,帶點憨氣,且野得很可愛。這些人都可愛得很。你一定歡喜他們。(《水手們》)[3]
這股勁兒不單單從嘴里喊出來,也在行為上一覽無余。在《一個多情水手和一個多情婦人》中,水手們固執而熱烈的特性被體現得淋漓盡致。文中的水手牛保為了與自己喜歡的女人多相處一會兒而違背約定的上船時間,多次拖延,不肯離開。船上的水手對他大罵著,他又罵回去。終于,他不依不舍地準備回來,臨上船前,偶然得到了一個蘋果,他便又毫不猶豫地跑回了吊腳樓人家里去,將那蘋果寶貝一般地獻給了女人,走前又要多絮叨幾句,承諾著再來的時候帶上些果子、糖什么的,船上其他水手的叫罵聲又一次傳來了,但他毫不在意似的,仍然停留在岸上不肯下河。
那水手雖然這時節或許正在急水灘頭趴伏到石頭上拉船,或正脫了褲子涉水過溪,一定卻記憶著吊腳樓婦人的一切,心中感覺十分溫暖。(《一個多情水手和一個多情婦人》)[4]
于是乎,我們的腦海中展現出這樣的一個湘西水手的形象——在河上常年日曬而變得黝黑的皮膚、干裂的嘴唇、粗糙的皮膚、眼白是有些渾濁的土黃色、在怒罵或是吆喝時大張著的嘴和嘹亮的嗓門,那聲音貫穿了一整條河流。而在面對河岸邊上那些女人們時,他們變得急切而熱烈。有時候將人放在了心上,他們又顯得真切而羞澀。如果多得了些銀錢,買到了好東西,又或者是給到了家里面去,他們便心滿意足,倍感自豪。
湘西鄉人的粗魯在他們表露情感的時候巧妙地轉化為一種率真,質樸,甚至是有些手足無措的笨拙,這使得他們的情感世界更加地濃墨重彩——嬉、笑、怒、罵、愛、恨、情、仇,這人世間的滋味兒,他們該有的都有,一個也不少。
二.卑微的社會地位與詩意的精神世界
自中國“五四時期”起,鄉村人一直是作家們筆下活躍的一個分子,沈從文的湘西鄉人更是其中的代表。與其他作家們筆下的鄉人共同的一點是,沈從文筆下的鄉人也多少帶點愚昧和無知,但這又是無可厚非的。在當時,看書漲知識和出門漲見識本就是“稀缺品”,湘西鄉人理所應當地不了解自己身份卑微,任人壓榨的處境,更不用談覺醒與反抗了。眼界限制了他們對于事物長遠地思考,所以解決眼前的生存問題成了最重要的事情,這其中不乏賣命、賣妻等行為。
像這樣大雪天氣,兩毛錢就得要人家從天亮拉起一直到天黑,遇應當下水時便即刻下水,你想,多不公平的事!……他們也常大笑大樂,為了順風扯篷,為了吃酒吃肉,為了說點粗糙的關于女人的故事。(《水手們》)[5]
縱然身處于社會的低位,水手仍然用自己的生命證明了“能活”與“苦難哲學”的價值,他們甚至超越了“苦難”本身,從而達到了“苦中作樂”的境界。湘西鄉人將生活的酸、甜、苦、辣、咸調和成自己最能夠接受的味道,從而構建起湘西世界獨有的生存體系,當無力改變自己的生存現狀的時候,便只能尋找最能夠延續生存的形式來維持這個地區的穩定,這其中作出的調整與割舍,湘西的鄉人們不可謂沒有思考過。這樣看來,我們又不能說他們是愚昧無知的了,這甚至是有些“大智若愚”的味道。
我們在大城里住,遇到的人即或有學問,有禮貌,有地位,不知怎么的,總好像這人缺少了點成為一個人的東西。真正缺少了些什么又說不出。但看看這些人,就明白城里人實實在在缺少了點人的味兒了。(《灘上掙扎》)[6]
整本集子里,沈從文還加入了一些對于城里人的描寫,他們高高在上地“指點江山”,將自己置于倫理制高點,只想展現出優越的一面,卻并未真切地了解過此間生活的困境,這種模樣只會顯得他們虛假十分。沈從文借此襯托了鄉人的真實,質樸與獨有的智慧,同時也有批判商人與知識分子“大愚若智”的味道。
在這里,形成文章人物矛盾和張力的不僅僅是湘西鄉人本身的對比,還有來自于外界城市人的對比——用湘西鄉人本身的愚昧無知和其參透生活的智慧這兩個矛盾形成頗具張力的對比,又用這份參透生活的智慧和城市人的裝模作樣形成對比。
三.破碎的人身權利和完整的人生意義
我們很難說《湘行散記》中鄉村人的“野性”和“蠻性”是毫無改變的。在沈從文的概念里,如同夢幻的“希臘小廟”一樣的湘西世界應該是不受世俗紛亂打擾的,可《湘行散記》不是《邊城》,它更真實地展露出一些問題。這些問題的根源是不可避免的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所帶來的,湘西鄉人是資本鏈條中相當簡陋的一環——“廉價勞動力”,他們被消費,被壓榨著,在這個過程中,天然的“野性”和“蠻性”遭遇了無情的“人的異化”[7]的影響,這種天性也會“異化”出粗魯、愚昧和怒氣來。
與完全被異化的人不同,當時湘西并非早早處于城市化和資本化的情境下,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它們仍然保持著早期的淳樸,所以這個“異化”并不徹底,現代化的倫理道德未能取代湘西傳統的倫理道德,即那份順其自然的“野性”和“蠻性”。粗魯的言行并不能掩蓋人的本心,我們仍然能夠透過此看到湘西鄉人們質樸,重情義,有活力的一面。因此人物外在的形象便與其內在的品格形成了頗具張力的對比,在這股張力的支撐下,湘西鄉人成了一個個站立起來的,多面的,活生生的人。
沈從文擁有他的“湘西情結”,珍惜湘西的好一直是他的選擇,《湘行散記》成書之前仍是零零散散的書信,起初被整理為《湘行書簡》,原本的內容里不少有沈從文對于水手們的控訴,但是在整理為《湘行散記》時,這些控訴大大減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對于景色的描寫,對于船夫行為的刻畫。
你瞧,這小船多好!你聽,水聲多幽雅!你聽,船那么軋軋響著,它在說話!山水美得很,我想你一同來坐在艙里,從窗口望那點紫色的小山。(《小船上的信》)[8]
又有了櫓歌,同灘水相應和,聲音雍容典雅之至。(《歪了一下》)[9]
他看到平緩的河水微微流動,兩岸連山綿延不絕,山上栽種著如江南五月般的翠竹,他們被煙雨一洗而凈。河邊的人家有淺綠色的白菜、有橙紅色的胡蘿卜,伴著雞鳴狗叫,船上水手們爽朗的笑。水手們如何“遣詞造句”已然不再重要,這人間煙火模糊了世人苛求的細節,只剩下一種純真質樸的意境在環繞。
在他的觀察中,這些湘西鄉人固然是有好有壞的,但是也好的壞的融為一體了,于是他不以絕好或絕壞去判定這里的人們,而是用一種關懷和理解的態度去看待這些好與壞的種種,從而給讀者們提供了另一種思路——當客觀現實與主觀精神產生矛盾時,讀者是否能夠不拘泥于客觀世界的固有邏輯與選擇,從而去理解文本中人物的深層情感,去珍視他們突破庸常生活的那股“力”,去接納人物奇特但又自然合理的選擇,由此發現那些可供挖掘的本真人性。
作為一個作者,同時也是文本中的“敘述者”,沈從文想要表達的對于生命意義與價值的思考的結果——人生在世縱然有所缺憾,卻也因真實而可敬、可貴、可美。那些湘西鄉人,他們的生命值得被熱愛,人格值得被尊重。如是,一些缺點就可以被原諒和理解,而這份毫無保留的“真”,讓生命顯得獨一無二,富有張力,矛盾與哲理,讓這份獨屬于湘西人的精神力量亙古綿延。
《湘行散記》憑借其舒緩的節奏,明凈質樸而又似水清冽的語言表達了這其中如野蠻生長的自然一樣的復雜而美麗的生命哲理,使讀者對文本的二次創作不僅僅停留在對于簡單故事的感嘆,而是產生了對于生活與生命的思考,這亦可被稱之為該文本對于讀者的最大價值。
參考文獻
[1][2][3][4][5][6][8][9]沈從文.湘行散記[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8.10
[7]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人民出版社,1932
(作者單位:廣東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