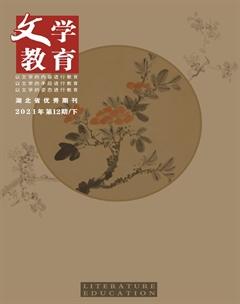廣度·深度·溫度:學(xué)術(shù)史書寫的三重維度
嚴(yán)曼華
內(nèi)容摘要:以往故事學(xué)術(shù)史的書寫以線性梳理為主,在梳理與議論之余難免落入單調(diào)、刻板的泥淖。《中國(guó)民間故事研究史論》通過運(yùn)用專題反思的方式對(duì)新中國(guó)成立70年來的中國(guó)民間故事研究進(jìn)行了深入剖析,資料翔實(shí),反思深刻,鮮活生動(dòng),既是一部靜態(tài)的充滿思辨意識(shí)的故事學(xué)術(shù)史,同時(shí)也是一部活態(tài)的有溫度的故事學(xué)人學(xué)術(shù)史,體現(xiàn)了學(xué)術(shù)史書寫的廣度、深度與溫度三重維度。
關(guān)鍵詞:故事學(xué) 學(xué)術(shù)史 民間文學(xué)
故事學(xué)術(shù)史的書寫不乏先例。20世紀(jì)90年代,在學(xué)術(shù)史討論的熱潮之下,民間文學(xué)的學(xué)術(shù)史意識(shí)開始覺醒。此后,劉魁立、劉守華、施愛東、劉錫誠(chéng)、萬建中等一批具有深厚民間文學(xué)學(xué)識(shí)素養(yǎng)的學(xué)者都開始對(duì)本學(xué)科學(xué)術(shù)史進(jìn)行勾勒描畫,以從不同角度展現(xiàn)現(xiàn)當(dāng)代民間文學(xué)學(xué)科的前行軌轍。然而,對(duì)于學(xué)術(shù)史,我們的一貫思維是“辨章學(xué)術(shù),考鏡源流”,通過總結(jié)學(xué)術(shù)成果,剖析源流,來梳理本門學(xué)科的發(fā)展脈絡(luò)與歷史走向,這是學(xué)術(shù)史的基本工作,但終歸有些美中不足。學(xué)術(shù)史雖為史,但終歸不是一次走馬觀花式的歷史巡禮,而是溯其根源,察其得失,為其未來之路指明方向。這就需要學(xué)術(shù)史書寫者在總結(jié)每一階段歷史性成果時(shí)能將自我置于歷史時(shí)空之下,與其對(duì)話。由于過度重視學(xué)術(shù)成果在學(xué)術(shù)史書寫中的重要性,學(xué)術(shù)史書寫者容易陷入自我言說的陷阱之中——圍繞現(xiàn)有學(xué)術(shù)成果盡情自我剖析反思,盡管剖析深入,反思深刻,卻總覺單調(diào)呆板。而一部有溫度的學(xué)術(shù)史除去書寫者的自我獨(dú)白,應(yīng)當(dāng)要有故事學(xué)人的應(yīng)答或合奏。在這一方面,漆凌云教授的《中國(guó)民間故事研究史論》無疑是一次新的突破。
《中國(guó)民間故事研究史論》是以專題反思的方式對(duì)新中國(guó)成立70年來的中國(guó)民間故事研究進(jìn)行深入剖析。在以線性梳理為主的學(xué)術(shù)史書寫傳統(tǒng)中,這一書寫方式能補(bǔ)足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史書寫中存在的蜻蜓點(diǎn)水式論述的不足,使得這一專題內(nèi)的學(xué)術(shù)走向更加完整、清晰地展現(xiàn)在讀者眼前。這是對(duì)局部的切割。但與此同時(shí),正因?yàn)槭菍n}式論述,它之所及也只限于這些專題,而不能兼顧整體,對(duì)于這些專題之外學(xué)術(shù)動(dòng)態(tài)的把握,仍會(huì)陷入蜻蜓點(diǎn)水式的品評(píng)論述之中,這是無可避免的事實(shí)。故而專題的材料選取廣度與內(nèi)容描寫深度在此處就顯得格外重要。如何通過這些個(gè)案研究來最大限度地從側(cè)面展現(xiàn)整個(gè)故事學(xué)發(fā)展歷程?如何從這些典型且普遍的研究范式中找出民間故事的未來發(fā)展方向?這是對(duì)每一位學(xué)術(shù)史書寫者的學(xué)識(shí)涵養(yǎng)與思辨能力的考驗(yàn)。
《中國(guó)民間故事研究史論》運(yùn)用了翔實(shí)的資料來呈現(xiàn)中國(guó)民間故事學(xué)近七十年的大致走向。作者發(fā)現(xiàn)了一直被我們所忽視的丹尼斯、詹姆森等海外漢學(xué)家對(duì)于中國(guó)民間故事學(xué)所起到的開創(chuàng)意義,進(jìn)一步豐富了中國(guó)故事學(xué)的內(nèi)容。同時(shí),作者還有意識(shí)地將本土與西方相對(duì)照聯(lián)系,在追溯其外國(guó)理論源頭的同時(shí)考察其在中國(guó)國(guó)內(nèi)的發(fā)展變異,從而揭示其中國(guó)化的過程。如在故事類型學(xué)專題中,作者介紹其理論源于西方,N.B.丹尼斯是第一個(gè)運(yùn)用民俗學(xué)理論研究中國(guó)民間故事的學(xué)者,同時(shí)也是第一個(gè)對(duì)中國(guó)民間故事進(jìn)行分類嘗試的學(xué)者。自鐘敬文等學(xué)者將西方故事類型學(xué)方法引進(jìn)中國(guó)后,在整個(gè)20世紀(jì),中國(guó)故事學(xué)幾乎都圍繞類型學(xué)展開①,在這之后,以劉守華、劉魁立為代表的故事學(xué)者將其進(jìn)一步與本土實(shí)際情況結(jié)合,形成類型文化學(xué)、民間故事生命樹等理論,逐步構(gòu)建起中國(guó)民間故事類型學(xué)術(shù)語體系。將本土之根與他山之石聯(lián)系起來考察,在追根溯源的同時(shí)更能揭示其發(fā)展演變過程,突出本土特色。此外,本書的描寫廣度也體現(xiàn)為方法上的新穎與獨(dú)到。在定量考察中國(guó)民間故事的研究狀況時(shí),作者以文獻(xiàn)計(jì)量法的方式分析了近四十年來高被引論文發(fā)布的年度、期刊、作者群體以及研究熱點(diǎn),從宏觀視角勾勒出了中國(guó)四十年來民間故事學(xué)術(shù)史的大致輪廓。
在《中國(guó)民間故事研究史論》中,不乏豐富而全面的研究資料,作者運(yùn)用了翔實(shí)的資料來勾勒民間故事學(xué)的學(xué)科進(jìn)程,卻不僅僅只局限于勾勒,而是在勾勒的同時(shí)對(duì)這些理論或成果進(jìn)行反思,以更為完整地展現(xiàn)這一專題的深度。如在“母題與中國(guó)故事學(xué)的術(shù)語體系”專題內(nèi),作者通過梳理普羅普、鄧迪斯以及中國(guó)一些故事學(xué)人等對(duì)母題這一故事學(xué)術(shù)語的界定與闡釋,亦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民間故事學(xué)中,事件才是母題,角色和背景是構(gòu)成母題的元素。母題是故事中與主角命運(yùn)相關(guān)的事件或行為,具有抽象性和具象性、穩(wěn)定性與變異性、易識(shí)別性與獨(dú)立性特征,是構(gòu)成民間故事的基本單位②。”這是基于原有學(xué)術(shù)理論的再闡釋,在剝除掉原有定義的不合理因素外為我們展示了一個(gè)更為清晰恰當(dāng)?shù)哪割}界定。
中國(guó)的民間故事研究走過了百余年的歷史,而自建國(guó)以來的七十年,諸多學(xué)術(shù)理論與學(xué)術(shù)成果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似乎正昭示著這一門學(xué)科的興盛與成熟。但中國(guó)的民間故事學(xué)研究果真是已到成熟之境嗎?作者從個(gè)案入手進(jìn)行反思,將歷來的成果與現(xiàn)今面臨的困境同時(shí)置于讀者眼前。比較故事學(xué)在以劉守華為首的故事學(xué)人的開拓下雖然達(dá)成了“多元共生”與“多元播化”的共識(shí),卻也給比較故事學(xué)設(shè)置了新的困境與挑戰(zhàn):民間故事的多元共生與多元播化論寓示著其起源及傳播過程的高度復(fù)雜,如此一來,探尋故事生活史的研究范式必然面臨危機(jī),如想在此領(lǐng)域有所突破,必須超越原有的故事生活史范式③;文化人類學(xué)經(jīng)周作人、趙景深等人引入中國(guó)后,雖然逐漸走出“遺留物”模式的泥淖,卻往往忽視民間故事文本自身反映的文化心理差異,未能將故事深層結(jié)構(gòu)中不同族群文化心理的差異與故事的形態(tài)結(jié)構(gòu)建立起有效連接④;以機(jī)智人物故事為典型代表的生活故事雖然在各個(gè)向度取得故事學(xué)人的關(guān)注,研究成果豐碩,卻缺少新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機(jī)智人物故事本身的主題和形式的單一性也限制了其學(xué)術(shù)發(fā)展空間,現(xiàn)有的故事學(xué)范式難以進(jìn)入機(jī)智人物故事領(lǐng)域⑤;民間故事志雖早已達(dá)成“忠實(shí)記錄與慎重整理”的共識(shí),但隨著學(xué)科的發(fā)展,從忠實(shí)記錄到立體全面展現(xiàn)故事講述狀況逐漸成為民間故事志努力的新方向,對(duì)于講述人的描寫也不僅僅只再局限于生活史,而是更多關(guān)注其心靈史的描畫,挖掘出“帶有個(gè)人文化觀念投射,經(jīng)過其心靈濾透,具有文化持有者特殊印記的精神產(chǎn)品⑥”。在不斷的整合與反思過程中,民間故事學(xué)“研究范式表現(xiàn)為頑固性,在故事形態(tài)學(xué)、文化人類學(xué)以及類型學(xué)、主題學(xué)等范式構(gòu)成的學(xué)術(shù)圍墻內(nèi)打轉(zhuǎn)、本體意識(shí)薄弱、是技術(shù)之學(xué)和分析之學(xué)而不是感受之學(xué)和生活之學(xué)⑦”等弊病逐漸顯露,民間文學(xué)未來之路任重而道遠(yuǎn)。對(duì)此,作者在《民間故事研究何為》一章中談到:“中國(guó)民間故事研究要擺脫模式化的困境應(yīng)眼光向外,對(duì)外不斷吸納相關(guān)學(xué)科方法,保持開放性;眼光向內(nèi),對(duì)內(nèi)夯實(shí)學(xué)科基礎(chǔ),整合多種研究理路,拓展新空間;眼光向下,關(guān)注民間故事的多重生存樣態(tài)⑧”,這是目前力所能及且行之有效的方式。
《民間故事研究史論》是一部靜態(tài)的充滿思辨意識(shí)的故事學(xué)術(shù)史,同時(shí)也是一部活態(tài)的有溫度的故事學(xué)人學(xué)術(shù)史,二者并行不悖。在學(xué)術(shù)評(píng)論之外,作者結(jié)合與民間故事研究專家的學(xué)術(shù)訪談,為讀者呈現(xiàn)了一部有溫度的學(xué)術(shù)史。劉魁立的故事類型地圖編制故事與“照亮黑暗”說、劉守華的民間故事研究之路、江帆與故事家譚振山建立田野情感的過程、袁學(xué)俊與耿村“故事村”發(fā)現(xiàn)的回憶……作者通過采訪這些民間故事研究專家,以故事學(xué)人自身講述的治學(xué)經(jīng)歷給讀者呈現(xiàn)出隱藏在學(xué)術(shù)成果背后的不為人知的故事,在呈現(xiàn)故事學(xué)人的知識(shí)生產(chǎn)過程,學(xué)術(shù)理論來源的同時(shí)這為一貫以莊嚴(yán)肅穆為主的學(xué)術(shù)史注入了新的活力與生命力,使其變得鮮活而生動(dòng)。而通過這些故事研究專家所講述的故事,也讓讀者感受到這些故事學(xué)人的可敬與可愛。一如江帆教授在回答“改變?nèi)松边@一話題時(shí)傾吐的言論:“我評(píng)上教授啊,得到遼寧省優(yōu)秀共產(chǎn)黨員的榮譽(yù),我和別人有什么區(qū)別呢?我無非就是認(rèn)識(shí)了這些故事學(xué)家,我對(duì)他們的研究成就了我的學(xué)術(shù)人生。但是我想,我對(duì)他們的生活有多大改變?所以有時(shí)候我在想,我們這些研究者,年輕的學(xué)者,他們什么時(shí)候能跟下面的人有這種感情的時(shí)候,可能他會(huì)發(fā)現(xiàn)相對(duì)真實(shí)的東西⑨。”學(xué)者的學(xué)術(shù)品格在其言談之中自然流露出來。而這些,在嚴(yán)肅的學(xué)術(shù)理論著作中往往是不被允許出現(xiàn)的。知其人,方能理解其著,在了解這些學(xué)者的治學(xué)思想與處世觀念之后,再回頭看其著作,自會(huì)有一番不同的感受。而這,正是一個(gè)學(xué)者的溫度,也是一門學(xué)科的溫度。
無論是從全息的定量視角角度看中國(guó)近四十年民間故事的發(fā)展,還是從局部的定性角度看近七十年熱點(diǎn)問題的研究進(jìn)度,它都顯示出:中國(guó)民間故事的土壤并不貧瘠,相反,它肥沃、深厚、廣博,有待于后來者的開墾。民間故事學(xué)發(fā)展至今,正是有賴于一代又一代故事學(xué)人的勤耕不輟,而通過這樣一部史書的勾勒描畫,我們可以看到,在未來,它亦充滿著無限可能。
注 釋
①萬建中:《20世紀(jì)中國(guó)民間故事研究史》,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頁。
②漆凌云:《中國(guó)民間故事研究史論:1949-2018》,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19年,第202-203頁。
③漆凌云:《中國(guó)民間故事研究史論:1949-2018》,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19年,第127頁。
④漆凌云:《中國(guó)民間故事研究史論:1949-2018》,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19年,第144頁。
⑤萬建中:《20世紀(jì)中國(guó)民間故事研究史》,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頁。
⑥江帆:《譚振山故事精選》,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頁。
⑦萬建中:《20世紀(jì)中國(guó)民間故事研究史》,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314-317頁。
⑧漆凌云:《中國(guó)民間故事研究史論:1949-2018》,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19年,第208-213頁。
⑨漆凌云:《中國(guó)民間故事研究史論:1949-2018》,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19年,第283頁。
(作者單位:湘潭大學(xué)文學(xué)與新聞學(xué)院)
——“民歌研究暨學(xué)術(shù)史研討會(huì)總結(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