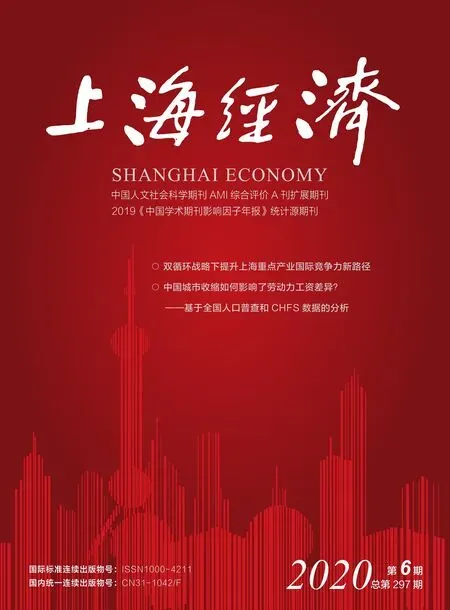中國城市收縮如何影響了勞動力工資差異?
——基于全國人口普查和CHFS數據的分析
劉玉博 孟美俠 張學良
(1.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上海 200020;2.上海財經大學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上海 200433)
一、引言
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中國流動人口規模從1982年的657萬增加至2019年的2.36億。1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2020年 2 月。盡管近幾年流動人口規模有所調整,流動速度趨于平緩,但從客觀結果看,流動人口向部分城市集聚,就意味著另外一些城市以勞動力為核心的經濟要素的不斷流失。國際學者通常將這種人口密集地區發生的持續人口流失的現象稱為“城市收縮(Urban Shrinkage)”。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作者發現中國2000年至2010年有85個地級市人口增長率為負,占比29.62%,即出現“城市收縮”現象。已有學者研究表明,收縮城市中企業生產效率將出現明顯下降(劉玉博等,2017),那么如此高比例的收縮城市的存在,將何種程度上影響中國勞動生產率繼而影響區域均衡發展?本文結合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數據,從勞動力工資收入的角度,觀察收縮城市和非收縮城市之間的區域差距,回應上述現實問題。進一步從勞動力技能結構的視角,分析區域差距產生的主要原因,為促進區域平衡發展提供新的思路。
區域收入差距問題受到學者的長期關注。前期相關文獻較多地關注人口規模變化對收入差距的影響(范紅忠等,2013;高虹,2014),較少從勞動力技能結構變化的視角分析這一問題。部分學者研究了人力資本質量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鈔小靜和沈坤榮,2014),但界定地區收入差距的空間尺度大多為“城鄉”“省域”和“東、中、西三大板塊”,常常忽略以中小城市為主的人口凈流出地區的發展問題。近年來,更多文獻關注到人口流動導致的人口年齡結構(陳蓉和王美鳳,2018)、就業結構(馬銀坡等,2018)、家庭結構(蘇麗鋒,2017)等的變化,而對流動人口結構變化導致的區域差距并未作進一步的深入分析。根據學者研究,城市收縮往往與就業率下降(Reckien and Martinez-Fernandez,2011)、住房空置率提升(Couch and Cocks,2013)、高技能勞動力流失(Anja, 2016)、企業生產率下降(劉玉博等,2017)、老齡化加劇(張學良等,2018)、公共服務資源錯配(劉玉博等,2020)等社會現象高度相關,因此收縮城市可能面臨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已不容小覷。基于前人研究,本文重點分析勞動力技能結構變化對收縮城市和非收縮城市之間收入差距的影響。一方面,勞動力規模變化,降低城市集聚經濟發生的可能性,影響企業效率,繼而降低企業勞動力工資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更健康和更高學歷的勞動力更容易流動(蔡翼飛和張車偉,2012;Combes et al.,2012),收縮城市勞動力的技能水平也將發生變化,降低勞動力獲取高工資回報的能力。兩個方面分別從供給方和需求方增加了收縮城市和非收縮城市之間產生區域差距的可能性。具體地,本文利用兩次人口普查數據(2000年和2010年),識別人口凈流出的“中國收縮城市”,并利用2011年和2013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分別控制不同類型的勞動力技能結構,觀察收縮城市與非收縮城市勞動力平均工資差異的變化,以尋找區域差異的主要來源。另外,考慮到中國不同區域的城市存在異質性,本文進一步對東部、中部和西部的子樣本分別進行分析,觀察三大區域內部收縮城市和非收縮城市勞動力工資收入的差距及來源。
目前,中國流動人口規模進入調整期,2015年起出現拐點,由上升轉變為緩慢下降,2016年和2017年分別下降171萬人和82萬人2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流動人口司,《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8》,中國人口出版社,2019年1月。。在流動人口規模趨于穩定并出現回調的情況下,如何精準施策,利用勞動力規模和勞動力結構的“組合拳”,干預收縮城市人口變化的軌跡,使其獲得永續發展的能力,對于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建立合理有序的城鎮體系和推進區域平衡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本文主要的創新之處為:第一,不同于以往文獻從“城鄉”“省域”和“東中西”的角度分析區域不均等的現象,本文從“收縮城市和非收縮城市”的角度,研究中國人口增減和技能結構變化對區域差距的影響;第二,探尋城市收縮造成區域差距的內在機制,即主要通過文獻分析和實證檢驗的方法,識別勞動力技能結構變化對區域差距的影響程度。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主要從人口凈流失可能產生的經濟社會效應的角度,簡要評述相關文獻;第三部分為數據來源說明,以及收縮城市和非收縮城市勞動力平均工資收入差異的描述性統計;第四部分建立計量模型并進行嚴格的實證分析與機制檢驗;第五部分為本文的結論和政策啟示。
二、城市收縮、勞動力技能與勞動力工資差異:基于文獻評述的視角
目前較多文獻雖然關注人口流動與區域差距之間的關系,但大多將區域差距的對象定義為“省份”“城鄉”或“東中西三大板塊”,忽略了作為人口凈流出地的中小城市可能面臨的發展問題。魏后凱(2014)發現2000年至2011年,中國城區人口20萬以下的小城市人口增長率為負,出現城鎮化發展的兩極化傾向。根據張學良等(2016)的研究,中國33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中,有90個樣本的常住人口持續流失,即出現了“城市收縮”的現象,占比26.71%。作為最活躍的生產要素,人口要素的流失往往與經濟萎縮(Wiechmann and Pallagst,2012)、人力資本流失(Anja,2016),以及就業率下降(Reckien and Martinez-Fernandez,2011)等問題相關。因此,人口凈流失地區與人口凈流入地區,即收縮城市和非收縮城市之間,很可能形成了除“省份”“城鄉”和“東中西三大板塊”以外的另一種不容忽視的區域差距類型,需要引起重視。目前與此相關的研究文獻仍然較少。
除此之外,雖然現有文獻對人口流動與東中西或省份區域差距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索,但極少探尋二者之間的傳導機制,將其進行定量化討論的研究更少。總體來說,人口流動主要通過改變城市人口規模和人力資本質量兩條基本途徑,影響城市的勞動力工資收入水平。首先,從城市規模的角度:現有文獻較多地關注城市規模與勞動力工資或經濟效率的關系,研究結論存在兩種相反的觀點。大多數學者,如高虹(2014)、蹤家峰和周亮(2015)、張天華等(2017)、謝衛衛和曾小溪(2018)、劉修巖等(2019)等,認為城市規模的上升將促進勞動力收入提高,陸銘等(2012)也證明城市規模與個人就業率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這主要依賴于城市規模擴大產生的正向的集聚經濟性(Duranton and Puga,2004)。與此相反,寧光杰(2014)利用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的收入數據,發現控制勞動力可觀測特征、不可觀測特征和選擇偏差問題后,大城市勞動者的工資升水不再存在,甚至出現劣勢,間接印證城市規模過大產生的擁堵、高房價等集聚不經濟的問題。同時Fallah(2011)認為,人口密度較高的城市由于交通擁擠、房價上漲等集聚不經濟,超過了集聚對生產效率的貢獻,大城市的工資溢價出現逐漸下降的趨勢(張少華和張天華,2018)。因此,從人口流動改變人口規模或集聚經濟水平的角度,人口凈流入和人口凈流出地區對勞動力收入水平的影響,孰優孰劣,目前仍無定論。
其次,從人口流動改變人力資本質量和結構的角度,研究區域差距的文獻相對較少。勞動力的流動具有選擇性,更高技能和更健康的勞動力更容易流出。可見總體上人口凈流出地區人力資本存在下降的趨勢(阮榮平等,2011),不利于當地經濟的健康發展。戴翔等(2016)、袁冬梅等(2020)雖然研究了勞動力數量、勞動力技能水平和勞動力技能配置效率對中國產業轉型的影響,但較少涉及由此帶來的區域不均衡現象。李晶晶和苗長虹(2017)分析了人口流動對流入地和流出地經濟增長的異質性影響效果,但文中并沒有對這一機制影響區域差距的程度進行細致和科學的定量化分析。近年來,少數學者開始關注人口流動改變人力資本繼而引起區域差距的問題,如彭國華(2015)建立了地區差異和勞動力流動的統一框架,認為東部地區吸引了更多高技術型崗位,導致東、中、西部地區差異進一步拉大,對本文的研究具有較多的啟示。
盡管缺乏人口流失引起人力資本質量下降,繼而拉大城市之間收入差距的直接證據,但現有文獻對不同技能勞動力群聚及其引起的經濟效率和工資水平變化的研究,對本文有重要的借鑒意義。Glaeser and Gyourko(2005)發現,高技能勞動力對城市便利性的偏好,以及對高價格住房較強的支付能力,導致高、低技能勞動力在區位分布上出現差異,表現為低技能勞動力不斷在收縮城市群聚的現象;Shapiro(2006)從崗位特征的角度,解釋了新崗位由于對知識和創新的要求更高,從而對高技能勞動力需求更高的現象;Diamond(2016)利用美國1980-2000年普查數據發現,地方生產率水平的差異導致高低技能勞動力分區(Sorting)。另外,Sylvie(2012)指出由于城市收縮導致失業率上升,繼而引發城市投資不足,不利于收縮城市持續發展,而在這一過程中,窮人、老年人以及低教育水平勞動力,最容易受到這一社會問題的影響;Nelle(2016)亦指出,人口減少的城市將降低長期教育投資水平,使城市的未來發展潛力下降。對中國而言,具有特色的戶籍制度則使高技能勞動力更容易在其他城市獲得正式的居住身份,并獲得享受城市公共服務的權利,也會導致不同技能城市人力資本空間分布出現差異(梁文泉和陸銘,2015;劉曄等,2019)。
綜上,人口選擇性流動導致人口凈流出城市即收縮城市出現一系列經濟社會效應,且與非收縮城市之間可能已經形成了明顯的區域差距。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有助于建立健康可持續的城鎮體系,同時對于區域不均等可能引發的工資收入等民生問題的解決路徑也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目前相關研究仍以“城鄉”或“東中西三大板塊”的區域差距為研究重點,對城市之間工資差異的關注不多。另外,國內外學者對于城市規模影響勞動力工資的研究存在爭議,這可能與同一規模等級的城市中集聚經濟的作用方向不同有關,且集聚經濟對不同種類的勞動者工資的影響存在差異,也是形成以上爭議的可能的原因之一。本文從人口選擇性流動的角度,對收縮城市和非收縮城市之間工資差異的解釋,以及作用機制的研究,對解釋上述爭議亦有所助益。
三、模型設計與數據說明
本文試圖尋找收縮城市和非收縮城市勞動力平均工資的差異,以及差異產生的原因。其中,由人口選擇性流動導致收縮城市和非收縮城市之間人力資本質量發生變化,繼而引發當地勞動力工資收入變化,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一)模型設計
根據論文研究目的,設計如下計量模型:

其中i為代表勞動者。Wi為勞動者i的小時工資數;Shrinkingi代表勞動者所在城市的收縮狀態,為1代表城市收縮,為0代表城市不收縮;X1i為勞動者個人基本情況,包括性別、婚姻狀況、政治面貌等狀態;X2i為勞動者技能水平,包括受教育程度、潛在工作經驗、工作職位、工作行業等變量;X3i控制了勞動者i所在城市所屬東部、中部的區域變量,以排除由于區位稟賦差異對工資的影響;X4i為勞動者i所在城市的人口規模、公路密度、財政支出等變量,以控制不同城市的集聚水平、公共服務、發展階段對勞動者工資造成的影響。在逐一控制X1i至X4i變量后,β1系數的變化即反映不同因素對勞動力工資的影響幅度,為本文關注的重點。
(二)收縮城市變量的獲取
根據國際收縮城市研究網絡(Shrinking City International Research Network)的定義,收縮城市被定義為“人口持續流失的人口密集區域”。Oswalt(2005)、Turok and Mykhnenko(2007),以及Schilling and Logan(2008)等學者根據研究樣本的不同,對人口流失率和人口流失時段均有不同的限定,但均以人口流失作為識別收縮城市的核心指標。龍瀛等(2015)、張學良等(2016)學者均利用常住人口的增減作為衡量中國收縮城市的具體指標。本文延續張學良等(2016)識別中國收縮城市的方案,將中國收縮城市定義為兩次人口普查年間(2000-2010年)常住人口增長率為負的城市。利用中國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常住人口數據,最終在28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中識別85個收縮城市22000—2010年,中國發生了頻繁的區劃調整,對本文收縮城市的識別結果造成嚴重干擾。因此作者首先根據各地區劃調整信息,增減對應行政區的人口數量,以獲得2000年和2010年一致的可對比空間的人口數據。以此為基礎計算人口增長率,并識別中國的收縮城市。,占比29.62%。
表1為中國收縮城市人口增長率的統計信息。在85個收縮城市中,51個城市人口增長率大于-5%,占比60%;25個城市人口增長率處于-10%至-5%之間,9個城市人口增長率效率-10%。由此可見,兩次普查年間,中國已出現普遍的城市收縮現象,應充分研究和探索與城市收縮相關的一系列經濟社會效應。

表1 中國收縮城市的識別結果
從識別結果判斷,中國收縮城市和非收縮城市的地理分布,較好地契合了中國目前的人口分布與發展現狀。中國收縮城市大多分布于中國的東北和長江經濟帶地區,多集中在農業占比較高,以及傳統工業部門為主導產業的城市。而非收縮城市主要分布于中國的幾大增長極區域,如京津冀地區、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另外,中國甘肅酒泉、西藏拉薩等地,也在不斷地集聚人口,形成了區域性的人口增長中心。根據國際城市收縮經驗可粗略地判斷中國城市收縮的原因:中國以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標志,受到世界全球化進程的影響,消費結構和生產結構發生變化,一些城市在全球城市網絡中地位下降,導致人口不斷流出,如湖北荊州。另外,產業結構升級導致傳統工業部門失去生產活力,造成勞動力摩擦性失業,引發人口流失,如四川自貢。再者,中國快速城鎮化過程中,人口向城市的大規模遷徙,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口在鄉村地區的流失,如湖北黃岡。
(三)中國勞動力工資、個人特征等數據
本文使用的勞動力個人特征、技能結構、工資收入等微觀數據來自西南財經大學2011年、2013年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項目(CHFS)。中國家庭金融調查項目每兩年進行一次,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收集了家庭資產與負債、收入與支出、保險與保障、家庭人口特征及就業等各方面的信息。2011年的調查樣本覆蓋了全國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80個縣(區、縣級市)、320個村(居)委會,樣本規模為8438戶;2013年的調查樣本覆蓋了全國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262個縣(區、縣級市)、1048個村(居)委會,樣本規模為28143戶。本文在數據處理過程中,合并了2011年與2013年的個人工資數據,并將樣本限定為工資為正的16歲至60歲的男性以及16歲至55歲的女性。最終獲得涵蓋29個省、166個城市的14995個有效樣本。
(四)城市與區域控制變量
本文控制城市與區域變量以排除可能影響勞動力工資水平的其他因素,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包含人口規模、財政支出比重、固定資產投資、公路網密度、醫療病床數等,分別控制城市的集聚水平、公共服務水平,同時控制產業結構指標以排除城市經濟結構的影響。另外,生成東部、中部兩個虛擬變量,控制地理稟賦因素對勞動力工資的影響。表2為上述各類控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由表2,收縮城市勞動力小時平均工資為2.33,非收縮城市平均工資為2.76,說明兩類城市勞動力收入水平已出現明顯差異;同時,相對于非收縮城市,收縮城市勞動力的學歷水平較低,擁有大學學歷尤其是研究生學歷的勞動力數量明顯少于非收縮城市;收縮城市勞動力潛在工作經驗和實際工作經驗偏高,這或許與收縮城市年輕勞動力較容易流出或受教育年限較短相關。另外,收縮城市勞動力工作職務等級明顯偏低,第二行業的從業者比例高于非收縮城市,而從事服務業的勞動力比重小于非收縮城市。下文將利用嚴格的實證檢驗,分析城市收縮對勞動力工資差異的影響,并量化由勞動力技能差異帶來的工資差異的程度。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

財政支出占比 財政支出占G D P比重 1 6.1 0 3 1 8.8 6 5 1 5.5 2 5固定資產投資占比固定資產投資占G D P比重 6 1.9 2 9 7 3.8 2 5 5 9.4 4 4人口規模 人口規模對數 5.5 2 4 4.3 4 0 5.7 7 1公路網密度 公路里程數/平方公里 1.2 5 4 1.0 8 2 1.2 8 9第一產業占比 第一產業產值占G D P比重 6.9 7 7 1 5.7 8 0 5.1 3 5第二產業占比 第二產業產值占G D P比重 4 6.1 7 6 4 8.9 5 8 4 5.5 6 0萬人病床數 醫療機構床位數/戶籍人口 6 7.7 3 0 4 2.0 0 2 7 3.1 0 7城市變量
四、實證檢驗與分析
(一)全樣本回歸
表3為勞動力工資對中國城市收縮啞變量的回歸結果。第(1)列為基本回歸,說明收縮城市比非收縮城市勞動力工資低33.08%。第(2)—(4)列,分別控制了勞動力個人基本特征、勞動力學歷狀況、勞動力技能水平等變量,收縮城市與非收縮城市勞動力工資差異由33.08%下降為19.84%,下降幅度約為2/5。第(2)列的回歸結果表明,收縮城市和非收縮城市勞動力的性別、政治面貌、婚姻狀態差別不大,控制這些變量后,收縮城市與非收縮城市勞動力工資差異由33.08%微弱下降至32.13%。第(3)列的回歸結果表明,收縮城市和非收縮城市勞動力的學歷水平有較大差距,增加控制這些變量后,收縮城市與非收縮城市勞動力工資差異由32.13%下降為19.26%,說明勞動力教育水平差距約可以解釋兩類城市之間勞動力工資差距的2/5。在第(4)列,當控制勞動力工作經驗等變量后,收縮城市與非收縮城市之間的勞動力工資差距出現波動。正如上一節變量描述中所說,由于收縮城市年輕勞動力較容易流出以及受教育年限較短,導致收縮城市勞動力潛在工作經驗和實際工作經驗偏高,可能是造成工資差距波動的主要原因。第(5)列控制了城市的產業結構、醫療服務、固定投資等宏觀因素,收縮城市與非收縮城市之間勞動力工資差異變得不顯著,即沒有證據顯示城市收縮會因為勞動力絕對數量的減少對勞動力工資水平產生負的影響。

表3 中國城市收縮與勞動力工資差距(全樣本)

注:①*,**,***分別表示10%,5%,1%顯著性水平;②括號內為t統計量。下同。資料來源:作者利用stata軟件計算。下同。
(二)分樣本回歸
考慮到中國東部、中部和西部的發展差異,論文進一步對中國東部、中部和西部的收縮城市和非收縮城市之間勞動力工資差異及其原因進行分析。表4、表5和表6分別為東部城市、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的樣本回歸結果。第(1)列為基準模型,第(2)列至第(4)列分別增加控制了勞動力個人特征、勞動力教育程度、勞動力工作狀態等微觀變量,第(5)列排除了城市宏觀要素對勞動力工資差異的影響。
由表4,東部地區兩類城市勞動力工資差異最大,收縮城市比非收縮城市勞動力工資低44.20%,其中勞動力教育水平的差異解釋了工資差距的1/2以上。當控制了城市發展宏觀變量后,收縮城市和非收縮城市之間勞動力工資差異變得不顯著。

表4 中國城市收縮與勞動力工資差距—東部
由表5,中部地區兩類城市勞動力小時工資收入差距最小,收縮城市比非收縮城市勞動力工資低12.21%,其中勞動力教育水平的差異解釋了工資差距的1/2左右。與東部城市和西部城市不同的是,當控制了城市發展的宏觀變量后,收縮城市對勞動力工資收入依然存在影響,在10%水平下顯著為正,幅度較小為0.06。

表5 中國城市收縮與勞動力工資差距—中部
由表6,西部地區收縮城市和非收縮城市之間勞動力小時工資差距相對較大,收縮城市比非收縮城市勞動力工資低23.30%,低于東部地區的44.20%,高于中部地區的12.21%。其中,勞動力基本特征、教育程度和工作狀態總體上解釋了兩類城市勞動力工資差距的2/3左右,其中勞動力教育水平差異解釋了工資差距的3/5左右。

表6 中國城市收縮與勞動力工資差距—西部
五、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文同時關注勞動力規模變化和勞動力技能結構變化對收縮城市和非收縮城市之間收入差距的影響。基于國際學者對城市收縮的通用定義,本文利用五普和六普數據,識別了常住人口增長率為負的收縮城市。基于文獻分析,結合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數據(2011年和2013)中166個城市的14995個有效樣本,對城市收縮造成的區域間勞動力工資差距進行實證檢驗。結果顯示,總體上收縮城市和非收縮城市勞動力小時平均工資存在顯著差異,即收縮城市勞動力工資比非收縮城市低33.08%。在控制勞動力基本特征、教育水平和工作狀態變量后,這一幅度下降為19.84%,即兩類城市之間勞動力個人差異是造成工資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其中,勞動力受教育水平差異對勞動力工資差距的影響最大,解釋了兩類城市工資差異的2/5左右。
同時,考慮到中國不同地區城市發展階段的差異,本文將樣本分為東、中、西三大板塊分別回歸。研究發現,不同區域兩類城市勞動力工資收入差距程度不一,東部最大為44.20%,西部次之為23.30%,中部最小為12.21%。另外,實證結果發現勞動力受教育程度的差異是造成兩類城市之間勞動力工資差異的重要原因,其中東部地區勞動力教育水平大約可以解釋兩類城市勞動力工資差異的1/2,中部為1/2,西部為3/5。以上研究結果印證了勞動力選擇性流動的事實,即低技能勞動力傾向于向收縮城市集聚,高技能勞動力傾向于向非收縮城市集聚,同時也說明收縮城市與非收縮城市之間可能已經形成除了“城鄉”和“東中西”以外的另一種不可忽視的區域差距類型,必須引起重視。
(二)政策啟示與進一步研究方向
首先,制定適合收縮城市的針對性的發展規劃和管理政策。根據本文研究,中國287個地級城市中,有29.62%出現常住人口持續下降的現象,即出現城市收縮,比重較大。應嘗試制定指導收縮城市發展的專門規劃和政策,思路上可以借鑒國際上流行的“精明收縮(Smart Shrinkage)”理念,強調“收縮下的集中式增長”,改變粗放型城鎮化模式,并結合當地特色,實現“更少的人”背景下的“精明發展”。其次,在關注人口總量增減的同時,注重人口結構變化對城市發展帶來的影響。本文發現,勞動力技能結構的差異,是形成收縮城市和非收縮城市勞動力工資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即收縮城市和非收縮城市在勞動力受教育程度、工作狀態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因此,收縮城市不僅意味著總量上人口規模出現下降,而且意味著包含勞動力技能水平下降在內的深層次的社會癥結,威脅中國健康可持續的城鎮體系的建設。在新型城鎮化的發展過程中,應該因地制宜,著重培育與本地優勢產業匹配的專業人才,遏制收縮城市人力資本質量持續下降的趨勢,為城市可持續發展做好智力儲備。最后,時刻關注由勞動力選擇性流動所帶來的其他經濟社會結構方面的變化。不難預見,作為經濟活動中最為活躍的生產要素,高素質勞動力的流出不僅造成收縮城市勞動力收入水平偏低,而且還會增加企業生產效率下降、土地資源浪費、資本流失、公共服務投資不足等問題發生的可能性。未來城市收縮相關研究和政策制定中,應時刻保持對上述問題的跟蹤,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