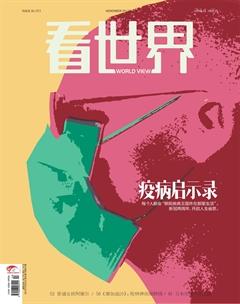莫迪尷尬得銅牌

鄧晨
人們往往用一種非常粗略的方式理解印度:
在古代,印度的土地廣大而貧窮,那時候“王權不下鄉”,社會運作靠的是宗教習俗。印度人口的構成復雜,因此信仰體系不能只談家族倫理,還要給各族群確定身份地位,并上升到宇宙論的層次去鞏固—于是就有了印度教的種姓制度。
這一理解印度的角度,部分解釋了種姓制度運行的方式,也顯示了當族群之間的宰制權力懸殊,古代人又需要解釋各種族裔的面貌、風俗習慣及生命境遇為何如此不同時,就采用了一整套因果輪回的體系,來合理化并鞏固業已存在的不平等。
前不久印度總理莫迪訪問梵蒂岡與天主教教宗會面,許多國際媒體看到教宗贈送給莫迪的銅牌,紛紛猜測其含義。該塊銅牌上的銘文,刻著舊約圣經《以賽亞書》的文字,這被懷疑是在影射與批評莫迪的施政。
畢竟,近年來在莫迪政權崇尚印度教的氛圍下,基督徒遭受迫害的新聞時有所聞。例如,去年被逮捕的83歲老神父斯坦·斯瓦米,被控幫助左翼游擊隊從事恐怖活動,結果在今年7月死于囚禁中。官方說法是,他死于新冠并發癥引起的心臟驟停。
從19世紀的“梵社”改革家(包括泰戈爾家族),到20世紀的“賤民神學”活動家,基督教的思想挑戰了印度教的種姓體系、男女不平等、迷信風俗等桎梏;很多受到歧視的低種姓與部落民族在基督教中找到平等,斯瓦米神父就是深入偏遠部落的傳教士之一。
可是,與印度最高法院前法官、前部長、電影導演和作家等人一起發聲,幫助低種姓與部落民族免受肆意“預防性拘留候審”的斯瓦米神父,自己也成為了同一司法過程的受害者。
當不同宗教碰撞在一起,理解的關鍵或許不是具體的教規(例如印度教不準傷害牛、猶太教規定如何吃魚、基督教規定洗禮等),而是把宗教還原到在不同環境脈絡中形成的“面對世界的姿態”。
比如說,猶太教是來自猶太人作為一個小民族面對外部壓迫的自我賦權,而基督教進一步把信徒身份擴大到猶太人之外的更多貧苦人群,這種“由神的救贖得到力量”在其他宗教里比較少見。在印度教、佛教、耆那教這些印度宗教里存在的,是“每個人減少盲目欲望及其所伴隨的苦難及傷害”。
印度宗教的姿態有什么局限呢?西印度群島出生的印度裔神學家阿南塔南·蘭巴強認為,問題在于印度教把重點放在個體的修行與解脫,但不從社會層面解除結構性的壓迫。
雖然現代印度的宗教家嘗試過很多改革,包括革除種姓制度、童婚、寡婦殉葬等陋俗,還包括將印度教導向一神教,但是這種內部改革作用有限。蘭巴強嘗試建立一種“印度教解放神學”,就像拉丁美洲興起的基督教“解放神學”那樣,旨在改造社會不平等,反對莫迪政權壟斷印度教的解釋權。但是,從個體修行轉向改造社會后,要解決的問題就不再是印度教所能提供指導的了。
“在群體層面解除痛苦”與“個體通過修行擺脫桎梏”是共通的,但卻不再是靠個人之力可以左右的,而是進入了混沌博弈的現實政治—這并非明確的選擇題,人類其實更多地是在改造外在世界與返回內心之間擺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