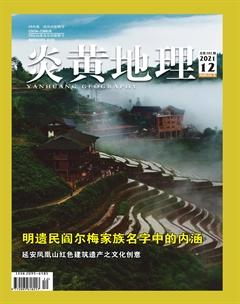司馬金龍墓石棺床樂種圖像釋讀
姜宇娓
北魏司馬金龍墓石棺床一側以“分幅式”呈現方式,刻畫了十三位樂伎手持樂器舞動的情景。筆者從音樂圖像學角度就其樂器合奏所產生的樂種意義進行釋讀,以期打開北魏音樂樣貌的一個窗口,側面解讀北魏王朝都城的音樂盛況。
司馬金龍墓石棺床圖像之樂器特質
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馬金龍墓于1965年11月被發現,1966年發掘完畢。該墓位于大同市東南方向的石家寨村,屬有明確紀年的北魏早期墓葬。
墓主石棺床置于墓葬后室西部,由六塊淺灰色細砂巖石板組合而成。棺床前立面石板呈“山”字型,上部以波狀纏枝四葉忍冬紋作長方形的邊框,中間雕波狀纏枝忍冬枝葉及形態各異的伎樂童子和珍禽瑞獸。伎樂童子均髡發,上身裸,帔帛從頸后繞兩肘飄舉,下身著犢鼻褲。伎樂童手持的樂器從左至右依次為:腰鼓、橫笛、檐鼓、貝、五弦、琵琶、排簫、長篳篥、鼓、鈸、吹指(如圖1)。文章藉圖像學知識,釋讀其中的樂器及其合奏的樂種意義。
司馬金龍屬東晉皇族司馬楚之被迫逃亡平城(今山西大同)與鮮卑貴族通婚的后代。對比與石棺床同一時期出土的司空瑯琊康王墓表與司馬金龍墓志銘,雖二者在文字記錄上稍有出入,但內容基本相同。可見墓主生前身份、地位之顯赫,方有資格享受這般高規模的哀榮。
精美的棺床雕刻,將歷史上活態的音樂瞬間永恒定格。通過對棺床樂雕圖像細致觀察,結合伎樂童手持的樂器形制、大小、演奏姿勢,遙想其音聲音色,釋讀各件樂器。
腰鼓:棺床所刻腰鼓類似目前所見瑤族長鼓,筒長腰細,兩端鼓膜各通過一個類似于“鐵箍”的東西繃于鼓兩側,鼓形兩端大小基本相同,故音色相差甚微,斜掛于奏者腰側,雙手同時擊打,或交替拍擊,形成多種節奏型。
檐鼓:棺床雕刻的檐鼓兩端形狀不一,兩面皮膜均繃于“鐵圈”上,再以繩索拉緊筒口,鼓身兩端以“網格狀”點裝四周,中間呈近對稱“線條”,鼓身呈對稱圖形,頗具美感。兩端鼓面大小各異,其兩面發聲有別,似有“一鼓雙音”之效果。奏時懸胸前,與腰鼓奏式相同,雙手或交替、或同時拍擊。
鼓:其形制更近于人們常見的腰鼓,其身較腰鼓更為“豐滿”。兩端鼓面略小于身,鼓身四周以“網格”案予以裝飾。奏時置胸前,由于體積比腰鼓和檐鼓更為“壯碩”,筆者推測其負責樂隊中的低聲部。
鈸:伎童雙手各拿一鈸片,呈圓形,中間凸起,呈半球體狀。鈸片大小與手握至拳狀相等,較小,聲尖。
琵琶:棺床刻琵琶,形屬半梨形音箱,頸曲而短,頸部長度只容一只手,屬短頸琵琶。頸上有四相(柱),四弦,以琴弦為中心的琵琶面板上呈對稱刻畫三組類似“同心圓”的圖案。右手似用撥子挑發聲音,左手配以彈奏。因頭部向后彎曲,稱“曲頸琵琶”。
五弦琵琶:棺床所刻琵琶,應屬半梨形音箱琵琶,頸直且短,上有五相(柱),五弦,以琴弦為中心的琵琶面板上刻有兩條波浪線,伎樂童左手按琵琶頸部琴弦,右手向上撥彈,眼睛更多是注意左手動作。此器與上述曲頸琵琶同由龜茲傳入,有西域風格。
橫笛:棺床上雕刻的童子,雙手前后交叉握笛,指尖放置于笛孔處,伎樂頭部側轉,口部對準吹孔,橫笛的尾端“上揚”,或是雕刻者考慮圖像的整體美觀,抑或是欲表達演奏時的熱烈場面。根據其演奏姿勢大致可判斷出流行于當時的橫笛,已經具備吹孔、膜孔、基音孔、助音孔,音域較寬,發展較成熟。
篳篥、長篳篥:即觱篥,亦稱管,名稱由古龜茲語音譯而來,是龜茲國創造的一種簧管樂器,有“必栗者,羌胡樂器名也”之說。雕刻于棺床上的兩幅樂伎吹奏篳篥與長篳篥的圖像,樂伎表情從容,雙手握管,口對吹孔,豎吹。因管子的長短不同形成鮮明的音色對比,由是,音樂的和聲與旋律更為豐富。
排簫:即“龠”,據說傳自伊耆氏之手。結構由長短不一的竹、木或銅管按音階編排而成。《說文》稱其“參差管樂,象鳳之翼。從竹,肅聲。”排簫一般以竹做管。筆者觀察,司馬金龍棺床刻排簫伎圖,雙手所握管子左長右短,形成音色對比,在樂隊中可能屬于旋律聲部。
貝:屬佛教法器。以海螺殼制成,厚實堅硬,中部似橢圓形,整體似“棗核形”。將海螺的一頭磨平作“吹孔”,聲清澈悠遠,給人以一種莊嚴肅穆之感。
吹指:即口哨音樂。它打破了樂器演奏的常規,屬演奏中的一種“色彩音”,正是口哨音樂的出現,使樂隊的演奏更加事俗化、人性化。可理喻為司馬金龍生前所喜愛的音樂,表現了其詼諧的一面。
由上述司馬金龍棺床雕刻伎樂分析,可看到作為北魏之都的平城在開放、交流與交融的社會生活中的一則剪影。反映了平城時期樂器流布樣態、合奏形式以及官方的禮樂制度。
司馬金龍石棺床圖像之樂種學思考
樂種的構成主要包括了“物質構成、形態構成、社會構成三個方面。”樂種形成的前提,關鍵在于樂器的選擇與使用。誠如有學者進一步釋說樂器“是人類文明的標志和音樂表現的重要手段”。樂器的產生和發展,是與其時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經濟基礎以及人文情懷相適應的結果。樂器的材料、形制、工藝等物理因素,會直接影響其音響效果和在樂隊中所承擔的固有“角色”。通過觀察司馬金龍石棺床雕刻的樂器圖像的形制以及其演奏姿態,有助于對其表演的形式,即合奏、重奏、協奏抑或是獨奏所形成的整體音色進行判斷,來進一步闡述當時音樂的構成以及宮廷音樂的使用情況。
北朝統治層是西域音樂的忠實“粉絲”。從司馬金龍棺床雕刻的內容推判,該組樂隊或來自西涼,即甘肅敦煌一帶。后涼呂光、北涼沮渠蒙遜(匈奴人)據涼州時,改造龜茲樂而成,所謂“秦漢伎”即西涼樂。該樂或包含一些佛教音樂。故有“西涼樂最為閑雅”之說。棺床刻“貝”,即佛教儀式中的法器之一。如此,進一步求證司馬金龍棺床雕刻的伎樂童子樂器演奏圖,當屬西涼樂。
在一個樂隊或樂種的結構中,主奏樂器對整體的樂隊演奏來說具有“統領性”作用。它與樂種之間的關系表現在“體系化的特征;歷時性的特征;融合性的特征”三方面。主奏樂器的不同對一個樂種的演奏者、演奏風格及地域特點等方面產生著直接影響。
將司馬金龍棺床上的一組伎樂童作為窺探北魏平城音樂樣貌的一扇窗口,力求從一個側面還原都城舊時音樂盛況。該棺床的一側以“分幅式”方式呈現了13位樂伎手持樂器的律動情景(如圖2)。這種呈現,可否屬于其社會典型樂器的“象征物”,將其刻于棺床是欲將人間所享之樂帶入另一個世界繼續使用,以顯家族之赫。或是生者賦其含義:或是墓主身前所愛,欲在另一個世界繼續擁有;或是音樂在其時有著特殊社會功能,可為墓主所奏的“安魂曲”……通常將該伎樂圖看作合奏之景。筆者猜想,這些圖像如僅僅作為北魏時期音樂符號化的“象征物”,只是將其雕刻于統一平面內,并非合奏,其亦可視為獨奏?
司馬金龍石棺床“演奏”文化學之義
平城,作為北魏“絲路”的重要起點,向西途徑盛樂、敦煌、喀什(疏勒)、塔什干等地,遠至達布哈拉;向南經晉陽(太原)、中山城、洛陽等地,到達西安(長安);向北、向東,都涉及北京(幽州)、朝陽(龍城)等地,可見,當時陸上絲綢之路的繁華。魏都平城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與各個地區聯系密切,留下諸多文化遺產,如:云岡石窟、司馬金龍和宋邵祖墓、平城明堂遺址等,皆是民族融合的實物象征,見證了人類文明在東西文化交流融合中的璀璨與輝煌。當下,“絲路文化”已成為象征一種文明的標志。平城“絲路”通達,為現代世界的和平發展提供了價值典范。
北魏石雕棺床伎樂圖“復現”了舊時音樂樣貌,使人們較直觀地對歷史上所存樂象有了一定認知。雖無法了解棺床圖像的旋律進行,但可從一個宏觀文化的層面去認知。司馬金龍石棺床雖僅有十三位樂伎(如圖3),亦可反映出某些歷史景象,如樂器形制與音色、樂的功能、社會作用以及樂與時代的關系。
此合奏流行于北魏時期的中原漢族、草原鮮卑族等活動場域,受到多族民眾的喜愛,反映了當時人們對于音樂欣賞的聽覺與視覺的接受范圍、社會風俗及音樂審美追求。音樂在官與民之間共享,有“通上達下”之作用。孝文帝在經濟、政治上進行漢化改革,文化中同樣出現漢化景象。官民共享的音聲效果,為平城營造了一種祥和的“樂舞風情”,當是官方之樂。通過棺床樂器圖像的探究,文物與文獻相互印證,還原司馬金龍生前的音樂活態場景,或許會對其他學科研究1500余年前的鮮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提供一些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作者單位:河北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