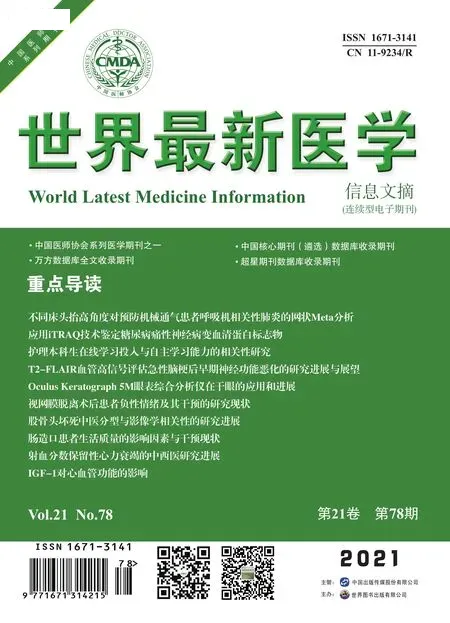心臟死亡器官捐獻供腎質量的研究進展
帕合努爾·孜亞丁,劉澤惠,桑曉紅
(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腎臟病中心,新疆 烏魯木齊 830000)
0 引言
目前,全世界大約有超過300萬人正在接受腎衰竭治療,預計截至2035年,這一數字將增加超過500萬人[1]。慢性腎臟病發展并嚴重化的最終表現是終末期腎臟病(ESRD),發病率較高,為十萬分之一,至今為止,最有效的治療方法為腎移植[2],相比于血液透析,腎移植具有更好的經濟效益[3],且可明顯患者的生活質量[4]。我國,等待腎移植的人有25472人,中位等候時間為17.5個月,大多數等待腎移植的患者已開始透析治療,其間151名患者從等候名單中移出,88.7%的患者接受腎移植手術[5]。根據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7月6日,我國已累計實現器官捐獻35030例,捐獻器官103923個,捐獻志愿登記人數為3557022人[6]。世衛組織估計,每年大約進行12萬例器官移植;然而,這一移植數量只能解決全球每年10%的移植需求。因此,如何擴大器官來源,解決器官短缺,以及如何正確的評估來自死者的腎臟是當務之急。
1 心臟死亡器官捐獻腎移植的發展及潛能
早在1954年美國醫師Merrill成功實施了首例活體親屬腎移植手術,我國自1960年在吳階平院士的帶領下實施了首例人體腎臟移植。近年,我國器官移植的來源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自2015年1月,中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donation after citizen-death,DCD)已成為我國在親屬活體器官捐獻以外的唯一合法的器官來源。DCD也被稱為無心跳捐獻(no heart beating donation,NHBD),是指根據血液循環標準,對判定為死亡的患者實施的器官捐獻,按發生心臟驟停的臨床情況從而分為可控型(cDCD)和不可控制型(uDCD)兩大類。DCD最常被重癥監護室和急診室考慮。循環系統死亡后可控型(DCD)是指患者應用機械輔助極大程度的來維持生命,且在撤離機械支持后很快會發生死亡的。循環系統死亡后不可控制的捐贈(uDCD)來自患者在醫院或醫院外發生不可控制的心臟驟停,這些患者在到達醫院時被視為死亡(馬斯特里赫特1類)[7]或“復蘇失敗”(馬斯特里赫特2類)。還有一部分的DCD是在獲取器官前患者已經診斷為了腦死亡并突發心臟驟停(馬斯特里赫特Ⅳ類)。在全世界每年5500萬人死亡中,因心血管和呼吸系統疾病導致的死亡人數超過2000萬,理論上這些疾病是DCD的重要來源,此外每年發生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數也在上升中,這極大的擴大了捐贈池,且可能為許多患者和家庭提供捐贈途徑,以及解決器官持續短缺的問題[6]。
2 DCD腎移植的優缺點
在過去的幾年中,由于擴大捐贈池的必要性,DCD的利用率有所提高,除了DGF和感染性并發癥的發生率較高和患者生存率較低外,這種移植保證了移植功能方面的良好結果[8]。且DCD供體在術前已完善相關的檢查,能夠較好的避免傳染病及移植禁忌證,保障了移植腎的安全性。一些國內移植中心的數據,顯示出親屬腎移植并沒有在腎功能方面表現出特別的優勢。最近的文獻表明,在長期的隨訪過程中,DCD腎移植受者與親屬活體腎移植受者的遠期預后并無明顯的差別。另一方面,DCD捐贈通常是一個不確定的過程,丟棄率高。盡管每年的捐獻人數在上升,但是整體數量仍較少,不能夠滿足大需求。DCD供體在搶救過程中可能出現低血壓休克、低氧血癥、失血性休克等情況,致使供體腎臟可能會出現急性腎損傷。嚴重感染是DCD移植后早期的一個挑戰。且多項研究表明DCD腎移植除有較高的DGF發生率外,急性排斥率也較高,重癥監護病房(ICU)供體感染時間長,受者免疫抑制狀況差,是嚴重感染的主要原因。有研究表明,除了受者的危險因素外,捐贈者的質量,與腎臟損傷的短期和長期預后相關,也是一定程度上決定著腎移植后存活率及并發癥的重要因素[9]。
3 DCD供腎質量評估
據先前報道,接受DCD供腎的患者也有更高的風險發生并發癥,包括腎功能不全。有多項研究表面,除了受者的危險因素外,供體質量也是決定腎損傷長期預后的重要因素。供體匹配度、供體高肌酐和供體死因、高血壓和糖尿病等慢性損害腎臟病史、年齡、冷-熱缺血時間、留置導尿管天數、及重癥監護病房(ICU)住院時間、腎移植術后原發性移植無腎功能(Primary graft nonfunction,PNF))和移植腎功能延遲恢復(DGF)是目前較為公認的DCD供腎評估危險因素,與腎移植術后并發癥和死亡率密切相關。供體高血壓、糖尿病、供體高肌酐和腦血管意外死亡可能增加DGF和移植物丟失的風險[10]。一般認為DCD移植與原發性無功能(PNF)和延遲性移植物功能(DGF)的高風險相關。
3.1 供受體的移植免疫學評估
腎臟移植被認為是同種異體移植,因為器官來自同一物種,但不同的基因組成,因此移植物被認為是“外來的”[11]。因此,我們需要在術前需要選擇相容的供體來降低排斥反應的發生率。匹配有兩種類型,血型匹配和組織相容性匹配(HLA分型)。血型主要有四種A型、B型、O型、AB型,O型被認為是萬能供者,因其不具備A型或B型的抗原,則會對這兩種抗原都會產生免疫反應,因此,O型血患者只能接受O型血的器官捐贈。AB型被認為是普遍接受者,因為AB型同時具有兩種抗原,A型會產生針對B的免疫反應,反之亦然。組織分型中主要關注的分子是MHC分子,然而由于MHC的多基因性和多態性,匹配難度很大[12]。因此在匹配中更關注的是盡可能匹配HLA-A.HLA-B和HLA-DR[13],且研究表明HLA匹配時,移植物存活率提高20%。[14]因此供體越相容,移植物的存活率越高。
3.2 供體年齡
供體年齡的增加是影響腎移植存活率的一個重要因素。供者選擇年齡在比較研究中,包括來自國家和大型中心數據庫的數據,對DCD腎移植進行多變量風險分析,供者年齡是PNF、DGF、移植后1年肌酐清除率和移植物存活率的獨立風險因素,與40歲或40歲以下的供者相比,60歲或60歲以上的供者進行DCD腎移植時,移植失敗率更高,可能增加一倍以上[15]。當考慮供者年齡對移植結果的影響時,重要的是要注意,登記分析可能包括一個選擇偏差,因為年齡較大的供者腎可能只會在其他方面被認為具有特殊品質時被選擇移植[16]。與移植結果獨立相關的其他供體因素包括高血壓病史和供體死前血清肌酐,盡管這些變量的關聯強度遠小于供體年齡。雖然老年供者移植腎的存活時間比年輕供者短,但對于年齡大于60歲的患者,接受年齡較大的ECD供腎移植與為等待SCD供腎而繼續透析的患者相比,相對生存獲益已被證實[17],且有助于提高生存質量并節約醫療成本。
3.3 腎臟缺血損傷
根據《中國移植器官保護專家共識(2016版)》,腎移植后的效果在供腎熱缺血時間>20min時明顯下降,而供腎可接受的最長熱缺血時間為60min,體外保存期間的冷缺血損傷不應超過24h[18]。多項研究證實了冷缺血時間的延長會明顯影響腎移植預后。有一項團隊對4680例DCD腎移植術中熱缺血時間進行了統計分析,得出了熱缺血時間為20-40min更有助于腎功能的恢復。另一項表明了17例腎移植冷缺血時間超過24h甚至30h都會使移植腎功能延遲恢復(DGF)發生率大幅升高[19]。小樣本研究發現2例DGF腎臟的冷缺血時間為(18.6±1.6)h,顯著長于非DGF組腎臟(10.8±4.1)h[20]。一項法國團隊回顧性分析了3898例腎移植患者,得出冷缺血時間每延長1h移植腎丟失率把都會成比例增加,經過30h冷缺血的腎臟移植后丟失率比6h冷缺血高出近40%的結論[21]。與熱缺血時間比較而言,冷缺血時間是相對來說比較可以控制的,所以在圍手術期提高腎移植手術的成功率的辦法是應該盡量的縮短冷缺血時間。
4 問題與展望
供腎的短缺使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增加,然而DCD的巨大潛力尚未實現,DCD不僅可以增加器官移植的可獲得性,還可以為更多的患者提供捐贈的機會。成功實施DCD計劃的國家主要通過建立國家道德、專業和法律框架來解決DCD途徑所有方面的公共和專業問題。穩健的DCD計劃在對其他捐贈類型的比率影響最小的情況下增加了捐贈池[22]。如果要使器官短缺甚至部分地與持續的需求相協調,未來的死亡捐獻必須包括DCD和離體器官修復。然而,即使是標準的DCD項目的大規模擴展也無法解決全球器官供應不足的問題,且供腎質量與腎移植預后密切相關,這推動了對提高器官質量和防止不必要地丟棄DCD器官方法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