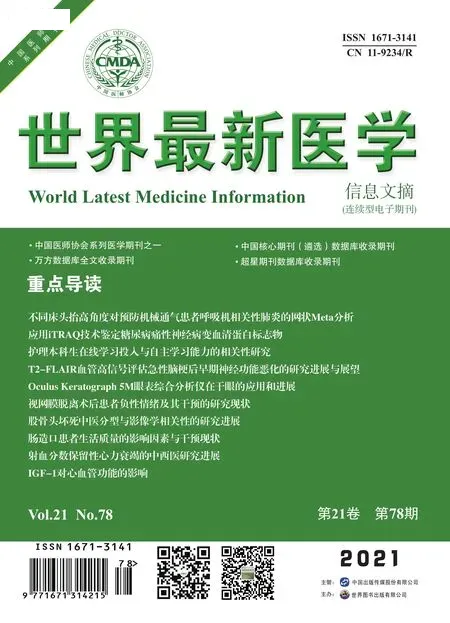惡性腫瘤相關急性腎損傷的研究進展
邱艷梅,李瑩
(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重慶 404100)
0 引言
惡性腫瘤是全球第二大死因,僅次于心血管疾病,在2017年估計有960萬人死于各種形式的惡性腫瘤,隨著腫瘤的早期篩查診斷及治療方面的不斷發展,腫瘤患者的生存期延長,腫瘤相關AKI的發也逐漸呈上升趨勢,影響腫瘤患者的生存及預后,因此早期識別AKI、明確相關病因及早期干預對改善腫瘤患者的預后十分重要。
1 流行病學
AKI是惡性腫瘤本身或其治療過程中的一種常見并發癥,其發病率隨AKI的診斷標準、腫瘤類型及分期不同而具有較大差異。丹麥的一項研究隨訪了37267個新診斷為惡性腫瘤患者的1年和5年AKI的發病率分別為17.5%和27%,其中1年內發生AKI(較基線值升高50%)風險最高的惡性腫瘤為腎癌(44.0%),其次為肝癌(33.0%)或多發性骨髓瘤(31.8%)[1]。美國德州安德森癌癥中心對2006年收治3558名癌癥患者采用改良RIFLE(Risk、Injury、Failure、Loss、ESRD)標準,發現12%的住院患者有AKI,其中Risk(危險)、Injury(損傷)、Failure(衰竭)的發生率分別為68%、21%和11%,4%的患者需要透析[2]。一項在中國25家綜合醫院和兒童醫院進行的全國性隊列研究發現AKI(KDIGO標準)的總發病率為7.5%,發病率最高的三種腫瘤類型是膀胱癌、白血病和淋巴瘤,AKI組住院死亡率(12%)高于無AKI組(0.9%)[3]。大量的研究表明嚴重的AKI與住院死亡風險、住院時間延長和每日費用增加有關[2-5],需要腎臟替代治療的危重腫瘤患者的28天死亡率高達66%-88%。存在以下情況的惡性腫瘤患者會有較高的AKI風險,如病情危重、接受造血干細胞移植、腎細胞癌切除術后以及因淋巴瘤或急性白血病行誘導化療的患者。
2 腫瘤相關AKI的診斷
關于AKI的診斷標準眾多,比較公認的是2004年的RIFLE標準、2007年的AKIN網絡標準和2012年的KDIGO標準,所有這些分類標準都僅僅依賴于腎功能指標(肌酐和尿量),而血清肌酐是腎損傷相對晚期的標志物,因此在AKI診斷的敏感性和特異性方面有局限性。新的尿液生物學標志物可能對AKI的早期診斷方面更加敏感,如胱抑素C、中性粒細胞明膠酶相關脂蛋白(NGAL)、白細胞介素-18(IL-18)、腎損傷分子-1(KIM-1)、肝臟型脂肪酸結合蛋白(L-FABP)等,但這些新型生物學標志物對腫瘤患者AKI的預測價值還需進一步研究。
3 多發性骨髓瘤與AKI
血液系統惡性腫瘤發生AKI常見于多發性骨髓瘤(MM)、淋巴瘤和白血病。大約有50%MM患者會在病程的某一階段發生AKI[6],部分病人以急性腎衰竭起病。MM患者發生AKI的常見原因有輕鏈管型腎病、輕鏈相關近端腎小管損傷、輕鏈沉積病、輕鏈淀粉樣變性、電解質紊亂以及其他因素,如膿毒血癥、容量不足、腎毒性藥物使用等。在尸檢或活檢研究中,輕鏈管型腎病是多發性骨髓瘤腎臟受累患者中最常見的原因,可占33%-60%以上,其機制為血清游離輕鏈(FLCs)經腎小球濾過后與腎遠曲小管和集合管上的T-H蛋白(Tamm-Horsfall protein)結合,形成不溶性管型阻塞管腔,從而形成局部炎癥導致腎小管損傷。另外血清FLCs在近端腎小管細胞中被megalin和cubilin受體系統內吞,FLCs的溶酶體降解可以激活NF-KB通路,從而產生炎性因子及活性氧導致腎小管損傷及纖維化[7-8]。AKI的發生與MM患者預后不良相關,有研究顯示MM診斷時血漿肌酐濃度正常的患者的中位總生存期為36個月,而中度和重度腎功能衰竭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分別為18個月和13個月[9]。因此早期識別及干預十分重要,對于存在AKI高危因素的MM患者應密切監測,避免AKI的發生,以急性腎衰竭起病的患者懷疑MM時應盡快完善血清游離輕鏈檢測以及血清和尿液蛋白電泳,必要時行腎臟活檢明確診斷。管型腎病治療最重要的是快速降低血清游離輕鏈水平,沙利度胺、來那度胺、硼替佐米和卡非佐米等藥物可通過不同的方法快速降低FLCs濃度,硼替佐米是首個治療MM的蛋白酶體抑制劑,研究已經顯示硼替佐米可改善腎衰竭骨髓瘤患者的腎功能及生存率[10]。高截留量血液透析是一種可以體外清除血清FLCs的方法,與普通血液透析膜相比膜孔徑更大,更利于血清FLCs的祛除,但尚未明確其在改善腎臟預后方面的作用。
4 造影劑與AKI
惡性腫瘤患者在病程中經常行增強CT檢查來明確疾病的診斷、分期以及評估療效,近年來隨著惡性腫瘤患者的生存期的延長,在隨訪過程中,也逐漸發現腫瘤患者的各種急慢性腎臟病,而其中造影劑相關急性腎損傷(Contrast-induced acute kidney injury,CI-AKI)值得關注,由于常常不能判斷造影劑與AKI的直接因果關系,歐洲泌尿生殖放射學會(ESUR)將之稱為造影劑后急性腎損傷(Post-contrast acute kidney injury,PC-AKI),被定義為血管內注射造影劑48-72h內,血清肌酐升高>0.3 mg/dL(或>26.5μmol/L)或>1.5倍基線值[11]。住院患者使用造影劑導致AKI約占所有病因的11%左右,腫瘤患者由于同時使用腎毒性藥物、抗腫瘤治療以及頻繁CT增強檢查,因此相比于非腫瘤患者使用造影劑有更高的AKI風險。Cicin等[12]報道了住院癌癥患者化療后的PC-AKI的發生率為20%,在最后一次化療后45天內接受CT增強檢查的患者中,AKI的發生率高出4.5倍(P=0.005)。Sendur等[13]發現在使用順鉑前一周內接觸造影劑的患者中,相關腎毒性的風險高于無造影劑暴露的患者2.56倍(95%CI 1.28-5.11,P=0.009)。目前造影劑所致AKI的機制并不完全清楚,可能與造影劑的直接細胞毒性以及血流動力學改變導致急性腎小管壞死有關[14]。研究表明高滲性造影劑(>1400 mOsm/kg)與低滲性(600-800 mOsm/kg)造影劑相比有更高的AKI風險[15],因此對于有AKI高危因素以及需要頻繁CT增強檢查的腫瘤患者推薦使用低滲性或等滲性非離子型造影劑。PC-AKI多數是可逆的,水化是預防PC-AKI的重要措施,目前無有效治療PC-AKI的藥物,N-乙酰半胱氨酸降低PC-AKI發生率目前仍存在爭議,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其有效性。
5 造血干細胞移植與AKI
造血干細胞移植(HSCT)已經用于治療血液系統惡性腫瘤和某些實體腫瘤,還可用于治療某些非腫瘤性疾病、遺傳性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在造血干細胞移植后,大約50%患者發生AKI,通常發生在移植后的三個月內,AKI的發生與HSCT并發癥和死亡率風險增加有關,其中發生嚴重AKI需要接受血液凈化治療患者死亡率高達80%。一項meta分析匯總了36個隊列研究總共5144名接受HSCT患者AKI和嚴重AKI(AKI 3期)的發病率分別為55.1% 和8.3%,且研究年份與AKI(P=0.12)或嚴重AKI(P=0.97)的發生率之間無顯著相關性[16]。由于AKI的定義、移植類型以及預處理方案不同,AKI的發生率存在很大的差異,波動在15%-73%[17]。Gruss等[18]對275例患者進行了回顧性分析,其中72例(26%)確診為急性腎功能衰竭(較基線肌酐值至少增加一倍以及高于177μmol/L),其中81.9%發生在第一個月內,異基因骨髓移植的患病率(36%)高于自體骨髓移植(6.5%)。Mima等[19]采用KDIGO2012定義的AKI診斷標準,發現異基因造血干細胞移植AKI的發生率為15.7%。清髓性預處理以及異體移植的AKI發病風險高于非清髓性預處理及自體移植,這與清髓預處理方案的強度更大、更容易合并感染和多器官功能衰竭以及異體移植存在的GVHD和免疫反應相關。HCT術后AKI的病因包括膿毒血癥、腎毒性藥物的使用、肝竇阻塞綜合征(SOS)、血管性微血管病(TMA)、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等,常常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由于HSCT患者的免疫缺陷狀態易并發膿毒血癥,細胞因子和炎性介質的釋放導致血管擴張及腎血流減少,致使腎臟缺血和急性腎小管壞死。
肝竇阻塞綜合征,亦稱肝小靜脈閉塞病(VOD),是一種系統性內皮病,通常發生在HCT后的幾天或幾周,伴有難治性血小板減少、肝腫大、腹水和黃疸,可以迅速發展為多器官功能衰竭和死亡。據報道,SOS在HSCT患者的發病率波動在5%~60%[20],這與移植類型、預處理方案、SOS診斷標準不同相關,歐洲血液和骨髓移植組的一項大型前瞻性隊列研究表明同種異體SCT后發生VOD的相對風險顯著高于自體SCT[21]。SOS患者病程中幾乎都會發生一定程度的AKI,其中約50%患者發生嚴重AKI[22],同時伴有多器官功能衰竭,病死率高達80%以上[23]。SOS引起的AKI的機制仍不清楚,可能是肝竇內皮細胞損傷導致門靜脈高壓、內臟血管擴張、水鈉潴留和全身血管收縮,類似于肝腎綜合征[24],肝竇內皮細胞損傷的原因與放療、化療及某些肝毒性藥物的使用有關。SOS的肝臟病理、影像學及病理生物學標志物并無特異性,故明確診斷存在困難。SOS目前缺乏特異性治療手段,重在預防,日本的一項隨機對照試驗發現熊去氧膽酸(UDCA)對于預防HSCT后SOS具有顯著效果[25],另有meta分析顯示UDCA預防使用降低SOS死亡率、對總生存期無影響且不增加不良反應[26]。其他的藥物如肝素、抗凝血酶Ⅲ、前列腺素E1(PGE-1)、己酮可可堿的益處未經證實。輕至中度SOS以支持治療為主,如維持水電解質酸堿平衡、容量管理和維持腎臟灌注、避免使用肝毒性藥物等,必要時行血液凈化治療,去纖苷目前被推薦用于治療而非預防嚴重SOS[27]。
TMA是癌癥本身以及治療過程中的并發癥,也可以發生在HSCT術后,臨床表現為微血管病性溶血性貧血、血小板減少、神經系統表現、蛋白尿血尿及血清肌酐升高等多系統累及,腎臟在移植相關TMA(TA-TMA)中最常受累,其病理表現為腎臟及全身微血管內血栓形成伴內皮細胞腫脹壞死。Girsberger等[28]發現在HSCT后17例腎活檢結果中,最常見為治療相關的TMA(n=5),而137例尸檢的腎臟發現最常見的變化是急性腎損傷(n=55),其中血栓性微血管病有14例。HCT術后TMA與放化療、鈣調磷酸酶抑制劑(CNIs)和GVHD等多種因素導致內皮細胞損傷有關,CNIs可以促進內皮素等縮血管物質的釋放,引起腎入球小動脈的收縮,導致腎前性AKI,還通過直接細胞毒性、血小板聚集、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和血栓調節素升高以及一氧化氮減少等機制引起內皮細胞損傷,導致TMA[29]。組織活檢病理仍然是診斷TATMA的金標準,但可能在移植患者受到限制,國內指南推薦Jodele等[30]提出的診斷標準。治療包括停用或減量可能誘導TMA的藥物、治療同時存在的GVHD和感染以及控制血壓,二線治療有血漿置換、依庫利珠單抗、利妥昔單抗、去纖苷等[31]。
6 腫瘤溶解綜合征與AKI
隨著靶向、分子和生物制劑的應用,不僅提高了抗腫瘤的療效,而且增加了惡性腫瘤患者發生腫瘤溶解綜合征(TLS)的風險。TLS是一種腫瘤急癥,是由腫瘤細胞自發性或抗腫瘤治療后大量溶解,細胞內物質的快速釋放導致高尿酸血癥、高鉀血癥、高磷血癥和繼發性低鈣血癥,多發生在腫瘤負荷較重或對抗腫瘤治療敏感的血液系統惡性腫瘤,如急性白血病和侵襲性非霍奇金淋巴瘤。美國一項基于全國住院病人的數據研究發現2010年至2013年共28370名患者被診斷為TLS,其中最常見的惡性腫瘤為非霍奇金淋巴瘤(30%)、實體瘤(20%)、急性髓系白血病(19%)和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13%),住院總死亡率為21%[32]。一項回顧性研究分析了來自四個歐洲國家的722個成人和兒童的TLS發病率為5%,在發生TLS的患者中,45%發生AKI,25%需要透析[33]。尿酸、磷酸鈣結晶沉積在腎小管導致小管梗阻和小管間質炎癥,進而導致AKI,高尿酸血癥也可通過腎血管收縮、活性氧生成、炎性細胞因子釋放等途徑促進AKI的發生[34]。TLS目前沒有明確客觀的診斷標準,Cairo-Bishop定義[35]常被應用,不僅明確了TLS的實驗室和臨床診斷標準,同時包括了TLS嚴重程度的評分系統。積極水化及使用降尿酸藥物是預防TLS的重要措施,是否堿化尿液存在爭議。對于中高風險的TLS患者,治療前24h至48h積極水化治療可以增加血容量和保持腎臟灌注,同時稀釋血清電解質濃度。降尿酸治療藥物有別嘌醇、非布司他、拉布立酶,拉布立酶是一種重組尿酸氧化酶,可以迅速將尿酸氧化為可溶性尿素囊,研究顯示但應注意藥物副作用以及禁忌,如拉布立酶禁用于G6PD缺乏癥患者和孕婦或哺乳期婦女[36]。另外需要及時糾正高鉀血癥、高磷血癥等電解質紊亂,嚴重時行血液凈化治療。
7 代謝相關AKI
惡性腫瘤病程及治療過程中可能會產生多種代謝紊亂,如高鈣血癥、高鉀血癥、高尿酸血癥、高磷血癥等,而這些代謝紊亂可能導致AKI或進一步加重AKI。高鈣血癥發生在20%-30%的惡性腫瘤的患者中[37],最常見于肺癌、多發性骨髓瘤和腎細胞癌中。惡性腫瘤引起的高鈣血癥與甲狀旁腺激素相關蛋白的釋放和局部骨溶解相關,輕度高鈣血癥可能無癥狀,但嚴重高鈣血癥會導致惡心、嘔吐、多尿、昏迷、腎功能不全或衰竭,且預示著惡性腫瘤患者預后不良,大約50%的患者在30天內死亡[38]。高鈣血癥通過促進腎入球小動脈收縮、抑制遠端腎小管的鈉鉀氯共轉運體以及阻斷抗利尿激素的活性導致腎臟灌注不足和鈉水丟失[39],持續高鈣血癥會導致腎鈣質沉積,導致腎小管細胞變性壞死,從而引起AKI。積極容量復蘇、改善腎臟灌注以及降低血清鈣離子濃度是治療的關鍵,嚴重AKI的患者需要行低鈣液透析治療,抑制骨鈣釋放的藥物如雙磷酸鹽類藥物、降鈣素、以及新型藥物地諾優單抗的應用,但應注依據腎功能情況調整藥物劑量以及注意低鈣血癥并發癥的監測。高尿酸血癥和高磷血癥分別通過尿酸鹽和磷酸鹽結晶沉積腎小管,導致AKI。
8 抗腫瘤治療藥物與AKI
抗腫瘤治療藥物有傳統的化療藥物、靶向藥物及免疫治療藥物,可以導致腎血管、腎小球、腎小管間質的損傷,引起AKI、蛋白尿、高血壓、腎病綜合征、孤立性腎小管疾病以及慢性腎臟病。
8.1 傳統的化療藥物
許多化療藥物具有潛在腎毒性,但并非所有病人應用腎毒性化療藥物都會發生AKI,容量不足、腎功能不全、尿路梗阻、同時應用非甾體類抗炎藥或造影劑是發生AKI的高危因素。傳統的化療藥物有烷化劑、抗代謝藥物、鉑類藥物、抗腫瘤抗生素等,順鉑、異環磷酰胺、培美曲塞、唑來膦酸等藥物可以通過各種途徑轉運入腎小管細胞內,通過誘導線粒體損傷、氧化應激和激活細胞內凋亡信號通路,從而導致直接的細胞毒性,引起急性腎小管損傷或壞死[40]。大劑量甲氨蝶呤(MTX≥500mg/m2)的腎毒性在于它本身或其代謝產物經腎小球濾過且由腎小管分泌到管腔,在遠端腎小管中沉淀,形成結晶導致腎小管阻塞,進而導致AKI,容量不足以及酸性尿會增加AKI的風險,因此積極補充血容量、堿化尿液以及亞葉酸鈣解救是預防AKI的常規措施,MTX引起腎功能障礙后會導致MTX的清除延遲和血漿濃度升高,從而導致全身毒性。谷匹卡酶可以將甲氨蝶呤迅速代謝為無活性的代謝產物,防止甲氨蝶呤的全身毒性,2012年被FDA批準用于AKI所致的MTX清除延遲的毒性甲氨蝶呤水平(>1μM)[41]。由于在血清中甲氨蝶呤約50%與血清白蛋白結合,所以普通血液透析清除MTX效果欠佳,而有研究顯示高截留量血液透析可以降低血漿甲氨蝶呤濃度[42-43],但其局限性在于血漿MTX濃度的反彈和出血、血小板減少等相關并發癥的風險,且其腎臟的短期及長期獲益尚需要大量隨機對照研究證實。
8.2 靶向藥物
與傳統的化療藥物相比,靶向藥物提高了腫瘤患者的生存率,但很多藥物也因此引起顯著的腎臟并發癥。以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或其受體(VEGFR)為靶點的抗血管生成治療已被證明在多種癌癥的治療中有效,VEGF在血管生成以及內皮細胞增殖方面有重要作用,而這也正是抗VEGF藥物的副作用所在之處,抗血管生成靶向藥常常引起輕中度蛋白尿和高血壓,且常常是可控的,而重度蛋白尿和急性腎功能不全則相對少見。腫瘤患者抗VEGF治療發生AKI的主要腎臟病理改變為血栓性微血管病,其他腎小球病變和間質性腎炎的發生率較低,多項研究報道了貝伐珠單抗治療惡性腫瘤患者后出現高血壓和腎病綜合征,腎臟病理提示血栓性微血管疾病[44-48],而在大多數病例中停用藥物后腎功能可以恢復。其他的靶向藥物如酪氨酸激酶抑制劑、BRAF抑制劑、ALK抑制劑等常常引起急性間質性腎炎和急性腎小管損傷[49]。
8.3 免疫治療
腫瘤的免疫治療主要包括非特異性免疫刺激、過繼免疫細胞治療、腫瘤疫苗、嵌合抗原受體修飾的T細胞(chimericantigenreceptorT,CAR-T)治療和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是目前主要的免疫治療方法,美國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準治療的ICIs主要針對細胞毒性T細胞相關抗原4(CTL-4)和程序性死亡受體(PD-1)及其配體PD-L1,已經成為部分實體腫瘤及血液系統惡性腫瘤的一線治療方案,但其免疫相關不良事件也逐漸成為關注重點。常見的免疫相關不良事件主要發生在皮膚、胃腸道、呼吸系統、內分泌系統等,免疫相關腎損傷則相對少見。一項研究分析3695個接受ICIs治療的患者中,AKI的總體發病率為2.2%,嚴重AKI的發病率為0.6%,其中接受易普利單抗和納武單抗聯合治療的患者AKI的發生率(4.9%)高于接受分別接受易普利單抗(2.0%)、納武單抗(1.9%)或培布珠單抗(1.4%)單藥治療的患者(P<0.01),13例腎活檢結果中最常見的腎臟病理改變為急性腎小管間質性腎炎(12例),1例為血栓性微血管疾病[50]。目前ICIs致AKI的作用機制尚不清楚,推測ICIs可以引起針對腎小管細胞表面潛在抗原的自身免疫反應,從而導致急性腎小管間質性腎炎[51]。嚴重AKI需要停止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及使用糖皮質激素,必要時腎臟替代治療,部分患者腎功可完全恢復。
CAR-T細胞免疫療法是將宿主的T細胞在體外經過基因改造構建能夠表達識別并結合腫瘤細胞相關抗原的受體,從而達到識別靶抗原殺傷靶細胞的作用。細胞因子釋放綜合征(CRS)、神經系統損傷、TLS等是CAR-T治療的常見并發癥。CAR-T細胞治療AKI的發生率約波動在5%-33%[52],CRS及TLS均會引起AKI,其機制可能為腎前性灌注不足以及大量炎性細胞因子釋放導致腎小管壞死[53]。
9 總結
綜上所述,惡性腫瘤相關AKI的發病率、死亡率高,影響腫瘤患者的生存,需要我們關注高危人群,正確評估腎功能狀態,及早識別腫瘤患者AKI的病因,選擇合理的預防及治療方案,對于改善腫瘤患者的長期預后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