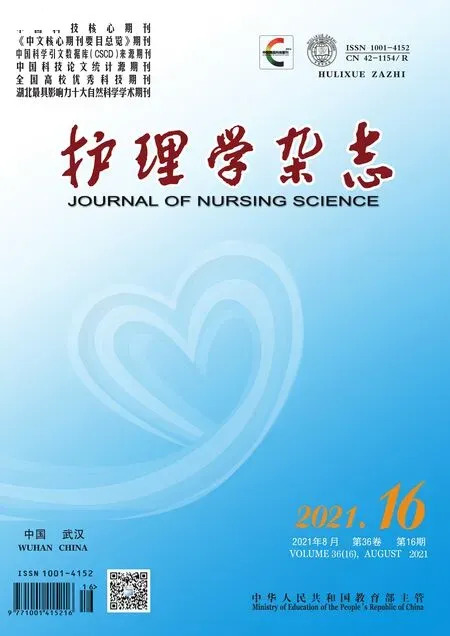癌癥患兒代理人決策沖突的研究進展
邵舒穎,李桃,劉衛娟
近年來,兒童腫瘤發病率呈上升趨勢,全球每年約新增30萬例,癌癥已成為目前兒童死亡的第一大病因[1]。近年醫療技術水平的提高和治療方案的改良在提升兒童癌癥治愈率的同時,也對醫療決策提出了新的挑戰[2]。父母通常作為患兒的代理決策者做出選擇[3],當對某個醫療決策感到猶豫時代表可能出現了決策沖突。決策沖突(Decisional Conflict)最初于1977年由Janis等[4]提出,指當個人在面臨存在潛在風險、可能導致后悔或對個人生活價值觀存在挑戰的多種選擇時的不確定性,而這種不確定性會增加患者或決策者心理和生理并發癥發生的風險。代理人決策沖突(Surrogate Decisional Conflict)是指當患者罹患破壞交流能力的疾病或尚未具備獨立做出醫療決策的能力時,其決策代理人在面對存在潛在風險或對個人價值觀存在挑戰的選擇時的不確定狀態。研究表明臨床上具有重大決策沖突的患兒決策代理人的決策后悔水平更高[5]、對臨床治療的配合度更低[6]。本文綜述癌癥患兒代理人決策沖突的研究現狀及影響因素,并指出相關領域研究及實踐努力方向,以期為促進兒童期癌癥決策支持系統發展提供參考。
1 代理人決策沖突的分類
1.1成人科代理人決策沖突 當成人患者因癡呆癥、精神疾病等導致個人決策能力受損時,基于監護者決策最接近患者真實意愿的預設,人們普遍認同監護人在醫療決策中代理身份的合法性[7]。研究表明,在成人科代理決策模式下,決策沖突的發生率為自我決策的2~3倍[8]。
1.2兒科代理人決策沖突 與成人科代理決策不同,多名家庭成員的共同參與使兒科的決策工作變得更為復雜[9]。尤其在患兒癌癥治療過程中,父母除了承擔子女罹患嚴重疾病的巨大打擊之外,還需要承擔患兒照顧任務以及巨額的治療費用,因此更難在照料者與其他社會角色之間保持平衡,從而極大地影響其代理決策水平[10]。
2 代理人決策沖突測量工具
目前臨床主要的測量工具為決策沖突量表(Decisional Conflict Scale, DCS)[11],其在替代決策者人群中的有效性已得到驗證[12],歐美地區兒童癌癥代理人決策沖突研究大多直接使用DCS作為評估工具,但其各維度條目數較少,所測得結果僅表示決策沖突程度,對決策需求深入解釋不足。考慮到我國兒童決策代理人這一群體決策模式的特殊性,在調查我國癌癥患兒代理人決策沖突水平時除了對DCS進行本土化以外,還應結合家庭功能量表、決策后悔量表、焦慮量表等工具對決策沖突來源進行全面分析。
3 代理人決策沖突水平與不良后果
美國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三成的父母在選擇治療方案時經歷了高水平決策沖突[13],兒科決策代理人DCS得分(平均30.2)與成人(平均32.8)無明顯差異[14],可推斷癌癥患兒代理人和成人患者決策沖突后果存在共同點。研究表現,對于患方而言,高水平的決策沖突會導致決策后悔、決策后焦慮和抑郁、降低醫療滿意度并影響醫患共同決策的開展[13,15]。對于治療而言,高水平決策沖突所導致的決策延遲將阻礙治療方案的早期實施,對其治療結果造成負面影響[13,15]。此外,當發生由醫療活動所致損害時,患方起訴醫療機構的可能性隨著決策沖突水平的升高而增加。盡管目前決策沖突領域很受重視,但尚無有關癌癥患兒代理人決策沖突導致身心不良后果的深入研究報告。
4 癌癥患兒代理人決策沖突的影響因素
為避免高水平決策沖突對決策質量帶來的負面影響,確定決策沖突的影響因素對制訂針對性的決策支持系統有重要意義,根據目前研究結果可將兒童癌癥代理人決策沖突影響因素整理為以下4個方面。
4.1信息獲取量 研究表明,醫療相關信息獲取的滿意度是決策沖突的最佳預測指標[16]。醫療知識的增加可降低決策不確定性,從而減少決策沖突發生率,而信息不足會導致情緒波動及疾病應對方式的改變[17]。多數癌癥患兒的父母將臨床醫生視為最可靠的信息來源,并希望獲得盡可能多的有關診斷及治療方案的知識[18]。然而,每個決策者的信息需求不盡相同。研究發現與年齡較大家屬相比,年輕家屬決策者的信息需求量更大[19],而診斷早期所提供的醫療信息不足以滿足治療后期決策需求[20]。
4.2家庭功能 兒童疾病的醫療決策一般以家庭作為決策主體、由多名成員共同參與[8]。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決策模式在亞洲更為常見。家庭成員的積極參與以及協商一致有助于患方從不同角度思考問題,減輕決策壓力。同時,家庭發言人角色的指定有利于減少家庭中因無人擔任最終決策者所帶來的沖突。研究表明家庭功能與決策滿意度呈正相關[21],總體家庭功能水平較高,如善于彼此分享想法和感覺的家庭成員更愿意參與到決策過程中;而在凝聚力較弱的家庭中,參與決策的成員增多反而導致無法達成共識的情況增加。
4.3決策過程的參與度 研究表明,積極參與決策制定過程的父母所經歷的決策沖突水平較低[22]。與認為自己無權做出醫療決策的家屬相比,自覺獲得決策選擇權的父母報告了高水平的醫療信息獲取率,并認為得到了足夠的支持以做出有把握的決策[23],因而對醫療決策的滿意度更高。
4.4代理人的價值觀 當決策者無法很好地澄清自身價值觀時,多樣的治療選項將對決策造成混亂[24]。在面對孩子罹患嚴重疾病的變故時,父母對照顧者角色產生質疑,許多父母會將孩子的疾病視為自己的失誤而產生內疚感,從而導致價值觀發生改變[25],此時有些父母可能會為延長患兒生存時間而選擇給孩子帶來巨大痛苦的治療方案[26]。
5 改善癌癥患兒代理人決策沖突的措施
決策沖突問題近年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作為最早開始進行醫療決策領域研究的組織之一,加拿大渥太華決策輔助工具研究小組創建了完善的決策支持框架和共同決策(Shared Decision-Making,SDM)理論模型,已有多位學者對其在降低決策沖突中的貢獻進行綜述[14,25,27],現有兒童癌癥決策沖突的改善措施亦多基于此。根據2020年渥太華決策支持框架可將兒童癌癥決策支持分為臨床診療咨詢、決策輔助工具(Patient Decision Aids,PDA)及決策指導[28],其中診療咨詢作為決策交流的基礎已成為臨床醫患溝通的日常,而決策輔助工具及決策指導系統正在構建和逐步發展完善中。
5.1決策輔助工具 決策輔助工具通過提供基于循證的醫療信息及協助患方進行價值觀澄清,可促進共同決策并有效降低決策沖突水平[27]。Wyatt等[29]的一項Meta分析證實決策輔助工具在癌癥患兒代理人決策領域的作用,目前兒童癌癥決策輔助工具已發展出視頻、宣傳手冊、網站等多種形式供臨床使用。尤其基于互聯網技術的現代技術決策輔助系統靈活度較高,可與視頻、音頻等多媒體形式相結合。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應用網頁為兒童癌癥家屬及專業醫務人員提供的一系列決策輔助工具,為癌癥兒童代理人決策提供了醫療信息及技巧性的幫助。
5.2決策指導 決策指導包括評估影響患者決策沖突的因素,提供滿足決策需求的支持,監測決策進度以及篩選影響實施的因素,通常由“決策教練”如受過專業培訓執業醫生、護士提供。決策指導通過面對面或電話進行輔導,可單獨或結合決策輔助工具使用以增加患方決策相關知識、提高決策滿意度。現有研究表明決策指導過程中父母雙方及患兒均在場可提高該決策支持的有效性。但與單獨使用決策輔助工具結果相比,輔以決策指導對決策結果并無明顯改善作用[30]。有關決策指導指南與決策教練的培訓規范化等為目前研究的重點。
6 展望
目前我國兒童癌癥代理人決策沖突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在借鑒部分歐美國家決策支持系統發展經驗的同時,應加快探索我國癌癥兒童代理人決策需求與影響因素研究,結合國情開展決策輔助系統的應用性研究,以推動共同決策模式在國內的落實,降低癌癥患兒代理人決策沖突水平。
6.1深入探討我國文化背景下癌癥患兒代理人決策沖突水平 與患者自主決策不同,代理人決策沖突與家庭結構與功能、代理人家庭角色等因素息息相關。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強調家庭作用的儒家文化為主體,家庭式決策模式使家庭內部偏好不一致對決策沖突影響較西方國家更大[31],因此國外相關研究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國國情下癌癥患兒代理人決策沖突狀況。未來研究應從癌癥患兒代理人決策沖突的影響因素出發,研發適用于我國的特異性代理人決策測評工具,深入探討癌癥患兒代理人的決策需求、困境、水平以及家庭功能等。
6.2基于決策支持框架,發展適合我國的兒童癌癥決策輔助體系 目前國外基于決策支持框架與理論發展了系列改善決策沖突的措施,而國內目前對兒童癌癥決策的研究還是空白,缺乏結合我國兒童癌癥狀況的決策支持體系,如共同決策的引進、決策團隊的構建、決策輔助工具的研發等。目前決策團隊多僅包括醫患(代理人)雙方,研究表明護士參與共同決策對于改善醫療決策質量有重要意義[32],未來可借鑒國外跨專業共享決策模型以及“決策教練”的概念,建立包括護士在內的多學科決策團隊。此外,從我國癌癥患兒代理人需求出發,研發適合我國兒童癌癥治療決策的決策輔助工具刻不容緩。
6.3探討在我國兒童癌癥治療領域引入共同決策模式的可能性 目前,部分國家的共同決策開展已得到法律及衛生政策支持,而現階段我國共同決策還處于初步探索階段,醫患對共同決策的認知和關注度有待提高,相關政策支持仍亟待完善。我國兒童癌癥領域共同決策臨床落實的難點在于對患兒是否可加入決策團隊的界定以及家庭多成員參與共同決策時權利與責任主體的判定。研究表明決策輔助工具可以引導共同決策的臨床實踐,尤其是對兒科的決策指導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33]。未來應基于兒童癌癥臨床實踐經驗對共同決策的本土化進行系統研究,探索出適應我國國情的完善的共同決策模式。
6.4進一步探究兒童治療決策參與度與能力 目前從法律角度患兒醫療自主權由其家屬全權替代行使[34]。然而兒童癌癥治療周期較長,隨著年齡的增長,患兒認知力不斷地變化和發展,對疾病相關醫療信息理解力增強并逐漸具有決策能力[35]。此外,兒童在醫療決策中的參與范圍是否需要有所限定亦值得進一步的探究。綜上,在臨床實踐中需對患兒的決策能力進行規范化評估,以避免將復雜的醫療決策強加于無法做出決策的兒童或剝奪希望參與決策且有能力的兒童的醫療自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