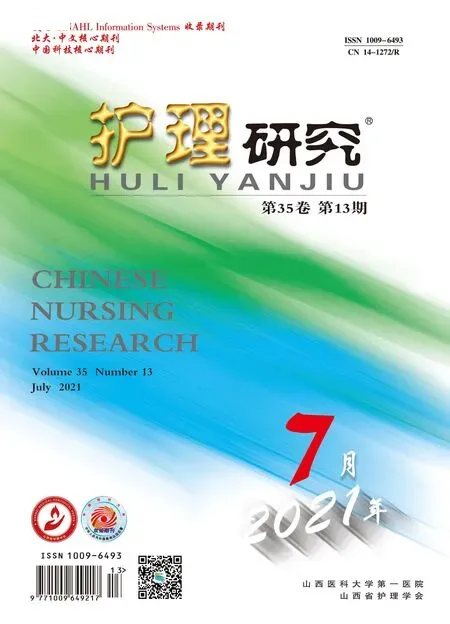同伴支持在截肢病人康復中的應用進展
袁 穎 1,李素云 1,張春麗 2,張小梅 3,張 艷 1,匡玉蘇 1,婁湘紅
1.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湖北 430022;2.黃岡市中心醫院;3.武漢市精神衛生中心
當受傷或病變的肢體感染嚴重甚至危及生命時,截肢成為挽救生命的必要措施。在美國每年估計有1.8萬人截肢,其中82%為血管性疾病,預計到2050年,美國截肢人數將增加到360萬人[1?2]。2018年,數據顯示,中國肢體殘疾者近3 000萬人,占總體殘疾人數的1/3[3]。截肢將會導致永久性殘疾,會影響病人心理、自尊、社交和生活質量,病人在文化上和社會上可能會受到很大的排斥[4]。支持性心理和社會干預,如正規的支持小組和同伴支持網絡,可成為截肢病人常規護理強有力的補充[5?6]。同伴支持在護理學領域的應用日益廣泛,主要集中于對慢性病(如糖尿病)、腫瘤、艾滋病病人的康復護理及母嬰健康項目(如母乳喂養、營養和產后抑郁癥)的研究[7?9],而對外科疾病的同伴支持研究相對較少。現通過對同伴支持在截肢病人康復中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探討促進截肢病人健康功能狀態更好的護理方法,以期為截肢病人制定更科學、合理的同伴支持方案提供參考。
1 同伴支持的相關概念及應用
同伴支持是一種以康復為導向,以病人為中心的社會支持方法[10],是指具有相似經驗或人口學特征(性別、年齡、生活環境、社會地位等)的個體在一起就某個主題互相分享、交流,從而得到相關的觀念、信息、情感或行為技能[11?12]。同伴支持包含支持者和被支持者兩個角色,在護理學領域,被支持者主要指患某種慢性病、腫瘤、精神疾病或處于康復期的病人,同伴支持者又稱為同伴導師,是具有與被支持者相似疾病的志愿者病人,是被支持者觀察、模仿和學習的榜樣。同伴教育和同伴支持相輔相成,截肢病人康復期的同伴支持效果大多依賴于同伴教育。同伴教育即在榜樣作用下,通過觀察同伴的角色模型來進行健康行為的練習,給受教育者一定練習空間,并不斷積極強化,最終成功習得社會行為的一個過程[13]。同伴支持在截肢病人康復中的應用可追溯到1977年的一項團體同伴支持研究,研究者觀察到,即使在同伴支持小組成員發生變化時,仍會有幾個討論主題反復出現,即抑郁、醫療問題、他人的反應、強迫依賴、個人健康責任及分享應對截肢的經驗,該項目持續時間很短,病人的反應從熱情到非常保守不等,但沒有人拒絕同伴支持,所有病人都覺得是有幫助的[7]。
2 同伴支持者的遴選標準
同伴支持者或同伴導師通常由招募、自我推薦、醫護人員直接挑選這3種形式產生[14]。Suckow等[15]研究中的截肢病人同伴支持者來自4個不同的醫療機構,招募方式是通過張貼海報或由這些機構的心血管、血管外科和康復診所工作人員親自邀請符合條件的病人,查閱所有符合條件的病人的醫療記錄,以確定截肢的適應證,然后通過私人電話邀請和發送一封電子郵件,解釋同伴支持焦點小組會議的細節、風險和好處,機構審查委員會在每個機構評估并批準這項研究。Laura等[16]則招募英國的一家國際慈善機構的參與者,該機構致力于為截肢病人提供幫助,同伴導師是該機構提供服務的成員,他們在兩年前經歷過截肢,并應慈善機構的要求向截肢病人分享他們的疾病相關知識和截肢經驗。有文獻顯示,同伴截肢病人在國內主要以網絡招募和醫護人員挑選為主[17]。
3 同伴支持者的培訓和維系
3.1 同伴支持者的培訓 同伴支持者的培訓主要涉及培訓者、培訓時間及培訓內容,國內外的培訓者角色基本都由醫療機構醫護人員擔任。May等[18]的一項關于截肢病人同伴支持的回顧性病例系列研究,對65例因腫瘤而截肢的病人開展為期30個月的同伴支持干預,該項目中同伴支持者需接受為期兩年的課程學習,方可對病人開展同伴訪問,訪問方案須經過康復理療科、骨科和腫瘤科討論和同意,訪問于術后5 d在醫院病房進行,同伴支持者分享他們的個人經驗、真誠回答病人提出的問題,并向病人演示假肢使用方法。Laura等[16]研究中的同伴導師未接受正式培訓,但慈善機構建議他們應與醫療專業人士或顧問有所區別,并反對他們直接向病人提供醫療、心理、法律或財務方面的建議。一項由香港“護理之家”同伴支持者主導的疼痛管理研究,對招募的46名同伴支持志愿者(PVs)進行培訓,讓他們領導“疼痛管理項目(PAP)”。PAP共12周,每周1 h,內容包括病人在PVs監督下進行20 min的體育鍛煉及30 min的疼痛管理教育,教育內容包括疼痛形式、影響疼痛的各種因素、藥物和非藥物疼痛管理策略,示范并讓病人展示和反饋各種非疼痛管理技術[19]。
3.2 同伴支持者的維系 關于同伴支持者的維系,尚未檢索到有關截肢康復病人的文獻介紹,但可見其他疾病關于同伴維系的報道。一項研究顯示,成功申請為艾滋病同伴支持者(經驗豐富的艾滋病毒陽性參與者)將獲得一筆小額津貼,以支持其培訓費用,且美國艾滋病衛生資源和服務管理局(HAB)向證明有經濟需要參加同伴教育培訓的參與者提供一些獎學金[20]。Paul等[21]在開展的一項通過同伴支持來預防病人自殺的干預研究中,招募的同伴支持者均為兼職,完成自殺學習課程,參加與學習相關的會議,培訓和活動時按小時支付報酬。通過發放經濟補助的形式維系同伴支持者是一項必要的舉措。為保證我國截肢康復期同伴支持者的延續性,建議醫療機構或利益相關方可對同伴支持者給予一定的經濟報酬和精神獎勵,也有利于病人出院后的延續護理。
4 截肢病人同伴支持的干預形式
4.1 小組干預形式 同伴支持小組干預形式包括面對面和在線支持(網絡支持)兩種。面對面支持小組通常是由相似經歷的組員集合在一起,根據截肢病人目前存在的某一個或多個健康問題開展針對性的行為和心理指導。Sousan等[22]研究證實,同伴之間的互動可以幫助截肢病人解決部分問題、提供信息、促進積極的情緒。Suckow等[15]開展的截肢病人面對面同伴支持項目中,同伴支持者為一個焦點小組,小組參與者包含病人、醫生及臨床其他醫務人員,由經過專業機構培訓的參與者主持,為避免參與者反應中的偏見,臨床醫護人員應避免擔任焦點小組領導,主持人根據臨床指南提出開放式的問題,這些問題涉及廣泛的生活質量領域,允許參與者自由描述他們的觀點。面對面同伴支持小組側重同伴導師和病人之間的現場互動,同伴導師在語言、動作、神態和心理活動上能更清楚地了解病人需求。
同伴在線支持干預在護理學領域應用逐漸廣泛,可彌補面對面同伴支持的不足。肢體癱瘓是脊髓損傷的常見并發癥。我國上海市靜安區殘疾人聯合會社會工作者依托“希望之家”脊髓損傷病人互助組織的優勢,為脊髓損傷病人構建同伴支持網絡,通過團體成員間的互動,促進脊髓損傷病人在交往中觀察、學習、體驗,逐漸認識自我、接納自我,另外,在線下互助組織服務的基礎上,建立“希望之家”微信群,為脊髓損傷人士提供線上交流平臺,協助其逐步建立同伴支持網絡,結果發現,病人的個人潛能、生活能力、認知能力等均得到顯著提高[17]。另有研究證明,網絡支持小組有為病人提供面對面支持所沒有的優勢,特別對于下肢截肢的女性病人,線上支持可能會彌補這些病人對夫妻性生活滿意度下降的缺陷,以提高其健康相關的生活質量[23]。
4.2 個體干預形式 個體干預包括“一對一”和“一對多”的同伴支持干預,即一個同伴支持者指導1例或多例病人,“一對一”同伴支持具有交流時間、地點和頻率均較靈活及易于協調等特點[24]。Laura等[16]的“一對一”研究中,同伴支持者可以去醫院或病人家里看望病人,或通過電話交談,同伴導師和被輔導者之間的接觸頻率是在“一對一”的基礎上協商的,因此,在訪問或接觸的次數和時間方面不存在典型的特征。Gassaway等[25]開展的“一對多”研究中,根據病人受傷程度、年齡、性別和興趣分配一名同伴導師,在住院期間和出院后90 d內,導師每周與病人們會面,向他們提供有關社區資源的信息,并向病人同伴的Facebook頁面發送了好友請求,同伴被鼓勵參加每月的同行贊助活動。
4.3 同伴支持在截肢病人康復中的應用效果
4.3.1 提高截肢病人生活質量 截肢病人的生活質量受到身體活動障礙、疼痛、負性情緒(焦慮、抑郁等)及截肢術后康復治療的影響。截肢術后的病人往往存在嚴重的焦慮、抑郁等心理狀態,在圍術期表現為精神上的痛苦和產生心理問題,對康復和未來的生活失去信心[26]。近年來,人們關注的康復焦點已從最初評估截肢后個人的適應日常功能,轉向截肢后的心理社會影響,其社會支持的重要性已得到廣泛認可[27]。Armstrong等[28]在美國的6個假肢康復中心完成了一項多層次橫斷面研究,結果顯示,307例上肢截肢病人中,超過一半的病人抑郁、創傷后應激障礙或兩者都呈陽性,其心理壓力的主要影響因素來自活動受限和疼痛干擾。Suckow等[15]對來自美國4個不同中心的嚴重缺血性下肢截肢病人開展焦點小組研究,其中88%的病人希望通過促進同伴支持來改善康復護理質量,40%的病人感覺自己的生活受到了限制,他們的抑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獨立性和社會支持。使用團體干預的同伴支持幫助截肢病人康復的已被證實是合理且有效的,護士發現對病人的社會心理需求有了更多的認識,醫生反映截肢病房的整體氣氛有所改善[7]。May等[18]的同伴支持干預內容及效果得到了截肢病人較高的評價,在出院后1~6個月后續隨訪中,92%的病人表示他們的病情明顯好轉是由于同伴支持者訪問帶來的益處。可見,同伴支持是加速截肢病人康復的重要步驟。截肢病人術后幻肢痛的發生率為50%~80%[29],而這種疼痛可能會持續半年甚至更長時間。Tse等[19]開展的由46名同伴支持志愿者主導的PAP研究證明,同伴支持者主導的PAP是可行的,可為病人帶來積極的體驗。目前,國內尚未檢索到同伴支持改善截肢病人疼痛效果的干預性研究,建議醫療管理者結合當地醫療條件集結更多的醫療和社會資源,適當借鑒外國的同伴支持干預方法,如建立社交媒體同伴支持群,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輕截肢術后病人的幻肢痛。
4.3.2 增強截肢病人自我認知和重返社會的信心 截肢會給病人自身及其家人和朋友帶來很大的壓力,病人常常對未知的事物、對未來的展望感到焦慮不安。印度的一項干預研究中,將截肢病人分為同伴團體心理干預組和常規治療組,干預組將更多的截肢病人聚集在同一醫院環境中,同伴導師分階段提供心理支持和各種應對機制,通過與其他截肢者比較之后,發現病人對肢體喪失所需要的新的身體功能模式產生了一種掌握感,一種情緒能力隨之出現,它的治療效果類似于團體治療過程,有助于截肢者適應現實生活的挑戰,重返社會[30]。Poonsiri等[31]在曼谷的5家公立醫院和泰國的假肢移動中心對424例單/雙下肢截肢的成年人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發現,近一半的病人在康復期借助假肢騎自行車,其中因外傷而截肢、有騎車經驗且收入較高的病人更傾向于騎車。由此可見,截肢病人在康復期可以借助假肢完成一些日常運動,也有利于更新自我認知。Ward等[23]對9例下肢截肢的女性病人開展的一項現象學研究發現,大部分病人身體形象的改變和自尊感給現存和潛在的社會關系及性生活帶來困難,并倡導通過讓病人配偶參與病人性康復對話,創建以性別為基礎、由同伴領導的支持小組,以解決與性幸福相關的問題,可能會提高這類病人的自我接納感和幸福感。女性截肢病人的配偶參與到同伴支持活動中對病人的康復效果仍有待干預性研究進一步證實。一項關于同伴支持干預對老年糖尿病足截肢病人自我接納水平的研究顯示,干預組病人的自我接納水平顯著高于對照組,說明同伴支持干預能夠有效改善老年糖尿病足截肢病人的自我接納水平[32]。Gassaway等[25]開展的一項隨機對照試驗中,按照脊髓損傷病人是否需要同伴支持的意愿將其分為試驗組(同伴支持組)和常規組,結果顯示,在出院后的前6個月,試驗組病人的自我效能感增長速度明顯高于對照組,且非計劃住院時間也明顯短于對照組。
4.3.3 提高同伴支持者的成就感和信心 通過與他人建立關系和聯系,同伴導師可以體驗到目標感、授權、增強的自尊、社會接納、價值和成就[19]。一項現象學研究中,對8例截肢病人同伴導師志愿者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從資料中分析和確定了兩個重要的主題:培養樂于助人的自我(提出了作為同伴導師的個人價值和意義)以及與脆弱相聯系(解決同伴病人的情感挑戰以及這些挑戰對幸福感的影響)[16]。同伴導師在明確自身角色和責任的同時,醫療或社區機構應向同伴導師提供相應的專業培訓和維系待遇,以增強他們在遇到困難時的信心。
5 小結
同伴教育已成為研究人員、管理人員和衛生服務提供者感興趣的一種日益流行的健康促進戰略,在康復護理領域已得到廣泛應用[33]。同伴支持作為一種社會支持,同時也是延續護理的一部分[34],對截肢病人身心康復也具有重要意義,可提高病人生活質量和疼痛管理水平,幫病人找回重返社會的信心,另一方面也給同伴支持者自身帶來積極體驗。這一結論在全喉切除術后病人康復效果研究中也得到證實[35]。我國康復護理發展仍處于探索階段,截肢術后病人大多在康復醫院或有專業人員指導的康復科進行康復訓練,但社區及部分醫院的病人較難得到技術上的支持[36]。我國護理領域采用的同伴支持干預主要集中于慢性病病人,對截肢術后康復期病人少有研究,國內截肢病人康復期同伴支持的干預研究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因此,提出以下建議:①多渠道招募同伴支持者,除了常規院內醫護推薦和出院電話隨訪甄選同伴導師外,亦可采用互聯網+和多媒體等網絡平臺擴大對同伴支持者的宣傳和招募。②嚴格規范同伴支持者的遴選標準,除了有相似截肢經歷、自主自愿條件以外,還需從同伴支持志愿者性格、品行或價值觀方面把關,注意保護病人隱私,以切實為截肢康復病人提供可靠的心理資源和積極引導。③加強同伴支持者的維系,從物質和精神層次鼓勵同伴支持者堅守這份職業。同伴支持者不管作為兼職人員還是全職人員,都應納入醫療系統中,享受相應的薪酬待遇,這對壯大同伴支持隊伍和制定長效的同伴支持服務計劃都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