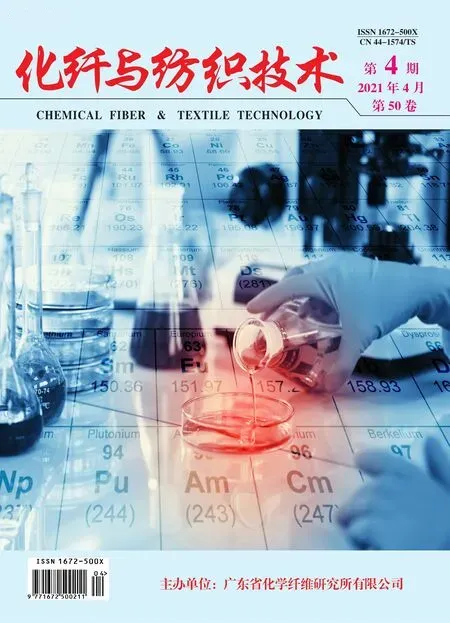“一帶一路”文化交流中民族服飾的變異與創新研究*
趙 燕
湖北美術學院時尚藝術學院,湖北 武漢 430000
絲綢之路作為世界上最早開通、勾連亞歐非三洲的交通、貿易、文化通道,沿線國家和地區之間進行著十分頻繁、密切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極大促進了中原和西域的社會發展和進步,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1]。時至今日,絲綢之路依舊發揮著重要作用,尤其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絲綢之路和“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都彼此受益,為世界經濟發展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做出了極大貢獻。可以說,從古至今,絲綢之路的“前世今生”都在中華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民族服飾作為中華文明、世界文明的一部分,由于絲綢之路的存在和發展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自張騫完成了“鑿空之舉”之后,中原和西域民族服飾就處在了演化或者變異之中[2]。期間,漢民族服飾在傳承、發展、演化當中不斷吸收大量來自西域異質文化因子,讓服飾設計、生產和用途都呈現出了不同以往的新變化。西域服飾也在借鑒中國絲綢服飾制作技術、絲綢服飾要素搭配方法的過程中,實現了服飾藝術和服飾文化的升華,既實現了東西方審美的融合,也形成了大量新的服飾元素。將這些元素與現代元素結合,一方面可以弘揚傳統文化、堅定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可以借此實現現代民族服飾的創新,為“一帶一路”的文化和貿易交流貢獻更多力量。
1 “一帶一路”與服飾文化
自秦漢時期開始,“絲綢之路”就走進了中原和西域人民的視野,先有士兵武將,后有政客商人和大量僧侶,偶爾也會有“和親”的公主與攜帶的隨從。在歷經了多年的人腳、車輪、馬蹄的“踏勘”之后,此“路”已經綿延了幾千公里,沿線經過多個國家和地區,匯集了大量的民族。在過去的兩千多年中,與古絲綢之路有關的國家、地區、民族、部落等政權更迭頻繁,社會或平穩安定或長期戰亂不減,無論何種意義上的文明交匯或者文化交流,都無法一書盡述,西方旅行者們給出的“不可思議”四字或許是最好、最恰當的形容[3]。從微觀層面看,絲綢之路從我國古時長安出發,盡管道路曲折,但是先后到達了現在中國的新疆地區、青藏高原,也橫穿了中亞、西亞腹地,甚至遠至南亞,再到希臘、羅馬等地。在此過程中,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之間交流緊密,尤以飲食、風習、服飾等為重。
1.1 “一帶一路”的絲綢服飾交流
絲綢之路作為一條最古老、最輝煌的人類“文化大運河”,在19世紀70年代被德國歷史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正式提出并一直沿用至今。(1)對絲綢的認知。由于不同國家對不同事物認知的差異,導致人們對絲綢的認知存在差異。在漢語中,絲綢指的是含蠶絲纖維織成的紡織品,在英語中,絲綢被翻譯成“silk”,指的是包括蠶絲纖維、絲線、絲綢面料、蠶絲面料制成品等在內的所有絲織物。在絲綢之路開通初期,絲綢或者“silk”就以商品和流通貨幣的形式存在,并經海、陸運輸后進行交換、行銷、加工,最終有了服飾的形態。(2)對服飾的認知。在廣義上,服飾指的是裝扮人體用到的、具體的、可見的物品的集合,無論衣服、佩戴飾品或者美容化妝等均屬此列[4]。在絲綢之路沿線上,不同國家、地區、民族之間的服飾各不相同,能夠展現出各自的物質追求、藝術審美和復雜的社會背景等。因此,絲綢服飾帶有鮮明的文化印記,在其背后隱藏著深厚的文化訴求,體現著特定區域、特定族群的社會制度與風俗習慣,甚至能夠體現當時的科技、藝術、經濟、政治等諸多問題。(3)對絲綢服飾文化交流的認知。絲綢服飾作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民族進行物質和文化交往的重要載體和媒介,在沿線政治、經濟交往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歷史上,絲綢之路沿線一直頻繁進行著絲綢服飾文化交流活動,讓中國絲綢服飾文化得以在異域傳承、發展和演化,并不斷借鑒和吸收來自西域的文化因素,讓中國絲綢服飾在形制、設計、用料、紋樣等方面均呈現了文化融合的風貌。
1.2 服飾文化與文化交融
中國絲綢和絲綢服飾歷史悠久,中國既是絲綢的發源地,也是絲綢服飾文化誕生地。在秦漢以前,江浙一帶的絲綢品種就已經極為豐富,不但花樣眾多、色彩華麗,在設計制作上也講求精巧細致,受到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人們的廣泛贊譽,一度成為“絲路貿易”的關鍵標記[5]。
服飾作為一種文化載體,歷經了不同時期、不同歷史階段的演化之后逐漸帶有了鮮明的地域性、民族性特征,服飾之間的差異也越來越明顯。比如,對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地區、民族的服飾來說,這些服飾不但具有御寒保暖的作用,還因其注重色彩、紋樣和款式的設計而彰顯出了鮮明的標識性、流行性和時代性。借助古絲綢之路這一“文化運河”,服飾文化的交融和交流一直生生不息,無論是漢民族服飾還是西域服飾,都在“互聯互通”的過程中,逐漸展現出了開放包容的姿態,不同國家、地區、民族的人們也開始以開闊的胸襟面對世界。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民族服飾一直處在變異的過程之中,這種變異不但形成了豐富多彩的服飾文化,還影響著人們的審美取向和精神追求。比如,自漢唐以來,西域服飾文化就極大影響到了漢民族文化,無論是服飾樣式還是裝飾手段,都體現了對西域服飾生產技法、配色、裝飾語言的借鑒,讓漢民族服飾得以多元化演進。
2 “一帶一路”文化交流中民族服飾的價值取向
作為一個絲綢古國、絲綢大國,中國借助絲綢之路推動民族服飾實現了實用與審美的深度結合,促進了基于服飾文化交往的中原與西域之間的文明交流[6]。在使用物品層面上,民族服飾屬于物質形態而存在,是人們生活的必需品;在使用價值層面上,民族服飾作為人類創作的設計藝術品,在文化交往和商業活動中自然而然就帶有了商品屬性。當然,由于其存在于人類社會當中,是人們生產生活不可或缺的內在訴求和外在表征,民族服飾也就成為一種社會形態而存在[7]。
2.1 承載非常多元的文化表現力
在歷朝歷代,服飾都能夠或多或少體現出特定群體、社會組織的文化主張、風俗習慣和精神訴求,并在集合了科學技術、歷史人文、經濟政治等因素之后,承載著非常多元的文化表現力。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不同民族的民族服飾,無論是在穿戴樣式、裝扮習俗還是在審美偏好、流行要素等方面,都能夠表現出當時特定的文化[8]。比如,在秦漢之際,中國民族服飾體現了十分典型的東方風格,尤其在服飾形態上,更是通過“上衣下裳”“衣裳連屬”的形式,向當時社會展現了民族服飾本身所帶有的裝飾工藝美感與身份標識功能,與地理位置上同屬“東方”的印度相較,漢民族服飾不但注重服飾的裝飾美感,更注重服飾的禮儀功能性,向外界展現著文化張力。
2.2 帶有十分鮮明的文化象征力
民族服飾是一個關聯性極強的“結合體”,它與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藝術等社會因素都存在緊密聯系。在絲綢之路文化交流中,沿線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人民在服飾裝扮方面不斷推陳出新,雖各有特色但也持續汲取外部文化和信息,其文化象征力得到了充分體現。在中國的秦漢時期,產自東南沿海的絲綢就通過古絲綢之路,由商人、僧侶、和親的公主們帶到中亞和歐洲,被制作成了民族服飾,先后被運輸到了敦煌、吐魯番以及絲綢之路沿線的其他國家和地區。在此過程中,胡錦、波斯錦等,也經過絲綢之路上的敦煌、吐魯番等地進入中國,極大豐富了漢民族服飾的面料、樣式、款式和設計風格。這些絲綢紡織品作為當時重要的流通商品,一度成為歐洲皇室貴族極度熱衷的物品,這些源自中國的絲綢與當地的民族文化結合,被制作成極為輕薄、絲滑、閃耀和飄逸的絲綢服飾,這些服飾也因此具有了明顯的身份與財富象征性。在中國的宋元時期,民族服飾更是與西域文化融合,讓民族服飾逐漸帶有了神韻和氣理韻味,廣為當時的文人墨客所接受和推崇[9]。
2.3 具有異常深厚的文化影響力
在“一帶一路”文化交流中,中國絲綢和以絲綢為面料的民族服飾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外貿易交往中銷售距離最遠、輻射范圍最大、產生價值最高、實際獲利最豐的重要商品,一個關鍵原因在于這些服飾本身的精致華美和異常深厚的文化影響力。同時,民族服飾作為“絲綢之路”物質流通和文化交融的主要文化表征,無論其經濟價值還是文化價值都能夠在流通環節以標價的形式展現出來[10]。在古代絲綢之路上,產自我國江南地區的精美織錦,或者由此制作而成的民族服飾會經由商隊送抵中亞、西亞、北非和歐洲等地,其中的織錦會被制成精美的貴族服裝,比如意大利的羅布袍服,或者被做成中亞貴族的華麗裝扮。最終,這些服飾的實際價值遠遠超過了使用價值。此外,由于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地區和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和融合,讓原本在民族服飾技術和文化相對單一或者落后的地區,其服飾文化與藝術欣賞水平獲得了顯著提升,極大提升了民族服飾的文化影響力。
3 “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引發的民族服飾變異
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重要的文化象征與文化載體,民族服飾尤其是絲綢類民族服飾具有柔軟滑爽、光澤明亮、手感細膩等優點,在中西方貿易交往中,以高檔絲綢面料制作而成的民族服飾備受關注。對擁有者或者穿著者來說,長期被視為具有較高社會地位和擁有較多財富的象征[11]。在中原文化與西域文化交融的過程中,來自中原和西域各國的民族服飾開始在色彩設計、款式廓形等方面做出改變,渴望在各自的服飾中融入對方的要素。經過了多年的發展演變,民族服飾無論是在面料選擇還是在設計生產方面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變異”,變異后的民族服飾繼續借著“絲綢之路”流入對方國家和地區,繼續促進著中外文化交融和進步。
3.1 中原的民族服飾變異
自秦漢以來,絲綢之路的開拓就促使中原與西域之間進行著十分頻繁的生活習俗的交流,其中的文化交流更是讓中原的民族服飾出現了漸進式的變異。在民族服飾設計文化的視角上,北齊時期的中原與北方游牧民族的交往越來越廣泛,胡漢之前的民族文化融合越來越頻繁。當時,孝文帝十分推崇漢文化,在遷都洛陽以后,鮮卑族人還是身著漢服[12]。此時,西域服飾文化與漢族民族服飾文化的交流越來越頻繁,其中的漢族民族服飾更是受到了西域文化的影響。到了貞觀年間,中原人戴胡帽、著胡服的現象已經相當普遍。可以說,胡服在當時已經成了中原民族服飾的流行模式。隨著中原與西域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這種地區間的開放引發了人們思想的開放,中原民族服飾也具有了包容的態度,不斷汲取西域文化。
3.2 西域的民族服飾變異
基于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服飾文化的傳播與借鑒雖斷斷續續但一直延續,這種服飾文化的交流和以此為基礎進行的其他文化的交往對西域民族服飾文化同樣帶來了深遠影響。比如,塔吉克人的帽子與當時哈薩克人相同,絲綢和棉布與中原地區相似,甚至在維吾爾族的民族服飾中出現了刺繡元素,這是中國江南服飾的典型特征之一。如果繼續延伸絲綢之路,在當時的羅馬國(以公元5世紀為例),當地的貴族在制作帕留姆長袍時開始采用絲綢面料并進行刺繡裝飾。可以說,由于絲綢之路的存在,讓中原民族服飾文化流通到了西域各地,極大促進了中國民族服飾文化的傳播,為早期世界服裝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4 結束語
隨著“一帶一路”的不斷發展,隱藏在民族服飾中的文化符號、文明要素借助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春風”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民族服飾和與之相關的文化產業將迎來一個全新的發展時期。在這一過程中,一方面要注意規避民族服飾設計中的常見問題,防止服飾元素、款式、品種設計停留在描述性層面,無法體現獨特的文化設計理念;另一方面要注重中國元素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元素的融合,將更多、更醒目的時代精神和時代符號融入民族服裝設計當中,實現民族服裝與流行服裝的深度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