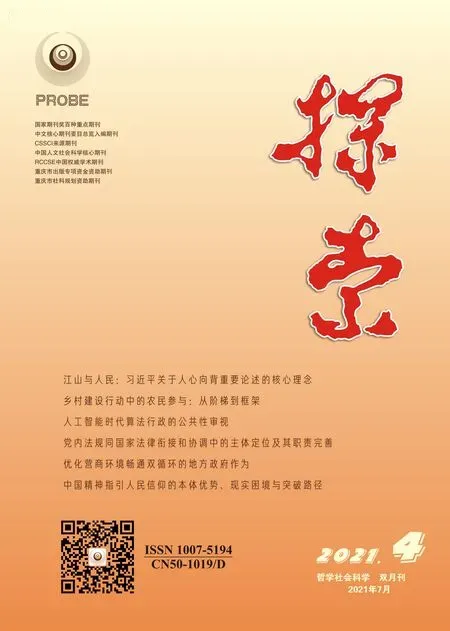中國精神指引人民信仰的本體優勢、現實困境與突破路徑
張敏娜
(西安工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陜西西安710048)
百年來,在中華民族如何增強凝聚力以抗爭困厄、博取生機、走向復興的探索中,從不缺乏開拓者的思想貢獻。20世紀20年代,魯迅就說“唯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唯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1]222。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提出“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2]30。其中的民魂就是人民信仰,中國的真進步就是國家力量、民族希望。那么,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人民信仰要如何構建?在“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2]16命題之下,中國精神怎樣為人民信仰提供精神指引,要回答三個問題:中國精神能夠指引人民信仰的依憑何在?中國精神指引人民信仰面臨怎樣的現實困境?能夠為人民信仰提供指引的中國精神應具備怎樣的義涵構造與意蘊覺解?本文試從中國精神指引人民信仰的本體優勢、現實困境和突破路徑作以探討。
1 中國精神指引人民信仰的本體優勢
中國精神作為“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統一”[3]1,可以被多維度解讀,如回到具體社會環境理解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各自不同的歷時性特質,或從縱貫歷史的人文視野考察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整合通契的共時性本質,或基于民族特征、中國特色梳理中國精神的傳承流變,以及從命運與共的世界意義、人類意義洞察中國精神的意涵生發等。但就“中國精神指引人民信仰”的視角看,邏輯起點應該是中國精神的價值功能,即中國精神因哪些本體屬性而具備指引人民信仰的效用優勢,歸結起來,有三個方面。
1.1 思想指南優勢
中國精神具有指引人民信仰的思想指南優勢,在于它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文化融合會通的精神結晶。習近平曾經以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兩種各有側重且互為支撐的精神內涵解讀過中國精神[4]235。其中,民族精神側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神,時代精神側重馬克思主義基本精神和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精神。但側重中又有融合,“民族精神雖然經歷五千多年的歷史演變,但它并不是過去的東西,我們現在理解的民族精神,注入了時代精神的成分”[5],比如開拓創新、艱苦奮斗、愛國敬業等時代精神,同樣凝結在革故鼎新、自強不息、忠義利群的傳統血脈中。正如習近平指出當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深受綿延幾千年至今的、由中國人民特質稟賦鑄就的中華文明影響,并以“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斗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偉大夢想精神”等具有鮮明時代色彩的精神氣質闡釋了中國人民的偉大民族精神[2]387-388。這一論述集中體現了時代精神與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融合度與同質性。這種同質融合在中國共產黨凝聚和領導中國人民取得翻天覆地革命、建設和改革成就中,所產生的強大精神力量,來源于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貫通融會的“核聚變”能量釋放。
“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6]1516這個“學會”之所以可能,這個轉變得以發生,靠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憑空降臨,而是馬克思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復蘇喚醒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本自具有但在特定歷史時期隱沒沉睡的精神基因。比如,馬克思主義對道義制高點的占據和對真理境界的抵達,完成了中華文化自古以來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社會理想的當代書寫;對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整體有機理論重構,完成了散見于包羅萬象中華文化中的社會進步發展思想片段的系統表達;對現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的批判性繼承吸收,完成了中華文化對天地萬物規律性認知的科學呈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也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神的理論化、體系化、現代化重張過程,也是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精神的孕育生發過程。
習近平指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科學社會主義的主張受到中國人民熱烈歡迎,并最終扎根中國大地、開花結果,絕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國傳承了幾千年的優秀歷史文化和廣大人民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融通的。”[7]正是這個融通,使馬克思主義能夠在社會、階級、生產力條件看上去都不盡具備的中國得到根深葉茂、蓬勃不息的實踐與發展,使社會主義道路和制度在中國得以確立并不斷發展完善成為必然。這個必然性從政治上看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綱領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實踐勝利,而從精神文化上看,則是充分融會滲透并潛移默化影響政治認知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母版的勝利。中國共產黨深刻把握了本民族文化傳統與馬克思主義的內在貫通,架起了二者之間血脈相連、經絡相通的橋梁,使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成果成功嫁接在了中國這棵大樹之上,“比起世界上所有的類型的‘政黨’,貌似歷史不及百年、執政不及七十載的中國共產黨其實樹大根深,擁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傳承”[8]。因此,從傳統精神與現代精神、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高度融合的思想脈絡來看,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會通而結晶的中國精神,能夠為指引人民信仰提供思想資源和方向指南。
1.2 價值導向優勢
中國精神具有指引人民信仰的價值導向優勢,在于它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精神底色。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代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凝結著全體人民共同的價值追求”[2]30,揭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國精神和人民信仰三者之間的有機聯系。中國精神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精神底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國精神的價值凝結,能夠指引全體人民共同信仰的中國精神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淬煉,包括三個方面。
其一,集中體現價值觀屬性的中國精神。價值觀是對價值導向的確認,如“對諸事物的看法和評價在心目中主次、輕重的排列次序”[9],能夠“判定事物的是非和美丑”[10],“是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對象中間……做出篩選決定的行為”[11]。人民信仰之所以需要指引,是因為陷入多元價值格局、出現價值選擇迷茫。集中體現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中國精神,之所以能指引人民信仰,是因為其能夠直面多元格局中的價值沖突并指引價值選擇。比如“只有‘小康精神’,是建設不了小康社會的”[12]就包含兩層意蘊,一是致富精神、“小康精神”已實然在社會成員的價值追求中產生著導向作用;二是僅被物質財富驅動的價值選擇不足以形成能激勵人民從小康社會走向更美好未來的人民信仰。這同時帶來兩重思考:一是當前社會成員精神世界除了受利益引導,還受哪些單極、片面的價值取向影響;二是如果多元化價值格局失之于蕪雜混亂,而單極化價值引領又必然走向偏激封閉,那么應該怎樣構建一個正確排布公與私、義與利、人與我、情與理、權與法等主次輕重關系的價值信仰格局?在中華文化精神特別是優秀傳統精神寶庫中,有俯仰皆是的價值導向及其精神本源,比如在義利價值選擇上的見利思義,在公私價值選擇上的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在人我價值選擇上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等等,這些集中體現價值觀屬性的中國精神都能夠指引人民走出價值迷沼。
其二,集中體現社會主義屬性的中國精神。中國共產黨作為具有先進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其共產主義理想信仰對于普通群眾而言,具有超越性。但中國的國家制度、政治制度、社會性質、領導力量以及全體人民為之奮斗的共同理想,都決定了堅定道路、理論、制度、文化自信的人民信仰構建,離不開具有社會主義屬性的中國精神引領:一是天下大同、立黨為公等“天下為公精神”;二是以人為本、人民當家作主、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等“人民至上精神”;三是勤勞致富、扶困助貧、先富帶動后富、消除兩極分化等“共同富裕精神”;四是愛國利群、家國天下、合作共贏等“集體主義精神”;五是實事求是、科學理性、尊重規律等“追求真理精神”。這些精神在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廣泛存在,可以直接拿來補給人民精神需求;同時也在傳統文化中深厚沉積,需要完成轉化與創生,比如“不患貧患不均”的傳統平等思想,轉化到當代中國精神中,就是“脫貧路上一個都不能少”的扶貧精神,“沒有全民小康,就沒有全面小康”的共同富裕精神。這些反映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精神境界,能夠引導人民保持對精神崇高與價值先進的認同與仰望,進而在行動上接受感召、無限趨近。而且,正如習近平強調要“以黨的優良作風帶動民風和社會風氣好轉”[13]82,中國共產黨人作為人民一員,其踐行共產主義精神的先進性表現,本身就對人民信仰構建產生著感召與引領。
其三,集中體現“核心”屬性的中國精神。對中國精神的“核心”提煉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那么怎樣理解“核心”精神?黨的十八大報告在“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中提出“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三個倡導”以及“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4]24-25后,一些理論研究和實踐推進都將“三個倡導”“24字”直接等同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或“核心價值觀”。但也有學者認為對核心價值觀的提煉不可以僅止于“24字”,如“中國精神的弘揚和培育需要簡潔明確、高度凝練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引領”[5],“‘三個倡導’仍然不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層級的最終概括,而是一個開放性的歷史性表述……應當基于這一重要表述并以此為新的起點……走向更深刻的理智思考和整合建構”[14]。這類觀點以對“以這一重要表述為新的起點”的肯定及“更深刻的理智思考和整合建構”的期待,開拓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構建的更廣闊空間。事實上,黨的十八大報告在“三個倡導”后提出的“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到今天為止都還是一個開放性命題。習近平2021年4月20日在清華大學依然提出“自覺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15],這說明核心價值觀的“樹”與“培”仍然在路上。這種“核心”提煉須堅持三個原則:一是立足價值觀范疇,不使本該具有鮮明價值導向的精神湮沒于泛泛的目標愿景、道德規范與公民操守之中,以集中發揮價值選擇的導向作用。二是立足社會主義本位,既以遠大理想為終極感召,又注重發揮共同理想的凝聚作用;既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又著力于完成傳統精神的社會主義價值轉化;既借鑒西方進步精神成果,又堅持馬克思主義對西方價值的批判與超越。三是立足“以文化人”立場,不追求宏大敘事、宏闊構建、面面俱到,但求深挖內核、觸及靈魂、直擊現實,以高度凝練、過目不忘、引人深省的表現形式,凝聚價值共識、倡導價值追求。
1.3 政治保障優勢
中國精神具有指引人民信仰的政治保障優勢,在于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實現中國夢的精神倡導。一種精神成果能不能指引一個民族、一國人民的信仰,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領導這個民族、這些人民的執政力量,對這種精神的理解深度和認同程度。一種社會意識要獲得主流地位與大眾認可,政治保障不可或缺,即必須上升為領導階級的精神訴求和意識形態,以執政者意志自上而下動員傳播。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忠誠代表并堅定維護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在帶領中國人民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歷程中,高度重視中國精神的凝聚引導作用,明確提出“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種精神是凝心聚力的興國之魂、強國之魂”[4]235。中國夢是中華民族的夢,是每個中國人的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寄托著人民對未來的期待與信念,也蘊含著中國共產黨以中國精神引領人民筑夢、追夢、圓夢的政治擔當。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精神的主要譜寫者、力行者、倡導者,必然會為中國精神指引人民信仰提供強有力的資源調集、力量動員、組織實施保障,理由有三。
其一,基于鞏固馬克思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地位的現實需要。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這是對社會主義本質論的新發展,也是制度優勢得以充分發揮的認識論前提。如果一種社會意識沒能有效轉化為全體人民的精神信仰,就不可能獲得意識形態主導地位。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理想信仰,集高尚性、純潔性、先進性于一身,而中國精神則集中融會了馬克思主義精神力量的價值追求。要確保蘊含共產黨人價值先進的精神倡導能夠在人民精神世界形成價值尊崇與價值向往,能夠對人民信仰產生積極的引領感召和示范帶動,同時也能夠為振奮人民士氣、激發人民潛能、涵養人民道德、安放人民心靈提供精神支撐,必然要發揮中國精神在指引人民信仰中的主導地位。
其二,基于以向上向善精神感召凝聚強大力量的經驗自信。正如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講到的,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弘揚“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在長期奮斗中構建起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16]。從革命與建設年代的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兩彈一星”精神、大慶精神,到改革開放時期的特區精神、奧運精神、絲路精神、抗疫精神等,在構筑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同時,也為鑄煉中國精神攢足了厚重而珍貴的精神資源,沉積了深層次與廣走向的精神富礦。從根本上看,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是當代中國精神中的紅色基因和紅色文化的源頭,是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的中國精神的先進內核和寶貴精華”[17]。中國共產黨百年黨建的成功經驗足以證明,接受向上向善精神感召所煥發出的強大意志力、戰斗力、凝聚力,是克服一切困難、戰勝一切強敵、取得一切成就的信心能力所在。已先行在精神世界探路覺醒并取得矚目成就的中國共產黨,對于中國精神指引人民信仰所能凝聚的民族復興偉大力量,充滿自信與把握。
其三,基于環境系統正向反饋政治生態的客觀要求。人民信仰是共產黨人理想信仰的外部環境和生長土壤,二者須血脈融通、連枝同氣才能共生共存。若放任封建特權等級思想和西方利己主義、資本至上價值觀的污水橫流、毒素泛濫,共產主義理想信仰的崇高性神圣性便難以伸張,黨內政治生態便難以自清獨善。因此,必須把堅定共產黨人理想信念與構建全體人民信仰密切結合,加強中國精神對人民信仰的引領,以昂揚向上的人民信仰厚培共產黨人崇高精神境界的良田沃土,營造堅定共產黨人理想信念的環境氛圍,在解決一部分黨員干部信仰迷失、理想動搖外部性問題的同時實現政治生態與社會生態之間的正向精神互動,匯聚民族復興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磅礴力量。
2 中國精神指引人民信仰的現實困境
思想指南、價值導向和政治保障優勢是中國精神指引人民信仰的應然邏輯,而指引作用的實然發生必須回到實踐。但就目前理論研究現狀來看,在推動實踐方面尚有不足:有的缺乏問題導向,陷入純理論的抽象討論;有的抱有熱切而強烈的現實關懷,但浮于對現象的感性認識;有的具有信仰構建的問題意識和回歸精神文化的方向感,但點題卻未破題,未能有效切入;有的從意識形態建設、核心價值觀培育等角度對人民信仰構建有所論及,但失之于瑣碎,缺乏集中專論。在中國精神義理構造與意蘊解讀上,還存在不適應信仰生成路徑疏浚、功能結構再造、主體差異細分等現實需求這三組矛盾。
2.1 精神梳理的條塊結構不適應信仰形成的螺旋過程
信仰作為精神生活的頂級范疇和生之為人意義價值的終極追求,其形成絕非淺層次的意識沖動和短時期的心靈寄存,而須經歷一個反復校驗的否定之否定螺旋升華過程,這個過程至少包括三個梯度遞進的境界升維階段:信仰找尋、信仰錨定、信仰堅守,非至“堅守”境界而不能稱之為信仰。
既起步于“信仰找尋”,不妨追問信仰何以“失落”。“人民有信仰”作為“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前置條件,一定程度上是對“中國人有沒有信仰”的直面與回應,其中包含兩層意蘊:一是中國人有信仰,否則無法解釋在中華民族歷史長河中弄潮逐浪的理想主義矯健姿影何以五千年不絕;二是在翻天覆地、風雨兼程、高歌猛進走向現代社會的歷程中,理想的神圣性曾經從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跌落。“現代化和市場經濟不斷放大滿足安身立命的基本約定,刺激、放任個體對物質享受的過度追求”,人們“好像得了一種‘迷心逐物’的現代病”“出現了某些‘遠離崇高’和‘信仰缺失’的精神現象”[18]46-49。正如有學者很難接受“被視為有著幾千年倫理本位傳統的中國,有著毛澤東時代幾十年理想主義強調和教育的中國,會在市場的降臨中潰敗到如此地步”,會“如此容易便被商業邏輯、商業媒體關于生活的理解與想象所穿透”[19]。無論身處喧囂的生活參與者,還是洞若觀火的社會觀察者,對于將價值王冠自理想主義頭頂打翻再轉身奉予功利主義的世態人心,都有著同樣的感知,“在這個時期里面,最具有精神象征意義的事件,莫過于‘信仰的失落’了”[20]。如果信仰的失落是一件極具精神象征意義的事件,那么信仰的找尋、重拾與回歸,也自然離不開精神之光的普照與引領。
然而遺憾的是,盡管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凝結出的精神成果已經形成了世所罕見的中國精神巨大資源,但相對于回答“為什么信”“信什么”“堅信什么”等境界漸次螺旋上升問題的人民信仰指引需求,還需要對中國精神的豐富蘊涵作兩方面的“供給側結構性”梳理:一是需要在體系結構上構建系統化、立體化的精神世界。當前中國精神的譜系歸集已相當充足完備,如時間名譜系(五四精神、二七精神等)、地名譜系(紅巖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人名譜系(白求恩精神、雷鋒精神等)、事件名譜系(抗震救災精神、抗疫精神等)等。但在這個基礎上、在條塊的縱橫貫通之間,還有必要直面人民信仰構建的階段性發展特征,從義理融會、邏輯疏通、理路勾連等方面,加強中國精神直接回應信仰找尋、錨定、堅守過程中具體困惑訴求的問題導向性、系統有機性建設,挖掘主體間性的內在張力,完成中國精神在指引人民信仰上的精神世界立體化構建。比如從“五四精神”的追求真理,到“二七精神”的英勇無畏、“抗戰精神”的大義擔當,再到“西柏坡精神”的團結奮斗之間,提煉出精神升華與力量煥發過程的完整內在邏輯,講好信仰力量的故事,回答好“為什么信”的問題,增強社會成員對信仰構建重要意義的心理認同。再比如從“井岡山精神”的依靠群眾,到“延安精神”的群眾路線,再到“雷鋒精神”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之間,梳理出“人民是創造歷史的英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等唯物史觀一脈相承、多維豐富的精神蘊涵,回答好“信什么”的問題,啟迪和引導社會成員在信仰構建中回歸以人為本立場。二是需要在哲學層面展開整全性、反思性、規律性義理整合。只有使中國精神煥發出辯證智慧光芒與永恒真理力量,才能有效消解現代化進程中的片面性、實用性、極端性、對立性思維所造成的精神危機。要通過哲學視角開展精神引導,以更好回答“我們要建設一個什么樣的國家、一個什么樣的文明,我們想成為什么樣的人的問題”[21]。要在最終極的思想境域回答最究竟的人生大問,以徹底解放陷入精神泥淖的靈魂。在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面對多元化世界與多元價值觀,精神文明建設要回答好何以抵制腐朽庸俗價值觀、何以避免信仰異化虛化等根本問題,就必須具備對立統一、執中平衡、辨證反思的科學思維和哲學思維,這也是對中國精神在哲學意義上獲得整體性、多層次、義理化融會重構的期許。這種于哲學意義上完成頂層設計的中國精神供給,能夠在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追求高品質精神生活愿望的同時,合規律性也合目的性地對人民信仰構建形成整體性、全面性引導。
2.2 精神激勵的一元取向不適應信仰功能的雙重向度
信仰作為人類精神文化現象,其存在價值在于具備滿足精神文化需要的功能,“通過它去安頓自己的生命、解釋自己的生活,甚至用它去化解人們遇到的各種各樣的實際問題”[22]。根據實際需要,信仰功能至少有兩個向度:一是向上提振、激勵升發。即助益信仰主體找到生命存在的終極意義,并激發出積極進取、精進不息甚至在所不辭的奮斗意志與精神狀態。100年前,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與國家富強的理想和使命激勵著中國共產黨人矢志不渝為之奮斗,并于其中迸發出堅不可摧、百折不回的革命大無畏精神和自我奉獻精神,不斷走向并抵達神圣精神境界。100年后的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發展階段,直面偉大事業對偉大精神的迫切需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成為連接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民族信念和人民信仰,這個信仰對于全民族形成共識、創生動力、振奮士氣,發揮著強大的精神凝聚作用。二是向下兜底、撫慰沉落。即能夠通達解釋個體人生的苦難、挫折、失意何以發生,曾為之奮斗追逐的人生意義何以幻滅、破碎,并穩妥承載其中的心理失重與精神沉落,為緩釋個體精神苦悶指明出路,為消解現實困頓做出方法論安排。當然,在上升與沉落的重合地帶,理論層面來看,信仰還需要具備精神內斂、安住當下的第三向度功能,但這種重合并不穩定,會繼續升降演變,因此不單獨討論。
現實問題在于,當前中國精神匯聚了強大的向上提振能量,如自強不息、開拓創新、與時俱進、敢為人先、奮勇爭先、積極探索、堅忍不拔等,足以發揮信仰第一向度的正向指引功能。然而對于第二向度信仰功能,需要拿什么精神加以引導?誠然,中國精神寶庫特別是傳統精神中不乏能在生命深邃處慰藉傷痛、釋放焦慮、化解仇恨、紓解焦灼、修復能量、煥發元氣的人文底蘊。如正道滄桑、好事多磨、晴耕雨讀、獨善其身等具有方法論意蘊的精神引領,以及安貧樂道、田園隱逸、超然物外等具有世界觀、價值觀內涵的精神導向,能在某些程度上幫助沉落人群減卻精神困厄,但終歸只是少數人的個體文化領悟與精神自救,尚未上升到人民信仰高度,未在信仰范疇整合生成安全線、兜底網。對于那些主觀上不愿以物質財富衡量成功或客觀上不具備創造充足物質財富能力的群體,要以怎樣的精神來指引他們釋義人生意義?假如不該漠視“失敗者”的存在,那么奮勇爭先、向上激勵的精神倡導,可能反倒會放大他們“不成功”的窘境,“使他們向更適合自我身心、更有意義感覺方向進行的追求更易招致多余的壓力和誤解”[19]。那些看不到希望的“失敗者”,如果難有一種安全穩妥的方式調集生存信念、本體能量并保持生命愉悅,就難保不走向自我傷害、傷害他人甚至危及社會。這赫然提醒著中國精神的構造、鑄煉與倡導,特別是對人民信仰的指引,不能忽略信仰本體必須具有的心靈救贖兜底功能向度,更不能忽略信仰主體中那些正在面對和遭受現實世界擠壓、困窘與挫折的人群,否則就會影響中國精神對人民信仰的整體重塑。
2.3 精神倡導的趨同境界不適應信仰主體的階層差異
如果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每個社會成員應努力踐行的價值規約,因此需要按照“最大公約數”的建制構造,那么中國精神作為照耀、溫暖、啟發每個中國人的精神光芒,則更適合作為“最小公倍數”理解,即中國精神有義務遍照每個中國人心靈乃至心靈每個角落。這就提出一個問題,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至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直至共產主義實現前的相當長歷史過程中,在作為整體的全體人民的內部,依然客觀存在屬類、圈層、職業等人群區別度,比如按政治信仰有中共黨員、民主黨派成員之分,按社會分工有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商人、官員之分,按收入有低、中、高收入者之分,等等。他們作為不同屬類信仰主體對信仰的訴求期待皆有不同。因此,人民信仰構建所需的精神指引,也應視人群不同而有所區分,特別需要扎根生活、貼近百姓,“根據不同群體的特點和需求”[23]施以相應的精神指引,“從精英式的指點江山轉向普通民眾的現實世界,從宏大的社會結構轉向微觀的日常生活”,“關注一般社會成員在尋常的人際關系中的體驗”[24]等。當然人群之間的精神需求差異,并非簡單、絕對的圣俗高下之分,比如雷鋒精神、鐵人精神等高尚精神生發在許多基層工作者身上,習近平講到“‘七一勛章’獲得者都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職、默默奉獻的平凡英雄。他們的事跡可學可做,他們的精神可追可及”[25]。可以確定的是,不同屬類人群信仰構建所需的精神指引,一定有不同的境界和主旨。
然而反觀中國精神對人民信仰的指引,目前還未形成基于辯證唯物主義中主觀符合客觀、一切從實際出發等原理指導下的世界觀、方法論自覺,即尚未體現人群細分的需求導向與現實關懷,尚未形成精準應對的“治愈藥方”。比如,對于“想發財”和“當干部”兩類人有不同要求,前者只要合法發財、靠勤勞能力智慧致富,就能“光明正大、理直氣壯”,而后者必須“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貧”[13]146;對于黨校教師和其他學者有“學術探索無禁區、黨校講課有紀律”[26]159的不同標準方向等,都是精神引導的精細化范例。那么,在分工不同、收入不同、訴求不同的人群之間,也同樣要體現精神倡導的層次性、差異性。如果對其不加區分地囫圇倡之以無私、高尚,其結果就是衍生出偽善、偽道德、偽信仰等精神世界的虛假繁榮。馬克思指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27]347,這對指引人民信仰的啟發,就是必須躬身直面基于生產方式、社會分工、物質條件等社會存在因素而形成的信仰主體人群差異及其精神訴求差異這個客觀現實,對人民信仰構建施以“有教無類”的精神光照和“因材施教”的精神引導。特別是在當前無論物質生活、生產方式還是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無論家國命運還是社會心理、個體體驗,都發生大開闔、大縱橫、大變局的時代,要怎樣照看好各階層精神世界,給不同人群以點亮生命的信仰指引?就更須以既仰望遼闊星空又心懷山河大地的姿態,在廣袤縱深的中國精神文化沃野上潛心于“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的精耕細作。
3 中國精神指引人民信仰的突破路徑
毛澤東曾指出:“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28]186當前,在中國精神對人民信仰的指引上,大的方向就是把對“怎樣的精神引領才能構建人民對生命真實不虛終極正信”的思考與回答,貫穿于對當前信仰神化、物化、虛化問題的破解中。習近平提出文化藝術要在鑄造靈魂的工程中追求真善美的永恒價值[29]134-135,中央《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要求,一切文化產品、文化服務和文化活動,“都要傳遞積極人生追求、高尚思想境界和健康生活情趣”[4]583,其中所指明的求真、尚善、審美三維引領方向,對應著中國精神解構信仰神化、物化、虛化的突破路徑。
3.1 以心性上的求真精神解構信仰神化
信仰神化的基本表現,是對超自然力量的神格化信奉。盡管信仰從其出發點來說,是要獲得人與世界的真相,是“一個民族對于它認為是‘真’的東西所下的定義”[30]46。但“求真”能否得真,要經受兩重考驗:是否承認真理相對性與絕對性的統一;是否能夠實現信仰主體與信仰客體的統一。
以第一重考驗看,被神化的信仰往往宣揚絕對“真理”,建立絕對相信、不容置疑的神化權威。當下中國,極端神化信仰“表現得不明顯,或者說中國文化總體上并不傾向于神學的信仰”[22]。存在于一些個體身上的信仰神化表現,主要是具備“‘求真’而未得真”特征:對某種外來文化價值、意識形態產生一種盲目迷信、絕對尊崇、不容置疑的賦魅式崇拜,以及對信仰主體內心執念固持一種不可觸碰、不可違逆的自封神式的抱守。比如對西方文明、西方價值觀的全面膜拜、全方位尊崇,而對我們這個民族自帶神圣性的傳統文明全然罔顧甚至全面否定;在中西文明對話中放棄本應堅守的西為中用立場,反而被西方中心主義附體,倡導西體中用,甚至主張全盤西化。這種信仰追求不僅因其本位立場的顛倒和執持一端的排他性、絕對化、極端化形而上學思維而難以達到“求真”目的,更因其拋棄我之為我的本民族文化根基、精神血脈而無法得到心靈最祥和安穩的依歸。所以,這樣的信仰主體往往表現出偏激狹隘的心胸、極具攻擊性的言辭文風以及極度缺乏安全感、固執己見、排斥異見的焦躁做派。這種信仰“神化”有悖于唯物辯證法中聯系的、發展的、對立統一的辯證否定科學思維,也是中華文化傳統的末流與邪徑,“中國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之所以結合,還在于中國文化有自身的特點,即中國的文化不是宗教文化,不具有排他性,這一點是很重要的”[31]52。
回歸中國人自己的精神文化世界,就會發現,在中華民族自古以心性論為本體論的尚本精神基因里,始終保持著“以人為本”“人與天地參”的主體獨立與精神主動。和西方近代哲學漸漸淡忘丟失了古希臘哲學家對人及人的生活的反思態度所不同,中國哲學“始終將生命的意義和生活方式作為自己的主要思考對象,儒道佛三種哲學無不如此。無論如何,總是要堂堂正正做個人”[21]。博大精深心性學體系和盡心知性、明心見性哲學意境中蘊含的中國傳統精神,超越了對人性以外、本我之外的依賴、盲從與束縛,不僅不會陷入人神、人我、自我的分裂與沖突,更有助于人經由知行信合一、身心意統一的方法路徑實現“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心靈自由,經受住“求真得真”的第二重考驗。
在中華民族“求真得真”以獲得持續發展的曲折探索中,最具劃時代意義的成功范例就是中國共產黨在百年自我建設中始終遵循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堅持以黨性涵養鍛造本體,并在主觀符合客觀的自我改造與社會改造中,實現人類社會發展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實現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與中國共產黨自身發展壯大、保持蓬勃生機的統一。始終不悖離自己的信仰宗旨的黨性修養,被習近平稱之為“共產黨人必修課”“共產黨人的‘心學’”[32],可謂一語中的之稱;而中國共產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常態化黨性教育也是向出發的地方問求遠行智慧力量的明心歸本之舉。中華民族立足本心的求真立場,不僅不會形成故步自封的困境,反而生成和充盈著不拒外來的自信與底氣:曾經在歷史上成功實現了儒釋道三教精義的融合,更在苦難深重的近代成功會通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展現出中國精神海納百川的開放心懷、包容胸襟和同化氣度,也富養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所以,中國人自古以來在個體信仰上選擇了一條“不宗教”而非“無宗教”的具有高度本民族文化自信[33]的心性自覺與精神自立之路,這條路也將是成功解構信仰神化的人心自由之路。“凡教必本于心,此亦中國古人所創之‘人文大道’,可以證之當前全世界之人類而信矣。”[34]7在以中國精神指引人民信仰的命題之下,須得保持對本民族精神自覺自立傳統的清醒認知,意識到“學術史上從未有另一種文化傳統對心性問題傾注數千年的哲學關注”的中華傳統精神優勢,以及由此而生成的中國精神哲學“純正濃郁的‘超越自然’的文化氣質”[33],以心性構建上的歸本求真精神為人民信仰開辟正信正念正行相統一的“求真自由”新途,也為人類立足此岸、走向此岸與彼岸相統一的新境界,做出中國精神哲學的獨特貢獻。
3.2 以德性上的尚善精神解構信仰物化
如果說信仰神化是人性對超人性(或稱神性)的拜服與依從,屬于形而上的信仰迷失,那么信仰物化則是人性對動物本能的蜷伏與屈從,屬于形而下的信仰淪陷。馬克思主義對物化的解釋是:人在脫離了“人的依賴關系”這個最初的社會形式之后,但尚未發展到“社會生產能力、社會財富從屬于人的個人自由全面發展”階段且為向這個階段發展創造條件的“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獨立性”[35]107-108存在狀態下,價值追求出現“異化”。這個原理投射出的信仰物化現象,就是“在物欲主義主宰人的精神生活的情況下……神圣也被物欲化了,各種信仰無不帶有功利的目的、物欲的期望”[22]。雖然馬克思批判的是資本主義社會,但西方世界的物質主義、利己主義在我們當下生活中也以各種形態頻繁出現。錢理群早年就曾批評一些大學正在培養“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繼而認為失去精神追求的人只能靠本能法則,發展到極端就成了利己主義,這是如今中國最大的困境[36]。這和袁祖社“由于一味將思想關注于動物本能和物欲層次,因此,我們的思想尚無法達到生命存在的一個更高層級”[37]的理解基本一致。
在物質和精神的關系上,只要高水平經濟發展沒有同步推動精神世界的高層級躍升,或者只要物質需求的不斷滿足未足使人獲得足以擺脫物質束縛的精神富足,那么就會反向刺激出對物質利益的更多貪欲,直至信仰物化的魑魅登場、精神純粹的神圣性退位。早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就發現國民財富的增加并不能帶來國民幸福相應增加,這被稱為“伊斯特林悖論”:經濟因素(即收入增長因素)帶來的幸福感的正向增長,被非經濟因素(主要是精神因素)導致的幸福感減少所抵消,結果是總幸福感并未增長。這就提出兩個問題:一是不帶來幸福感增長的經濟增長意義何在?二是假如精神上的滿足感對物質財富增長缺乏彈性,或者說更多的物質生活滿足感并不能滋養出更多精神生活滿足感,甚至還在降低精神生活滿足感時,人們用什么拯救精神、喂養靈魂?信仰物化就是其中一種飲鴆止渴、愈飲愈渴卻別無它飲的選擇,即不斷強化物質欲望的刺激并在滿足這種欲望中獲得更多物質生活滿足感,以填補精神生活滿足感的虧空。殊不知,此之填補正是彼之虧空的根源,越空虛就越消費,但越消費恰恰越空虛,由此形成惡性循環,人也因此成為物欲滿足的奴隸。而掩蓋在物質光鮮流溢之下的,是精神煉獄里的人枯如鬼、人惡如魔,越掙扎越緊縛,非徹底覺醒而不得解脫。所以從根本上來說,這種“拯救精神、喂養靈魂”的“物化”選擇就是一個消耗精神、銷蝕靈魂的偽命題,只能南轅北轍,陷人性于欲海沉淪、陷人格于物役卑微。
那么精神淪陷危機何以化解?精神超越何以實現?無論中西方,或許此心同理:唯有向心中的道德律反思、向頭頂的星空仰望,才能獲得力量。然而中西方近現代化所走的路徑不同,導致了獲取精神力量的顯著差異,而且,“中國以西方不認可的模式迅速崛起,給世界帶來了相當的震感”[38]1。早在2 000多年前的先秦典籍中,就密碼一樣刻錄著收伏物欲的機宜,即厚德載物。在中國文化精神中,對人們形成信仰引領作用的恰恰是德感追求,“以道德理想的提升而達到超越自我和世俗的限制,以實現其超凡入圣的天人合一境界”[39]13。正是幾千年傳承不衰的德感文化,施展著高尚對于物欲的化解作用,釋放著德性對人性的救贖能量:不僅富貴不能淫,還要貧賤不能移;不僅倉廩實而知禮節,還能孔顏樂處、安貧樂道。也就是說,無論貧窮與富足,只要在德性生命上獲得了成長與構建,就拆解了精神世界對物質滿足的依賴,使人得以超然物外,安之若素。正是在個體修養作為第二生命需要的精神自覺中,物質作為生命第一需要的困難和問題就被消解和轉化了[22]。
進一步追問德性的價值指向,是“止于至善”。這個指向里有根基、有目的,還有路徑。縱然“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也無法阻攔“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登攀意志和制惡信念。正是幾千年“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諸惡莫作,諸善奉行”的道德踐履點滴積累,匯聚了中華民族向善逐善、行善從善的精神富足,也滋養著炎黃子孫的人格高貴。富者,物質之豐也;貴者,精神之悅也;高者,品行之潔也。和近代西方人性本惡罪感文化之下只有擺脫衣食之憂、名位之憂的世襲貴族才有可能積累高雅趣味、造就超越的自由的貴族精神所不同,五四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眼中的貴族精神“指的是一種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貴的精神氣質,既無關乎門第、血統,更與消費水平無關”[37]。這種精神氣質在共產黨人堅信人心向善,堅持尚善揚善,源源不斷激發舍生取義、舍身求法、舍己為人等善行善舉內在驅力的精神追求中,得到集中體現。正是共產黨人作為黨員個體在與人趨利避害本性艱苦抗爭、寸心收復中,在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崇高境界永續登攀中,使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整體雖百折而不催、愈歷久而彌新的先進性得以持續保持。
共產黨人的黨性修養和高尚風骨所蘊含的巨大感召力、凝聚力,被習近平作為“人格的力量”,與“真理的力量”并稱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兩個強大力量[40]。沒有中國共產黨向上向善身體力行的價值引領,沒有中國人民對這一引領感召的深切領受、堅定追隨并甘愿為民族解放做出巨大貢獻和犧牲的高尚德性追求,中國就走不出水深火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會,中華民族也不可能走向偉大復興的未來。所以當下出現的信仰物化亂象與西方以資為本的根本區別在于,它只是市場經濟法則快速注入社會生活并急劇調動財富創造、物質積累熱度的激素病,而和“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霸世界的基因”[41]一樣,并不是西方資本逐利邏輯下“為了尋覓財寶甘愿下地獄,縱使地獄之火燒焦了帆船也在所不惜”[42]52的基因病。相反,幾千年中國性善論傳統所熏化生成的人性向善基因,從未退場,一旦經由尚善向善中國精神的激活與煥發,則足以在人民信仰構建中發揮主場優勢,不僅能自我治愈物欲之惡的紅腫潰爛,也能為資本主義世界價值審視及信仰重構,產生德性啟發與尚善借鑒。
3.3 以靈性上的審美精神解構信仰虛化
神化物化信仰既不具有終極價值,也不能許生命以終極安頓,屬于信仰異化。解構信仰異化是有的放矢的,破掉偽信漏洞,就能以破為立、構建正信。但信仰的虛化則屬于信仰空洞,信無所信,依無所依。比如當下被熱議的佛系心態、低欲望生態、“躺平”姿態等,表面上看是喪失生命目標及追逐熱情,往深里究或有以佛系消解焦慮、以低欲望抵制被收割、以躺平對抗內卷等消極放棄心理。對于信仰虛化,所謂解構,其實并無構可解、破無所破。如果一個人他既不形而上地迷信神靈,也不形而下地崇拜物質,那么破除什么才能讓他有所相信?或者說心性求真的精神和德性尚善的精神如果都不足以成為他的終極關注,那么以什么引領他的信仰?其實,這種既不拜神也不拜物的人,某種意義上體現著“過著心靈生活”的中國人最原樸的、理性與人情相融通的純美溫良,中國人的這種人格心靈“有一種沉靜、理智、節制的柔美,如同一塊韌性良好的金屬呈現的質感一樣”[43]32。對于這種不為神迷也不為物役的中國人,他們依然保持著不盲從、不輕信的審慎,只是那把能打開信仰之門、確立人生意義、激活生命能量的鑰匙,還在找尋之中;也唯有向著靈性生命審美境界的精神開拓,最能帶給他們恒久的靜篤與精進。這種生命審美境界有四種表現形式,精神指引理路各異。
其一,精進技藝之美,即在挖掘發展與生俱來技藝天資中得到審美體驗。每個人之所以獨一無二,在于他/她天生具有的獨特稟賦。這種稟賦若非足夠自我體察能力或特別被發現際遇,大多被終身埋沒。所以,激活技藝層面的靈性生命,須專注于生命本體,開掘可以終身發展的生命志趣,若能在日臻精湛的技藝審美中安享生命本身的陶然盛放,內心必然溫潤純良。這種內心狀態既是一種神圣性歸來,也是一種超然物外,具有終極信仰基本指征,也體現著中國人我之為我的民族基因。李澤厚曾對中國古典技藝作過“美的巡禮”,并于其中討論了馬克思對“審美心理學”的關注,認為凝結在古典技藝作品中的審美趣味和藝術風格之所以還能令今天的人們備生親切、流連忘返,或許因為藝術作品的永恒性中蘊藏著我們民族的共同心理結構,體現了中國人把“美作為感性與理性,形式與內容,真與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44]216-217。正是中國人這種審美情趣,“充溢著與精神生命相契合進而達到融貫心靈于一體的無差別的精神境界”“同樣是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動力和淵源”[45]176-179。
其二,化成天下之美,即在獨到感知理解日月山川、天地萬物中獲得審美體驗。這種反映客觀世界的意識能力來自生命本體,雖指向外在世界(當然也包括人自身),但首先需要向內發覺,因為只有深層蟄伏于生命意識,屏蔽干擾、專致蓄能,才能深度激活生命能量。一旦耦合到成熟的時機條件,厚積薄發、久蓄而緩釋的感知與領會表達,將化作思想之光,煥然自我,也照亮世界,如軸心時代爭鳴的百家、文藝復興時期“發出了新時代的啼聲、開啟了人們的心靈”的文藝巨匠;或將化作文藝創作之美,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如習近平出訪德國時向東道主講述自己讀《浮士德》的故事,就是因為文化藝術是人類共有的審美,最容易相互理解、溝通心靈[29]123-124。但凡在文化維度啟動靈性生命的人,斷不會有信仰虛化的空洞,因為鑄造杰出已然成為他們的天職與品性,其生命延續本身必然盛產精神信仰成果。正所謂,“凡作傳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傳世之心”[29]134。
其三,人情練達之美,即在領悟生命本體、會通生命關系中獲得審美體驗。這種深度洞察世道人心的悟性孕育于靈魂深處,甚至不需要言辭表達,僅以拈花一笑的淡然,就貫通了醍醐灌頂的力量和攝人心魄的靜氣之美、豐儀之美、靈慧之美。比如那些對中華民族以和為貴、理性中正、崇道尚德、寬厚包容等符合人類命運與共發展需求的優秀精神品質和為人處世智慧,有著本然的領會、力行與傳播自覺的中國人,他們不僅能于各種現實生活的失落、挫折甚至苦難中從容自證自定,更在這種磨礪中具備撫慰人心、激勵精神的能力和器量。這種具有覺悟力的生命信仰在中國人的精神家園中是根深葉茂而日用不覺的,“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是內發的,也就是人自己從觀察到感覺,以至醞釀、吸收,最后到達內心的覺悟。這種精神生活,其特點是最終能夠達到圓融的境界”[46]278。
其四,英雄無畏之美,即在秉持人間正道而無所畏懼中獲得審美體驗。這種體驗不僅使信仰主體具有自覺覺人的人性光輝,更肩負著奉獻自我、救拔苦難的神圣使命,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構成令人信任、仰望、追隨的高度。比如為天下勞苦大眾得解放、為創造一個光明自由新世界、為救亡救國探求出路而犧牲寶貴生命的仁人志士、革命先烈,他們“愉快而嚴肅地下定自己的決心,來擔負實現共產主義這種人類歷史上空前偉大而艱難的任務”[47]38,他們“為大眾的幸福而被殺頭,也就是我的幸福”[47]102。“無數在戰場上、刑場上為中華民族解放而視死如歸的英雄,都既是共產主義精神又是中華民族傳統基本精神的當代體現。”[28]169這種功成不必在我、雖苦猶甜、雖死猶生、視死如歸、超越生死的大無畏氣概,這種主要由中國共產黨人所涵養、傳承和賡續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英雄主義精神,具有震撼天地人心、凝聚浩然正氣的壯麗之美、恢宏之美、圣潔之美。這種精神以其對百折不撓民族精神的表征、對人民是真正英雄普遍真理的蘊含,而能對所有不畏邪惡、崇尚正義、不信神也不拜物的中國人,天然產生審美吸引與信仰指引,也是激勵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戰勝一切困難挑戰的力量源泉”[48]。
遍觀以審美精神解構信仰虛化的四種靈性生命類型,其實蘊藏三點共性:皆是立足生命本體,于不同生命層次,發現人、美化人、鑄造人,助推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皆是放眼變革時代,于生態審美觀中,豐富著“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生動內涵;皆是回歸人性天然,于向內問求中,調動和攢聚自我審美、自我駕馭、自我掌控、自我淬煉的精神力量。這樣的根植于中國人心靈生活的審美精神,以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為根基,實質上就是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所講的“中華美學”,習近平提出“我們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范”[49]。對于我們來說,“只有保持對中華文化理想和價值、生命力和創造力的高度信心,堅守中華文化的民族立場,扎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進行文化創造,在建設文化強國中不斷增強和發展民族審美意識,我們終將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強中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50],從而解構信仰虛化,達至崇高信仰的建立。
4 結語
自從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并與中華優秀文化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緊密結合,中國共產黨就在足以占據人類社會發展制高點的遠大理想感召下,走過漫長的風雨坎坷,走到滄桑巨變的今天,雖已歷時百年,卻風景獨好、風華正茂。自從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逐步在中國取得主流地位,中華民族就從近代四面碰壁、處處擱淺的艱難險惡境遇,一步步轉入精神主動,直到走上世界舞臺中央、無限接近偉大復興的今天。無論對于一個政黨,還是一個民族,信仰都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對于推動社會變革、創造歷史的決定性力量——人民,就更是如此。在辯證唯物主義視域下,提出“人民有信仰”,就是觸碰了開啟人類新文明形態的“核聚變”按鈕,就是點破了如何化解人類危機的偉大命題,也就是立下了構建人類新信仰形態的宏大愿景。
以中國精神的蘊涵覺解與義理再造,指引人民在求真、尚善、審美的最高哲學維度重構信仰,將在同場解構信仰神化、物化、虛化的同時,摧枯拉朽地整合出人類新信仰形態的誕生空間。這種新信仰形態牢牢堅守人的主體地位,以人的自由、高貴與純良為終極價值追求,以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終極構建目標,深度發掘發揮中華優秀文化精神對于人的心性、德性、靈性生命的深層激活與感召,經由人心、人格與人品的再塑造,完成對人的發現與解放。只有這種信仰,才是能從根本上回應人民精神需要、滿足人民精神訴求、煥發人民精神主動、凝聚人民精神力量的人民信仰;只有這種指引才是大變局時代最及時也最徹底,最能把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相結合、把偉大復興民族夢想與追求美好生活個人夢想相統一的終極精神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