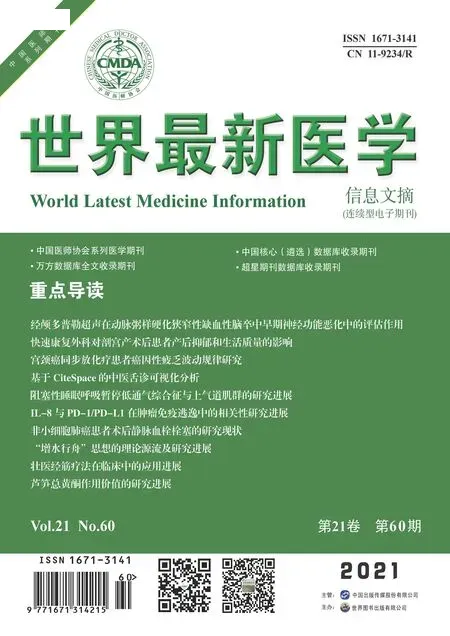PLR在肺癌中的研究進展
李敏,賈喜花
(承德醫學院研究生學院,河北 承德 067000)
1 炎癥與腫瘤的關系
早在十九世紀,德國病理學家Virchow發現腫瘤通常發生于機體的慢性炎癥部位,在腫瘤組織中也發現了大量炎性細胞浸潤,由此推測腫瘤的發生與慢性炎癥之間存在某種聯系[4]。流行病學數據顯示,慢性非可控性炎癥會增加腫瘤的罹患風險,據統計全世界約有15%-20%惡性腫瘤的發生與感染、接觸刺激物或自身免疫性疾病所引起的慢性炎癥相關[5]。
慢性炎癥反應可能早于腫瘤出現,這些致癌性炎癥包括幽門螺旋桿菌感染可致胃癌和MALT淋巴瘤,炎癥性腸病可致結直腸癌,乙型或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可致肝癌等[6]。有研究表明[7-8],環境暴露也會誘發慢性炎癥,吸入石棉和二氧化硅顆粒可影響炎癥小體對促炎性細胞因子IL-1b的釋放而引發慢性炎癥,煙草煙霧等空氣中的刺激性微粒物質可導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這些炎癥反應大大增加了肺癌的發病風險。
炎性介質的表達及炎性細胞的募集會重塑腫瘤微環境并促進腫瘤的生長,這種炎癥被定義為腫瘤引起(或相關)炎癥(TEI)。腫瘤微環境(TME)中免疫細胞釋放的炎性物質,例如細胞因子和生長因子,可通過促進癌前細胞和癌細胞的增殖,以及增強這些細胞對死亡和應激的抵抗能力,直接促進腫瘤的生長和進展。此外,炎性信號可以通過樹突狀細胞、未成熟髓細胞和其他抑制因子誘導免疫抑制,增強TME中其他促腫瘤的輔助細胞(例如成纖維細胞,髓樣細胞和新生血管內皮細胞)的募集、增殖,并改變TME對腫瘤代謝的調控作用[9]。腫瘤干細胞(CSCs)被認為是腫瘤生長和轉移所必需的,但腫瘤中CSCs的數量和比例并不像正常組織中的干細胞那樣是恒定的。相反,各種刺激,包括通過轉錄因子NF-kB和STAT3在腫瘤細胞中發出的炎癥信號可以驅動它們的增殖,增加CSCs在腫瘤細胞群體中的比例,從而提高腫瘤細胞的侵襲能力[10]。總而言之,腫瘤細胞和免疫元件之間的相互作用可能直接促進腫瘤的發展,或導致腫瘤的免疫編輯,從而使腫瘤進入休眠狀態或促進腫瘤免疫逃逸。
另一種重要的炎癥類型是治療誘導的炎癥,它是在各種抗癌治療手段,包括化療、放療、各種生物治療以及免疫治療所引起的免疫浸潤反應下發展起來的。垂死的腫瘤細胞會釋放具有免疫調節活性的損傷相關模式(DAMP)分子,如高遷移率蛋白1(HMG1)可以刺激IL-1a等免疫刺激性細胞因子的產生,而這些腫瘤新抗原的增加可能誘導或維持抗腫瘤T細胞反應,或可能誘導免疫抑制[11]。
淋巴細胞、血小板、中性粒細胞等免疫細胞可以以自分泌或旁分泌的形式控制和塑造腫瘤微環境,并促進腫瘤生長。血小板-淋巴細胞比值(PLR)作為新興炎性標志物,可直接反應機體炎癥反應程度,從而作為判斷腫瘤預后的預測指標。
2 血小板與腫瘤性炎癥的關系
血小板是由巨核細胞釋放的無核細胞碎片,在機體內通過止血功能來保護血管的完整性。血小板除止血作用外,還可以促進血管內免疫反應的啟動以及協調免疫反應的平衡。血小板持續監測血管的完整性,密切協調血管運輸功能,幫助機體建立對感染和腫瘤的有效免疫反應[12]。血小板計數升高,或血小板增多癥,最近被確定為惡性腫瘤的標志物。有研究表明[13]。血小板增多癥的患者患腫瘤的風險增加,血小板計數增加也是隱匿性惡性腫瘤患者的腫瘤預測因子。
在感染或腫瘤患者體內,血小板與血管內皮細胞相互作用,通過促進血管生成、保護血管的完整性、調節血管通透性和血管張力、釋放促轉移因子,為腫瘤細胞的播散提供血管床,形成轉移前的腫瘤微環境。粘附在腫瘤生長部位的血小板分泌原發性生長因子(如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前列腺素E2(PGE2)和溶血磷脂酸(LPA),可觸發上皮-間質轉化(EMT)并促進血管侵襲[13]。血小板是最早與血管內癌細胞相互作用的細胞之一,血小板幾乎在進入血液后立即與循環腫瘤細胞(CTCs)結合并在其周圍形成聚集體。血小板被膜可作為CTCs的機械保護屏障,血小板還可抑制自然殺傷性T細胞(NKT細胞)的細胞毒作用并逃避NK細胞的攻擊。此外,血小板還可分泌促癌因子,并為腫瘤細胞提供粘附受體,促進腫瘤細胞的遠處轉移[14-15]。這些研究表明,腫瘤細胞能夠通過“劫持”血小板,從而顛覆宿主對腫瘤的免疫反應。血小板與腫瘤細胞的相互作用構成了腫瘤進展的重要病理生理機制,因此將血小板作為靶點可能成為腫瘤的一種新的治療方向,而血小板與CTCs的緊密結合使其可能成為靶向運送抗癌藥物的理想運輸系統[16]。
3 淋巴細胞與腫瘤性炎癥的關系
淋巴細胞是人體免疫反應的主要細胞之一,它們通過抑制腫瘤細胞增殖、監測細胞變異、對抗感染,在腫瘤免疫反應中發揮重要作用。CD8+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CTL)是適應性免疫的主要力量,也是機體抗腫瘤機制的重要環節,其通過細胞毒性破壞作用和分泌效應因子來發揮抗腫瘤作用[17]。CD8+CTL能夠以識別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體I(MHC-I)的方式直接殺滅腫瘤細胞,目前大多數過繼細胞療法(ACT)以激發CD8+CTL介導的抗腫瘤反應為主要研究方向[18]。CD4+輔助性T細胞(Th)可為CD8+CTL應答提供“幫助”,防止CD8+CTL產生免疫耐受,促進效應性和記憶性CD8+T細胞的存活,從而增強CTL的抗腫瘤活性[19]。此外,CD4+T細胞產生IL-2可增強干擾素γ(IFNγ)介導的NK細胞的抗腫瘤活性[20]。Foxp3+Tregs已被證明是腫瘤免疫耐受形成的重要因素,介導免疫抑制作用。在一個肺癌模型中,Tregs細胞被證明在腫瘤相關的三級淋巴結構中發揮作用,以抑制T細胞的抗腫瘤反應[21]。Tregs細胞可以通過直接的細胞毒作用介導CD8+T細胞的凋亡,而腫瘤衍生因子可以誘導Tregs細胞表達顆粒酶B,從而導致CD8+T細胞的殺傷和抗腫瘤免疫能力下降[22]。B細胞抗腫瘤免疫的潛在機制可能涉及腫瘤浸潤的B細胞能夠在腫瘤部位招募T細胞,從而促進和維持抑制腫瘤發展的T細胞反應。此外,腫瘤浸潤性B細胞可能作為抗原呈遞細胞來輔助抗腫瘤免疫[23]。因此,外周血淋巴細胞數與腫瘤免疫密切相關。一項薈萃分析表明,低淋巴細胞計數與多種實體腫瘤較短的OS和PFS有關,淋巴細胞減少患者的存活率明顯低于淋巴細胞計數正常的患者[24]。
4 PLR在肺癌中的研究進展
近年來肺癌的發病率與死亡率逐年上升,盡管肺癌的診斷和治療技術日益先進,但肺癌的預后仍然很差。因此,尋找更簡單、有效的預測肺癌患者預后的生物標志物,尤其是血清生物標志物,有助于臨床醫生制定更有效的肺癌治療策略。PLR作為外周血炎性標志物,在肺癌患者中具有潛在的預后作用。
肺癌的發病原因尚不明確,目前尚無明確的指標可作為肺癌發生的預測標志物。在一項對肺癌發病高危人群的隨訪中發現,PLR的年平均變化率與肺癌的發病相關,患肺癌組的PLR年平均變化量是對照組的11倍,而PLR每年增長值≥4%的人群的肺癌發病密度較對照組增高112%,因此年度PLR的評估可能作為肺癌的篩查指標[25]。
對于不能或不愿接受手術的早期肺癌患者,立體定向放射治療(SBRT)是一種推薦的治療方式,可以改善患者的局部控制率(LCR)和總體生存率(OS)。但在一項對SBRT治療RTOGII期肺癌患者的研究發現,雖然放療對腫瘤的局部控制率很高,但仍約有20%的患者在3年內出現遠處轉移[26]。有研究表明[27],治療前的PLR是SBRT治療早期非小細胞肺癌(NSCLC)患者生存的預后指標,PLR升高的患者預后較差,而高PLR值(PLR≥250)患者在SBRT治療后發生轉移的風險更高。在早期肺癌患者中,SBRT治療后的輔助治療仍存在爭議,PLR的水平對于患者后續全身治療方案的選擇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化療和放療是局部晚期或晚期肺癌患者的主要治療方式。化療耐藥和局部復發或轉移是治療肺癌的主要障礙,慢性炎癥在放化療抵抗中起重要作用[28]。PLR作為全身炎癥的反映指標,對肺癌患者的預后具有一定的預測價值。一項薈萃分析表明[29],在NSCLC患者中,PLR與OS獨立相關,PLR值升高可顯著預測NSCLC患者的不良預后,但在小細胞肺癌(SCLC)患者中,PLR值與OS無關。另一項對局限期小細胞肺癌(LS-SCLC)的研究中發現[30],在接受同步放化療的患者中,治療前的PLR值與OS相關,較高的PLR(≥140.1)與較差的OS相關,而與無進展生存期(PFS)無關。有研究發現[31],治療前PLR升高是Ⅳ期NSCLC合并惡性胸腔積液患者較差預后的獨立預測因子,PLR在NSCLC中有預測價值。一項對肺癌術后輔助化療的研究發現[32],術前的高PLR是影響PFS和OS的獨立預后因素,PLR升高預示著術后輔助化療的NSCLC患者預后不良。
隨著分子醫學和新的靶向藥物的發展,肺癌的治療已逐漸由以含鉑方案為主的化療發展到靶向治療為主的個體化治療。有研究發現[33],在ALK基因突變陽性的患者中,較高的PLR與較低的PFS和OS相關,因此PLR變化趨勢可作為判斷ALK陽性NSCLC患者接受克唑替尼治療的病情進展情況的指標。另有研究發現[34],PLR可能是接受EGFR靶向治療的晚期NSCLC患者的預后因素,治療前高PLR組(PLR≥190)患者的PFS顯著低于低PLR組(PLR<190)。
近年來,免疫治療迅速發展,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CIS)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多種惡性腫瘤的治療格局。在免疫治療時代,疫檢查點抑制劑在肺癌的治療中獲得突破性進展,外周血炎性指標或可以作為免疫治療療效的預測標志物。一項大型多中心回顧性研究表明[35],免疫檢查點抑制納武利尤單抗(nivolumab)在二線及二線以上的晚期NSCLC患者的治療過程中,治療前的PLR值低于200時與較長的無進展生存期(PFS)和總體生存率(OS)、較高的客觀緩解率(ORR)和疾病控制率(DCR)相關,治療前PLR水平較高的NSCLC患者使用nivolumab的療效可能較差。近期的一項薈萃分析發現[36],在接受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CIS)治療的NSCLC患者中,治療前PLR升高與較低的PFS和OS相關,而治療后PLR與OS和PFS無明顯相關性。一項對接受阿替利珠單抗(atezolizumab)治療的NSCLC患者的回顧性分析發現[37],治療前的高NLR、低LMR和高PLR,與較短的PFS和OS顯著相關。
5 結語
全身炎癥反應在腫瘤的發生發展中起重要作用,炎癥反應了免疫系統抗腫瘤與促腫瘤功能之間的動態平衡。炎癥主要表現為外周血細胞參數的改變,可以通過計算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單核細胞和血小板的比值來評估腫瘤患者的全身性炎癥[38]。因此,PLR作為外周血炎性標志物,在肺癌患者中具有潛在的預后作用。目前大多數研究證實PLR可作為腫瘤預后不良的標志物,但PLR對腫瘤的預后價值機制尚不清楚,尚需要對肺癌患者進行大規模前瞻性隊列研究,以證實PLR在肺癌患者中的獨立預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