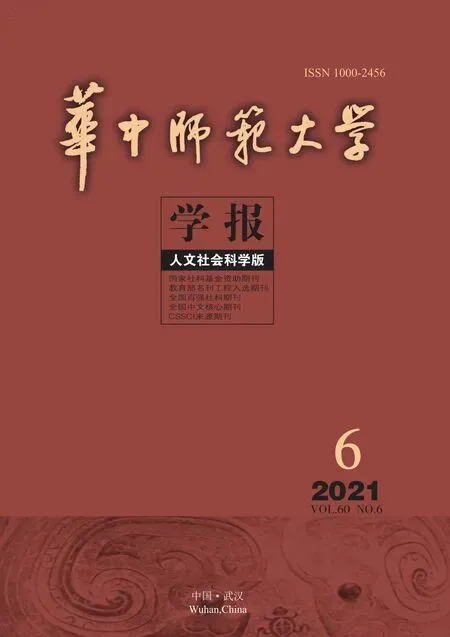論中國傳統語言研究的問題意識與應用導向
龔瓊芳
(武漢理工大學 法學與人文社會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70)
近年來,黨中央和教育主管部門都非常重視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弘揚,這對于漢語語言文字研究具有重要指導性和啟示性。就語言文字領域來說,中國傳統語言文字研究(以下簡稱“中國傳統語言研究”)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對其杰出成就、優良傳統、歷史局限等進行深入分析,對于當今的漢語語言學研究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王力的《中國語言學史》在“全書的結論”部分指出,“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定了中國古代語言學是為了實用的目的的”①。王力認為,識字是為了通經,通經是為了確知“先王之道”,而“先王之道”被認為是鞏固封建統治的法寶。
李智明《中國古代語言學史稿》將中國傳統語言研究的特點概括為五點,其中第一點也是“注重實用”:“從歷史上看,漢民族喜歡研究和解決實際問題,而不太喜歡作純理論的探討……語言研究也不例外,人們研究小學,其目的在于用它來掌握當時各門其他學科……我國古代語言文字方面的著作,大都是為了實用的目的而撰寫的。”②
胡奇光的《中國小學史(修訂本)》也指出,小學,即中國傳統語言學“原是‘征實’之學,常用來解決識字、解經、寫詩時碰到的實際問題”(修訂本前言),其“根本方向是解決古代文字上的實際問題”③。
可見,學界早已認識到中國傳統語言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實用性”。那么,我們如何站在當今學科發展的高度來看待這種“實用性”?又如何全面準確地認識這種“實用性”的具體表現?這一特點對于我們今天的語言研究有何借鑒意義?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進行思考和梳理。
在目前的學術研究分類中,一般根據是研究某一知識體系本身還是研究該知識體系的實際應用,可大致分為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兩大類型。兩種研究類型常常互相結合,很難截然劃清界限,很多情況下只是側重有所不同。中國傳統語言研究固然也關注漢語和漢字本身的若干問題,并提出了關于漢字造字方法和形體結構的“六書理論”、研究音義關系的“因聲求義”方法論、歸納上古韻部系統的“同聲必同部”原理、語音演變中的“陰陽對轉”規律等一系列理論學說,從而在基礎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總體來說,這些研究較為零散,其目的主要不是為了全面系統地探究語言文字的規律,更談不上構建科學完整的漢語言文字學知識體系和學科體系,這也就是李智明所說的“不太喜歡作純理論的探討”。學界已經認可的“實用性”,在本質上反映的是中國傳統語言研究更加側重應用研究,其特點可概括為“具有鮮明的問題意識、以應用為導向”,具體表現為:密切聯系社會生活的實際,以解決現實問題為目的,關注并參與時代熱點問題的探討,從而引領學術發展、服務封建國家的政治和文化及教育建設需要。這一特點值得當代語言學者深思。
一、語言研究指向現實問題
中國傳統語言研究一般從漢字的形音義三個方面出發,分為文字、音韻、訓詁三個部類。從其產生、發展、成熟的過程來看,依次為訓詁、文字、音韻。無論哪一部類,都具有指向現實問題的共性特點,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為特定現實需要服務的。
(一)訓詁學:服務于解經和通經
訓詁學產生于對經典的解釋,這是中國古代語言研究的源頭之一。正因為此,傳統語言學一向被認為是經學的附庸。雖然語言學界很多學者對“附庸”的定性不太滿意,但如果拋開感情色彩而從研究類型的角度來看,傳統語言研究尤其是其中的訓詁學,確實是為解經、通經服務的,這種“服務性”正好證明了其問題意識及面向現實需求的應用性導向。訓詁學中,無論是形訓、音訓、義訓等各種訓詁方法,還是隨文釋義式的傳注或訓釋資料的匯編性著作等訓詁形式,都是為了適應解經、通經的現實需要而不斷發展完善的。比如,中國第一部訓詁學著作《爾雅》,就是對先秦時期已有的各種零散故訓材料的整理匯編,其編纂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便于更好地閱讀和理解經典。魏晉以后,隨著學術發展的需要,訓詁學的注解范圍不僅以儒家經典為主逐步擴大到史部、子部、集部及佛教典籍,還出現了義疏、集解等新的形式。此外,訓詁學為現實需要服務的特點,還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辭書編纂的杰出成就。中國的辭書以《爾雅》為開端,從訓詁學逐漸延伸到文字、音韻乃至語言之外的其他學科,數量不斷增多,形式不斷豐富,知識涉及面不斷擴大。辭書以詞條的方式對各種知識進行系統整理和分類存儲,以便于查詢利用,其自身的發展始終是面向社會和文化發展的實際需要的。二是方言詞匯的調查和采集。從周秦時代的軒使者到漢代的揚雄,所從事的采風及方言調查和整理,均是為了服務于上達天聽、讓統治者了解民風民情的政治目的,也就是揚雄所說的“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帷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④。三是虛詞研究與文言文教學。古代的虛詞研究隸屬于訓詁學,元代以前主要混雜在傳注之中。較早的虛詞專著如元代盧以緯《語助》、清代袁仁林《虛字說》等,作者都是教書先生,其編寫目的,是為了便于針對學童的文言文教學,包括虛詞教學與辭章之學。王德修《〈虛字說〉跋》概括《虛字說》的寫作目的就是“為予小子輩說書而作也”⑤。
(二)文字學:服務于識字和用字
古代所謂“小學”,最初是指對貴族兒童進行初等教育的學校,后來通過借代的方式指稱小學階段的主要學習內容,即識字教育,這就是文字學的雛形,其主要成果形式為童蒙識字課本⑥。可見,文字學起源于漢字教學的實際需要,其產生之初就是面向漢字教學的現實問題的。在其后的發展過程中,以許慎《說文解字》作為標志性成果,文字學研究服務社會的職能不斷拓展,表現為以下方面。一是為經學和政治服務。《說文解字·敘》概括的文字的性質就是“經藝之本,王政之始”⑦,這反映出傳統文字學研究明顯的問題意識和現實指向。二是對漢字進行整理規范。從秦朝“書同文”到漢代的《說文解字》再到唐代的字樣之學與正字法著作,文字學的發展始終面向漢字的書寫和應用問題,為漢字的統一和規范化做出了不懈努力。三是對俗字的研究。文字既有通用的正式使用的標準形態,也有在民間隨意使用的俗寫、簡寫形態。從規范用字的角度來說,需要了解并研究俗字。所以唐代顏元孫《干祿字書》作為一部正字法著作,對于每個字的字形,都收錄了“俗”“通”“正”三種形體。漢末的《通俗文》、唐代的《俗務要名林》等主要收錄俗語和俗字,后來影響較大的字典如明代《字匯》、清代《康熙字典》等也都收錄了大量的俗字。實際上,從歷時發展的角度來看,很多過去的“俗字”往往成為后來的“正字”。此外,一些特殊領域的用字,俗字使用較多,比如碑刻用字、寫卷用字、印刷用字等,文字學研究對此也有關注,產生了以《龍龕手鑒》《碑別字》等為代表的著作,體現出文字學研究對社會用字情況的關注和跟進。
(三)音韻學:服務于注音和用韻
音韻學的產生與發展始終是為現實需要服務的。首先,拼讀字音的需要與反切的創制。漢末至曹魏時期,學者們根據漢字音節特點并在梵文拼音原理的啟發下,創制了反切的注音方法,從而標志著音韻學的建立。此后,出于實用的需要,為了拼讀更順利,對反切還不斷進行了改良。比如,《廣韻》中“東”小韻的反切是“德紅切”,“德”為入聲字,有塞音韻尾,妨礙它與“紅”字的順利拼切;到了《集韻》,“德紅切”改為“都籠切”,反切上字改為了開音節字,且上字和下字開合、聲調一致,這就使兩字拼讀起來更順利了。其次,音韻學對文學發展的推動。漢魏六朝時期,文學創作特別重視語言的形式美。齊梁之際,周颙、沈約等人利用漢語的四聲進一步豐富了詩歌的語音形式變化,形成了“永明體”。至唐代,以講求平仄協調為語音特征之一的格律詩正式產生。魏晉以來出現的韻書,也是為了方便作詩時查找韻字的需要應運而生的,此后,從《切韻》到《中原音韻》以及明清之后的各種韻書,同時還具有規范用韻、識字正音的編寫目的,從而進一步促進了文學尤其是詩歌戲曲等韻文的發展。音韻學與文學之間一直互惠互促,正好體現了傳統語言研究始終面向社會文化發展的特點。再次,音韻學的其他分支對現實問題的關注。上述《切韻》和《中原音韻》分別是今音學和北音學的代表作。在音韻學的其他分支中,等韻學產生于將韻書反切系統用圖表形式進行直觀展示的實際需要,古音學從清初起,更是與“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潮密切相關,關于這一點詳見第二部分的討論。
二、語言研究關切社會熱點
從先秦到清代,傳統語言研究基本都緊跟時代潮流,密切關注時代熱點,從熱點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或者站在時代發展的高度從事相關研究,或者從時代思潮中汲取營養,或者從語言文字角度回應時代的熱點問題。比如,春秋戰國禮崩樂壞與“正名”思想、漢代今文經學對文字的錯誤說解與《說文解字》的正本清源、六朝隋唐佛教文化對語言研究的影響、唐代“選學”的興盛與李善《文選注》、元代《中原音韻》對元曲用韻的規范和元曲創作流傳的廣泛影響、明清來華傳教士對漢語語言文字研究的影響、清代研習《說文》的社會風氣與“說文學”的興盛,等等。以下略舉兩個具體個案予以說明。
(一)百家爭鳴背景下的名實之辯
語言文字研究的起源,一般有兩大源頭:一是哲學家關于名實問題的探討,如古希臘;二是對于古代經典的解釋,如古印度和阿拉伯。漢語語言文字研究的起源,則與這兩者都有關系。前面已提及第二點,這里對第一點再做一些簡單論述。
與古希臘哲學家對名實問題進行論戰大致同時,我國春秋戰國時期也曾發生過類似的關于名實的辯論。春秋戰國時期,在諸子百家爭鳴中,哲學、政治、邏輯、倫理等方面的問題都是時代的焦點話題,而名稱問題則與這些領域都有或多或少的關聯,從而成為討論的熱點,諸子各家幾乎都對這個問題發表過看法。名實之辯主要包括兩個層次的問題。首發其端的,是儒家針對名稱使用混亂現象提出的“正名”問題,儒家、墨家、名家、法家等都發表過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這一問題的核心在于如何正確使用語言及其對維護政治倫理的意義,主要涉及名稱與語言使用者的關系問題。第二個層面的爭辯,則是名稱與事物的關系問題,問題核心在于:名稱與事物之間是否有必然聯系?名稱何以成為指稱事物的符號?老子、墨子、尹文子、公孫龍子、荀子等都留下了相關論述,最終以荀子提出的“約定俗成”論作為階段性小結。可見,中國傳統語言學在萌芽時期,就體現出對社會熱點問題的高度關注和參與,從而奠定了其與社會生活密切聯系的品格。
(二)清初實學思潮中的古音研究
“清代語言學是在批判宋明理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⑧,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大思想家所倡導的“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潮是明末清初思想界的主流,雖因各種原因未形成思想解放的潮流,但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事實上在清代前期思想文化界占據主導地位,并為樸學的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礎。顧炎武作為清代古音學的奠基性人物,認為語音研究的目的是通經致用,向古書尋求真理,他提出,“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⑨。這就明確指出文字、音韻、訓詁為經學之根底,其中古音研究又是基礎的基礎、關鍵的關鍵,是首當其沖的突破口。這一理念,不僅明確了古音研究的問題導向,極大提升了古音學的學術地位和應用價值,更是從語言研究的角度對于反對理學空談心性義理學風這一時代思潮的積極響應和努力實踐。
三、語言研究引領時代學術
一個學科對同時代其他學科的貢獻度和影響力,可以體現出該學科的活躍程度和應用價值。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中,語言研究經常走在時代前列,對其他學科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比如名辯思潮之于先秦諸子之學,老莊注疏之于魏晉玄學,古書注釋之于宋代理學等都有引領作用,下面著重以漢代和清代為例進行概略性論述。
(一)語言文字研究對漢代經學的引領
漢代的學術主流是經學,經學的學術形態體現為對儒家經典的闡釋。在漢代,經學發展的主線是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激烈競爭,在競爭過程中,語言文字問題始終是關鍵性因素之一。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分野首先來自經典文本的文字差異,前者是以漢代流行的隸書書寫,因此稱作“今文”;后者則是用戰國時期的文字書寫的,所以被稱作“古文”。“古”和“今”在此是相對而言的。古文經于漢代發現,但當時的人們基本已不認識上面的文字,對這些文字的釋讀就成為古文經學的首要工作。《漢書·儒林傳》說,“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⑩,這就決定了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在解經方式上的本質差異。今文經學是官學,重在闡述微言大義,在解經時較多結合政治與神學;古文經學剛開始是私學,注重文字訓詁,力求還原經典本義,較少聯系現實政治。東漢以后,古文經學逐漸壓倒今文經學,東漢中后期涌現的著名古文經學家許慎、鄭玄等人,都在語言文字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并引領了經學的時代發展。周予同《經學史與經學之派別》指出,“因經今文學的產生而后中國的社會哲學、政治哲學以明,因經古文學的產生而后中國的文字學、考古學以立”。因此可以說,語言文字研究一直引領著漢代經學的發展,漢代經學則孕育了其他很多學科,是很多學科的源頭和雛形。
(二)乾嘉之學對清代樸學的奠基
清初顧炎武等人確立的以客觀材料為依據進行嚴謹考證的學風,在乾嘉時期推向了極致,涌現出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錢大昕等著名學者,從而形成了乾嘉之學,并奠定了清代學術講求實事求是的樸學特征。乾嘉學者特別重視古音研究,通過建立科學的古音系統,從語音的角度解決了語言文字領域的一系列疑難問題,其研究成果不僅帶動了文字、訓詁及整個語言文字研究,對于古籍整理和研究也具有輻射作用和應用價值。此外,樸學方法對于經、史、子、集、金石、考古、天文、地理、歷法、數學等學科都具有廣泛影響。由此可見,“清代的學問之所以能登上中國古代學術的巔峰,正是有了古音學”。總之,乾嘉之學在文字、音韻、訓詁等傳統語言研究領域取得了卓越的學術貢獻,代表了傳統語言學的最高水平,而且,以語言文字為學術根底,精校勘、善考證,在傳統學術的很多領域也都取得很高成就,因此,乾嘉文學不僅在清代學術中具有重要地位,并且對于整個清代學術具有奠基和引領作用。王國維說:“自漢以后,學術之盛,莫過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經學史學足以凌駕前代,然其尤卓絕者則曰小學……然其尤卓絕者則為韻學”。
四、政府對語言研究的重視
傳統語言研究具有面向社會需要、解決實際問題的應用性特點,與歷代朝廷對于語言文字問題的重視密不可分。由于語言文字問題與國家統一、政令傳達、戍邊安邦、民族交往、思想文化、科舉教育等國家治理的方方面面都有關系,因此,歷朝歷代政府對語言文字的規劃、規范、研究及與之相關的文化教育建設都十分重視。這也促使傳統語言研究始終以服務封建國家各項事業發展為己任,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問題導向和應用特征。
《禮記·中庸》中說:“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這說明,周代各種典章制度的確定及語言文字問題的處理都是由周天子親自負責的。周代不僅形成了我國最早的民族通用語“雅言”,還重視民族語言之間的溝通問題,專門設有掌管翻譯的官員,稱作“象胥”。據《周禮·秋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戰國時期“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朝統一后,為了政令暢通,迅速啟動了統一文字的工作。“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漢代政府建立之初,由于秦始皇“焚書坑儒”造成的文化斷層,十分重視語言文字問題:一方面,繼續組織編寫童蒙識字課本以供教學之需;另一方面,將語言文字能力與官員的選拔及其仕途發展相結合。《漢書·藝文志》記載:“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之’。”《說文解字·敘》也有類似記載。此外,漢末用隸書來確定五經文字書寫標準的“熹平石經”,是“由最高統治者欽定的規模空前的文化工程”,“在統一書面語言文字的同時,也提高了全社會語言文字的規范意識”。到了唐代,隨著科舉制度的建立和文化事業的發展,需要重新確定儒家經典的標準文本及對經典的權威解釋,唐太宗親自組織學者考訂五經文字、推出《五經定本》,全面注釋經典、撰成《五經正義》。此后,張參考證五經文字的形音義而作《五經文字》、為規范經書文字而刻的《開成石經》以及唐玄度再次校訂經典字體所撰《新加九經字樣》,均是奉詔而為,都體現了政府對語言文字規范的重視。宋代以后,官方對于語言文字問題愈加重視。宋代皇帝先后下詔校訂《說文解字》、重修《廣韻》和《玉篇》、編寫《集韻》和《禮部韻略》等。明朝朱元璋下令編寫《洪武正韻》。清朝政府更是主持編寫了很多大型語言文字工具書,如《佩文韻府》《康熙字典》《音韻闡微》《西清古鑒》等。
五、中國傳統語言研究對當今漢語研究的啟示
中國傳統語言研究與社會緊密聯系,以現實需要為問題導向,力圖解決社會文化發展和封建國家各項事業中的實際問題,體現出強烈的問題意識和鮮明的應用性傾向。這些優良傳統,對于今天的漢語語言學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受文章主旨和篇幅所限,這里只進行一些簡單的思考和梳理。
第一,語言的基礎研究固然重要,但一定要與應用研究密切結合。基礎研究的目的不僅僅在于探索自然的奧秘和社會的規律,還在于推動人類進步、創造美好生活,其最終目的仍是為了應用。對于語言的基礎研究,也應該站在這樣的高度來進行認識。
第二,語言研究應多關注社會現實問題,更好地回應社會發展的各種現實需要。當前,世界政治、經濟、科技的新格局、新變化,對于語言文字研究提出了大量問題。僅就語言與國家的關系而言,語言與國家地位、國家安全、經濟發展、科技創新、社會文明、文化建設、政府風貌等諸多問題密切相關。語言研究應在促進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中貢獻更多的智慧、承擔更多的責任。
第三,語言研究應多關注其他學科的發展,為其他學科提供有價值的借鑒。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和思維工具,任何一種文化的傳承發展、任何一門學科的話語表達都離不開語言。在西方的科學發展史上,歷史比較語言學、結構主義語言學、轉換生成語言學等都對其他學科產生過重要影響。西方的現代哲學,更是提出了“語言學轉向”。我國當代的語言研究,也應繼承傳統語言研究的優良傳統,不僅要不斷壯大自身,還應立足學科前沿,加強輻射能力,在引領學科發展中大展宏圖。
第四,只有更好地為國家和社會發展服務,成為名副其實的“領先的科學”,語言學才能更受重視,才能得到更多更好的發展機遇。
當然,由于歷史發展的局限性,中國傳統語言學的應用研究也存在很多不足之處,要而言之,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一是非常零碎、不成系統,沒能形成完整的學科框架和知識體系,用當代應用語言學學科的標準來衡量,還存在較大差距。二是本體研究尤其是理論研究的薄弱,導致應用性研究的深度不足。比如,即使是最為著力的語言教學方面,也主要局限于編寫識字課本、匯編故訓材料、梳理虛詞用法等較為淺層次的層面。三是應用性研究的涉及面比較有限,主要集中在與教育和文化有關的少數幾個領域,與其他學科尤其是自然科學的交叉研究還存在大量的空白。
中國傳統語言研究自身也是一門學科,一般稱之為“中國語言學史”。目前,這一學科呈現出百花齊放的良好勢頭,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模式。就通史性研究而言,我們將各種模式概括為以下幾類。第一類為“本體模式”,即注重傳統語言研究自身的發展演變及其規律,代表作有王力《中國語言學史》、何九盈《中國古代語言學史》、趙振鐸《中國語言學史》等。第二類為“文化史模式”,即將傳統語言研究與文化史的研究相結合,代表作有胡奇光《中國小學史》、申小龍《中國古代語言學史》等。第三類為“對比模式”,即側重將中國傳統語言研究與國外的語言學史進行對比研究,代表性成果有王建軍《中西方語言學史之比較》,俞允海、潘國英《中外語言學史的對比與研究》等。
基于本文指出的傳統語言研究具有應用導向的特點,中國語言學史或許可以再開創一種新的模式——“應用模式”,即側重從當代應用語言學的視角切入,系統總結傳統語言研究的應用性特點。
關于中國古代應用語言學史的研究,已有研究只是零星涉及,總體來說還比較薄弱。邵敬敏、方經民《中國理論語言學史》偏重理論語言學,且涉古較少;李建國《漢語規范史略》只側重應用的一個方面,即“語言規范”;于根元《中國現代應用語言學史綱》第一章《中國古代應用語言學研究》對古代的應用語言學研究情況僅略有提及。因此中國古代應用語言學史還需加強研究。
注釋
①王力:《中國語言學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9頁。
②李智明:《中國古代語言學史稿》,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頁。
③胡奇光:《中國小學史(修訂本)》,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8頁。
④華學誠:《揚雄方言校釋匯證》,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040頁。
⑤見袁仁林:《虛字說》,解惠全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44頁。
⑥宋代以后,“小學”的含義才擴大為包括文字、音韻、訓詁在內的整個傳統語言學。
⑧何九盈:《中國古代語言學史(新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239頁。
⑨顧炎武:《答李子德書》,見《亭林文集》(卷四),山隱居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