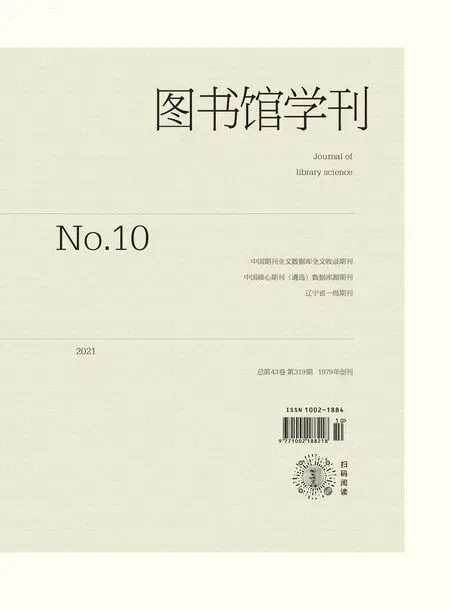基于為視障者服務的圖書館版權例外權利擴展芻論
崔 蕾
(河南省圖書館,河南 鄭州450052)
利益平衡是版權制度的基石。法律之所以在賦予權利人享有版權這種壟斷性權利的同時,又對權利人行使權利作出約束性規定,是因為要使全社會從版權制度中受益。利益平衡一般是通過一系列的版權限制與例外政策來實現的,“限制”和“例外”分別針對權利人和版權使用者而言。為視障者提供無障礙服務是圖書館的重要職責,然而圖書館制作和傳播無障礙格式版需要版權制度的授權,并且相對于其他業務和服務活動,圖書館在這項工作中需要更寬泛地使用版權的例外權利。2013年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外交會議上締結的《馬拉喀什條約》(以下簡稱《條約》)在版權限制與例外制度方面作了科學合理的設計,賦予被授權實體較為廣泛、動態化的,同時也極具前瞻性、適應性的行使版權的權利,這為我國完善視障者版權制度提供了依據,有利于發展和深化圖書館視障者服務。
1 版權例外權利與圖書館視障者服務
1.1 寬泛的例外權利有助于圖書館制作無障礙格式版
雖然從整體上看,我國圖書館開展制作無障礙格式版的比例還不高,但是這項工作已經進入了圖書館的視野,首都圖書館、佛山圖書館等還為制作無障礙格式版建立了專業化設施和設備。圖書館制作無障礙格式版涉及對復制權、翻譯權、表演權、改編權等權利的利用,而且制作一種無障礙格式版可能會涉及對多項權利的復合利用,如果圖書館完全適用授權制度,在每一次制作無障礙格式版之前都要向權利人取得授權,那么不僅不具可操作性,還會使圖書館付出高昂的時間和經濟成本,從而出現市場失靈和反公地悲劇問題。另外,視障者版權制度如果把某項權利或者某類作品排除在適用范圍之外,還會使圖書館完全沒有制作某種無障礙格式版的例外權利。比如,按照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第十二款的規定,視障者版權制度適用的只是“盲文”和“文字作品”,那么顯然圖書館不能以為視障者提供服務之理由制作有聲書和無障礙電影[1]。可以說,在我國現行法律框架內,圖書館制作有聲書、無障礙電影等只適用普通的版權限制與例外制度。更需要強調的是,嚴格來看,《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第十二款關于制作盲文的規定,也不適用于圖書館,而只適用于出版機構,在我國法律制度中,圖書館和出版機構并不是同類型的主體。
1.2 寬泛的例外權利有助于圖書館提供無障礙格式版
圖書館制作無障礙格式版的目的,不是為了單純的保存或者陳列、展覽,而是為了向視障者提供服務。為此,應使圖書館在版權制度中享有傳播無障礙格式版的權利,包括發行權、信息網絡傳播權等。如果圖書館能夠成為被授權實體,那么按照《著作權法》第十二條第十二款、《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六條第六款的規定,圖書館享有向“盲人”傳播“盲文”“有聲書”的發行權、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例外權利,但是由于權利范圍被限制,且不說這些規定不適用于對大字本、無障礙電影等無障礙格式版的傳播,即便是對“盲文”“有聲書”的傳播也會受到制約。比如,在數字技術條件下,權利人出于保護自身利益的考量,往往對作品采取技術保護措施,而圖書館傳播無障礙格式版又可能必須對作品解密,所以應當在視障者版權制度中享有解密權。按照《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圖書館為“盲人”提供“盲文”“有聲書”享有的解密權只適用于通過網絡獲取的作品,意味著圖書館對線下無障礙格式版的傳播不能對原作品或者無障礙格式版的技術措施擅自解密,如此即便是視障者能夠獲得無障礙格式版也不能利用,這不符合版權制度關于權利窮竭原則的規定。另外,在我國現行版權制度中,圖書館也不享有跨境交換無障礙格式版的例外權利。
2 《馬拉喀什條約》中版權限制與例外制度的特點
2.1 版權限制范圍的基準性
《條約》立法討論中,版權限制和例外的范圍是爭論最為激烈的焦點問題之一。因為,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文化、教育水平不同,視障者群體數量不同,無障礙格式版的生產和提供情況也不同,而版權限制與例外的范圍的確定將影響其各自的國家利益。但是,從滿足視障者基本的無障礙獲取信息的原則出發,《條約》為締約國的視障者版權立法提出了最基礎的標準,強制要求各締約國達標。按照《條約》第二條第(一)款的規定,凡是屬于“文字、符號和(或)相關圖示的作品”都在版權限制與例外制度適用之列,而且按照《條約》第四條第一(一)款的規定,對這些作品必須進行復制權、發行權、信息網絡傳播權的限制。這些規定被學術界稱之為視障者版權限制與例外的“最低標準”,是締約國必須履行的國際立法義務[2]。為了實現“最低標準”的立法目的,《條約》第四條第二款還規定,被授權實體可以出于向視障者服務的需要,在制作和傳播無障格式版中“采取任何中間步驟”,也可以對原作品進行“必要的修改”。鑒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被授權實體在版權制度中從事跨境交換無障礙格式版的法定權利不明確,《條約》第五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如果無障礙格式版屬于合法制作與獲得,那么應通過締約國的國內立法,允許被授權實體將無障礙格式版向境外被授權實體或者視障者直接提供,其前提條件是在跨境傳播和交換之前,無障礙格式版來源國的被授權實體不知道或者沒有合理的理由知道該無障礙格式版將被用于為視障者服務之外的目的。
2.2 版權限制范圍的動態性
既然是“最低標準”,那么就意味著視障者版權制度中權利限制與例外的范圍具有動態性、可擴展性。同時,為了平衡不同締約國在權利限制、適用作品、無障礙格式版跨境交換、商業供應檢驗法、版權補償金等問題上的不同訴求,應允許其在“最低標準”的基礎上根據國情開展自主立法,這也是國家主權的象征[3]。《條約》第十二條規定:締約各方承認,締約方可以依據該締約方的國際權利和義務,根據該締約方的經濟條件與社會和文化需求,對于最不發達國家,還應考慮其特殊需求、其特定的國際權利和義務及這些權利和義務的靈活性,在其國內法中為受益人實施本條約未規定的其他版權限制與例外。該條款同時規定:本條約不損害國內法為殘疾人規定的其他限制與例外。這就是《條約》中著名的“發展條款”,按照該條款的要求,締約國對是否將電影作品納入限制范圍、是否對表演權和翻譯權提供限制、是否在視障者版權制度中為“商業供應檢驗法”立法,或者是否制定版權補償金制度等行使自由裁量權。《條約》的“發展條款”對締約國健全視障者版權制度,保障視障者無障礙權益具有重大意義。目前,部分國家已經按照《條約》第十二條“發展條款”的要求,在遵循版權限制與例外設置“三步檢驗法”的前提下,在“最低標準”之外針對視障者獲取和利用無障礙格式版建立了新的版權限制與例外規則。比如,作為世界上第一個批準《條約》的國家,印度《版權法》第五十二條第(1)款(zb)項規定,無障礙格式版適用于任何作品,而且可以被任何類型的“殘疾人”獲得,而不僅僅限于“視障者”。
3 制約圖書館擴張為視障者服務例外權利的立法因素
3.1 立法的傾向性
版權立法的初衷是保護權利人的利益,但是最終目的是要維護公共利益。視障者是人類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其無障礙權益得到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國際人權憲章的認可,而聯合國《殘疾人機會均等標準規則》也提出了視障者享有在獲取信息和服務上的“機會均等原則”和“同等權利原則”。我國《殘疾人保障法》制定了“無障礙條款”,《無障礙環境建設條例》專門設立了“無障礙信息交流”的規定。我國《公共圖書館法》明確要求圖書館為視障者提供適合其需要的文獻信息、無障礙設施設備和服務。中宣部、文化部、中國殘聯等部門聯合出臺的《關于加強殘疾人文化建設的意見》要求各級公共圖書館建立視障者閱覽室,配置盲文讀物及相關設備。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殘疾人一個也不能少”的戰略目標[4]。在此背景下,當權利人的經濟利益與視障者的無障礙權益相沖突時,應堅持有利于視障者獲取和利用無障礙格式版的立法價值取向,一切從視障者的信息接收特點出發,完善版權制度。
3.2 規則的復雜性
實踐表明,法律規則越簡單、明晰,就越有利于圖書館行使權利,越有利于基礎業務和服務工作的開展,同時越有利于圖書館厘清法律的邊界,防范和化解侵權風險。反之,如果法律規則過于繁鎖和復雜,或者模糊不明,那么就會增加圖書館正確理解法律內涵的難度,還會加大立法的不確定性,使圖書館面臨較大的侵權責任風險。比如,《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條約》)第七條專門為圖書館等文化遺產部門設立了合理使用條款,但是由于限制條件過多,而且許多重要問題不明,所以增加了圖書館行使權利的困難。在此種情形下,為了防止侵權,許多圖書館不得不放棄對權利的行使,最終使法律規定流于形式。所以,我國視障者版權制度應盡可能作到規范、簡單、量化、限制條件少,對于一些法律概念要作出專門的釋義,對于不能量化的問題同樣要提供原則性的判斷標準。比如,應對圖書館等被授權實體制作和傳播無障礙格式版可以“采取任何中間步驟”予以解釋。又比如,應明確提出圖書館等被授權實體應盡的法律義務,使圖書館能夠合理地防范跨境交換無障礙格式版的侵權風險。
3.3 制度的合理性
任何一項法律制度的建立,都應有其法律依據。沒有充分法律依據而建立的制度,既不科學,又不合理,在實踐中不僅起不到好的立法效果,甚至難以執行[5]。比如,《條例》第七條為了保護權利人的利益,對圖書館行使權利設置了一項約束性規定,即“商業供應檢驗法”,這也是我國版權合理使用制度中惟一適用“商業供應檢驗法”的情形,是對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家法律的借鑒。但是在實踐中卻遭到圖書館界的極大詬病。其一,其不合理地加重了圖書館的法律義務,因為圖書館不是市場管理部門,既無開展市場調查的專門人才,又無這方面工作的經驗。其二,立法對“商業供應檢驗法”中涉及的“市場上無法購買”“只能以明顯高于標定的價格購買”等問題規定不明,圖書館無法把握法律界限。其三,權利人在“商業供應檢驗法”的執行中沒有承擔任何法定義務,這是與美國、澳大利亞國家法律規定的不同。《條約》第四條第四款將“商業供應檢驗法”的立法權交給締約國,如果我國在視障者版權立法中確認其地位,那么就必須從科學性、合理性、可行性等方面作出周密的制度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