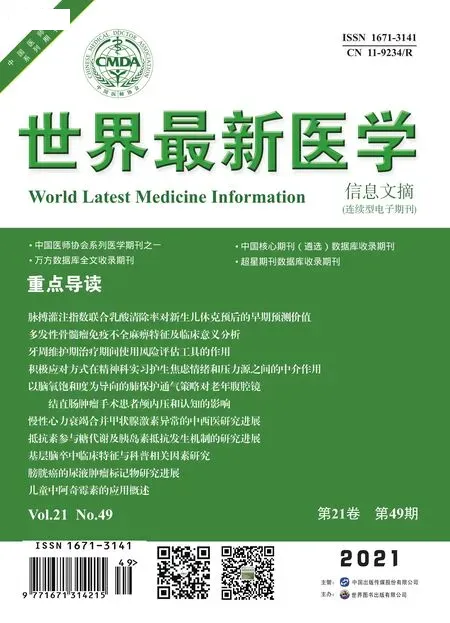抗生素相關性腹瀉的中醫治療研究進展
鄭杉,劉毅
(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天津 300381)
0 引言
抗生素相關性腹瀉(Antibiotic associated diarrhea,AAD)是指臨床上應用抗生素后出現的與抗生素使用相關的腹瀉,是當前在臨床上使用抗生素病人群體中常可見到的一種并發癥。發生率為接受抗生素治療患者的5%-25%,幾乎任何一種抗生素都能引起腹瀉的發生,尤其屬使用抗厭氧菌類藥物的病人多發[1-2]。
嚴重感染發生時,患者胃腸功能紊亂,腸蠕動減慢,消化液分泌減少,腸黏膜屏障受損,腸道的免疫功能下降,導致腸道正常的菌群環境被破壞,而造成菌群失調。在此基礎上,醫源性廣譜抗生素的應用更進一步打破了腸道菌群的生態平衡,而導致腹瀉的發生。AAD輕癥僅表現為腹瀉,而重癥可表現為假膜性結腸炎,甚至出現中毒性巨結腸等一系列嚴重并發癥。目前西醫針對AAD的治療方案主要有停用廣譜抗生素、維持水電解質平衡、使用微生態制劑、嚴重者需要手術治療或采取糞便移植療法等,但臨床療效尚不滿意。臨床處理此類患者時,往往因為患者感染嚴重,不能簡單地依靠停用或更換抗生素來控制AAD的發生,因此目前大多使用蒙脫石散止瀉,同時予益生菌調節腸道菌群的治療方案,這樣的處理確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腹瀉癥狀,但對于重癥腹瀉或者一些伴隨癥狀(如胃脘不適、食欲不佳、倦怠乏力等)改善并不明顯。由此可見,西醫治療并不能完全解決它給患者帶來的困擾。因此針對AAD的有效治療及預防措施亟需我們深入研究探索。
近年來,中醫藥在抗生素相關性腹瀉的治療方面已經進行了一系列研究,并從中醫辨證論治的角度給出了治法方藥可供臨床參考。通過整理總結此類文獻資料,現將有關文獻綜述如下。
1 中醫研究進展
1.1 病因和發病機制
傳統醫學中沒有“抗生素相關性腹瀉”這個疾病名稱,根據其臨床癥狀,可將其歸于“泄瀉”病。在《素問·臟氣法時論篇》中有記載:“脾病者,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3]脾胃為氣血生化之源,脾失健運,則運化無權,濕濁內生,如果脾胃升降功能失常,則水谷精微不能正常輸布。清氣在下,則生飧泄。
當前醫家普遍認為,抗生素為苦寒瀉火之品,若濫用抗生素,或長期大量應用廣譜抗生素,易導致脾胃臟器虛損,運化功能失常。高齡患者更易發生本病,究其原因,可能是年老臟器功能本就虛弱,陽氣不足,命門火衰,不能輔助脾胃腐熟水谷。水谷不化,則清氣下陷,遂成泄瀉。
1.2 辨證分型
目前AAD的中醫辨證分型尚未有統一標準。眾醫家從不同的角度對AAD進行了辨證分型,比如李云虎等[4]將本病根據患者臨床癥狀、舌脈分為3個證型,分別是脾胃虛寒證、腎虛失固證、虛實夾雜證。胡強[5]在其研究中將本病分為脾腎陽虛證和濕濁內阻證。沈志華[5]收集88例病人,進行中醫辨證,其中40%為脾虛濕盛證,31%為濕熱蘊結證,19%為脾胃虛寒證,10%為其他證型。袁玲[6]通過分析60例AAD患者臨床癥狀及四診信息,發現其中脾胃虛弱證、脾腎陽虛證較多見,占78.33%,而濕熱證及寒濕證病人較少,占比為21.66%。
通過總結整理,可見大家對于本病的致病因素基本統一為“熱”“濕”“瘀”。并且眾醫家更傾向于采納脾腎陽虛、血瘀內生、濕熱內生的辨證分型標準。其中以脾腎陽虛、脾胃虛弱、濕熱蘊結證最為常見。
1.3 中醫治療方案
胡強[7]選取40例重癥肺炎合并AAD患者,對照組僅予西藥干預,具體為甲硝唑400 mg+金雙歧2片 Tid,治療組中辨證為“脾腎陽虛”者,予加味胃關煎100mL Q6h,辨證為“濕邪內阻”者予人參敗毒散100mL Q6h。結果顯示治療5天后在中醫證候(大便次數、大便形狀、腸鳴音、乏力疲倦等)評分方面,治療組改善情況明顯優于對照組。治療2月后進行隨訪調查,治療組患者AAD復發率及住院費用均較對照組低。岳愛霞[8]選取66例脾腎陽虛型AAD老年病人,在內科對癥治療的同時,對照組予金雙歧2g Tid,治療組予腸寧湯100mL Q6h,治療2周后對比兩組病人,發現治療組總有效率明顯優于對照組。孫娜娜等[9]應用姜芡止瀉湯治療60例脾腎陽虛型AAD病人,發現姜芡止瀉湯治療脾腎陽虛型AAD療效顯著,在患者臨床癥狀改善方面明顯優于單純西藥治療。利春紅[10]選取腦卒中合并肺炎,并反復使用抗生素引起AAD的老年患者80例,在內科對癥治療的基礎上,對照組予金雙歧420 mg+蒙脫石散3g Tid,治療組予附子理中湯加味結合神闕穴、氣海穴、關元穴、大腸俞等穴位艾灸療法。治療2周后,在中醫癥候評分改善及治療總有效率方面,治療組均明顯優于對照組。袁玲[11]選取56例中醫辨為“脾胃虛弱”證AAD患者,對照組予雙歧桿菌四聯活菌片3片 Tid,治療組予參苓白術散加味聯合神闕穴艾灸療法,結果表明治療2周后,參苓白術散加味聯合艾灸治療對于本病的療效優于單純西醫治療。羅勇[12]觀察了84例AAD患者,在內科對癥治療的基礎上,對照組予甲硝唑400mg+金雙歧1g Tid,治療組采用中藥敷貼法。選取肉桂、附子、干姜、白術、黨參、炙甘草、小茴香、白芥子、細辛,并加入姜汁調和制成敷貼,陽虛證患者選擇足三里、中脘、天樞、神闕、大腸俞等穴位;痰濕型患者選擇足三里、神闕、脾俞、豐隆、至陽等穴位敷貼2h Qd,5日后進行評估,發現治療組患者癥狀評分改善方面優于對照組,該研究表明中藥敷貼法聯合西醫內科基礎支持治療可提高AAD臨床療效。陳莉娜等[13]選取40例AAD患者,對照組予甲硝唑+金雙歧,治療組予神闕穴隔姜灸+中藥灌腸(中醫辨證為“脾腎陽虛”者予加味胃關煎,辨證為“濕邪內阻”者予敗毒散)。該實驗表明神闕穴隔姜灸聯合中藥灌腸在治療AAD方面療效確切,臨床上可效仿。王楠[14]分析大量AAD患者病例資料,觀察發現脾腎陽虛兼寒熱錯雜證AAD最為常見。運用《傷寒論》方“烏梅丸”對癥治療,治療效果滿意。文中還舉出現代藥理學證據,烏梅、肉桂具有廣泛抗菌作用,對多種腸道致病菌有抑制作用,并且對機體免疫系統功能有促進作用。
總結以上文獻資料,中醫藥在治療AAD時遣方用藥可歸納如下:對于脾腎陽虛型患者,治以溫腎固攝,可予加味胃關煎、烏梅丸、姜芡止瀉湯、腸寧湯等方化裁治療;對于脾胃虛弱型患者,治以溫中健脾,可予參苓白術散、四君子湯、附子理中湯等加減;對于濕熱蘊結型患者,可予葛根黃芩黃連湯清熱化濕。另外艾灸、敷貼、中藥灌腸等方法也被臨床證實有滿意療效。
1.4 中西醫結合治療
張勝睿[15]在中醫辨證指導下,納入92例AAD患者,對照組予萬古霉素或甲硝唑,聯合金雙歧干預;實驗組在對照組基礎上,將其中證屬“正虛邪犯”,表現為排水樣便者,予人參敗毒散;屬“脾腎陽虛”證,表現為排稀水泡沫樣便者,予健脾止瀉湯。治療1周后對比兩組患者癥狀改善情況,發現實驗組患者治療有效率高于對照組,且具有統計學意義,于是指出中西醫結合治療AAD患者的臨床療效確切。
高寶蓮[16]運用甲硝唑400mg Q8h+桃花湯100mL Bid治療下焦虛寒型AAD,有效緩解了患者大便泄瀉、腹脹腹痛、腸鳴、脘腹痞滿、小便不利、畏寒肢冷等癥狀。而對照組單用甲硝唑,結果發現僅部分癥狀得到改善,倦怠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痛等癥狀未見明顯好轉,于是指出中西醫結合療法由于單純西醫治療,可更加全面的改善患者癥狀。
2 小結
對于重癥感染患者,目前臨床上抗感染多采取“重拳猛擊”的方法,治療早期往往足量使用廣譜抗生素。從而導致接受抗感染治療的患者抗生素相關性腹瀉的發病率較高。然而西醫對本病治療思路較局限,方法單一,一般常予益生菌以調節腸道菌群,配合蒙脫石散止瀉,輕癥臨床療效尚可。而重癥患者采取此種治療方法療效欠佳,目前指南推薦可予甲硝唑或萬古霉素抗艱難梭菌感染,然而這些治療方案都僅能緩解腹瀉癥狀,不能改善患者脾虛導致的其他癥狀,如神疲乏力、納差等,患者臨床獲益程度仍待提高。中醫藥已在AAD的治療上取得了一些進展,中藥湯劑、敷貼、針灸、中藥灌腸等方法治療本病效果滿意,毒副作用小,中醫臨床癥狀改善明顯,預后滿意,從而間接減少患者經濟負擔。因此在中醫辨證思想的指導下,準確辨證施治,對于AAD治療乃至經濟效益層面意義重大。
3 展望
目前眾醫家對抗生素相關性腹瀉的中醫辨證分型原則尚未形成統一意見,各家都僅按照各自臨床經驗予以治療,雖然取得不錯的治療效果,但缺乏確切的理論依據。同時通過分析已發表的文章,發現各臨床試驗均為小樣本、單中心,循證醫學證據不足,對于判斷臨床效果的標準也未統一,不利于分析總結。
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應采納眾家之長,從中醫學整體觀念、辨證論治角度來考慮。爭取開展大型多中心、大樣本、隨機對照的臨床研究,盡可能更加整體全面的分析AAD的中醫辨證分型,并依法選方、據方議藥,制定全面合理的辨證體系、治療方案,為今后的臨床工作提供循證醫學證據。
祖國醫學提倡“未病先防”,因此臨床也應更加關注AAD的預防策略,若能早期識別患者的發病風險,及早進行預防干預,顧護脾胃,想必對于降低患者住院期間治療難度、住院時長、醫療費用,甚至對于患者預后的改善都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