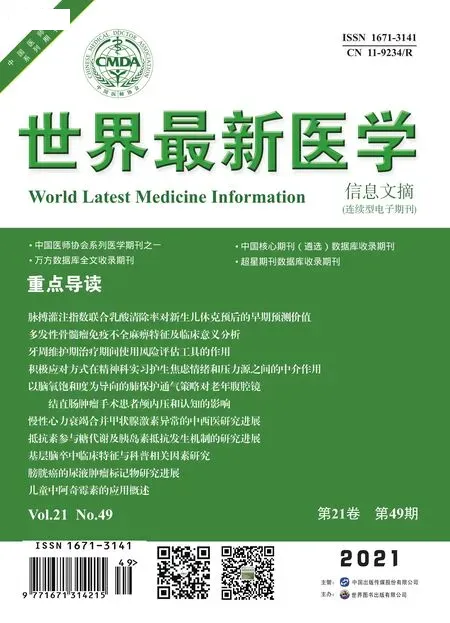從氣血辨治潰瘍性結腸炎2例
賈珧藝,王靜
(1.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國家中醫針灸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天津 300193;2.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消化科,天津 300192)
0 引言
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一種慢性非特異性炎癥性腸病,發病與飲食,遺傳等有關,典型臨床表現為大便次數增多,腹痛、腹瀉、黏液膿血便.[1]本病病程長,難以治愈,且需長期服藥,藥物副作用較大,而且極易復發,發作時癥狀令人難以忍受等問題,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
本病歸屬于“大瘕泄”“休息痢”“久痢”等,自古就有古代醫籍記載,如《難經·五十七難》“大瘕泄者,里急后重”里急后重與本病發作期常見的典型癥狀相同,又有如《諸病源侯論》“休息痢者,胃脘有停飲……其痢乍發乍止,謂之休息痢也”。這里的時發時止與本病極易復發的表現相同。發病病機為脾胃虛弱,而誘發的原因不外乎飲食,外感以及先天稟賦虛弱。如《諸病源候論》“由脾胃大腸虛弱,風邪乘之,則泄痢。虛損不復,遂連滯涉引歲月,則為久痢也”。指出素體本脾胃虛弱,加上外感風邪,終發展為久痢。而《景岳全書》指出,“若飲食失節,起居不時,以致脾胃受傷,則水反為濕,谷反為滯,精華之氣不能輸化,乃致合污下降,而瀉痢作矣”。指出飲食失節損傷脾胃,水飲與谷食中的精微物質不能運化致積而發病。
關于發病,《雜病源流犀燭》“泄雖有風、寒、熱、虛之不同,要未有不源于濕者”,《內經》“濕盛則濡泄”,由此可以看出不管何種泄瀉,其根本都是由于濕邪作祟,在UC的整個病程中,濕邪貫穿始終。而UC除了誘發原因有不同外,更有發作期與緩解期之分,每一個患者的先天稟賦及體質也有所不同,使得本病不能簡單地歸納為風、寒、熱、虛任意一種,正如《景岳全書》“凡熱痢、寒痢、虛痢皆有之,不得盡以為熱也”。
1 氣血關系與UC
“氣”與“血”是人體正常生命活動的基礎物質,源于脾胃,存在于五臟六腑。正常情況下,氣行于脈外,血行于脈內,《四圣心源·卷一·氣血原本》中指出“肝藏血,肺藏氣,而氣原于胃,血本于脾”,UC的發病之源均為脾胃的損傷,脾胃為氣血之源,脾胃損則必然出現氣血的逆亂,發作期的腹痛,里急后重等癥狀均為大腸“氣滯”的主癥,而氣為血之帥,氣滯則飲停血瘀,氣有余生熱,故形成了濕熱瘀的病理產物。正是《仁齋直指方·治痢要訣》所指出的:“痢出于積滯。積,物積也;滯,氣滯也。物積欲出,氣滯而不與之出,所以下墜里急,乍起乍止,日夜凡百余度。”所以氣血關系與UC的發作密切相關。
而每個人發病誘因不盡相同、先天稟賦體質等差異有病情輕重之分,遂可能出現氣虛血淤、氣滯血瘀、氣不攝血等不同類型的病理變化。所以使氣血和順是治療的關鍵,正如《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合》中“行血則便膿自愈,調氣則厚重自除”。
本文列舉2例從氣血角度辨治UC的經驗案例,供學習與參考。
2 病案一:氣虛血瘀
劉某,女,27歲,3月前因受涼感冒后誘發腹瀉,大便次數20-30次/天,不成形,伴較多黏液膿血,排便前腹痛腹脹,就診于天津市南開醫院,查結腸鏡:全結腸黏膜粗糙,呈彌漫性充血、水腫及大片狀潰瘍性改變,并可見假息肉形成。鏡下診斷:潰瘍性結腸炎。病理示炎性病變,潰瘍性結腸炎不除外。后住院予激素(具體不詳)以對癥治療,癥狀好轉,腹瀉次數有所減少,出院后規律服用美沙拉嗪腸溶片1g Tid進行維持治療。為求中醫診治于就診于我院脾胃科。首診時癥見:腹脹,大便7~8次/天,大便成形,伴少量黏液膿血,肛門有墜脹感,乏力,納食少,寐可,小便正常,訴自發病以來體重減輕15kg。查體:貧血貌,腹平軟,臍周輕壓痛。舌紅苔薄白,脈滑。中醫診斷:休息痢。辨為脾胃氣虛證。治法采用補氣健脾,升陽止瀉。處方黃芪20g,黨參片20g,炒白術20g,升麻5g,北柴胡 10g,當歸 10g,陳皮 10g,炙甘草 10g,醋延胡索 10g,白芍20g,炒蒲黃10g,醋五靈脂5g,薤白10g,煅赤石脂10g(先煎),茯苓30g仙鶴草20g,粉葛10g。7劑,水煎服,日1劑,每次150mL。
按:該患者發病因外感引起感冒,首襲肺衛,而在《醫經精義》中指出“大腸之所以能傳導者,以其為肺之腑,肺氣下達,故能傳導”;《證治百問》亦指出“肺氣虛,大腸亦虛,而不能禁錮,時時欲去……”肺與大腸關系密切,大腸功能的正常賴于肺的正常宣肅,故外感導致肺氣受損牽連及腸,導致其不能正常傳導,正是“肺氣虛大腸亦虛”。大腸為六腑主傳化物,以通降為和,大腸虛通降失司則易氣滯血瘀濕停發為潰瘍性結腸炎[2]。而每日20-30次的久瀉、暴泄必大傷脾胃之氣,脾胃為氣機升降的樞紐,脾胃虛不能升清降濁,正如《四圣心源》中說“脾主升清,脾陷則清氣下郁,水谷不消,脹滿泄利之病生焉”《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中“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脹”。無法上輸的精微物質等均滯留于腸中與血與濕等互相蘊結,最終形成了導致黏液膿血便的病理產物。加上脾氣虛無力行血,加重了血瘀飲停的情況,所以治療的重點在于補氣升陽,同時行氣化瘀。采用補中益氣湯作為基礎方,黃芪、黨參、炙甘草補氣健脾,使生氣之源充足;陳皮、白術、茯苓健脾燥濕化痰,同時與黃芪、黨參等合用可同補肺氣,再結合北柴胡、升麻、粉葛等風藥升陽止瀉,使得氣能夠循路而行,氣行則血不淤滯;白芍酸收斂陰,以調和風藥過于辛散之力,同時緩肝養血;醋延胡索、炒蒲黃、薤白、當歸活血化瘀助氣行血;仙鶴草、煅赤石脂澀腸,止血。
3 病案二:氣滯血瘀
趙某,男,24歲,5月前因飲食不慎出現排黏液膿血便,3-4次/天,不成形,排便前腹部隱痛不適,遂就診于天津市人民醫院,查結腸鏡:以潰瘍性結腸炎為首要考慮(E1 活動期),病理:(直腸黏膜活檢)黏膜急慢性炎癥,不除外潰瘍性結腸炎,后服用美沙拉嗪腸溶片 1g Tid及美沙拉嗪栓 0.5g bid外用治療,大便仍每日3次,偶見鮮血。1月前因大量進食生冷飲料及燒烤,癥狀加重,大便6-7次/天,可見鮮血量較前增多,不成形,排便前腹痛,就診于天津市人民醫院查結腸鏡:以潰瘍性結腸炎為首要考慮(E3 活動期),現為求中醫診治就診于我院脾胃科。就診時癥見:大便6-7次/天,可見鮮血量較前增多,不成形,排便前腹痛,時有便意,里急后重,納少,食后腹脹,反酸,口苦,乏力,近10天消瘦10kg。查體:腹平軟,上腹及左側腹部壓痛,腸鳴音活躍。舌紅,苔黃厚膩,脈滑。中醫診斷:大瘕泄病,辨為腸道濕熱證。治以清熱化濕,調氣行血。處方:白芍20g,黃芩片10g,黃連片6g,炒白術20g,肉桂6g,白頭翁 10g,北敗醬 10g,地榆 30g,黨參片 20g,白及 5g,炙甘草 10g,粉葛 30g,大棗 3個,茯苓 30g,薏苡仁 30g,炒薏苡仁 30g,山藥 30g,鹽車前子 20g,麥芽 30g,海螵蛸 30g,7 劑,水煎服,日1劑,每次150mL。
按:該患者發病因飲食不節發病。《景岳全書》說:“若飲食失節,起居不時,以致脾胃受傷,則水反為濕,谷反為滯,精華之氣不能輸化,乃致合污下降,而瀉痢作矣。”飲食不節致脾胃受損,脾胃為氣機升降的樞紐,受損一則氣無法正常運行而發生氣滯,二則水飲與精微無法傳輸,且二者性屬陰,均下沉于腸道。水飲聚濕生痰,氣滯有余化火,腸道中的血液無氣行之,同濕痰火蘊結形成致毒的病理產物。日久熱入血分,形成氣滯血瘀,致腸絡失和,血敗肉腐而下痢赤白。治療以調氣行血,清熱解毒祛濕為主。以芍藥湯為基礎方,粉葛味辛能升散,升陽可起凝滯于胃腸之氣,氣行而血不滯,合肉桂、黨參來鼓舞氣血生長,從而行氣行血;黃連、黃芩苦寒,清熱燥濕,與白頭翁、敗醬草、車前子合用,清熱解毒燥濕之力強,再聯合地榆、白及等涼血止血的澀腸藥物,共同清利濕熱,行滯止瀉。
4 結語
UC作為一種難治性疾病,對于本病關鍵的治療在于遵循“既病防變”的思想防止和減少發作期的出現,避免接觸誘發因素;對本病的治療應當以調氣和血為主要基礎,臟腑調和,瀉痢自止[3]。在此基礎上再根據寒熱虛實的不同進行辨治,發作期以清熱化濕祛瘀為主,緩解期則側重于補虛,以健脾益腎為主[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