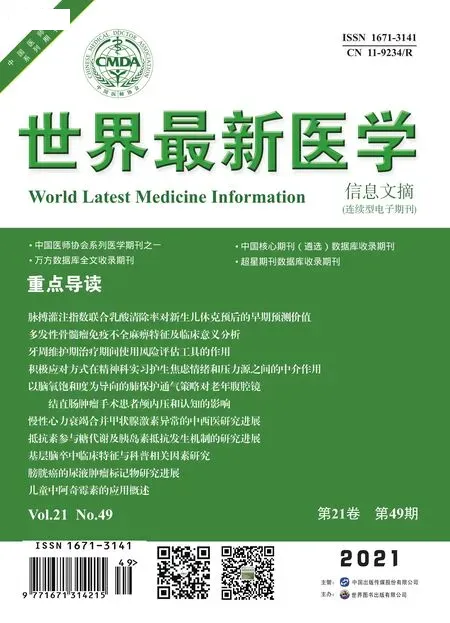基于五臟生血理論淺析血虛致哮
唐雙,楊繼,王強
(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天津 300250)
0 引言
支氣管哮喘是臨床上的多發病、常見病,并且在全世界范圍之內,其發病率逐年增加。其典型的臨床表現是重復發生的喘息、胸悶、氣急、咳嗽及喉間哮鳴音,屬于中醫“哮”病范圍。一般認為,哮喘發生的病因病機為宿痰伏肺,受外邪侵襲、飲食不節、情志不遂、體虛勞倦等要素誘發,伏痰隨氣而升,相互搏結,礙阻于氣道而致氣道痙攣,肺失宣降而致氣急喘促,病情纏綿難愈。筆者認為五臟皆可生血,五臟生血的功能失調亦會招致哮喘的發作,以此豐富中醫哮喘的病因病機,為臨床診治提供新的思路。
1 歷代醫家對五臟血虛致哮的認識
有關五臟生血的闡述早在《內經》中就有所提及,五臟各自的生血功能的正常發揮與否,對哮喘的發作及轉歸亦起著重要作用,哮喘發作的病位在肺,亦和五臟緊密相關,在《素問·咳論》中載道:“五臟六腑皆令人咳,非獨肺也。”首次明確提出咳嗽與五臟相關,可見哮喘治療重治肺卻不止于肺。《素問·調經論》中云:“人之所有者,血與氣耳。”血是形成人體和維持人體生命活動的根本物質之一,精血運轉于周身,內至臟腑,外達肢節,周而復始并充盈敷濡于肺,若五臟生血功能失節,血虛失養,則陰津乏源,澀肺宇之脈,最終金失血養,而致肺失濡養或瘀阻肺絡,肺不能宣發肅降,從而誘發哮喘。北宋《太平圣惠方》中認為肺血虧虛,氣失所主,壅聚于肺,肺氣升降失常則發為咳喘。明代《醫學入門》認為哮喘血虛者,陽無所依托而上奔,以至哮喘發作,并選用四物湯倍芍藥,輔以人參,五味子治療。清代唐容川在《血證論》中云:“血虛則火盛津傷,肺葉痿而不下垂,故氣不得降,喘息鼻張,甚則鼻敞若無關欄。”這一觀念指出了血虛致哮的重要病機。清代吳儀洛在《成方切用》一書中也指出婦人產后血海易虛,故氣喘、呼吸困難等危癥容易發作。當代醫家李今也庸認為失血是導致咳喘的病因之一,并擅長用百合固金湯加減治療喘證。現代研究[1]也發現貧血會導致相關呼吸系統癥狀,譬如胸悶、氣喘、呼吸艱難等,因為血紅蛋白降低,攜氧量不足,以致組織缺氧。肝藏血,主疏泄,能調理全身之血,心主血,取中焦致精汁并奉心化赤。脾胃者,氣血生化之源,與心共奏運轉血液之功,肺朝百脈,主治節,生宗氣,布血于周身,腎主藏精,精血互化,以下分別從五臟生血角度淺析血虛導致哮喘。
2 肝生血的生理基礎
肝五行屬木,主升發,與春氣相通應,充滿了生機,肝借其生發之性,化生氣血而養五臟,表明肝亦可生血。再有中焦脾胃之水谷精微輸送全身,一部分轉送至肝膽,如《素問·經脈別論篇》載:“食氣入于胃,散精于肝,淫氣于肝。”肝主疏泄,并輔助氣血化生,兩者相輔相成。
3 肝血虛致哮的病機相關性
血虛易生風,易受外邪引動。肝無血藏則無以制衡肝氣,肝血虧虛進一步發展則致血虛生風,風氣通于肝,肝氣和風氣實則同氣相求,同源而生,正如“外風引邪,致喘發作;內風急作,加劇哮喘”,痰隨肝風而升,相互搏結,以至氣道痙攣,誘發哮喘。再有虛風內伏于易感之體,因而更易受到外邪的引動,內外合邪上擾于肺,致宣發肅降失節,津液輸布不能,故而積液成痰,風痰夾雜則氣道痙攣。肝血虧虛則不能制肝氣,肝風內生,肝火上炎,木叩金鳴。此外,“血虛咳嗽之脈……左脈弦數,肝火煎熬,兩尺細數,腎虛水竭”,若有腎水盜肺金之母氣,又可轉歸為金不制木之患。
另外,脾胃主運化,肝主疏泄,兩者密切相關,肝血不足致疏泄失常,病及脾胃之運化而影響哮喘的發生、發展。肝木克脾土則氣血生化乏源,脾虛損及肺氣,土不生金而致正氣不足,終成“哮喘體質”。
肝調達氣機與哮喘的相關性。肝肺為氣機升降之通道,左升右降,如龍虎回環,肝血不足,則肝疏泄失常,肝氣易郁而致升發不及,進而肺氣失宣降,津液停聚于肺,積液成痰,誘發哮喘。再有肝疏泄功能失衡,氣失調暢,氣病致血病,肝藏血不足則致血虛,脈道無血充盈則致血瘀,痰瘀互結,誘發哮喘。
另外,“肝藏血,血舍魂”。“魂”即精神或情緒,魂之安藏必依賴于肝之藏血,肝有血藏,魂則守舍,人之神志等活動就有了物質保障。若肝藏血不足,魂失所藏,則易引起情志異常,而情志病變進而誘發或加重哮喘。
4 心生血的生理基礎
《內經》曰“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最早提出了心生血的理論。并且在后世臨床治療中,“心生血”的理論也一直被運用,《內經》中對于“心生血”的闡釋,并非虛設,而是有待考據的[2]。中醫理論以為,“心”對血液生成起著主導作用。第一,奉心化赤。如《侶山堂類辯》所言:“血乃中焦之汁,流溢于中以為精,奉心化赤而為血。”心陽通過溫化水谷精微,奉心化赤而為血。第二,心臟除了本身能夠生血外,亦可協助激發它臟生血。唐容川在炙甘草湯中以參、棗、姜、草,發揮中焦取汁之用,桂枝入心化氣,采其奉心化赤之用;地黃、麻仁滋補肝腎,精血互化;麥冬、阿膠補肺生血。此方以促心生血為主,兼調他臟,心生血功能減弱,則協助它臟生血的功能也降低。
5 心血虛致哮的病機相關性
氣為血之帥,血為氣之母,久病的哮喘患者,血虛及氣,導致心肺氣虛,心氣虛則則推動無力,血虛瘀阻;肺氣虛則宣發肅降失節,肺失通調則痰飲內停,故礙心行血,痰瘀互結,終成窠臼,此為哮喘纏綿難愈,屢次發生之宿根。心主血,肺氣依賴于心血的充養,肺吸人之清氣亦須以血液為載體,并依靠心的行血功能輸養于全身。若有哮喘久病及心者,心之氣血陰陽不足,脈道不充,氣行無力,以至脈道瘀阻,進而影響肺之呼吸[3]。對于臨床上CVA久治不愈者,多少伴有精神上的焦慮或煩躁,擔心疾病難愈,如此日積月累耗傷心營之血,導致心火妄動,正常情況下,肺金受到心火的制約,兩者是動態平衡的,而心火最易擾動肺金,從而引起肺部疾病,王檀教授根據自己的多年的臨床經驗,提出哮病主于火的新理念,并且論證了心火上炎致喘的重要性[4]。
6 脾生血之生理基礎
《靈樞·決氣》云“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中焦之胃受納食入之水谷,脾運化水谷之精微并化生為氣血,并輸布于五臟六腑。在《景岳全書·傳忠錄·臟象別論》中也有記錄“血者水谷之精也,源源而來,而實生化于脾”,均表明了脾化生氣血之功。脾也主統血,然其統血之功需依賴于氣的固攝,正因脾能生血故脾可統血,兩者是密不可分的。
7 脾血虛致哮的病機相關性
清代何夢瑤認為:“飲食入胃,脾為運行精英之氣雖日周布臟腑,實先上輸于肺,肺先受其益,是為脾土生肺金。”故脾胃運化水谷之精氣,首先上輸濡養于肺,如若脾生血功能減弱則肺失濡養,肺氣虛弱導致宣發肅降失調,津液不歸正化,聚濕生痰,遇外邪誘發則為哮喘。《素問·五臟生成》曰:“咳嗽上氣,厥在胸中,過在手陽明、太陰”,由此可見,脾胃亦能成為哮喘發病之根。脾胃虛弱則津液停滯不行,運化失司則聚濕為痰,根藏于肺,成為哮喘發生之宿根。此外,脾胃所化之水谷精微也影響著宗氣的生成,自然之清氣與水谷精微合而為宗氣,宗氣助肺司呼吸,宗氣不足則加重哮喘的發生。現代醫學也研究發現,哮喘的發病主要與過敏有緊密關聯,臨床發現,過敏體質是由于肺脾氣虛、宗氣虧虛、氣機失調所導致,宗氣走息道,貫心脈,肺脾是生成宗氣的源泉,宗氣不足則會發展為過敏性體質[5]。
另外,脾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脾的生血功能正常則機體所需之營養物質源源不絕。正所謂“正氣存內,邪不可干”“四季脾旺不受邪”,因而脾之生血功能旺盛對人體正氣的強弱有著直接的影響,脾虛則無力抵御外邪侵襲,外風引邪,致喘發作,故“哮證扶正應以扶脾為先”。
8 肺生血的生理基礎
肺主司一身之氣的生成和運行,《素問·五臟生成篇》言“諸氣者,皆屬于肺”,《素問·六節臟象論篇》“肺者,氣之本”,而氣參與并促進血液的化生,故肺臟在血液的生成中發揮重要作用。《靈樞·營衛生會篇》云:“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莫貴于此。”故只有肺臟協同諸個臟腑,才能將血化生為有用之血以營養周身[6]。津血同源,兩者由水谷精微化生,互滋互生,津液是血液的物質基礎之一,也是重要組成部分。如《靈樞·癰疽篇》云“津液和調,變化而赤是謂血”,唐容川言“肺為華蓋,肺中常有津液”,此為津液生血。
9 肺血虛致哮的病機相關性
9.1 血為氣之主,血虛則肺氣宣降不利
肺為血臟,血屬陰,主靜;氣屬陽,主動,血能載氣,血能養氣,肺血虧虛則肺氣不降。《太平圣惠方》道:“夫產后虛喘者,由臟腑不和,氣血虛傷……血沖于肺,氣與血并,故令虛喘也。”《證治準繩》有“因產所下過多,榮血暴竭,衛氣無主,獨聚肺中,故令喘也”。可見,咳血、失血會引發咳喘,“血為氣之守”,肺血虧虛則致肺氣不足,氣無所主則肺氣不得宣降而引發咳喘。現代研究也發現,在臨床診治哮喘中予以養血之法,可顯著提升臨床療效,并且在通過研究后發現,養血方(白芍、川芎、熟地黃、當歸)可顯著提高血清中IgG、IgA水平 (P<0.01),改善 FVC、FEV1.0及 MMF(P<0.05)的功能,可見肺血虛也是引起哮喘的重要原因之一[6]。
9.2 血虛衛外不固,易受外邪侵襲
血虛或因損耗過度,如氣滯血瘀而致肺血虛者、咳血、外傷、月經過多,手術出血、多產、產后失血等,或因生成不足,或者兩者皆有,皆可出現血虛的病證。血能養氣載氣,血虛則衛外不固,容易遭受邪氣的侵襲,外邪是誘發哮喘的重要原因之一,外邪觸發宿根以至哮喘發生[7];有研究發現,貧血的兒童免疫力下降,對病原體的抵抗力降低,易患各種感染,誘發哮喘發作,故而如何預防外邪侵襲成為減少哮喘發作的重要一環。
9.3 瘀血留滯,是為成因
瘀血是血液運行不暢而形成的病理產物,其形成與肺關系密切。肺朝百脈,主治節,輔心行血,肺血虛日久,久病必累及血絡,血枯則不榮,脈道不充則血行不暢而致瘀[8],唐容川在《血證論》中言:“內有瘀血,氣道阻塞,不得升降而喘。”《金匱要略》又言:“經為血,血不利則為水”,指出血行不暢會導致水液代謝失常,以至痰水產生,痰為生瘀之基,痰留于肺則氣血津液宣降失常,間接產生瘀血,瘀可釀痰,瘀血阻礙津血互化或正常運行,故聚而生痰,痰瘀互為因果,痰瘀膠結,阻滯于氣道,誘發氣道痙攣而出現哮喘。
肺血虛證,可單獨出現,也可與它臟血虛并存,如肺脾血虛、心肺血虛。值得注意的是,津血皆屬于陰,肺血與肺陰津常相互影響,相兼發病,肺血虛證常伴有肺陰虧耗。故肺血虛證的病變特點之一是與肺陰津虧虛并存,二者常相兼為病,難以截然分開。
10 腎生血之生理基礎
腎主藏精,為封藏之本、精之處。《素問·上古天真論篇》載“腎者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精能化血,是化生血液的主要物質,張介賓也以為“腎為精血之海”。在中醫理論中,精血互化,精血同源,腎精可化為髓,髓充于骨亦可化為血。此外,腎也可輔助它臟生血,如《張氏醫通》云“精不泄,歸精于肝而化清血。”張介賓言:“腎之精液入心化赤而為血。”可見腎對血液的化生起著重要作用,諸多用來治療哮喘的名方如蘇子降氣湯、金水六君煎、貞元飲等,都有熟地、當歸等養血上品。臨床上的實驗研究也表明,通過補腎填精法能夠影響造血干細胞的增殖與分化,促進造血功能而“化血”[9]。
11 腎血虛致哮的病機相關性
11.1 精血同源,互滋互化
《諸病源侯論》曰“精者,血之所成也”。腎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反之,若五臟六腑之血虧虛,則腎藏之精不足,精血難以互生,則致諸疾叢生。“正氣存內,邪不可干”,若有小兒稟賦不足,先天之精不足,影響臟腑的功能活動,腎精虧虛則氣不歸根,肺失宣降,而先天不足則機體抗邪能力降低,“肺為嬌臟、最易感邪”,故易誘發哮喘。腎藏后天之精,來源于五臟六腑,如難治性哮喘反復發作,影響肺之生理功能,再加上其它病理因素的形成,如痰、瘀等,亦可導致五臟之精損耗,終致腎精不足,故腎精不足與哮喘發作相互影響[10]。
此外,“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腎精不足,體內正氣虧虛,人體對疾病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會相應下降,外界環境稍有變化則易誘發哮喘。
11.2 腎為氣之根,血為氣之母
血為氣陽之母,血之所以可以化氣,一則因為氣依附于血而存在,二則因為與氣生成有關的肺脾腎等臟腑同樣需要血的滋養方能化生成為人體之氣,故“血旺則氣旺,血盛則氣盛”。正如臨床所見,腎疾久病血虛之人,如西醫腎性貧血等,多有氣虛之象,故而治療之時多以補血益氣之品同用。腎為氣之根,主納氣,腎藏血不足,氣失攝納,致氣不歸根,則呼吸不合,氣機出入升降失常,趙獻在《醫貫》云:“真元耗損,喘出于腎氣之上奔,素日若無病,但覺氣喘,非氣喘也,乃氣不歸元也。”若有腎血虛曠日者,津血乏源則脈道滯澀而易形成瘀血,痰瘀互結致氣道狹窄,又可因血不榮脈而致氣道痙攣。
此外,“隱秘性腎虛”一直存在于哮喘發作期和緩解期,采取統籌補腎益氣法醫治,發時治肺兼顧腎,平時要治腎兼顧肺,可降低氣道高反應性,減輕氣道炎癥和氣道重塑[11]。“痰”的產生亦與腎緊密相關,腎氣虧虛則肺、脾失腎陽之溫煦,使得肺失通調、脾失健運,伏痰內生。俞景茂也認為腎虛是哮喘痰飲形成的根本所在,腎之氣血陰陽不足則致肺脾氣虛,運津失司,衛外不固則哮喘頻作[12]。
12 小結
人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五臟的重要生理功能都參與了血液的生成,五臟協同,方可化生一身之血。五臟皆可生血,五臟血虛亦會導致哮喘發生,諸多醫家在臨床診治時以“痰”為哮喘主要病理要素,痰與瘀關系密切,在醫治時多以活血化瘀之法,以期去除哮喘之宿根,哮喘涉及多臟,往往虛實挾雜,五臟血虛致哮這一病機也應當得到重視,對于血虛所導致的哮喘,應用補血養血之法為重要前提,助推五臟生血功能的發揮,在哮喘臨床治療中亦可提高臨床療效,筆者認為從血虛辨治哮不失為一種新的有效的辨治思路,有可能獲得我們意想不到的滿意療效。
13 討論
血虛之證在《中醫診斷學》主要提及了心血虛、肝血虛、心肝血虛等,卻少有論及肺血虛、腎血虛、脾血虛;歷代文獻也同樣對肺脾腎三臟血虛少有論述。但并不是不存在。從生理上來看,人體血液的生成與五臟有關,且與脾腎更為密切。脾胃者,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脾病則血之化源不足,則何以不產生脾血虛之證?腎主藏精,主骨生髓,髓充于骨乃化為血,腎精不足,精血轉化不能,亦可在臨床上形成腎血虛的病理改變。肺主一身之氣,周身之精微物質在肺氣參與下化生為血,并輸布于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以此保證人體正常生理功能,故肺氣虧虛而致不能化生血液,出現肺血虛也是符合邏輯的。
結合現代醫學,腎性貧血、肺性貧血、脾性貧血也并非罕見,其中腎性貧血最為常見。研究發現,血虛證患者的血紅蛋白含量與血虛證的程度和癥狀出現率存在一定關系,即血紅蛋白含量越低,血虛證的程度與癥狀出現率越高[13],貧血是反復哮喘發作的獨立危險因素,目前尚不能將其與中醫臟腑理論等同,但是它們之間仍有不少共性。如慢性腎小球腎炎患者,由于腎臟損害,其分泌的紅細胞生成素減少,則會導致貧血,同樣肺臟、脾臟本身的病變也可以出現貧血。因而血虛之病,不能僅局限于心、肝兩臟,應是五臟共有。
《內經》之五臟生血理論超越了現代西醫的邏輯范圍,本質上而言,五臟之“血”是指血中精微,是生命的源泉所在,“血”于五臟化生并濡養本身,從而保證肺宣發肅降、通調水道功能的正常運轉。故筆者認為五臟生血不足導致血虛致哮這一病機應得到大家重視,這不僅能夠拓展中醫哮喘的病機學說,又可以為臨床醫治哮喘提供新途徑新思路,進一步提高臨床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