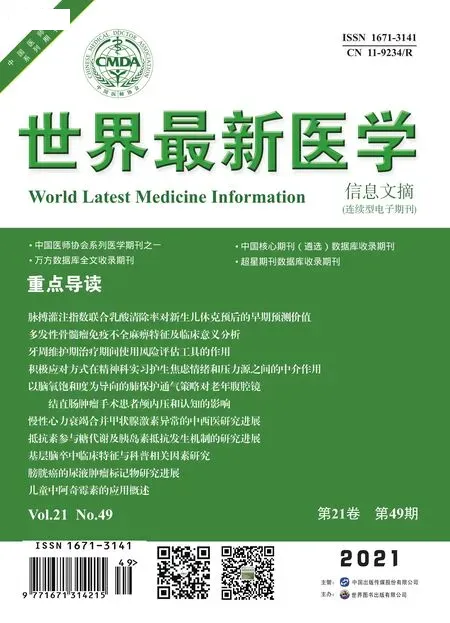真性紅細胞增多癥轉化為急性白血病后合并彌漫性肺泡出血1例
周莉莉,朱振華,張曉艷(通信作者*)
(1.長治醫學院 研究生處,山西 長治 046000;2.長治醫學院附屬和平醫院,山西 長治 046000)
1 病例介紹
患者女性,63歲。2016年主因“顏面部潮紅數年”就診于山西大醫院,行多次血常規提示紅細胞壓積及血小板計數升高,骨髓象提示增生明顯活躍,紅細胞壓積增高(具體紙質報告未提供),診斷為真性紅細胞增多癥。院外間斷口服“羥基脲”治療。2020年4月自行停用羥基脲。
2020年5 月患者出現發熱,體溫最高38.9℃,伴寒戰、咽痛、口腔潰瘍,自行口服“阿司匹林”,效果差,多于下午、晚上發熱。6月6日就診于長治市第二人民醫院,血常規示:白細胞3.8×109/L、血紅蛋白103g/L、血小板145×109/L,胸部CT檢查未見明顯異常,甲狀腺功能正常,先后給予“頭孢呋辛鈉、頭孢他啶、阿奇霉素、奧司他韋”治療,仍有發熱,體溫波動于37.3℃-38℃之間,伴右膝關節腫痛,6月20日考慮“結核”可能,給予試驗性抗結核治療2天,患者出現惡心、干嘔,遂停藥。6月26日因再次發熱,體溫大于38℃收住我院呼吸科。患者既往“高血壓”病史20余年。2019年2月于山西大醫院行“右腎錯構瘤破裂介入術”,術后第二天出現“肺栓塞”,口服“利伐沙班”,復查肺動脈CTA未見栓塞于2019年8月停藥。患者無有害及放射物接觸史。
入院體格檢查:體溫 38.5℃;脈搏82次/分;呼吸22次/分;血壓131/70mmHg;SpO293%,神志清楚,貧血貌,皮膚穿刺部位可見瘀斑,淺表淋巴結未觸及,心率82次/分,律齊,各瓣膜區未聞及雜音,雙肺呼吸音清,未聞及干濕性啰音。肝脾肋下未觸及。完善輔助檢查,結果如下,血常規:白細胞23.3×109/L,中性粒細胞百分比2.7%,淋巴細胞百分比9.3%,單核細胞百分比87.4%,血紅蛋白55.7g/L,血小板 26.5×109/L,涂片鏡檢提示見原始及幼稚細胞。血清葉酸118.0pmol/L,鐵蛋白1421.0μg/L。血清降鈣素原0.12ng/L,C反應蛋白50.46mg/L。女性腫瘤標記物基本正常;新冠病毒核酸及抗體檢測陰性。胸部CT提示:(1)雙肺散在間質性炎癥;(2)肺氣腫、肺動脈高壓征象;(3)肝臟低密度灶。給予經驗性莫西沙星聯合更昔洛韋抗感染、輸血等治療。
6月28 日患者出現呼吸困難,干咳,血氣分析(無創呼吸機吸入氧濃度33%)示:PH 7.45,氧分壓48mmHg,二氧化碳分壓33 mmHg。轉入重癥醫學科,給予氣管插管,呼吸機輔助通氣,輸血,改用哌拉西林鈉他唑巴坦鈉聯合莫西沙星抗感染治療。復查血常規白細胞50.9×109/L,中性粒細胞百分比1.9%,淋巴細胞百分比8.0%,單核細胞百分比89.8%,血紅蛋白52.2g/L,血小板 28.1×109/L;血清降鈣素原0.49ng/L,C反應蛋白45.14mg/L。行外周血涂片回報示:有核細胞極度增多,原始、幼稚單核細胞占88%,該類細胞大小不等,部分形態不規整,漿色蘭,部分含小灰塵樣紫紅色顆粒,核形態不規整凹陷、扭曲、折疊,染色質細,核仁尚清;成熟紅細胞明顯大小不等;血小板少見;POX:2%弱陽性,98%陰性。考慮急性單核細胞白血病(M5)可能大,因患者病情危重,出血風險大,未行骨髓活檢明確分型。6月29日胸片示:雙肺間質性肺炎;局限性肺氣腫。7月2日10時從患者氣道內吸出較多鮮紅色分泌物,行凝血功能示:凝血酶原時間23.80秒,血漿D-二聚體測定7732.00ng/mL,纖維蛋白降解產物測定66.32u/Ml,血漿纖維蛋白原測定2.62g/L。7月2日14時,患者口鼻部分泌大量鮮紅色液體,并發彌漫性肺泡出血,病危出院。
2 討論
PV是一種慢性骨髓增生性腫瘤(MPN),其特征是紅細胞過度增殖,有時白細胞和血小板計數升高,或可出現皮膚瘙癢、高血壓、出血和血栓等并發癥,并具有發展為急性髓性白血病(AML)的內在風險。在Tefferi A等的研究發現,PV發展為AML的概率為1.5%~6.8%[1]。其向白血病轉化的高風險因素包括:(1)年齡>61歲;(2)白細胞計數 >15×109/L,以及異常核型[2]。患者的預后不佳,總體生存率(OS)為2.6~7.0個月[3]。但是PV向AML轉化到底是疾病的自然進展過程,還是與接受的治療藥物有關,目前尚不清楚。
JAK2V617F和JAK2exon12突變可分別在95%和3%的PV患者中檢測到[4],臨床診斷上建議將JAK2V617F檢測作為絕大多數PV患者的確診依據[5]。Xie M[6]等發現,獲得性JAK2V617F突變并不依賴于年齡,而是在60歲后呈指數增長。JAK2V617F突變與年齡的關系和PV向白血病轉化年齡的高風險因素相吻合,但JAK2V617F突變是否是PV向AML自然轉化的原因尚未明確。Spivak JL[7]等研究表明自發性白血病轉化通常發生在PV轉化為骨髓纖維化(PMF)后,而羥基脲(HU)誘導的PV白血病通常發生在JAK2 V617F陰性的HSC中。目前圍繞HU藥物和白血病的問題仍存在爭議。盡管有研究報道HU有誘導PV患者轉化為白血病可能[8],但英國血液學會建議認為一部分PV患者會自然發展為AML和PMF,與其他治療PV的方法或藥物相比,目前還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單獨使用HU會加劇這種風險[5]。本例患者4年前診斷PV,但未行骨髓活檢明確有無基因突變,院外間斷口服HU治療,本次入院患者因病情危重未行進一步檢測明確基因及免疫學分型,且患者HU用藥不規律,無法明確病情演變原因。
不同亞型的急性白血病均可出現凝血障礙[9]。凝血障礙的存在與潛在的致命性血栓、出血事件有關。高D-二聚體水平預示著血栓形成可能。對于AML患者來說,PT延長與出血性死亡的高風險相關[10]。DIC可并發于白血病患者,尤其是APL。本例患者病情重,且進展迅速,雖未能行骨髓活檢明確AML分型,但結合外周血涂片結果考慮患者急性單核細胞白血病(M5)可能大。患者因呼吸衰竭行呼吸機輔助呼吸,可從氣道內吸出鮮紅色分泌物,患者血常規提示重度貧血,并伴有凝血功能障礙,患者DIC診斷明確。后期患者口鼻部分泌大量鮮紅色液體,考慮并發彌漫性肺泡出血。
彌漫性肺泡出血(DAH)是一種臨床病理綜合征,多與毛細血管炎、系統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有關,少數可由凝血障礙、DIC、惡性血液腫瘤引起[12,13]。DAH可表現為咯血、貧血、彌漫性放射性肺部感染和呼吸衰竭[12,14]。該病起病急驟,進展迅速,早期診斷困難,病死率高。因臨床特征及CT及常不典型,支氣管鏡肺泡灌洗在DAH的診斷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組織病理學顯示肺毛細血管炎、彌漫性肺泡損傷和非特異性病變[14]。
現對本案例進行回顧,患者入院時無咳嗽、咯血癥狀,胸部CT提示雙肺散在間質性炎癥,轉入ICU時出現干咳及呼吸困難,胸片示雙肺間質性炎癥,局限性肺氣腫。患者既往無嚴重的肺部疾病及心臟疾病,肺部感染癥狀不明顯,考慮呼吸衰竭與彌漫性肺泡出血相關,且后期可從患者氣道內吸出較多鮮紅色分泌物,晚期患者口鼻部分泌大量鮮紅色液體,支持彌漫性肺泡出血診斷,但因患者病情危重,無法行支氣管鏡肺泡灌洗明確病情。臨床上因DAH病因復雜,對DAH認識不足,可能延誤了診斷和干預的最佳時機。血液系統疾病并發貧血較為多見,貧血癥狀加重常未能引起足夠重視,并且常伴有血小板異常。但當患者在無明顯誘因出現呼吸衰竭、凝血功能異常、貧血加重且與出血量不相匹配時應警惕DAH的發生,早期行全血細胞計數并動態觀察,了解病情動態發展,必要時行支氣管鏡肺泡灌洗,以助于臨床診治及改善患者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