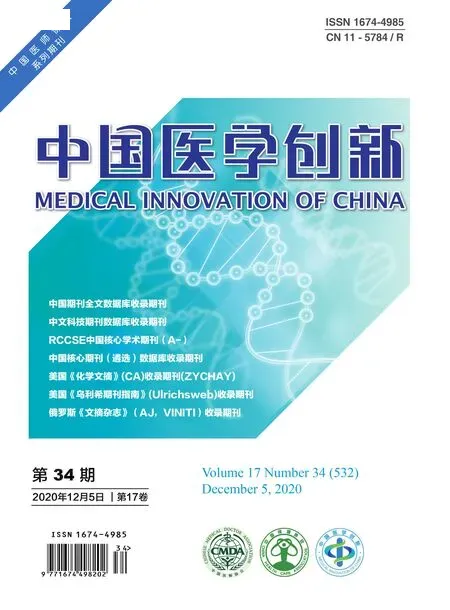頭針聯合膀胱功能訓練治療脊髓損傷患者神經源性膀胱*
張麗蓉 連紅強 寄婧
神經源性膀胱(neurogenic bladder,NB)是指由于控制排尿功能的相關中樞神經和周圍神經受到損害而引起的一系列排尿功能障礙[1]。NB 的嚴重后果在于因下尿路排尿障礙引發的上尿路功能受損,甚至導致腎衰竭、尿毒癥等并發癥。研究表明,長期留置導尿管發生上尿路損傷并發癥的概率為18%,截癱患者傷后的病死率約為49%,其中膀胱功能障礙是導致死亡的主要原因[2]。現因交通及建筑事故發生的增加,脊髓損傷已成為一種造成勞動力損失、影響患者生活質量的外傷性疾病之一,而神經源性膀胱亦成為脊髓損傷患者急需解決的重要功能障礙[3]。本文采用頭針聯合膀胱功能訓練治療脊髓損傷患者神經源性膀胱,取得較好效果,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 般資料 選擇2018 年10 月-2020 年6 月在本院康復醫學科住院的脊髓損傷后神經源性膀胱的患者60 例,男45 例,女15 例;平均年齡(42.3±13.9)歲;頸髓損傷者18 例,胸髓損傷者28 例,腰髓損傷者14 例。納入標準:(1)符合2013 脊髓損傷患者泌尿系管理與臨床康復指南的診斷標準[4];(2)年齡16~65 歲,意識清楚,脊髓休克期已過,生命體征平穩,無認知障礙和神經病學體征的加重,無嚴重合并癥;(3)不完全性脊髓損傷;(4)留置尿管已拔除,患者有不同程度的排尿障礙,主要表現為膀胱脹滿而無法排尿或尿頻、尿不盡,下腹脹滿不適,B超檢查殘余尿量>100 mL。排除標準:(1)伴有嚴重其他重要臟器疾患;(2)嚴重水電解質、酸堿平衡紊亂;(3)既往有嚴重腎臟疾患或前列腺疾患;(4)嚴重腎積水、膀胱造瘺術、尿道前括約肌切開術及嚴重的排尿自主神經系統過反射等疾患;(5)合并嚴重泌尿系統感染;(6)有暈針史患者;(7)患者依從性、配合度差;(8)治療前后數據資料不完整者。中止與剔除標準:在臨床研究過程中,存在以下任意情況者,(1)納入課題后發現與納入標準不符或者沒有按照研究方法規定治療的患者;(2)入組患者出現嚴重并發癥不能繼續參與研究、主動放棄退出或者還沒有結束整個療程而影響治療或安全性評價的患者[5]。依據就診順序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對照組(指導患者執行飲水計劃,并進行間歇導尿及常規膀胱功能訓練、常規藥物干預)30 例和治療組(對照組治療基礎上結合頭針干預)30 例。患者均同意參加本次臨床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研究經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
1.2 方法
1.2.1 對照組 (1)間歇導尿:定時飲水,每4~5 個小時用一次性導尿管導尿1 次,且在每次導尿前行膀胱功能訓練進行輔助排尿。自主排尿間隔每次大于2 h 或者排尿后殘余尿量小于100 mL,膀胱容量在250 mL 以上,且無感染時可終止導尿;(2)膀胱功能訓練:采用聽覺視覺等多種感覺刺激誘發自主排尿功能,或在小腹周圍輕輕叩擊或擠壓膀胱(在患者有這種意愿的情況下進行),拍打大腿內側,拉扯陰毛,聽流水聲,手法排尿(按摩膀胱區、增腹壓屏氣法和恥骨上叩擊法)、核心肌群鍛煉(盆底肌為主)。每天治療1 次,25~30 min/次,每周治療7 d,共治療4 周。
1.2.2 治療組 在對照組基礎上加以頭針治療,頭部分多區,有多條經絡通過,且與機體臟腑生理區相對應。筆者根據大腦皮質功能定位在頭皮的投影來選穴,使頭針治療在頭頂形成一個立體針場,并在這些主穴上施加較強針感。通過循經傳感達到調節機體臟腑功能的作用治療疾病。中醫學認為,腎為先天之本,主骨生髓藏精,上通于腦,故臨床常以調補肝腎、益精生髓、醒腦開竅、養心益智、疏經通絡、強筋壯骨為基本治療法則[6-9]。依據神經源性膀胱的病機,筆者頭針研究選取百會,百會穴屬督脈,別名“三陽五會”,百脈于此交會,能通陽化氣行水[10-11]。平刺四神聰穴,可以醒腦開竅,鎮靜安神,改善患者睡眠質量,提高免疫力;雙側眉沖、曲差、五處、承光均采用斜刺法,亦可通經理氣、調補腎氣,促進腎和膀胱對水液的氣化固攝。以上腧穴每日針灸治療一次,陣法多以補法為主,25~30 min/次,促進臟腑恢復正常。治療7 d 為一個療程,中間休息1 d,連續治療4 周后統計療效。
1.3 觀察指標及判定標準 (1)膀胱功能積分參見《中國針灸》論文,電針八髎、會陽治療脊髓損傷性尿潴留療效觀察[6],0 分:通過反射能自行排尿,殘余尿量0~50 mL,排尿及終止排尿受意識控制;1 分:通過反射能自行排尿,殘余尿量50~150 mL,排尿及終止排尿緩慢但受意識控制;2 分:經反射刺激能排尿,殘余尿量150~250 mL,排尿及終止排尿不完全受意識控制,需定期間歇性導尿排空及沖洗膀胱;3 分:不能通過反射自行排尿,排尿及終止排尿通過留置導尿管或間歇性導尿,不受意識控制。(2)功能獨立性量表(Function Independent Measure,FIM)為醫療服務人員提供記錄患者殘疾程度和醫療康復的效果,可用于比較康復結局的常用測量量表[12]。FIM 系統的核心就是功能獨立性測量的應用工具,是一個有效、公認的等級評分量表。量表共18 個條目,其中13 個身體方面,5 個認知方面。FIM 總分18~126 分,分值越高說明獨立性越強。(3)臨床療效評價標準,治愈:患者膀胱功能恢復,能自主排尿,臨床癥狀消失;顯效:患者膀胱功能達到3 級,能自主排尿,有尿意時自控時間超過2 min,每次排尿間隔超過2 h,偶有漏尿現象;有效:患者膀胱功能達到2 級,臨床癥狀未完全消除,有尿意時自控時間超過1 min,每次排尿間隔時間超過1 h,偶有滴尿與遺尿現象;無效:患者排尿功能未明顯改善,不能自主排尿,每次排尿間隔不足30 min[13-14]。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21.0 軟件對所得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用(±s)表示,比較采用t 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兩組性別、平均年齡、平均病程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2.2 兩組膀胱功能積分、FIM 評分比較 治療組的膀胱功能積分、FIM 評分均明顯優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膀胱功能積分、FIM評分比較[分,(±s)]

表2 兩組膀胱功能積分、FIM評分比較[分,(±s)]
2.3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 治療組顯效率為63.3%,高于對照組36.7%,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 例(%)
3 討論
首先,神經源性膀胱是與排尿功能相關的大腦、脊髓和支配膀胱尿道的神經系統病變引起的排尿障礙,其神經分配包括大腦皮質、基底神經節、腦干網狀結構等支配中樞,對排尿均有控制調節作用。(1)大腦皮質(旁中央小葉)為排尿高級意識支配區,皮質逼尿肌區是控制逼尿肌功能的中樞,皮質的陰部神經感覺運動區控制尿道周圍橫紋肌。(2)基底神經節內黑質病變導致多巴胺神經遞質分泌減少,引起逼尿肌無抑制性收縮,出現運動緊迫性尿失禁。(3)腦干網狀結構神經元發出纖維傳至丘腦、基底節、邊緣系統、下丘腦及小腦,且腦干網狀結構也接受這些部位發出的下行性神經纖維至骶髓的逼尿肌核和陰部神經核。所以腦干網狀結構的神經元,如同樞紐對膀胱逼尿肌和尿道周圍橫紋肌具有協調作用。控制排尿的高級中樞是大腦,大腦損傷后會引起隨意排尿控制功能障礙。脊髓病變使上運動神經元對下運動神經元抑制作用解除,引起排尿障礙。此外,周圍神經病變直接損傷了膀胱逼尿肌和尿道內外括約肌的控制,根據病變性質、程度和范圍出現一系列復雜的排尿功能障礙癥狀。
目前神經源性膀胱按臨床表現不同分為尿潴留及尿失禁兩類,但兩種類型的排尿障礙治療手段效果均不佳,治療頗具挑戰,因此對其深入研究非常有必要。目前,臨床采用的治療方法包括間歇性導尿、膀胱功能訓練、藥物、電刺激技術(低頻、生物反饋等)及外科手術等[15],但多數治療方案的缺點是有創、經濟成本高、患者難以接受等。傳統中醫學治療有中藥、針刺(電針、頭針、體針等)、艾灸、按摩等保守治療方法,與西醫治療相比,傳統治療更具多樣性,低成本、安全系數高、實施難度低、易于廣大患者接受。
其次,針灸可改善脊髓損傷后神經源性膀胱的尿流動力學參數[16-17]。筆者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頭針治療脊髓損傷患者神經源性膀胱的研究中發現,結合頭針治療可以更好地改善脊髓損傷患者的膀胱功能,頭針的治療作用主要在于“通其經脈,調其血氣,營其逆順出入之會”。從整體治療效果來看,傳統治療的介入不但能增強整體療效,而且對于疾病復發也具有一定的預防作用。筆者通過運用經絡和神經支配理論及其神經源性膀胱的臨床表現分類進行針對治療和研究發現,頭針治療能改善患者的排尿障礙,提高自主控尿能力。頭針和康復訓練是脊髓損傷后排尿功能障礙的重要治療手段,本研究擬選脊髓損傷后神經源性膀胱的患者,分別采用不同的干預方法進行療效對比研究,為患者排尿障礙的后期康復提供規范有效的治療方法。本次研究治療的一個重要原則是確保儲尿期和排尿期膀胱壓力處于安全范圍內重建下尿路功能,減少殘余尿量,防止并發癥。
最后,運用頭針治療結合膀胱訓練既能醒腦開竅、減輕乏力,又能安神助眠,保證患者具有良好的訓練狀態,增加患者的訓練主動性,不但對自主性膀胱功能的恢復起到良好療效,而且為后期鞏固訓練創造了良好基礎。這項技術無創、成本低、實用性強、有效性和安全性高,減輕廣大神經源性膀胱功能障礙患者的痛苦,適于在基層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