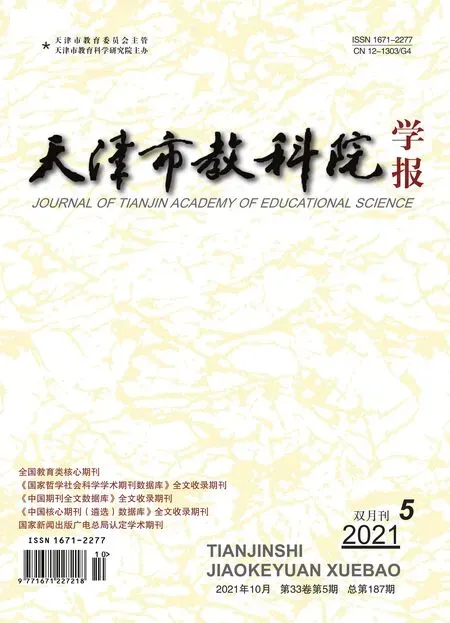“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社會規律本質探析
馬開劍
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以下簡稱“教勞結合”)的思想無疑是我們實施勞動教育的理論基點,然而,仔細考察馬克思主義者提出“教勞結合”的具體語境、理論邏輯內涵和勞動教育的實踐步履,就會發現對它的解讀仍有局限。主要體現為人們往往僅從教育的角度來看待這一思想,而未能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待它。要在新時代真正實施好勞動教育,有必要對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社會本質進行探討。
一、“教勞結合”的現實關注點探源
馬克思主義者們在不同時期所提出的“教勞結合”思想,不僅表述方式帶有時代特征,而且其現實關注點也有不同,這是準確理解“教勞結合”的原點。
(一)馬克思闡述“教勞結合”的最初關注點是勞動與謀生
馬克思闡述“教勞結合”的最初關注點并不是教育,而是勞動與謀生問題。原因很簡單,因為當時的工人階級也必須服從人類生存最基本的法則,即“為了吃飯,他必須勞動,不僅用腦勞動,而且用雙手勞動”[1]。也因此,他強烈反對全面禁止童工,“普遍禁止兒童勞動是同大工業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這是空洞的虔誠的愿望”[2]。顯然,以馬克思所處時代無產階級的經濟狀況,其子女不可能停下工來去接受全日制的教育,只能在不影響他們勞動謀生的情況下接受教育。由此可見,馬克思在提出“教勞結合”時,所關注的要點不是教育,而是當時工人階級的生存及其子女通過勞動來謀生的問題。
但是,馬克思又反對讓工人階級的子女單純地、機械地做工,強調在做工的同時,還要“結合”著接受教育。在《臨時中央委員會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指示》這封信中,馬克思提出“如果不把兒童和少年的勞動和教育結合起來,那無論如何也不能允許父母和企業主使用這種勞動”[3]。這里的教育是提高工人改造不合理社會制度的意識與知識水平的教育,而不是“資產者唯恐失去的那種教育,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是把人訓練成機器”[4]。又說,“把有報酬的生產勞動、智育、體育和綜合技術教育結合起來,就會把工人階級提高到比貴族和資產階級高得多的水平”[5]。可以看出,馬克思又將“教勞結合”看作是一種“抗毒素”,一種防止單純、機械地參加生產勞動的手段,以抵制資本家把工人及其子女僅僅當作資本積累的簡單工具。
句式結構分析是研究語句意義的重要方法,分析上面所引相關表述,可以發現,馬克思顯然是對“勞動”提出了要求——與“教育”相結合,而不是相反,在句式結構上是“勞動”在先而“教育”在后。按這種分析,“生產勞動與教育相結合”與“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所包含的意義并不完全相同,一個是著力于生產勞動并對其提出要求——與教育相結合,一個是著力于教育并對其提出要求——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著力點的不同,反映著特殊的時代語境。
(二)早期共產黨人倡導“教勞結合”探尋民主革命的道路,并意在改造舊知識分子
“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當時“民主”與“科學”精神的影響下,20世紀20、30年代的一些先進知識分子,猛烈抨擊“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觀念,倡導知識分子自食其力,躬身勞動。他們主張教育機會人人均等,主張工人、農民要受教育,要有知識。倡導知識分子走向田間、進入車間,與工農打成一片,參加勞動。革命先驅李大釗(1888—1927)提出,“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到社會里面,非把知識階級和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6]。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早期共產黨人倡導“教勞結合”的目的,在于探尋在中國實現民主革命的道路,并希望借此改造舊知識分子身上輕視、鄙視勞動和勞動人民的封建思想,這是當時極其進步的革命思想。
“教勞結合”的這種意在改造知識分子的意味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前,期間它甚至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在這一或明或暗的意識指導下,知識分子被作為改造的對象,當然不屬于勞動人民,也不屬于工人階級,甚至大批知識分子還一度被打成“牛鬼蛇神”,被下放勞動,接受改造。1968年開始,大批知識青年被派到農村,參加生產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在校學生也必須參加生產勞動,以保持勞動人民的本色。直到1978年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鄭重宣布,中國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教勞結合”的改造意味才逐漸消退。
(三)新民主主義革命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提出“教勞結合”旨在保障生計和發展經濟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政府,明確提出“教勞結合”,可追溯到1934年中央蘇區所提出的文化教育總方針,當時的提法是“教育與生產取得聯系”。1942年,鑒于根據地所面臨的嚴重困難,毛澤東同志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指出,“教育(或學習)是不能孤立地去進行的,我們不是處在‘學也祿在其中’的時代,我們不能餓著肚子去‘正誼明道’,我們必須弄飯吃、我們必須注意經濟工作。離開經濟工作而談教育或學習,不過是多余的空話”[7]。這與當時的斗爭形勢是分不開的。1943年,邊區政府根據毛澤東“一切機關學校部隊,必須于戰爭條件下厲行種菜、養豬、打柴、燒炭、發展手工業和部分種糧”的指示,[8]在根據地開展了包括機關學校在內的大生產運動。在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一首流傳很廣很久的歌曲《軍民大生產》。
1958年,我國在經濟領域開始了不切實際的“大躍進”運動,這一年,正是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當時的經濟氣氛是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爭取實現國民經濟發展的新躍進,這是當時黨的中心工作之一。同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明確提出“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顯然,前一句是說教育的政治功能,而后一句則顯然是基于教育的經濟功能,教育被看作是服務生產勞動、促進經濟發展的手段。兩句話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強調了教育的兩大基本現實功能——政治功能和經濟功能。很明顯,1958年提出“教勞結合”,與當時經濟大躍進的整個社會氛圍和價值導向是分不開的,也是基于發展經濟的考慮而提出的。“事實上,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內涵既不在于思想意識的教育,也不在于教學方法的改革,它的基本指向是經濟問題,是從發展振興社會主義經濟的角度規范教育發展的基本方向”[9]。
但是,這一時期的“教勞結合”顯然對學校教育產生了重大影響。在《關于1958—1959學年度中學教學計劃的通知》中明顯加強了“勞動教育”。高中各年級規定了每周2課時的“生產勞動”,包括農業實習和工業實習,另外還專門設立了“體力勞動”科目,規定高中各年級每學年要參加14—28天的體力勞動,其主要內容仍是生產勞動。在1963年制定的《全日制中學暫行工作條例(草案)》中,還對生產勞動作了這樣的闡述:“學生參加生產勞動,主要目的是養成勞動習慣,培養勞動觀點,向工農群眾學習,克服輕視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的觀點;同時,在勞動過程中學習一定的生產知識和技能,擴大知識領域。”[10]
追溯“教勞結合”的淵源,讓我們看到了它的別樣含義,有助于我們認識其本質內涵及其對學校勞動教育的影響。
二、“教勞結合”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
馬克思主義經典原著關于“教勞結合”的表述,既有對他們所處時代的洞察,也有他們對未來社會發展趨勢的把握。在學習與理解“教勞結合”時,必須將其當時的現實內涵與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發展趨勢的把握區別開來。
(一)人的發展、社會發展與“教勞結合”的統一性
馬克思從社會生產方式與人的發展的關系入手,深入考察了當時的英國工廠制度,發現資本家不僅把工人看成是資本積累的簡單工具,而且也由此造成了工人自身的畸形發展。更重要的是,馬克思看到了這些現象背后深刻的社會基礎。“工場手工業人為地加速了勞動者的片面技巧的發展,犧牲了生產者的全部素質和本能,從而使勞動者畸形化,把他變成某種怪物”[11],“只要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構成社會生產的普遍基礎,勞動者對專一職業的依附,他的能力和職業的原有多面性的破壞,就可以被看作是歷史發展的必要因素”[12]。由此,要想恢復被工場手工業破壞的“能力和職業的原有多面性”,就必須改變社會生產的基礎,改造社會。
大工業生產的出現以及生產技術基礎的持續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生產方式,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可能。但是,技術革新和大工業生產方式的出現,也會產生另一種災難,即大批工人失業。對此,馬克思有其獨特的深刻認識,“大工業所產生的災難本身必然要求承認勞動的變換,從而承認勞動者盡可能多方面發展能力是現代生產的普遍規律,并且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使各種情況適應于這個規律的正常的職能”[13]。為此,就必須將工人從單純的機械的生產勞動中解放出來,讓他們接受教育,從而使“勞動者盡可能多方面發展能力”以適應大工業生產的要求。這樣,“教勞結合”不僅可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而且也促使社會生產方式發生變革,正如馬克思所說,“生產勞動和教育的早期結合是改造現代社會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14]。由此,社會變革、人的發展與“教勞結合”是統一的,統一的結點就是人的發展。關于這一點,馬克思說得很清楚,“未來教育對所有已滿一定年齡的兒童來說,就是生產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的結合,它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5]。
(二)“教勞結合”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
馬列主義經典作家在闡述“教勞結合”時經常是站在“未來社會”的高度。考察馬列主義經典,不難理解,“未來社會”顯然就是指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社會。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原著中,“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個概念是被混同使用的,只是后來列寧才將社會主義定位為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基于大工業生產方式的“未來社會”,既可以體現為發達的資本主義階段,也可以體現為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社會,而且,由資本主義發展為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馬克思甚至認為英國、法國、美國和德國等當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可以首先向社會主義過渡。
實際上,前面引述的馬克思關于“勞動者盡可能多方面發展能力是現代生產的普遍規律”,表明馬克思已經清楚地看到了大工業生產方式產生以后未來社會的發展規律——當社會生產方式達到大工業生產水平時,人的全面發展不僅成為可能,而且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由此,社會發展與人的發展是統一的。“教勞結合”作為人的全面發展的手段——通過人的發展促進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因而也是社會發展的手段。在以之作為手段實現了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之后,便客觀上革新了社會形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或共產主義社會。
反過來,當我們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或共產主義社會時,“教勞結合”就是必然的。不然就會破壞社會發展與人的發展之間的和諧共進關系,或者根本進入不了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社會。從終極的意義上講,在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社會,科學和技術高度發達,社會生產方式將發生根本的變革,對人的要求也會同時發生變化,教育與生產勞動將有機地融合為一體,從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并促進社會發展,這是一條不依人的意志而轉移的客觀規律。正如列寧所指出的,“沒有年輕一代的教育和生產勞動的結合,未來社會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無論是脫離生產勞動的教學和教育,或是沒有同時進行教學和教育的生產勞動,都不能達到現代技術水平和科學知識現狀所要求的高度”[16]。
由此,我們發現,“教勞結合”實際上是表述“未來社會”發展規律的一種形式、一個視角。換言之,“教勞結合”實際就是“未來社會”即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
(三)“教勞結合”也是發展中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
社會主義既可體現為制度,也可體現為意識形態,但更是一個過程。馬克思主義既把握理想社會主義,也關注現實社會主義,當代馬克思主義則更關注發展中社會主義。那么,“教勞結合”是發展中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嗎?回答是肯定的。
教育與生產勞動兩者之間的聯系是本質的、必然的、客觀的、穩定的。教育的目標、內容、教學都受到一定社會生產方式的制約,甚至教育的質量最終也是由它對社會生產方式變革所能發揮的作用來評判;而生產方式的改進、生產效率與質量的提高、勞動關系的改善,都與工人受教育的水平緊密相關。教育世界與勞動世界通過教育所培養的工人的發展狀況而必然地聯系在一起。如果違背了這一規律,就像我國的封建社會以及19世紀中葉以前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某些時期,結果只能導致社會生產方式的停滯不前和人的發展的異化,這顯然是不和諧社會才會有的現象。但即使在這種狀況下,仔細分析貴族階級子女的教育和勞動人民子女的教育(包括日常生活和勞動中的教育),就能發現各階層所經受的教育與相應階層特定的生產勞動,仍然存在穩定的、本質性的緊密聯系。
目前,我國正處在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向理想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邁進的過程中,若教育與生產勞動相分離肯定不行,但“結合”到分不清你我的程度,也是違背這一規律的表現。在這一過程中的初級或初始階段,“教勞結合”在主觀上可作為變革社會的手段,而客觀上它依然是向共產主義邁進中的必然規律。
三、新時代“教勞結合”的境界升華
時代不同了,馬克思所處時代的教育與勞動早已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語。故,馬克思主義“教勞結合”的經典理論雖然依然是指導我們實踐的理論基礎,但要在新時代煥發生機,有效地實踐它,還必須把握其境界升華。
(一)“勞動”概念的時代內涵
有學者考察了馬克思、恩格斯經典原著中有關“教勞結合”的論斷,發現其中使用過“勞動”“體力勞動”“生產勞動”“工廠勞動”等概念,得出結論認為,馬克思主義“教勞結合”經典理論中的“勞動”是指“以機器大工業為前提的、以體力(手工)勞動為內容的物質生產勞動”[17]。這里,顯然是將勞動看作是以工農業生產為背景的、基于體力消耗的物質生產實踐。
“勞動”是一個十分復雜的概念,既包括簡單勞動,也包括復雜勞動。對此,馬克思也有清楚的認識,他指出“從簡單勞動過程的觀點得出的生產勞動的定義,對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絕對不夠的”[18]。于是,他給出了“更貼切的規定:生產勞動是直接增殖資本的勞動或直接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19]。但令人遺憾的是,受社會發展過程的局限,這個定義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
今天,以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為標志的科技因素,為勞動注入了嶄新的內涵,而且,勞動的形式也早已不限于基于體力消耗的物質生產勞動范疇。比如,我們該怎樣理解籃球明星姚明當選全國“勞動模范”呢?為此,我們既要看到物質生產勞動,還要看到各種非物質生產勞動;不僅看到生產勞動,還要看到義務、責任、自立意義上的非生產勞動等。更不用說,即使在經典理論中,勞動的涵義,除了指體力勞動、生產勞動外,還包括列寧主張的公益性義務勞動。
(二)“教勞結合”的境界升華
新時代教育的功能屬性早已發生了根本改變。我國新時代教育為人民服務、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服務、為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已經成為新時代教育的新功能、新屬性。由此,在新時代背景下,我們必須突破傳統認識,去達到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新時代境界,即新時代、新教育與新勞動、新創造進行新的結合。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提出:“要在學生中弘揚勞動精神,教育引導學生崇尚勞動、尊重勞動,懂得勞動最光榮、勞動最崇高、勞動最偉大、勞動最美麗的道理,長大后能夠辛勤勞動、誠實勞動、創造性勞動。”同時提出要把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作為根本任務,這是新時代關于“教勞結合”的新思想,其中蘊含的關于勞動、勞動價值、勞動與幸福、勞動與發展等豐富內涵,是對馬克思主義勞動思想的繼承與發展,代表了新時代有關“教勞結合”的新境界,蘊含著理論和思想的升華。新時代“教勞結合”不是出于經濟意義上的利益獲取,不是出于單純的思想改造,也不是出于技術技能的訓練,甚至也不是出于簡單的理論聯系實際等的考慮,而是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進行的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的系統實踐。
新時代要做好“教勞結合”,就要按社會生產方式調整教育結構,對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同等重視;按社會生產方式調整專業設置,學校特別是大學就要按社會的需要來確定人才培養類型及質量規格,按社會需要設置、合并或撤銷專業;按社會生產方式調整學校課程設置和人才培養模式。教育結構、專業與課程設置的調整,所體現的正是教育對社會發展要求的呼應,它所追求的是人才培養模式的重大轉向,即按照社會生產方式變革的需要來培養人才,這顯然就是對“教勞結合”規律的真正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