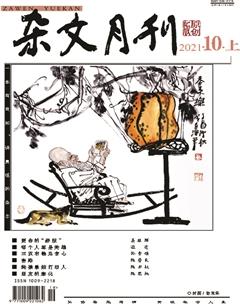三人行
張小華 等
諧音傳統與價值取向
張小華(甘肅靖遠)
在《“諧”物教》(《雜文月刊》2021年8月上原創版)一文中,作者伍里川指出高考、商業廣告、雕件飾品乃至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諧音現象。其實,諧音不是現代人的創造,而是古已有之的傳統,且蘊含了特定的價值取向。與直接、粗放相比,諧音表達了較為細膩、含蓄的抱負與志向。我們還能從一些出土器物上觀察到古人的價值取向,比如漢代石刻畫像中的“射爵射侯”圖。
目前,在山東、四川多地漢代石刻作品中都發現有“射雀射猴”畫像。如山東省微山縣兩城鎮出土的一塊畫像石上,樹下兩人持弓仰射,樹上有20多只雀和猴。古代“雀”“爵”相通,“猴”“侯”同音。這類畫像在漢代石刻中較為常見。這反映了追求名利、希冀顯貴的“漢代核心價值觀”。古人喜歡以物詠志、托物言志,漢代畫像石不是濫觴,卻是明證。
其實,諧音也曾留下許多妙趣橫生的美談。以福為吉,每逢過年一定會在大門上貼“福”字,且將“福”字倒過來貼,取“福到了”的口彩,這里的“到”與“倒”諧音。再如,民間年畫中魚是最流行的題材,光身胖娃雙手抱著一條大魚,旁有蓮池、蓮花等,以“魚”諧“余”(表示富余),以“蓮”諧“連”,取“連年有余”之意,希望每年的日子都能過得富余、富足。據傳,蘇軾曾諧音調侃佛印“狗啃河上(和尚)骨”,佛印不甘示弱諧音相譏“水流東坡尸(詩)”。也是宋代,流行過這樣的歌謠:“殺了穜蒿割了菜,吃了羔兒荷葉在。”歌謠運用諧音手法大罵當時的奸臣賊黨童貫、蔡京、高俅、何執中等人。金圣嘆刑場的絕命聯令人嘆為觀止:“蓮(憐)子心中苦,梨(離)兒腹內酸。”古代文武官員之間通過文字博弈,也充滿諧音的趣味:“兩舟競渡,櫓速(魯肅)不如帆快(樊噲);百管爭鳴,笛清(狄青)難比簫和(蕭何)。”魯肅、蕭何屬于文臣圈子,樊噲、狄青屬于武將圈子。學者林帆曾分析過《紅樓夢》的諧音與雙關妙語的匠心:“甄士隱諧‘真事隱’(去),賈雨村諧‘假語村’(存),里面暗藏玄機,諧音寓情,指物借意,兼而有之。榮國府的四位千金名為元春、迎春、探春、惜春,便是以‘原應嘆惜’四字諧音,預示各人的命運。就連甄士隱一個三歲的獨養女兒英蓮,也諧音寓意:英蓮英蓮,可真是‘應’予‘憐憫’的薄命女。至于《紅樓夢》的主題,當頭就經警幻仙子點破,仍是諧音雙關的妙用,她借款待寶玉的茶香酒香和異卉之精制成的油香,說是‘千紅一窟(哭),萬艷同杯(悲),群芳髓(碎)’,通過大觀園的聲色,更進一步暗示出眾位女兒的悲慘宿命。”
近年來,國內一些商家為追求廣告效應,以諧音手法竄改成語,如“衣衣不舍”“一戴添嬌”“默默無蚊”“首屈一紙”“酒負勝名”“有痔無恐”“咳不容緩”等。這些所謂的廣告創意,表面上看僅僅是改變了成語的本意,實質上卻是對我國傳統文化的褻瀆。進一步看,濫用漢字的情況,在相當程度上已產生了社會危害,不利于人們正確認識民族文化,混淆視聽,產生了不少誤導。好在,各地以立法手段強制文字使用規范化、禁止廣告竄改成語。至于考場外手舉葵花希冀“一舉奪魁”,身穿旗袍盼望“旗開得勝”,兼備諧音傳統與行為藝術,“法無禁止即可為”,權當是一種文化現象吧,靈不靈驗,誰想試試就試試。
廉政建設要靠他律
王海銀(山西太原)
多年來,勸諫領導干部防微杜漸、廉潔自律的文章可謂汗牛充棟。如果筆者沒有理解錯的話,《洗凈塵埃,輕松前行》,(《雜文月刊》2021年8月上)也屬于此類文章。筆者以為,我們讀、寫這類文章,首先要弄清一個問題,即究竟何為“自律”。筆者以為,所謂自律,就是在沒有外在監督、制約的情況下,憑借自己的信仰、良心和意志,抵御誘惑,將行為約束在法律和道德的框架之內。具體到官員的廉潔自律,就是作為一個有職有權的官員,本有條件以權謀私,而且遭受法律制裁的風險很小,但憑著崇高的信仰和頑強的意志,抵制住了誘惑,保持了清正廉潔。由于受到嚴格的監督沒法下手,或者害怕法律的制裁不敢下手,不能算自律,因為監督和法律制裁屬于外在的制約力量——他律。比如我們在野外用餐,小鳥們無論饑餓到何種程度,都只能躲在樹上垂涏,而不敢下來搶食,這能算是自律嗎?如果這也算是自律,那么,這種小鳥也能做到的自律,是相當廉價的。
筆者想說的是,企圖通過官員的自律來遏制腐敗,未免太天真了。嚴格意義上的自律,需要具備崇高的品德、虔誠的信仰和頑強的意志,這是只有圣人才能達到的境界。以圣人的標準來要求普通人,是不現實的。還是那句話,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那些清廉指數名列前茅的國家的官員,道德水準不見得有多高,他們見到金錢美色也會心動,只是懾于法律的威嚴,不敢付諸行動。總之,廉政建設主要要靠他律。只有致力于監督制約機制的架構,大幅度提高腐敗的風險,才有希望將腐敗遏制在最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