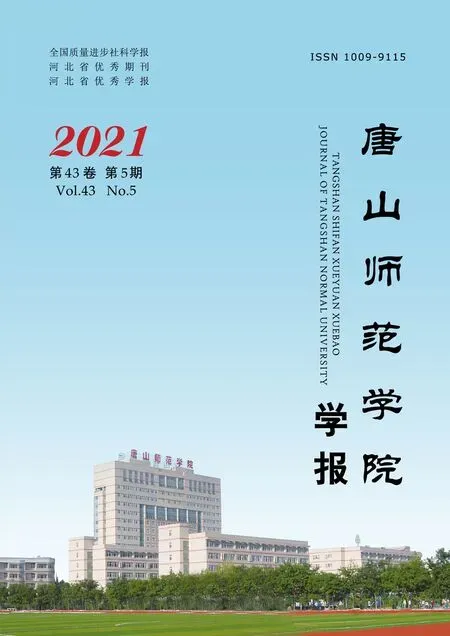宋代艾草的應用——以社會生活為面向的思考
劉 暢
宋代艾草的應用——以社會生活為面向的思考
劉 暢
(信陽師范學院 歷史文化學院,河南 信陽 464000)
宋代艾草的社會應用十分廣泛。宋人飲艾食艾,以艾驅蚊;端午節慶時,掛艾人、艾天師等門飾以及簪艾花、艾虎之類的頭飾去穢避邪;生病治療時,也會以艾入藥,其使用方式有服、灸、熏、洗、敷、涂等多種方式。艾草與宋代社會交互影響,宋人對艾草的認識深受理性博物觀念的浸染,用艾活動則反映出重視實用、融攝三教的特點,宋人衛健意識的流變更是呈現出艾草與社會之間聯通互動的生動圖景。
宋代;艾草;應用;社會生活
艾草是我國常見的本土草本植物,古人對其早有關注,并且利用頗多。至宋,文人多追求“探索現實生活的安然意趣”[1],受此影響,艾草與社會生活的聯系也相當密切。目前學界對宋代艾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宋代艾灸療法上,對艾草在宋代社會生活中的應用及其與當時社會的關系則缺乏關注。
本文擬從社會生活的視角,梳理宋代艾草的應用情況,并結合當時社會與時代的特點展開進一步探討。
一、艾草與日常生活
艾草作為中國本土植物,常見易得,在宋代日常生活中應用普遍。艾草在當時不僅被視作食材,用于制作各色飲品與食物,也是宋人驅蚊的重要選擇。
(一)飲食用艾
宋代的飲食十分豐富,《東京夢華錄》甚至還對當時開封的飲食作了分門別類的記載。不過,名目品類繁多只是宋代飲食豐富性的一面。在這一時期,飲食的制作更趨精細多樣,食材的選擇、口味的偏好也都較為復雜多元,社會中出現了以崇尚“素食”“藥食同源”為代表的飲食新風尚。至于入湯可飲、入飯可食的艾草,因其具備較高的藥用價值,故而成為了追求健康、講究保健的宋人在日常飲食中的重要之選。
艾草制酒。艾酒就是宋代常見的艾類飲品。酒既是飲料也是保健食品,以艾制酒之事古今皆有。宋代陳著的《醉中示梅山弟二首》有“時節往來容易事,菜湯艾酒一家風”的句子,陳元靚在《歲時廣記》中也說“洛陽人家端午造術羹艾酒”[2]238。可見,艾酒在當時可以算得上是普通人家的常備酒品。一些宋代藥方也常常透露出以艾入飲的情況。《圣濟總錄》中記有一則“艾蒿醞酒方”,此方對艾蒿酒的制法以及飲法作了詳細記載:“白艾蒿十束(每束如升許大,凈擇,水洗,細剉)一味,煮取濃汁,拌曲米一如常醞法,酒熟去糟取清,稍溫飲之,令常醺醺然。”[3]271另外,在該書中還載有另一則制法更為簡單的“艾蒿酒方”:“艾蒿一握。切上一味,以水、酒各一盞,煎至八分,去滓,分溫二服”,以該法制成的艾蒿酒對緩解“諸魚骨鯁在喉中”的困擾有奇效[3]1219。
艾草入食。宋代以艾草為食材的情況應屬常見。在宋代醫書中常有以艾葉粥送服藥物的記載,然而當中卻未見這類艾制粥湯的詳細做法,可見這類食物在當時并非少見,故無須再多加說明。此外,當時不僅宋人食艾,周邊的契丹、高麗等國也有食艾的風俗。據載,遼君在端午大宴群臣時,專門指定膳夫制作“艾糕”,以此作為宴席的必備食品[4]。另外,高麗在上巳日亦有“以青艾染餅為盤羞之冠”之俗[5]。可見,當時食艾現象之普遍、食法之多樣。
然而,艾草雖有藥用價值,卻也不是食用起來毫無禁忌的。宋人蘇頌就關注到這一點,他提醒世人:“近世有單服艾者,或用蒸木瓜丸之。或作湯空腹飲之。甚補虛羸。然亦有毒,其毒發則熱氣沖上。狂躁不能禁。至攻眼有瘡出血者。誠不可妄服也。”[6]可見,食艾雖好,但也要得法適度。
(二)驅蚊用艾
夏日蚊蟲叮咬,令人不勝其煩,宋人亦受其苦。據宋人記載,當時的蚊子十分兇殘,“鱉與蝤蛑被蚊子叮了即死”[7],甚至在有些地方,人也難以抵擋,《甕牗閑評》中提到:“秦州西溪多蚊子,……有廳吏醉仆,為蚊子所嚙而死,其可畏有如此者”[8],當時蚊子之毒,可見一斑。歐陽修也曾專寫《憎蚊》一詩感嘆:“雖微無奈眾,惟小難防毒。”[9]這也道出了當時人們的煩惱與心聲。
雖然宋人深受蚊叮之苦,但也不是毫無應對辦法。宋人梅堯臣在詩中曾多次提到用艾驅蚊的方法:“枕底夕艾驅蚊蟲”[10]“驅蚊爇蒿艾”[10]。另外,宋代《孫公談圃》也有用艾熏蚊的記載:“泰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煙熏之。”[11]可見,用艾草驅蚊已成宋人的常用之法。
二、艾草與端午節慶
在宋代節慶中,使用艾草最多的,當屬端午節。古人認為五月時節,蛇蟲出沒,暑毒盛行,環境條件較為惡劣,故而重五之日“驅邪避惡”漸成傳統。宋時,人們的端午習俗與活動也大都是圍繞“驅病攘災”這一節日主題展開的,而艾草與端午節慶的聯系亦在于此。
(一)掛艾
宋代端午,人們常常將艾草制成各種門飾懸于門上來避邪驅毒。這類門飾形狀不同,名稱各異,主要有艾人、艾虎、艾天師三種。
所謂“艾人”,即人形的艾制門飾,通常用艾葉編制而成。宋人林景熙詩中所記“束艾肖人形”[12],即是言此。艾人作為端午門飾的傳統由來已久,成書于南北朝時期的《荊楚歲時記》曾載:“端午日荊人皆蹋百草,采艾為人懸于門上,以禳毒氣。當是以師曠占有歲病,則艾草先生故也。”[13]可見,這種“艾人懸門”的節俗也是出自端午除邪禳毒的目的。至宋,此俗更盛。在東京開封,每逢端午節慶,不僅百姓們紛紛“釘艾人于門上”[14],就連皇宮大內也要“以青羅作赤口白舌帖子,與艾人并懸門楣,以為禳檜”[15]42。除此之外,艾人這一意象在宋人端午詩詞中也很常見,如“門巷陰陰掛艾人”[16],“角簟橫龜枕,蘭房掛艾人”[17]488,“恰就得端陽,艾人當戶”[17]1171等等。由此可見,“艾人懸門”這一民俗活動在宋代端午時節甚為普遍。
另一端午門飾“艾虎”,其用法與艾人相同,均是懸于門上,不同的是,其形類“虎”。古人認為虎是百獸之長,“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18]。艾與虎相結合,前者的作用在于禳毒消災,而后者的寓意則是辟邪除兇,兩者合二為一,艾為表,虎為形,禳毒辟邪,相得益彰。
艾天師又稱“天師艾”。其中“天師”指的是漢代的“張天師”,即五斗米道的創立者張道陵。傳說張天師道法高強,擅長治病辟毒、捉妖降鬼,宋人對其十分尊崇。北宋開封府“端午都人畫天師像以賣,又作泥塑張天師,以艾為須,以蒜為拳,置于門上”[2]242。這種泥身艾須的“張天師”就是“艾天師”。吳自牧《楚梁錄·五月》亦云:“家家……以艾與百草縛成天師,懸于門額上。”[19]另外,道教傳說張天師于五月五日乘艾虎出游,消滅五毒妖邪,故人們也常常將兩者相聯系,用于端午節飾,如《武林舊事》記宮中端午“插食盤架,設天師艾虎”[15]54。除此之外,當時也有端午門飾合艾、虎、天師三者而一的,即將艾草做成天師御虎狀,魏掞之《失調名》“掛天師,撐著眼,直下覷。騎個生獰大艾虎”的描寫就十分形象。
(二)簪艾
宋人酷愛簪飾,宋時端午時節的艾制簪飾也別具特色。艾花就是當時女性普遍喜愛的端午簪飾,具有原料易得、樣式應時的特點。《歲時廣記》載:“端五,京都士女簪戴,皆剪繒楮之類為艾或以真艾,其上裝以蜈蚣、蚰蜒、蛇蝎、草蟲之類,及天師形像。”[2]244可見,艾花的制作材料既可以是真艾,也可以是絲織品,并且其樣式也是相當豐富的。真艾所制艾花新鮮自然,制作時多選用艾枝、艾束,宋詞“艾枝應壓愁鬟亂”[20]1815“斜插交枝艾”[20]2282“艾束著危冠”[21]等句即是證明。這類艾花制作簡單,但略顯粗糙,且時效性差。相比之下,絲織品類艾花雖制作略微繁復,但較為精致耐用,劉鎮《賀新郎》:“金鳳亸,艾花矗”,洪咨夔《菩薩蠻》:“翠翹花艾年時昨,斗新五采同心索”皆是指的此類艾花。將作為簪飾主體的艾枝用繒帛替代,其上再添綴各式的昆蟲或天師像,以為裝飾,精巧美觀又富有寓意。
另外,宋人還將門飾艾虎發展為簪飾。不同于門飾艾虎,簪飾艾虎更加小巧精致,但是制作難度也更大,通常是“以艾為虎形,至有如黑豆大者,或剪彩為小虎,粘艾葉以戴之”[15]54。由于直接用艾枝編成黑豆大小的制法難度較高,因此將布帛彩線做成虎狀再粘于艾葉之上的制法頗為常用。雖說只是節慶簪飾,卻也有制作極其精巧的,如鑲金的“蒙金艾虎兒”,以及“裊裊綴雙虎”類的雙簪艾虎。然而,不論樣式繁簡、價格貴賤,宋人端午簪艾的習俗及其美好心愿都是相同的。
五月初,蛇蟲增多、天氣濕熱,人易生病,而此時,艾草生長旺盛、氣味濃烈,人們自然而然地想到借艾辟邪禳毒,宋人端午節慶多用艾草也正是因此。宋代端午掛艾、簪艾等民俗形式,也表現出了宋人對生活的熱愛以及對生命的珍視。
三、艾草與疾病醫療
《師曠占》曰:“歲多病,則艾草先生。”[22]艾草最突出的特性就體現在其藥用價值上,據記載,早在兩千多年前艾草就已經入藥。至宋代,在醫療方面,人們對艾草的認識更加深入,應用也日趨熟練,并形成內服、外用兩大療法體系。
(一)內服
艾草入藥,可制成藥丸內服。在現存的宋代醫書中,有關這類艾制丸藥的記載屢見不鮮。例如:紫桂丸,將“禹余糧(火煅,醋淬七次,三兩);龍骨;艾葉(醋炒);牡蠣”碾為細末,“面糊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濃煎艾醋湯空心下,常服”。對于治療“沖任氣虛,經脈不調,或多或少,腰疼腹冷,帶下崩漏”[23],十分有效。香艾丸,“熟艾、陳皮(一兩),共末。酒糊丸,梧桐子大,鹽湯下二十丸”,專治“氣痢腹痛,臥眠不安”[3]795。另外,《十便良方》也曾記一則“艾硫丸”,將“熟艾(十兩,用糯米一升煎成粥,澆在艾上,用手拌,令勻,于日中曬干)、干姜(十兩)、生硫黃、附子(各二兩)”,制成細末,“面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或五十丸。溫米飲下,食前”。此方有“去邪養正。補員益脾”之功效,對治療“髓冷血虛,腰疼腳弱,及傷冷心腹疼痛,霍亂吐利,自汗氣急,下元久虛,小便頻數,婦人沖任不足,月水愆期,腹肋刺痛,崩漏帶下,全不思飲食”[24],療效顯著。諸如此類還有很多,不再一一列舉。
除此之外,艾草還多以各種湯藥的形式出現,或作為送服藥物的藥引子。例如“艾醋湯”,據《衛生家寶方》所記,婦人“血海冷”,服聚寶丹時,“以艾醋湯下”效果更佳[25]113。此外還有艾葉湯、艾姜湯、膠艾湯之類,均常見于宋代藥方。
(二)外用
艾灸是艾草醫療外用的典型方式。中國古人以艾灸醫疾治病的歷史由來已久,孫建[26]認為其起源當在西周之前。經過長期實踐,宋代的艾灸技藝較前代有了很大發展。
首先是艾灸器物的新發展。北宋王惟一受官府委派,專門設計鑄造了用于艾灸的經穴銅人模型。所鑄銅人“內分臟腑、旁注溪谷,井滎所會,孔穴所安,竅而達中,刻題于例”,可“使觀者爛然而有第,疑者煥然而冰釋”[25]2,如此一來,經穴教學和練習可更加形象化、直觀化,大大提高了施灸者對取穴技能的熟練程度。
另外,宋代艾灸理論也有了新發展。南宋竇材在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艾灸治療理論,其代表作《扁鵲心書》認為:“保命之法,艾灼第一”[27],這將艾灸療法推到了一個很高的位置;其次,強調在具體的施灸過程中應遵循“選穴少而精,灸壯數宜多”的原則,他認為:“世俗用灸,不過三五十壯,殊不知去小疾則愈,駐命根則難。”[27]最后,竇氏還強調應注意灸藥合用,以達到鞏固的效果。
雖然宋代艾灸有所發展,但是也并非為宋人廣泛接受。《備急灸法》記:“要之富貴驕奢之人,動輒懼痛,聞說火艾,嗔怒叱去。”[28]可見,接受艾灸時的人體感受是較為痛苦的,并非所有患者都愿意忍受。
在宋代,除了艾灸之外,艾草在治病時的外用方式還有熏、洗、涂、敷四種。《圣濟總錄》記有“艾汁涂方”一則:“艾一兩。細剉上一味,以釅醋半升,煎取濃汁,去滓,涂摩癬上,日三五度即差。”[3]1322這種治癬方子就是通過外涂藥物來起作用的。當然有時為了增強療效,也會有幾種方式結合并用的情況。《朱氏集驗方》就記有治療痔疾的“石膏熟艾散”之法:“用小口酒壺盛藥坐其口上熏之。如藥稍溫略略洗之。”[29]這種便是熏洗結合,先熏后洗。另外,《仁齋直指》中的“北艾湯”方子在使用時,則需更多步驟:“北艾一把。煎湯,密室中洗,仍以白膠燒煙薰之,縷貼膏藥,仍多服排膿內補散、加味不換金正氣散。又方瘡口已成大窟,以:桑白皮一分當歸半分上為末,干摻,外用北艾蘸蜜水,研細塞口。”[30]此方可謂是洗、熏、敷、涂四法的集大成者,對于治療癰疽瘡口十分有效。
四、結語
在宋代社會生活中,人們對艾草的使用情況大致如此。無論是平日起居保健還是節慶祈福禳毒,抑或是生病除疾養身,宋人用艾的現象不在少數。雖然宋人用艾的情景與目的都不盡相同,但也都是圍繞艾草的植物特性展開的,這也反映了宋代人們對艾草認識之深入、運用之廣泛。
隨著艾草融入人類生活,其與社會的互動也愈發豐富。至宋,艾草與社會生活聯系緊密,人們不僅留心其性狀,對其產地、用法亦有講究①。在不斷認知和利用艾草的過程中,人們也賦予艾草更多新的社會價值與寓意。艾草的眾多別名:冰臺、醫草、灸草等,即是例證②。也正是因此,艾草超越了原本植物屬性的限制,具有了聯接人類與自然、反映社會與文化的特殊意義。
宋人對艾草的認識是當時理性博物觀念的反映。兩宋時期是儒學復興的重要階段,其中宋學各派都十分注重對天道、天理的總結,宋儒往往樂于關注自然與社會,從世俗中存在的人情物理中概括出各種“理”,在這種文化氛圍下,人們對物的認知更為客觀理性。宋代以前,艾草常常被賦予迷信色彩,人們對艾草的具體名實往往關注不夠。然而,從宋代關于艾草的記載來看,人們不僅對艾草的生長、品性、用法有了較為細致的認識,并且重視艾草實用性。以蘇頌所著的《本草圖經》為代表,宋人記述有關艾草的名稱、性狀、生長習性等知識,頗具近代植物學的“科學”語言色彩。這反映出宋人對艾草的認識,已經不再主要受神仙方術以及道德迷信的桎梏,轉而追求對艾草作為自然植物本身的價值,這對于宋人與自然的關系而言,無疑是重大突破。這反映了在格物窮理的宋學研究中,以艾草為代表的更多自然之物進入了士大夫理論認知體系,相較于以前,物在世人的認知中有了更為突出的本體價值。
宋人對艾草的利用活動也與當時社會和文化相伴而行。人們的用艾活動在繼承前代的基礎上,又融合當時的社會特質,沾染了特征鮮明的時代氣息。
第一,重視實用。宋人講求積極實用,“宋型文化是積極昂揚的入世型文化,講究履踐,注重實用,強調經世,從根本上關注人怎樣生存發展、國家如何安寧強盛,體現出一種淑世情懷”[31]。當時人們對艾草的認識和應用也充分體現了這一實用傾向:驅蚊用艾是為衛生保健;飲食用艾是為調理養生;節慶用艾是為祛穢禳毒;至于治病用艾,其實用傾向就更為明顯,不僅有民間眾多醫者苦心鉆研艾灸技術、發掘艾草入藥功效,甚至朝廷也對此多加重視,仁宗時命王惟一鑄造銅人推廣艾灸技術即是證明。也正是出于追求實用的目的,宋代包括艾灸在內的艾醫理論與實踐實現重大突破。
第二,融攝三教。“三教合一”是宋學最為顯著的特征,漆俠先生認為:“宋學是在儒家思想同佛道兩家思想既互相排斥、沖突和斗爭,又互相作用、影響和滲透之下的一個產物。”[32]具體來看,宋以前的儒、佛、道尚處于兼而未融的狀態,而入宋以后,三者在新的社會環境中出于生存、發展的需要而相互融攝、相互滲透、相互補充,在思想層面上開始了深層的、廣泛的、有機的融合,逐漸形成了以儒學為主體,佛、道為輔翼的“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格局[33]。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不僅宋代士人對儒、佛、道人生哲學兼攝、融會,普通民眾也受到了其文化的熏陶。宋代社會從上至下都不同程度地滲透著三教融攝的因子,宋人的用艾活動也不例外。正如宋代端午節,“寺院鬻艾”[34],人們將艾草制成道教的天師形象,而不少文人儒士以端午“艾”事為題,賦詩作詞、抒發胸臆。這圍繞端午艾草而展開的一系列活動,看似平常且入情入理,但實際上也恰是宋代社會三教合一潮流彌漫的表現,是宋代用艾活動時代特征的彰顯。
艾草與社會生活的交互影響,也在宋人觀念與意識的流變中得到了充分詮釋。在日常生活中,艾草的應用與宋人的衛生保健觀念相映成趣。古人的衛生防疫意識相對薄弱,生活習慣多無衛生禁忌,這也對古人身體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損害。出于趨利避害的本能,人們有了“衛生”的意識。就宋人的用艾活動而言,在久受蚊蟲威脅的境況下,宋人通過熏艾、掛艾、戴艾等活動來應對或預防危險,這也正是宋人的“衛生”反應。而隨著人們對艾草認識的深入,艾草的藥用價值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在生存需求方面,人們不再滿足于僅是改善外部環境,而是進一步發展到了關注自身、強調養生保健的層面。宋人將艾草入飲入食,甚至以此來追求“甚補虛羸”[35]的效果,就是出于這種心態。從文化傳承的角度來看,宋代這種普遍的食艾現象與前代“空腹食之為食物,患者食之為藥物”[36]的“藥食同源”思想不無關系。不過,宋人飲食用艾,將食艾常態化,這顯然已經超出了“治病”的范疇,人們更多的是為強健體魄、養生“防病”。可見,宋人食艾與以往“藥食同源”思想所主張的“食物即藥物”的做法不同,人們更強調“藥物即食物”的這一面,即重視選擇具有藥用價值的食材。宋人食艾既是宋人為滿足自身保健需求的真踐,同時也實現了對前代“藥食同源”文化的繼承與發展。總之,不論是以艾驅蚊還是以艾入食,這些用艾活動都與宋人的衛生保健意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也是艾草與宋代社會聯通、互動的縮影。
較之前代,宋代社會已呈現出商品經濟繁榮發展、社會等級差別縮小、財富地位流動不居、民族之間并存融合、社會文化多元兼容等明顯不同。在這些新變的合力之下,人們對艾草的認識深受理性博物觀念的浸染,用艾活動則反映出重視實用、融攝三教的特點,而艾草與社會生活的聯通互動更是反映和促進了宋人衛生保健乃至養生意識的流變。在以上各方面的協同作用下,艾草與社會呈現出緊密融合、交互影響的態勢。
①蘇頌撰、尚志鈞輯校:《本草圖經》,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94年,第208頁。“艾葉,舊不著所出州土,但云生田野。今處處有之,以復道者為佳,云此種灸病尤勝,初春布地生苗,莖類蒿,而葉背白,以苗短者為佳。三月三日、五月五日采葉暴干,經陳久方可用。”
②參見(明)李時珍撰。《本草綱目》,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年,第430頁。其中對“冰臺”、“灸草”名稱的由來作了解釋:陸佃《埤雅》云:《博物志》言削冰令圓,舉而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則艾名冰臺,其以此乎?醫家用灸百病,故曰灸草。一灼謂之一壯,以壯人為法也。
[1] 紀昌蘭.醉里杏花:宋人詩詞里的“桃源意象”[J].江西社會科學,2019(8):121.
[2] 陳元靚.歲時廣記[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
[3] 趙佶敕.圣濟總錄校注[M].王振國,楊金萍,點校.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
[4] 葉隆禮.契丹國志[M].賈敬顏,林榮貴,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52.
[5] 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5:14035.
[6] 李時珍.本草綱目[M].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 431.
[7] 蘇軾.物類相感志[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1935:25.
[8] 袁文.甕牗閑評[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1935:68-69.
[9]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64.
[10] 梅堯臣.宛陵先生集[M].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1936: 129.
[11] 莊華峰.中國社會生活史[M].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14:203.
[12] 林景熙.林景熙集補注[M].章祖程,注.陳增杰,補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177.
[13] 高承.事物紀原[M].北京:中華書局,1985:307.
[14]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箋注[M].伊永文,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754.
[15] 周密.武林舊事[M].錢之江,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1.
[16] 陸游.劍南詩稿校注[M].錢仲聯,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377.
[17] 任汴,武陟仁.宋詞全集[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95.
[18] 應劭.風俗通義全譯[M].趙泓譯,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317.
[19] 吳自牧.夢粱錄[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22.
[20] 王諍,等.全編宋詞[M].延吉:延邊人民出版社,1999.
[21] 張春林.陸游全集[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513.
[22] 宗懔.荊楚歲時記[M].宋金龍,校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48.
[23] 齊仲甫.女科百問[M].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16: 73-74.
[24] 朱橚.普濟方[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755.
[25] 朱端章.衛生家寶方[M].楊雅西,等校注.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5:113.
[26] 孫建.中國艾文化遺產研究[D].南京:南京農業大學, 2016:71.
[27] 竇材.李曉露,扁鵲心書[M].于振宣,點校.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2:9.
[28] 聞人耆年.備急灸法[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 1955:32.
[29] 朱佐.類編朱氏集驗醫方[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1983:83.
[30] 楊士瀛.仁齋直指[M].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16.
[31] 虞云國.略論宋代文化的時代特點與歷史地位[J].浙江社會科學,2006(3):158-165.
[32] 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140.
[33] 張玉璞.宋代“三教合一”思潮述論[J].孔子研究,2011(5): 107-116.
[34] 賈大泉,陳世松.四川通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562.
[35] 李時珍.本草綱目[M].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4:431.
[36] 王者悅.中國藥膳大辭典[M].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 2017:54.
The Application of Mugwort in the Song Dynasty: A Reflection on Social Life
LIU Ch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Mugwort was widely used in the Song Dynasty. In daily life, people used mugwort in their diet and also used mugwort to drive away mosquitoes. During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people hung Ay Tsao in the shape of people or Heavenly Masters on their doors, and hairpin Ai Hua and Ai Hu on their heads to ward off evil spirits. When sick, people took mugwort as medicine, which could be taken, moxibustion, smoked, washed, applied, coated, ect. The understanding of mugwort of the Song Dynasty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oncept of rational natural resources. The use of mugwort of the Song Dynasty also reflected the emphasis on practicality and the unity of the three religions. In addition, the changes in the health care of the people of the Song Dynasty presented a vivid pictur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ugwort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society.
the Song Dynasty; mugwort; application; social life
K244
A
1009-9115(2021)05-0076-06
10.3969/j.issn.1009-9115.2021.05.014
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項目(2020M672192)
2021-03-25
2021-07-01
劉暢(1996-),女,河北衡水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宋史。
(責任編輯、校對:劉永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