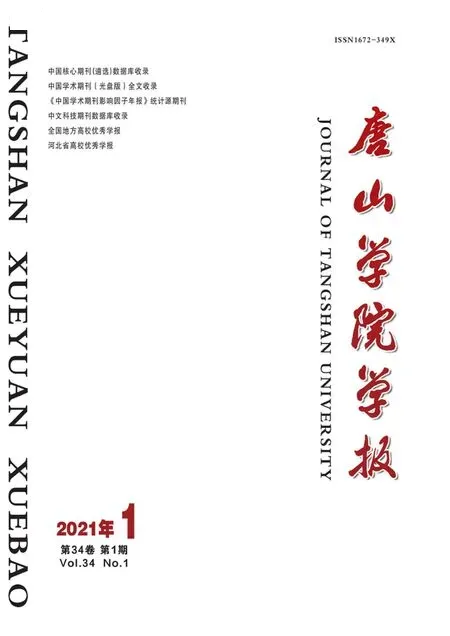消費社會中的審美泛化問題與美學策略
冀志強
(貴州財經大學 文學院,貴陽 550025)
從建構主義的視角來看,人的審美力發展是一個建構的過程[1]。對于具體的審美事件來說,這種建構表現出來的基本模式則是多樣性的。簡單來說,對一件藝術作品的審美鑒賞,通常是一個從對它的形式感知到對它的意義理解并從而達到更高層次意蘊領悟的過程。這是一種典型的審美建構。對于一般的形式對象,我們則可以直接由形式而產生一種無利害性的愉悅。這也是一種審美的建構。不管怎樣,審美建構的邏輯起點都是我們對對象形式的感知。但是在消費社會的環境中,以文化工業為基礎的形式對象,已經普遍性地阻礙人們完成這樣一種審美的建構。
一、消費社會中的審美泛化
最初是在西方,隨著文化工業的發展和消費社會的形成,關于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討論也走到了美學的前臺。“日常生活的審美化”(1)費瑟斯通的《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是由他以前的幾篇演講稿組成,其中第五章《日常生活的審美呈現》是他在1988年所作。韋爾施的《重構美學》也是由他以前的幾篇演講稿整理而成,而這些多是發表在20世紀90年代,在時間上略晚于費瑟斯通。這個說法最早是由英國學者費瑟斯通(M. Featherstone)提出來的,他在1980年代就提出了“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這一觀念。劉精明先生將其譯為“日常生活的審美呈現”,這其實也正是我們現在常說的“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另外,德國美學家韋爾施(W. Welsch)也在他的《重構美學》中描述了全球的“審美化”進程和生活中的“審美化”現象,而這樣的過程和現象也就是“日常生活的審美化”。
隨著這些理論的譯介與國內消費社會的日漸形成,學界也出現了關于“日常生活審美化”的熱烈討論。當然,中國社會目前還并沒有普遍性地達到西方學者所說的日常生活審美化的那種程度。在筆者看來,這主要是由中國社會的多元狀況決定的。中國的城市與農村基本上處于完全不同的兩種生活狀態,并且大量的農村也呈現出不同的發展層次。不過,在工業化和信息化大潮的沖擊下,中國農村的消費模式也在逐漸靠近城市風格。譬如,網購也開始在農村得到普及,女性的穿著與美容方式也在接近城市女性。所以,這種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趨勢在客觀上是無法避免的。對于這種現象所產生的問題,我們如何從美學的角度提出相應的策略,就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課題了。
其實,除了日常生活的審美化,還有一種是國內學者所謂的“審美的日常生活化”。這兩種情況的表現是不一樣的,并且各自也是多樣化的。我們這里先對這兩種情況的主要表現簡單地作一闡述,然后針對其中的問題提出策略。
首先是日常生活的審美化。我們可以再將其分為兩種情形。其一是生活環境的審美化。它的基本內涵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按照審美規律美化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器具以及我們生活于其間的空間環境。其實,這種現象自從人類進入文明時代就開始了。馬克思說:“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2]58這是人的生產生活的必然結果。這種審美化,只是古代和當代的程度有所不同罷了。其二是社會生活本身的儀式化與虛擬化。它尤其表現為消費社會中媒體對很多公眾人物所作的形象包裝,這種經過包裝而被推向公眾視野的形象通常包含很大成分的虛假呈現。這種審美化也是韋爾施所批評的主要方面。
其次是審美的日常生活化。這里說的主要是對藝術的審美。審美在傳統社會日常生活中當然也是很常見的,但它與消費社會中審美的日常生活化卻有質的不同。在傳統時代,對藝術的審美通常是一種特殊的欣賞活動,它的目的主要是為獲得一種具有超越性的精神享受,甚至于達到一種心醉神迷的忘我境界。但與此不同,在消費社會中,盡管人們也會在特定的場合中欣賞藝術作品,但更多的是將審美融入日常生活當中。這在以前是不可思議的。文化工業的發展,導致了技術復制藝術的迅速增長。在這樣的背景下,藝術作品可以通過現代媒介得到更大范圍和更快速度的傳播。這個過程一方面推進了藝術接受的民主化,但另一方面卻也導致了審美活動在日常生活中被邊緣化。如一個汽車司機在行駛中對車載播放器中音樂的傾聽,在這種狀態下,藝術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去了它的升華心靈的功能。邊緣化帶來的結果就是表層化。
總之,我們現在的生活中,處處可以審美,但這帶來的結果卻是審美的泛化。我們這里稱其為“泛化”,主要就是指消費社會中日常生活審美化與審美日常生活化中所包含的那種審美的普遍化與表層化狀況。這也就是深度審美的失落。
韋爾施認為,真正的審美不僅要有“感知的因素”,也要有“升華的因素”。這種“感知的因素”就是形式,而“升華的因素”就是這種形式所具有的向上的張力,比如它可以讓我們進入某種擺脫功利的情境。韋爾施嚴厲地批評了當今時代的全面審美化現象。他說:“全面的審美化會導致它自身的反面。萬事萬物皆為美,什么東西也不復為美。連續不斷的激動導致冷漠。審美化劇變為非審美化。由此觀之,恰恰是審美的理性,在呼吁打破審美化的混亂。”[3]34也就是說,現在這種審美的泛化導致我們的生活充滿了形式,但這些形式卻缺少了讓心靈安頓的功能。
二、媒介影像對真實的遮蔽
在闡述消費社會中日常生活審美化現象所包含的意義時,費瑟斯通認為,它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指在消費文化中充斥于日常生活各個領域中迅速閃現的“影像之流”;消費文化內部實現的是一種以影像為其主要內容的“符號操縱”。也就是說,符號和影像越來越決定著我們的消費選擇。這種消費的推動是以審美的方式或說是以感性刺激的方式來實現的。伴隨消費社會形成的,就是大量符號和影像的生產。
在消費文化中,藝術作品失去了“靈韻”(aura),而我們所接受的越來越多的會是波德里亞所說的“擬像”(simulacra)。這就是說,影像只是一種奇觀的展示,它與真實不再具有一種表征關系,而影像本身卻變成了真實。文化工業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出現了專門的符號生產者和文化媒介人等文化資本家,他們“生產出了各種消費的影像與場所,從而導致了縱欲的快感。這些影像與場所,還混淆著藝術與日常生活的界限”[4]131-132。此外,“實在與影像之間的差別消失了,日常生活以審美的方式呈現了出來,也即出現了仿真的世界或后現代文化”[4]98。所以,費瑟斯通認為:“后現代主義發展了一種感官審美,一種強調對初級過程的直接沉浸和非反思性的身體美學。”[4]179這就是審美的表層化和膚淺化。
這導致的結果就是,在日常生活的審美泛化中,我們已經很少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審美,我們通過耳目感官接受到的更多的只是多樣化的聲色刺激。在這樣的審美化中,我們的心靈失去了安頓與寄托。在筆者看來,生活當然需要審美化,但是與文化工業相聯系的審美化方式卻出現了問題。審美是人之為人的一種確證方式。審美化應該通過人的生產實踐活動使其自身的本質力量實現既符合真又符合善的對象化。并且,這種對象化要通過對象的形式結構呈現出來。但是,消費文化中的審美化卻是通過媒介與符號使得某些人或事轉化為一種虛擬性存在,即成為一種虛假的呈現。這實際上只是一種“漂浮的能指”。這樣,我們沒有生活在實在的“大地”之上,卻是生活在由無數影像所構成的“世界”之中。這個“世界”失去了“大地”的依托。
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蘇格拉底所說的‘美是有用的’命題,今天終于實現了。”[5]他們將文化工業視為“作為大眾欺騙的啟蒙”。在這種狀況下,文化通過娛樂影響大眾,然而文化與娛樂的結合卻導致了文化的虛假。這表現為,它既許諾著大眾,又欺騙著大眾;而它所使用的手段就是符號的生產。在消費社會,廣告是最出色的大眾媒介,廣告意味著一種“偽事件的統治”,它使得身體成為推動消費的主導力量。在這種審美方式中,身體成為了一個核心對象。廣告中的身體是商家建立的“典范”,然而這大多只是一種空虛的符號,它只是提供一種“虛假的承諾”。這就是現實的虛擬化。韋爾施說:“現實的重力正趨于喪失,其強制性變成了游戲性,它經歷著持續的失重過程。”[3]96這是由于當代傳播現實的主要工具就是媒體。所以,他對媒體美學進行了猛烈的批判。
當代社會中由于媒體的作用日益強大,尤其是其商業作用的強大,媒體的占有幾乎就是利益和財富的擁有,甚至是文化權力的占有。當下的娛樂明星、體育明星等諸如此類的時尚人物都是媒體推送的核心形象。但正如上文所述,那些活躍在大眾視線中的娛樂明星,在媒體中是以“擬像”的方式,而并非作為其真實存在的表征傳遞給大眾。這也就是波德里亞所說的“意指文化的勝利”(triumph of signifying culture)。我們通過他們在媒體當中的形象,無法獲知他們在真實生活中的行為與觀念。譬如,在某個明星的神圣影像背后,隱藏著的也許是那個人物在其真實生活中的墮落。在藝術作品中,人物形象雖然也是以虛構的方式呈現,但它要傳達出社會生活的本質與真相;然而,消費媒介中的虛構卻要讓人們相信這種虛假的呈現即為真實。所以,如果我們將他們的傳媒形式視為他們真實的生存方式,那就大錯而特錯了。但媒體文化所塑造出來的粉絲這一特殊群體,卻極易進入這種媒介的陷阱。所以,當代媒介導致了“文”與“質”被嚴重地撕裂。
三、基于形式的審美建構
對于審美泛化的問題,筆者主張以形式為基礎進行深度化的審美建構。消費文化以給我們提供大量形式為手段;而我們要進行審美建構,也依然要以形式為基礎。這是因為形式對于人的存在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馬克思所說的“美的規律”,首先必然表現為種種形式規律。《周易》中的“賁”卦也可以幫助我們說明形式對于人的意義。什么是“賁”?《周易·序卦》中說:“賁者,飾也。”[6]336許慎《說文解字》中也釋:“賁,飾也。”顯然,“賁”就是“文飾”的意思。《周易》“賁”卦中還說:“文明以止,人文也。”[6]105這是“賁”所包含的一個重要方面。那么,什么是“文明”?《說文解字》中說:“文,錯畫也,象交文。”也就是說,“文”就是交錯的線條,這是指形式上的修飾。因此,“文明”的基本要素就是作為“文”的形式。由此可以說,形式是將人類提升到超越動物層次的基本方面。馬克思以吃的活動為例,說明了人的感覺與動物感覺的本質區別在于,動物只能感覺食物的“抽象存在”,而人作為人要感覺到食物的“形式”,并且不是“最粗糙的形式”[2]87。因此,人的感覺超越動物感覺的本質就是對形式的自覺,并且人對形式的感知可以實現一種文化的建構。
但是,在文化的諸多領域,過度專注于形式,則極易產生虛假呈現或形式主義。中國古人也早就看到了這一點。對于作為形式因素的“文”來說,先秦諸子很多也提出了不同的策略以解決形式可能墮入虛假的問題。孔子強調這個“文”必須與“質”相關聯,達到與“質”的和諧,以實現一種“文質彬彬”的狀態。如果“文勝質”,那就是“史”,就是虛偽與浮夸。然而,老莊則主張人在進入文明之后還要重新解構掉這個“文”而以此達到一種超越的狀態。當然,道家這種解構的策略是不可能徹底實現的,因為“人”的存在就決定了“文”的存在。我們也可以說,有了“文”才有了“人”;或者說,有了“人”也就必然有了“文”,這二者是相互規定的。因此,在這層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審美是人與動物的重要區別,而馬克思又將其具體到“形式”的層面。
根據《周易》“賁”卦的闡述,我們可以說,文明的基礎就是“文飾”。在人的生活中,最典型的“文飾”莫過于服飾。服飾是文明的產物,它是使人區別于動物的重要標志。服飾的基本功能是使人不再始終停留于動物的需求沖動上。當然,人通常也需要服飾具有一種保持在“性”與“美”這二者之間的審美張力。但是在資本的控制下,人的本質已被深度地異化,社會關系則被全面地物化(2)這里說的“物化”并非莊子意義上的“物化”,而是盧卡奇所說的“物化”(reification)。。在這種狀況下,形式的升華功能受到嚴重的阻礙。我們已經很難基于形式完成一種審美的建構。
消費文化中最典型的影像模式就是廣告。廣告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應該就是女性的身體形式,她們的身體主要表現為商業價值的載體,其主要目的則在于以其形式催生人的消費欲望。廣告就是以這種感性刺激的方式實現其聚集財富的目的。面對消費文化語境中的這種女性身體形式,我們應該盡可能地保持一種審美的態度。席勒曾說,對于“有生命的女性”和“畫出來的女性”,我們經常更喜歡前者。但他指出,如果這個女性是有生命的,她“就不是作為自主的假象使我們喜歡,不是使純粹的審美情感感到喜歡”,因為“要使純粹的審美情感感到喜歡,有生命的東西必須作為現象出現,就是現實的東西也只能作為觀念出現”[7]。當然,他說的“生命”主要還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席勒也看到,在有生命的東西中,只感到純粹的“現象”(美的形式)是極其困難的。但話又說回來,即使我們的對象是作為“現象”出現,我們有時也并不能保證,我們可以對這個“現象”產生無利害性的審美愉悅。廣告中的身體現象就是不讓我們僅僅停留在對形式的無利害性觀賞中。
廣告媒介傳達給我們的雖是影像,但它卻要想方設法以此推動我們的消費沖動。現在的問題是,形式的泛濫淹沒了內在之物。人們離不開形式,但“人”作為真正的“人”卻在很大程度上又消失于形式。形式失去了深度,而被緊緊捆綁在了與本能和欲望的關聯之中。這是異化的結果。真正審美中的形式具有向上騰躍的張力。如果影像形式只是引起人的本能沖動或對文化中其他異化之物的沖動,那么這就是非人文的和反審美的。
因此,對于消費文化中的影像,我們的策略就是只把它視為影像,并且自覺地割斷影像制作者試圖將其與某種所指相關聯的那條臍帶。明白了廣告的商業策略,我們就應該自覺地對廣告形式作出一種相對孤立絕緣的觀賞,擱置其中不斷出現的指示性圖謀,從而產生無利害性的愉悅。當然,在實際的生活中,我們有時也需要將其作為消費的參考。如果能夠擺脫消費文化中形式對于我們各種欲望的牽引,我們就很容易通過對形式產生無利害性快感而實現一種審美的建構。
四、擺脫影像異化的審美方式
我們現在身處“美”的形式泛濫的世界,但是這帶來的結果卻是我們審美力的遲鈍和麻木。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8]在媒體紛擾的文化工業背景下,老子所說的這種現象顯出了其特殊的深刻性。然而,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即使這只是形式上的美。文化工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借助這種美的影像來實現其目的的。對于這種美的影像,我們不可能當然也沒必要完全拒絕它、遠離它。只要我們采取一種合適的態度,就能在很大可能性上不陷入文化工業的圖謀。
對于消費社會中充斥的大量美的影像,我們可以將其只是作為形式本身進而實現一種無利害性的觀照。古詩《陌上桑》是關于審美的一個很好的案例。當羅敷采桑之時,眾人陶醉其中。詩中描述審美中的人們說:“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須;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怒怨,但坐觀羅敷。”[9]他們因“觀”羅敷而“忘”其犁鋤,他們不僅忘了犁鋤,而且大半也忘了自身的存在。這是一種典型的“審美主義者”。與此相反,詩中的那位“使君”則是對于“形式”的“功利主義者”。前者只是對美的容貌保持一種無關利害的凝視;而后者則是意圖將美的對象占為己有,這當然是權力使其審美態度發生了向欲望的轉變。美本身當然是無罪的,但它卻是極具魅惑力的。消費文化通常就是利用美所具有的這種魅惑力來產生作用。廣告通常暗示甚至直接告訴我們,只要購買了產品,就可以達到它所呈現的那種美的形式或者那種完美生活。然而,這通常只是一種難以兌現的承諾。
但是,總是沉醉于美的形式(即使是以審美的方式)也會帶來問題,因為美的形式通常會消弭我們的理性判斷。因此,基于消費文化中泛濫的、浮華的形式,韋爾施提出的對策是“審美化的中斷”。他說:“在今天,公共空間中的藝術的真正任務是:挺身而出反對美艷的審美化,而不是去應和它。”[3]14現代藝術對“美”的抵制也是出于相似的邏輯。在提供美的對象方面,大眾傳媒與古典傳統有相似之處。現代藝術對于古典藝術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對美的放逐。這就表現為現代藝術中有了大量丑的形象。前衛藝術家特里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曾說:“我有一個瘋狂、星光閃閃的渴望,要謀殺美。”[10]這主要是由于藝術家們看到,我們生活的世界有很多惡的事物,但是美的泛濫會讓人們忘記了現實中的惡。在這一方面,古典主義與消費文化中美的呈現帶來同樣的問題。所以,為了防止消費文化中的美的形象鈍化我們的敏銳度與判斷力,我們要盡可能多地接近現代藝術,而不是一味陶醉在古典主義與消費文化中的美的形式。這樣,我們就容易對美的事物保持一種警惕。
為了抵抗消費文化給我們帶來的感知力麻木,另外一種方式就是與自然親近。由于消費文化中的審美泛化帶來的技術異化,韋爾施寫到,那些加利福尼亞的電子精英們白天在電腦前工作,傍晚便驅車去看加利福尼亞落日。我這里說的是真正的親近,因為消費文化也會讓我們走近自然,但那通常不是真正的親近自然。
我們以對自然景觀的觀看來說明這種文化技術所帶來的異化。走到山水之間,我們本應該用自己的眼睛“觀看”周圍的風景。但事實上,我們的眼睛已經被相機所異化,我們的觀看已經被拍照所異化。風景本來應該是我們“觀看”的對象,但是現在卻成了我們“拍照”的對象。在消費文化中,風景進入了我們的相機,進入了我們的手機內存,它存在的意義就得到了實現。對于眼前的景觀,我們當然可以將其“保存”,用其“曬圖”,但我們應該更多地去凝視它們、去體驗它們。沒有了凝視,景物對于我們也便很難產生詩意。
在自然中,我們容易實現與世界的統一。親近自然,首先就是我們用自己的眼睛觀看自然,用自己的耳朵聆聽自然。這種觀看與聆聽容易使我們忘掉日常生活中的功利。在日常生活中,“心”通常是對象性的,它總是通過感官與外在的世界相對立;但在自然當中,我們通過移情于自然而更容易實現與世界的合一。心在身體之中,身體會成為阻礙心物合一的一個障礙,所以心與物的合一是需要條件的。健康的身體固然可以讓我們心態平和,但是欲望的身體讓我們不停地心猿意馬。
心與物之間最純粹的“人的方式”其實就是審美方式。在自然審美中,當我們由觀看和聆聽進而真正陶醉于自然,我們便會忘掉自然的外觀。這時候,我們的“心”就容易達到一種“無意”,我們的身心就容易達到一種“自在”。在這種“自在”中,我們便擺脫了文化給我們心靈的壓力。這種“無意”通常在我們對自然的移情與體驗中實現。在這種情境中,我們的心可以使身體在世界之中實現某種程度的超越。這種體驗著感性自然而又不執著于自然外觀的狀態,就達到了身心一體的超越。這可以視為一種深度的審美建構。這時,世界已經不是一個被我們所凝視的對象。同時,這樣的身體也不是一個需要被凝視的對象。當我們的心使得我們的身體實現了在世界中的超越,我們的身體也就成了一個自然(naturalness)。這時,它真正地實現與世界的統一。當然,這種帶有莊禪意味的超越方式對于我們常人來說可能只是一種不可企及的理想境界。但是至少,我們在觀看媒體中的影像形式之時,也應該讓自己的眼與心盡可能地保持在平衡本能與升華之間的張力上,這是對感性的親近,也是對欲望的抗拒。我們應該讓審美成為對感性的拯救,而不能冠以審美的名義讓感性墮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