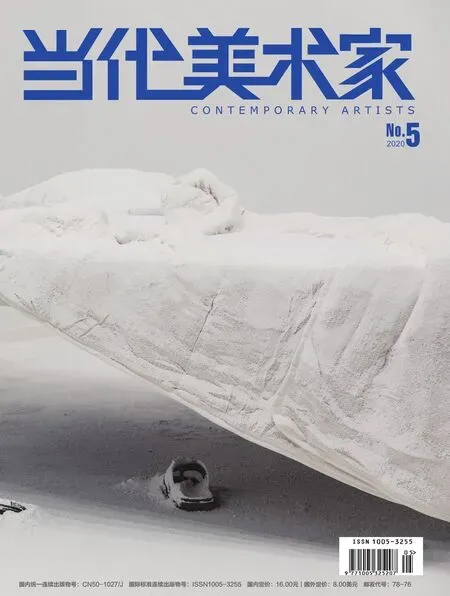當代國畫傳統創作精神缺失的批判性思考
陳樺 羅念 Chen Hua Luo Nian
引言
縱觀人類文明史,誕生過優秀人類文明的土地上,都會形成一種文化風貌和繪畫形式,在這種繪畫形式背后都會有文化意識形態,也會承載國家的文化意志,而在繪畫內容當中,民族文化會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無論從遠古時期的石器時代還是到科技應用的當下,繪畫這一門藝術形式一直在人類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也一直被歷代統治階層所重視和運用。
國畫,作為中國特有的藝術形式,由于根植在延續千年的中華傳統文化中,所以能夠看到一個清晰的發展脈絡,也能看到大國文化意識的彰顯。中國畫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繪畫方法和審美品評要求,因此,也極具鮮明色彩。傅抱石作為中國國畫藝術大家曾就構成中國畫的基本條件做了如下的簡要說明:即凡是用紙、筆、墨或淡色所作的畫,可以卷或掛的,內容以山水花鳥居多1,這些東西加在一起就構成了中國畫。簡單幾句話便道出了中國畫所要具備的特點,道出了中國畫與西方繪畫的區別。談論中國畫繞不開中國畫的精神,關于這一點,傅抱石更在其文章《中國繪畫之精神》中從:超然的精神(包括筆法、氣韻、自然)、民族之精神和寫意的精神等三個部分詳細闡述了其內涵。這三種精神代表了中國傳統繪畫的藝術成就和創作思想。然而,隨著十九世紀末西方繪畫理念和藝術作品傳入中國,中國畫一枝獨秀的傳統局面被打破,無論從創作思想還是創作方法都開始發生轉變,伴隨著世紀末的動蕩和舊體制的瓦解,封建傳統文化沃土也逐漸消亡,享受特權的文人士大夫階層也消失,之后的社會變革等一系列事件,使中國畫傳統創作精神也在歷史的蕩滌中慢慢缺失。
一、現狀與思考:
中國畫所使用的獨特物質材料和審美原則造就了中國畫藝術形態,而它反過來又促進了繪畫民族風格的完美發展2。中國畫創作中的骨法與線是密切聯系的。筆法也稱線條,是中國畫最顯著的基本條件,謝赫在《古畫品錄》中曾提到“骨法用筆”或“骨法,用筆是也",事實上,中國畫就是以線勾勒對象造型、結構、表情、體態等,以線的準確性、力量感和變化感來把握物相的諸多形態,線成為了中國畫表現的核心內容,線成就了中國傳統繪畫的基本面貌,線也成為了一種可獨立欣賞和品評的形式要素。中國畫的線開始于物象描繪,卻又超乎于物象形態之外,將線在造型中的表象性功能和表現性功能合二為一3,線就具有了超越物象的自身獨立性,也自成為另一種藝術樣式——書法。中國書法一方面最能表現一個人的文化素養和氣質人格,它既是文明的承載也是一門藝術,這些是任何其他民族文字所無法企及的;另一方面,書法的審美原則和用筆規律也極其獨特,它追求的是一種虛實的平面結構布局關系,完全利用線的組合去表現思想與情感。所謂“書畫同源”,這個“源”就是中國畫的線條融合了書法線條的特點,線條密切地與運筆法則和立意相結合4,使表現范圍通過承載媒介的不同得到充分擴大,畫家在運用骨法用筆去概括自然物象時,可以更好地融入個人的書法氣韻。石濤曾說過“畫法關通書法津”,由此可見,中國繪畫與書法的使用工具與藝術本質是共通的。

顧愷之女史箴圖(局部)絹本設色34.8cm×348.2cm東晉
《石魯談中國畫》中曾明確表示:“……要把東西畫像,而且要把東西畫神,沒有神就沒有風格,中國畫的精神就沒有了。所以我們把書法、筆法叫基礎。這就是最重要的基礎,其它都是條件。”5而當下中國畫創作中線條(書法)的缺失是最先出現的,其表現是傳統造型和畫面的平面布局中毫無書法的用筆痕跡,取而代之的是西方速寫。線條缺失了骨法,繪畫只剩下對肌理質感、體量感、三度空間感的追求6,中國畫中無骨也無神,這種現象主要是受西方繪畫思想、造型手法和審美觀的影響。中國繪畫傳統是以散點透視來安排畫面,遂形成了平面布排的構圖形式,筆的力道與墨的濃淡干濕表現物我合一的天人意象,是以骨法的線加筆墨陰陽營造平面性的畫面結構。而西方繪畫所運用的焦點透視,更注重用光影與明暗來塑造一種視覺真實體驗,物像的體量感和空間感所營造的視覺真實是建立在以輪廓線加明暗的立體結構基礎之上。作為完全不同的兩種繪畫形式,如果將筆墨施諸于西方的三維結構造型上7,那么,筆與墨的力量會被降低甚至弱化為營造物象明暗或質感的成分,那就沒有線條語言的獨立審美性可言了8,而這正是當代中國畫的矛盾點;其次便是筆墨的問題。筆即是用筆,墨即是墨法。中國畫歷來倡導畫外功,提倡涉獵要廣泛,厚積方能博發。當下國畫發展日趨西化,專注寫實功力,忽視對支撐中國畫,尤其是寫意畫筆墨語言的書法能力的提升9,傳移模寫不再重視,中國畫構圖法式與程式更無從談起,致使中國畫審美品評和文化內涵大大降低。中國畫的品評高下用六法論之,缺乏筆法(書法)的內在支撐,外加傳統的應物像形和經營位置皆無,如果再忽視傳統繪畫法式與圖像程式,那么中國畫在何種意義上還能被視為是國畫呢?
氣韻是中國畫的精髓,也是品評的最高標準。如謝赫主張“形神兼備、氣韻生動”,顧愷之提出“傳神論”,潘天壽說“畫事以筆取氣,以墨取韻”,齊白石論“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太似為媚俗,不似為欺世”。可見,氣韻是中國畫的最高境界。而當代中國畫氣韻的缺失卻是不爭的事實。一直以來,中國畫本身自帶一種懷古的韻味,無論是用的紙墨筆硯,還是作畫方法等,都已傳承千年。
要談論中國畫創作,必定繞不開“傳統”這一詞匯。在新的時代,“傳統”與“現代”顯得格格不入,要讓中國畫走入現代的文化語境,是否就要拋棄傳統?保持傳統,并非拒絕現代。同樣離不開對國畫創作工具、材料和創作方法技藝繪畫理論的重視、使用和解讀。當代國畫創作,卻在一前一后的文化撞擊中,有點迷失方向。中國畫在與西方文化相遇時,一直嘗試做出一種改變和創新,能更好地融入時代語境,更具國際語義。結果西方繪畫理論和方法成為當代國畫創作的指導,在學院派(藝術高校)國畫繪畫領域中,書法已成為一個單獨的學科從國畫中被分離出來,國畫朝兩個方向發展,一個是摹古、仿古;一個是以水墨實驗為主的創新。前者的創作就是將古人經典作品進行復制,這里的仿古被視為一種創作方式,并不等同于六法當中的摹寫,六法中所指摹寫,一是可學習基本功,二是可作為流傳作品的手段,而謝赫卻并不將它等同于創作,因此放于六法之末。后者是將水墨作為一種材質,通過各種手段激發水墨的可能性,造成不同肌理藝術效果,形成一種新的視覺感受。學院派兩種學習路子,又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陣營為之搖旗吶喊,讓國畫的傳統創作與之偏離得更遠;另外占主流的國畫藝術圈及市場,也形成了兩種派別:“西畫為主,融合國畫傳統”和“國畫傳統為主,融合西畫”10,無論上述哪種,中國畫的精髓都不在其中。將西方繪畫明暗光影關系轉變為墨色的濃淡表現、用速寫線條代替書法用筆11,這一簡單的形式置換,其實質是對中西方藝術做出的單純折衷式的拼湊,絲毫沒考量傳統和圖像的語法關系12,沒有建立起國畫完整的生態語義。當下存在不少畫家運用西方繪畫理論和方式創作國畫,乍看頗具國畫意味:詩、書、畫、印皆全,也構成了國畫新面貌,但在這類繪畫中卻無法呈現出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經驗感受以及個人情感13,只是為了國畫創新形式而忽略了中國畫的寫意靈魂,他們看重的是國畫工具和材料為作品附加的中國標簽,傳統符號為其增加的市場價值,傳統文化和藝術傳承并不是他們考量的對象。又例如,走“國畫傳統為主,融合西畫”路線的國畫作品,在造型、用筆、構圖基本形式上是模仿古人,山石皴法不是來自王蒙就是來自馬遠,江南的畫家所創作的作品多與倪云林相仿,北方的畫家則努力把畫面畫黑方顯得厚重,這種“摹古”,僅僅單在技術上刻意模仿出一種畫面的古意表現,只簡單學到了國畫的外在皮毛,不深究向內的力透紙背的筆法來呈現國畫筆力和寫意精神。少見恣意揮毫、見情見性的寫意佳作,更談不上國畫的氣韻之生動,做的都是表面功夫14。

懷素苦筍帖絹本書法
寫意精神在中國畫藝術中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也是中國畫能夠被稱之為“中國畫”的重要原因,它是中國畫藝術獨特的身份,一種必不可少的精神。然而,二十世紀卻是中國畫寫意精神遭受嚴重打擊的時期,薛永年對二十世紀中國畫寫意精神的缺失過程做了簡略而溫和的概括:“經過20世紀以來洶涌的西學東漸,對文人寫意畫的簡單批判,不少企圖革新的藝術家,都努力向西方尋求真理,以寫實的觀念、寫實的方法、寫實的基本功,改造中國畫15,改革開放以來又把西方現代各種風格流派都實驗了一遍,學來了很多東西,但消化得并不是很夠,就用西方現代主義改造中國畫,致使寫意精神在不少畫家那里不同程度地丟掉了。”16直至當今,許多的國畫家更是把主要的精力用于技巧和個人符號的發明復制中,而忽視了傳統文化認知和中國畫理論思考,盲目求新、求異拋棄了國畫創作的本質屬性和寫意情感,寫意精神缺失的一大體現就是該類作品的縮減。當今國內,除了寫意專項展以外,幾乎所有的大展都存在這樣一種現象,即參展作品主要是以工筆畫為主,寫意作品僅占據很小的一部分,在獲獎作品中的寫意作品更是鳳毛麟角。當然這和參展呈送寫意作品的質量有很大關系,但更重要的是與展覽的導向、評委品評標準以及參展者的心態有關。鑒于當代中國藝術西化的朝向,評委在評審作品時大都會帶著一種西方標準來看待作品,這樣真正的傳統國畫就不適應品評口味。再者,畫家通常認為制作一張夠大、夠精細的工筆畫作品送展參評,即使不獲獎,入選的機率也總能比寫意畫參展大的多。內外因所致,很少有人甘愿冒險送評寫意畫,造成的結果是中國畫傳統創作局面很難打開當下的藝術市場。
二、批判與反思:
導致中國畫傳統創作精神缺失的原因有很多,總結重要幾點供關注和思考:
首先是社會變革導致的傳統文化與現代的斷裂,文人階層消失。中國封建文化體制造就了一個文人士大夫階層,這一階層在當時的社會中具有很高的政治話語權,這種權利的獲得來自他們對內極高的文化修養,也憑借高水平的文化素養區別與社會其他階層。他們向內精修詩、書、畫、藝,不僅具備較高的文學素養,更長于書法和各類技藝,向外通過文化品味所形成的圈子影響和固守他們的政治地位。他們并不被視為繪畫匠人的原因也在于他們自身文化身份的這一特征,通過文人這一身份將書法筆墨進一步擴展到到繪畫領域,以文人畫區別于工匠畫,并將文人專長的詩和書法用筆與繪畫相融合,自成一種繪畫的意境,開創了中國畫獨特的文人風貌。這一點也證實了繪畫對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相互關系。像盛唐時期的王維,不僅在文學上造詣極高被公認為“詩佛”,也被稱為文人畫領域的“南山之宗”、錢鐘書先生稱其為“盛唐畫壇第一把交椅”,他還精通音律,善書法并篆得一手好印,是少有的全才。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以文人為代表的繪畫是蘊含極高文學成分的。中國繪畫體制至宋日臻成熟,宋代極重文官與文人的政策也影響了后世的政治和文化發展,他們在政治所具有的話語權,也為他們對文化的捍衛提供了一種便利。中國畫文人審美趣味也自此左右了中國傳統繪畫的長遠發展,形成了中國畫的獨特審美品格。像蘇軾、米芾、董其昌、倪云林等這些精于詩詞書法的文人們,提出詩、書、畫結合使中國繪畫走向詩化17。正是文人的審美和綜合素養,提高了中國畫的精神質量,也提高了文人畫家們的繪畫水平,推動了中國畫的新發展。而自封建制度走向滅亡,沒有了傳統文化的存續,文人階層也就逐漸退出歷史舞臺,沒有了賴以生存的物質和文化沃土,無法再享受到特權階層的優待,中國畫的傳統創作還靠何人來支撐,傳統藝術精神更將如何存續和發展?
當代中國,也有文人階層,他們普遍是受現代教育培育下的新文人。這些文人修養與繪畫技巧是斷裂的。自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整個國家就自上而下開始實現政治體制和教育體制的現代化,在西方現代教育體系之下進行的中國傳統繪畫教育,專業和職業的分工又被細化,只注重對繪畫技巧的培養和學習,畫家們綜合文化素養的培養則被逐漸忽視,這又造成了兩種后果,一種是學習西方的繪畫技巧,因為沒有全面的掌控能力和足夠的西方文化和知識背景,無法獲得預期效果;另一種則是學習古人的繪畫技巧,卻因為沒有豐富的文化底蘊修養及綜合素質,同樣無法達到古人高度。這種綜合素養和繪畫技巧的斷裂使得中國畫成為一種空洞的線條和墨色的堆積,缺乏精神內涵。
其次是強勢文化介入弱勢文化,導致文化不自信,盲目崇外。改革開放之初,西方文化思潮涌入中國,傳統文化尚存的最后一點根基也被丟失。一方面,由于西方畫科不斷引入,“85”新潮美術運動之后西方藝術理論在中國全面開花,在面對中國社會和思想出路的這一時期,對西方思想文化的學習得到高度提升,西方的各個哲學、藝術派別得到熱烈的追捧。這使得中國畫傳統創理論的研究,無論在觀念上,還是在概念上;不管在文化立場,還是在審美角度,抑或是創作態度上都渾然不覺地偏向了西方美術觀18。另一方面,當代畫家大多是受近代美術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這種繪畫教學體系由徐悲鴻先生一手創建,在這種體系中,西方繪畫理論和思維教育遠超于傳統國畫思維教育,教學中強調素描的空間造型、明暗光影及色彩塑造,注重寫實技巧的訓練,淡化了對傳統文化修養的要求。當代畫家們成長在一沒有豐厚傳統文化,二沒有中國畫傳統造型方法,三沒有書法線條的骨法和用筆功力的背景下,接觸的又是輪廓加明暗的立體結構,造成無法分辨中西造型手法和造型能力的缺失,在這種情景下學習的中國畫,還時常以無法區分中西造型而竊喜,以素描寫實能力的強化而樂此不彼。在不少人的認知觀念中,國畫就是素描功底加墨水顏料,這也成為新時期中國特有的國畫風貌。將技法訓練和文人修養割裂的培養方式,最終導致中國畫傳統境界和精神的缺失。
第三,國家對傳統文化保護的力度以及文化政策導向不足。一段時間以來,無論各行各業只要提到創新,就會提到高度化。傳統繪畫的盲目創新,造成傳統國畫思維缺失。在西方審美觀的影響下,為了進入時代語境,中國畫家們潛移默化地把創新視為中國畫新發展的追求,這促使不少畫家在追求創新的同時忽略了對傳統的品格和思想的研究,而這正是國畫傳承發展所要被重視的。對中國畫創作而言,創新只是一種手段和方法,畫家們通過創新,發掘新的主題和視角,提高其藝術創作內容和主題的新穎性,使作品更加具有時代氣息,國畫內在品質更完善、思想更加豐富。這種具有較高時代思想特質的作品,不可否認是具備優秀創新作品潛質的。遺憾的是,當代很多繪畫者視手段和方法為創作的最終目的,綿綿不斷地繪制出有新意卻不具品質和思想的作品,創新被簡單地理解為用“民族文化符號”進行挪用、拼貼和復制,這種左右逢源的藝術操作,即迎合了當下呼喚傳統回歸的文化訴求,又讓其在藝術市場得到特殊青睞,這種操作無疑是讓國畫創新誤入歧途。另外,長期以來,國人秉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思想將西方審美現代性作為中國畫時代發展的要求。把中國畫發展建構在西方繪畫的現代性坐標上,從而制約甚至延緩了中國畫的時代發展19。我們并不反對創新,反而一直強調要開拓創新,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吸收西方繪畫發展的良性因子,也要在創新中保持傳統文化的姿態,明確創新的宗旨。因為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傳承中國畫的繪畫思想和語言才是創新和借鑒的前提,強化中國畫傳統繪畫方法和宣揚民族文化精神才是藝術發展的真正目的。
三、傳統與復興: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代中國畫傳統創作精神的缺失是一個歷史性問題,是時代轉換下社會各類因素綜合作用的長期結果。解決這一問題也非一朝一夕。然而由于中國畫的傳統精神是中國畫立足于現在,發展于未來的根本,必須重視,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從內至外、從上至下的梳理發掘。提出幾點拙見供睹參考:

粱愷太白行吟圖紙本水墨81.2cm×30.4cm
一方面,要改變當下國畫人才培養模式,在重視繪畫技巧的同時一定不能忽視傳統文化的教育,要懂得只有先培養出具有較高綜合素質和文化修養的人,才能培育出高水平藝術家這一關鍵點;另一方面要跟隨國家主流文化政策,強化對傳統文化的學習,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從小培養和樹立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形成國人自己的優秀審美觀。例如,借鑒日本對紙藝傳統的保護和傳承實例,從中小學開始將傳統文學、書法和國畫納入國民美育教育范疇,從小強化對傳統文學作品的品讀,對書法、國畫藝術的認知,落實對中國畫的審美教育。努力為中國畫傳統創作精神的傳承營造一片生長的沃土,從小播下一顆文化的種子,才能等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大樹扎下堅實的根基,在國人的呵護和共同努力下,中國畫創作精神才能實現本體回歸,能在未來發展中去創作和創新。
四、小結
國畫在近代發展歷程中經歷了全盤西化到改良主義再到中西調合、中西融合的理論發展,中國繪畫中創作精神一直如螢螢之火一般時隱時現,這是歷史進程中中國傳統文化遭遇的落寞與悲哀。堅持傳統并不等同于因循守舊、死守窠臼,像白石老人、黃賓虹、傅抱石、潘天壽等這些傳統國畫大師,他們的創作一直是傳統地道的國畫風貌,但卻極具個人特色,一直在國人和西方人眼里被視為極作。他們的傳統來自于厚積薄發的傳統文化修養,更來自于他們業精于勤的傳統功力的掌握。他們既沒有過多“融西”也沒有沉迷于死守傳統摹古的窠臼,他們的藝術成就在于畫里始終存在著中國畫幾千年來一脈相承的靈魂——文學、書法等文化綜合修養在一個畫家身上的集中彰顯。正因這些隱形的綜合修養,才成就了他們的藝術,也讓他們成為國畫藝術中大師而區別于普通畫師,在他們的創作中彰顯了國畫的品格:“氣韻”、“境界”和“意境”,保持了中國畫的傳統精神而不被流失20。面對這些保持傳統的生動實例和當代中國畫的現狀,不得不反思當下:為何寧愿選擇從屬于西方的審美而不愿建立自己的美術觀?為何寧愿放棄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而追求炫目的技藝?為何寧愿相信只有西方才能夠拯救當代中國畫而不愿相信中國傳統文化的厚積之力?
歷史的進步難免會造成急功近利、舍本逐末的情景,中國畫傳統創作精神的缺失正是前進中扔掉沉舊“包袱”的后果。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丟掉的能被撿拾回來或許要耗費更大的氣力,如若遺失,那就謂之損失。沒有了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民族將何以為繼?沒有了傳統繪畫的風貌,如何讓世界認識國風,民族精神、民族力量以及中華民族的國家意志將如何彰顯?“路漫漫求修遠兮”,守好民族文化,傳承好傳統精神,方能顯示中華民族強大而深厚的文化意志。
注釋:
1.傅抱石:《中國繪畫之精神》,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年1月。
2.岳婷:《淺談從中西方繪畫中比較談中國畫線條的獨立藝術價值》,中國知網。
3.莊姝:《淺論國畫的筆墨與線條》,《藝術教育》,2011年第9期。
4.徐歡、王蔚然:《論中國畫線條的獨特魅力》,《美與時代(中)》,2018年10月。
課程整合比較主流的理解是“把計算機技術融入到各學科教學中,就像使用黑板、粉筆、紙和筆一樣自然、流暢”。這種觀點將課程整合的重點放在CAI,即計算機輔助教學上。它突出計算機作為工具,去輔助各傳統學科的教學。
5.吳文莉:《論當代中國畫缺失的靈魂》,《吳文莉隨筆散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32b0c50100c6v8.html,2009年2月。
6.張桐瑀:《從“中國美術觀”的缺失反思當代中國畫發展現狀》,《美術觀察》,2010年第10期。
7.鄧楠、孔光、莫婷婷、王婷:《從造型觀念與造型手法看中西方繪畫的同異》,《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8期。
8.易從網:《萬壑千巖鎖翠煙——李林宏中堂(書畫)文化賞析》,易從網,2019年9月4日。
9.李林宏:《青山迎旭日賞析:一山一水盡顯自然氣韻》,中國書畫藝術網,2019年9月19日。
10.同 5。
12.尹丹:《批判性傳統主義之“轉譯與重構”》,《藝術中國》,2016年7月8日。
13.同 5。
14.同 5。
15.俞劍華:《中國古代畫論類編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57年10月,第99頁。
16.薛永年:《談寫意》,《國畫家》,2006年第2期。
17.同 5。
18.張桐瑀:《從“中國美術觀”的缺失反思當代中國畫發展現狀》,《美術觀察》,2010年第10期。
19.同 18。
20.廖永躍:《論中國畫的品質》,《職業》,2010年第8期,第133-1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