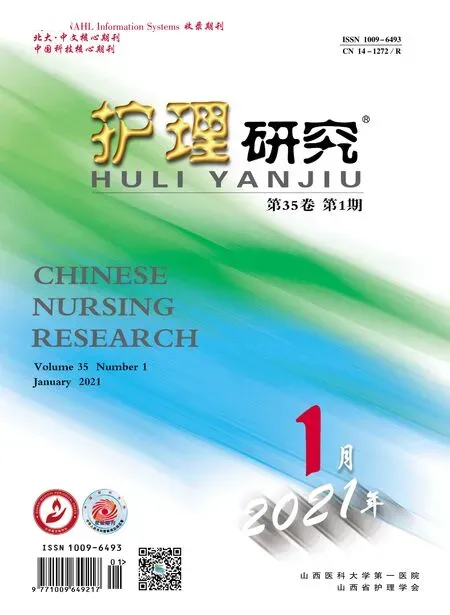癌癥病人夫妻疾病溝通的研究進展
成 香,杜若飛,鄭可心,周會月,王 濤
鄭州大學護理與健康學院,河南450000
癌癥的診斷和治療是產生長期影響的心理痛苦事件,會改變病人及其配偶原有的溝通模式和家庭角色[1]。大多數病人并不是孤立地對抗癌癥,配偶是其主要照顧者和情感支持者[2]。由于治療效果和預后的不確定性,病人及配偶在疾病應對中可能會出現焦慮、抑郁、疲勞和性功能障礙等問題[3]。人際動力學理論強調夫妻溝通在心理調整和疾病應對中起重要作用,夫妻癌癥溝通不僅直接影響心理健康,還可以通過調整其應對方式來影響心理壓力[4]。2011 年,美國癌癥協會提出要鼓勵病人和伴侶公開表達自己的感受和需求,隱藏情緒會導致更大的心理壓力和隔閡[5]。目前,研究者已經認識到夫妻疾病溝通的重要性,已有研究從基于夫妻的角度制定心理康復措施來提高夫妻的疾病應對能力[6‐7],其中,夫妻溝通技巧培訓通常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國外研究已經證實,夫妻疾病溝通對病人的康復及親密關系至關重要,但國內缺乏疾病溝通與生活質量因果關系的調查。現將國內外夫妻疾病溝通概念和現狀以及對健康結局的影響、影響因素、相關干預措施等進行梳理,以期為疾病溝通研究提供參考。
1 溝通相關概念及現狀
1.1 溝通相關概念 溝通是人與人之間、人與群體之間思想與感情的傳遞和反饋的過程,以求思想達成一致和感情的通暢。在癌癥相關的文獻中,溝通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Reblin 等[8]稱溝通是滿足需求,表達親密、支持或不滿的手段,疾病溝通包括任何關于藥物、癥狀、保險、預約等方面的信息交流或情緒表達。Lixin等[9]認為夫妻疾病溝通指病人和配偶交流疾病治療信息以及個人對治療的感受和憂慮的過程。Fisher 等[10]認為疾病溝通包括開放型和回避型溝通兩種模式,開放型溝通指愿意表露自己的感受、經歷或信息,而回避型溝通指試圖阻止或終止對特定主題的討論。在應對疾病時公開交流與健康的結果相關,逃避會導致關系功能較差和身心痛苦。
1.2 夫妻疾病溝通現狀 國外學者對夫妻疾病溝通做了多項質性研究,而量性研究較少,主要存在夫妻疾病溝通水平低、回避敏感話題、內容缺乏情感支持等問題。Reblin 等[11]對83 例晚期癌癥病人及配偶的溝通內容進行錄音,結果顯示,1 d 中夫妻交流平均總時間少于2 h,關于疾病溝通時間中位數僅為1.46 min,且常局限于藥物治療和預約等內容,避免對癌癥治療、副作用、疾病發展、復發及負性情緒等話題的討論,22%的夫妻甚至沒有討論癌癥話題。但本研究中錄音方式缺乏對面部表情、擁抱、撫摸等非語言溝通的記錄,例如配偶可以通過面部表情識別病人是否處于疼痛狀態避免談及相關話題以免增加病人心理壓力。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探索語言和非語言溝通策略對溝通時機的影響。Masjoudi 等[12]研究表明,開放與回避型溝通中會同時出現,適應良好的夫妻開放性交流較多,但對于性生活話題存在溝通障礙,其主要體現在乳腺癌、前列癌病人中。
2 夫妻疾病溝通對健康結局的影響
夫妻疾病溝通主要分為開放型和回避型兩種類型,開放型溝通有利于改善夫妻親密關系、降低心理痛苦、減少疾病不確定感,回避型溝通會加重夫妻焦慮、抑郁水平和不良的應對方式。韓國一項調查顯示,回避溝通是病人抑郁水平的預測因素,病情越嚴重,夫妻溝通回避程度越高,可能原因是病人產生自我責備感,家屬擔心提供錯誤幫助,因此,雙方不愿意公開討論癌癥話題[13]。Yu 等[14]研究對乳腺癌病人疾病溝通回避、應對方式和心理痛苦進行了調查,結果表明,病人疾病應對在溝通回避和心理困擾之間起到了中介作用,夫妻主要回避關于情感表達、疾病進展和死亡恐懼感等話題的討論,這也減少了病人獲得心理支持的機會,因此,病人通常采取自責和否認等逃離應對方式,進一步加重了病人的心理困擾。Manne 等[15]對147 例乳腺癌病人及配偶的溝通模式、心理壓力和婚姻滿意度進行縱向調查,結果顯示,相互建設型的溝通與更低的焦慮、抑郁水平和更好的夫妻關系滿意度有關,相互回避與更高的焦慮、抑郁水平有關,但與夫妻關系滿意度相關性不顯著,9 個月的隨訪中溝通模式沒有改變,且病人的溝通水平對配偶的心理痛苦和婚姻滿意度有負面影響,而配偶的溝通水平不會對病人產生影響。Kershaw 等[16]研究表明,病人與配偶溝通癌癥發展、癥狀變化和治療效果,有利于減輕配偶的疾病不確定感。但也有研究表明,夫妻間過多的溝通癌癥話題會增加病人的絕望感[17]。可見并不是溝通所有疾病話題對雙方都是有益的,可能原因是過度談論癌癥會減少對生活其他方面的關注,特別是當配偶與病人溝通性功能等話題時,會導致病人的身心狀況較差。未來可以將量性研究和質性研究相結合,探討哪種情況下開放和回避溝通癌癥話題對于病人和配偶都是有益的。
3 夫妻疾病溝通的影響因素
3.1 配偶因素
3.1.1 社會人口學因素 影響夫妻疾病溝通水平的因素主要包括性別、年齡、文化、經濟收入、照顧時長等。Bachner 等[18]對77 例晚期癌癥病人及其配偶溝通水平進行調查,結果表明,開放型溝通與配偶的宗教信仰、教育、經濟狀況或情緒狀況沒有顯著關聯,與配偶的年齡、抑郁情緒、照顧時長呈負相關,女性配偶比男性配偶開放性溝通水平高。可能原因是女性比男性容易情緒化且對人際關系較為敏感,更加善于溝通,而男性配偶通常照顧負擔較重,因此會避免與病人討論死亡相關的敏感話題。照護時間越長,配偶與病人對于疾病和死亡話題的溝通就越多,可能原因是配偶已經接受疾病惡化的事實,這種適應使夫妻雙方坦誠交流。 Saimaldaher 等[19]研究顯示,年長者、女性、文化水平低、低收入、照顧時長、健康狀態等是造成照顧負擔的壓力源,較為嚴重的照顧壓力會對配偶的角色轉變和溝通模式產生不良影響。
3.1.2 心理因素 影響配偶疾病溝通的心理因素主要為自我效能感和情緒狀態。自我效能感是一種重要的人格特質,指個體在某種情景下實現目標所需能力的信念[20]。Bachner 等[18]研究表明,配偶的自我效能越高,與病人的溝通水平越高,可能原因是自我效能感高的配偶把照顧病人視為一項富有挑戰性的工作并積極去應對,他們較少感覺到負擔和情緒疲憊,因此愿意與病人進行更多的疾病溝通。Magsamen 等[21]研究表明,病人和伴侶談論癌癥能力的信心即溝通效能,是癌癥管理的預測因子,癌癥管理涉及治療策略、情感、疾病治療進展等方面信息,配偶本身的負性情緒會降低夫妻疾病溝通水平。Bachner 等[22]研究表明,配偶的情緒越疲憊、越抑郁,其與病人關于疾病和死亡的溝通就越少,高強度的照顧需求會引起配偶的消極情緒反應,因而降低照護效率。未來可以對不同疾病病人的配偶心理壓力與溝通水平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
3.2 病人因素
3.2.1 社會人口學特征 Munro 等[23]研究顯示,病人的種族、年齡、性別、學歷、居住、就業狀況、自診斷以來的時間以及病人在接受診斷時是否有伴等與疾病信息表露水平沒有顯著關系,男性對親人、朋友和醫護的疾病信息表露程度更高,因此,應該避免女性更加健談的刻板印象[24]。治療類型和外向性格是病人表露的預測因素,手術病人較放化療病人的信息表露較少,原因可能與化療和放療方式治療周期長、副作用嚴重和需要更多疾病信息溝通等有關。
3.2.2 疾病因素 晚期癌癥病人癥狀嚴重和身體狀況較差會削弱病人正常溝通的能力[25]。Song 等[26]對病人及配偶疾病評價、疾病溝通和生活質量的關系進行縱向調查,結果表明,較高的疾病負面評價與較低的溝通水平和生活質量有關,且溝通水平越低,生活質量越差。Xu 等[27]研究表明,乳腺癌病人和配偶的疾病感知水平越高,夫妻間積極溝通的可能性更高,病情越嚴重的個體在日常生活中表達的負面信息可能越多,溝通在疾病表現與疾病復發恐懼中起著中介作用。因此,改善癥狀嚴重程度可以促進夫妻疾病溝通水平進而緩解壓力。
3.2.3 心理因素 影響病人與配偶進行疾病溝通的心理因素主要包括疾病復發恐懼和病恥感。癌癥復發恐懼指病人對癌癥在原發部位的復發、進展或發生轉移的恐懼,且癌癥復發恐懼在已經歷復發或是未經歷復發的病人中廣泛存在[28]。Soriano 等[29]研究表明,感知到伴侶不感興趣或回避行為會抑制雙方癌癥話題、想法和情感的表達,癌癥復發恐懼高的夫妻多采用相互隱瞞、溝通回避等消極應對策略。Warmoth 等[30]對華裔乳腺癌女性的一項質性研究表明,病人存在自我污名感,擔心脫發和乳房切除遭到家人和朋友的嫌棄,認為配偶沒有給予足夠關心與支持,因此拒絕與配偶溝通內心感受。造口病人因害怕造口滲漏、造口袋有異味和響聲等問題盡量避開人群,這嚴重影響了病人正常的溝通交往行為[31]。可見身體形象紊亂的病人更可能存在溝通問題。
3.2.4 社會支持 Munro 等[23]研究表明,病人的溝通水平與社會支持相關,但該研究為橫斷面研究,不能明確得出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Figueiredo 等[32]研究表明,愿意與親人溝通疾病情況的病人獲得社會支持較多,相反則會感到更加抑郁或悲傷,病人缺乏社會支持會導致其不愿意袒露情緒。Wertheim 等[33]使用主客體互倚模型研究感知伴侶支持對夫妻溝通隱瞞的影響,結果表明,感知伴侶支持與夫妻自身溝通隱瞞行為呈負相關,女性病人的配偶溝通隱瞞與感知伴侶支持呈負相關,可能的原因是女性病人獲得配偶支持意味著夫妻有較好的親密關系,因此夫妻間隱瞞行為減少。這也提示應提高男性對配偶支持重要性的認識,鼓勵其肯定配偶的付出并給予感激互動。
3.3 其他 隨著手機等電子通信工具普及,溝通的方式更加多樣化,病人可以利用網絡平臺進行交流、尋求支持。Darabos 等[34]調查61 例癌癥病人溝通方式與心理健康的關系,結果顯示,36.1%的病人通過社交媒體方式進行癌癥相關信息交流,使用移動技術交流的病人疾病溝通水平高、功能狀態好、抑郁水平更低。可能的原因是在線技術溝通主要依靠文字信息傳遞,添加了如表情包和圖形交換格式(GIF)等元素,這類工具更加人性化,從而有利于情感的自然表達,文本信息交流減少了非語言暗示的推斷過程,因此,對雙方的心理健康更加有益。利用移動技術進行交流主要集中在年輕癌癥病人中,但在老年病人中推廣仍然存在難度。
4 國內外促進夫妻疾病溝通的干預現狀
4.1 夫妻表露干預 夫妻表露干預是指將夫妻作為干預整體,鼓勵夫妻雙方表達各自的感受。目前運用于癌癥病人主要的為書寫和語言交流兩種表露類型[35]。Barsky 等[36]對結直腸癌病人夫妻使用基于電話的親密關系增強方案,實驗組共經過4 次50 min 的電話干預,分別對性相關溝通技能和行為練習進行指導,幫助夫妻做出認知和行為上的轉變,結果顯示,夫妻性功能、親密關系和自我效能感有顯著改善。這也提示對敏感性話題采取電話溝通比面對面交談更加可取。Porter 等[37]對晚期胃腸道癌癥病人及配偶使用夫妻溝通技能培訓的視頻會議干預來改善雙方的溝通,鼓勵夫妻雙方彼此分享想法、感受和討論癌癥有關的問題,如安排醫療預約、癥狀管理、家務安排、情緒困擾和臨終關懷,結果顯示,夫妻關系滿意度和溝通水平提高。但是該研究僅僅是鼓勵夫妻溝通這些話題,沒有指導如何去處理這些敏感話題[38]。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探索促進夫妻溝通復雜、敏感話題的溝通培訓指導措施。
4.2 基于成熟的培訓課程 Wittenberg 等[39]進行了一項肺癌病人的個案研究,給予照顧者書面溝通指南及電話指導,書面溝通指南來自COMFORT 課程,該課程提供全國性的溝通培訓,以提高癌癥護理中以病人為中心的溝通技能,被廣泛用于病人、照顧者和醫務者的溝通培訓中[40],電話指導內容包括如何共享信息、選擇溝通時機和開始對話等內容,結果顯示,有效降低了照顧者的心理困擾水平,提高了照顧者與醫護人員、家人和病人的溝通信心。護士是照顧者分享經濟負擔、身體狀態和情緒反應的主要傾聽者,因此,可以將護士作為主要指導者,制定符合我國文化特征的溝通培訓方案,其中照顧者可以具體分為子女、配偶和朋友等不同角色,并將溝通負擔作為心理護理的重要內容。
4.3 基于溝通工具 目前,有研究者使用家庭照顧者溝通工具——The Family Caregiver Communication Tool(FCCT)[41]衡量病人照顧者二元溝通類型,包括管理者、承辦者、合作伙伴和孤獨者4 種類型,管理者通過利用醫學知識主導與病人溝通,承辦者則由病人主導,伴侶型雙方促進各種話題的開放式交流,孤獨型僅專注于生物醫學問題。這有利于護士調整溝通方式,針對溝通類型的需求和偏好處理照顧者的負擔和溝通沖突。Wittenberg 等[42]研究將FCCT 應用于APP 的開發,以期減少配偶的溝通負擔,這是目前唯一關注照顧者溝通需求與支持的應用程序,但是本研究應用效果沒有經過大樣本驗證,未來研究可以探究癌癥的類型、治療階段和生存率對溝通類型的影響,以及不同溝通類型在應對方式、健康素養和溝通偏好方面的差異。
4.4 基于娛樂視頻工具 Beach 等[43]為實驗組制作以病人和家屬通過電話進行實際對話為基礎的80 min娛樂視頻,該視頻該主要講解真實故事和一系列活動(如傳遞和接收好消息和壞消息、同情和開玩笑等),揭露對常見避免談及話題的不同見解,引起思考,并設計可行的方法來改善癌癥中的社會關系,對照組給予癌癥營養和飲食視頻,結果顯示,實驗組病人自我效能感、外部支持和癌癥溝通水平都有顯著提高,視頻中真實的社會環境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場景,引導人們思考并認同角色,這也提示可以從夫妻角度將健康觀念融合到量身定制的微視頻中。
4.5 家庭支持性談話 支持性談話是指以增進雙方相互理解,提高生活質量,促進共同參與,包括家庭功能、生活管理和夫妻親密問題的心理社會干預方式。Ledderer 等[44]對原發性肺癌或者婦科癌癥病人和家屬之間進行支持性談話干預,并給予談話指南,包括介紹疾病、對醫務人員的期望、家人彼此期望、情緒表達和日常生活5 個部分,結果顯示,病人和配偶在護士的參與下進行支持性談話時感到放松,認為支持性談話是一種促進開放交流和加強親密關系的方式。但本研究由于樣本量較小,沒有進一步區分家屬中配偶和子女之間的差異。聶志紅等[45]對配偶實施“助她治愈”的夫妻溝通干預措施,主要包括自我放松、傾聽、開放式提問和共享休閑時光4 個主題,結果顯示,配偶溝通水平提高,夫妻焦慮、抑郁水平降低。有護士在場指導的支持性談話是病人愿意接受的方式,但目前缺乏接受過專業溝通培訓的護士,因此,限制了該干預類型的推廣。
國外干預措施較多,而國內缺乏相關研究。多數干預研究將疾病護理、心理教育和溝通技能培訓相結合,在提升配偶護理能力的同時,也緩解了心理負擔。這些溝通方案有效促進了夫妻關于癌癥話題的溝通和負性情緒表達,從生理角度改善了由于性生活引起的溝通障礙及心理痛苦水平,從社會關系角度改善了夫妻雙方的親密度、關系質量和滿意度,提高了配偶的自我效能感。這些干預研究效果明顯,但研究對象多數為病人與照顧者,考慮到配偶與子女的差異較大,僅針對病人與配偶的干預措施仍然有待研究,且缺乏足夠的夫妻疾病溝通相關理論支撐。
5 小結
夫妻間開放性疾病溝通有利于雙方疾病心理適應,但其受病人和配偶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我國目前相關研究較少,缺乏疾病溝通需求評估的研究工具,未來需要更多橫斷面研究探討其影響因素,對于疾病不同階段也可以采取縱向研究調查夫妻溝通水平的變化趨勢。我國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具體實施促進夫妻疾病溝通干預措施仍然存在困難,因此,可以從提升夫妻溝通意識、給予溝通策略和網絡資源等角度入手,降低溝通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