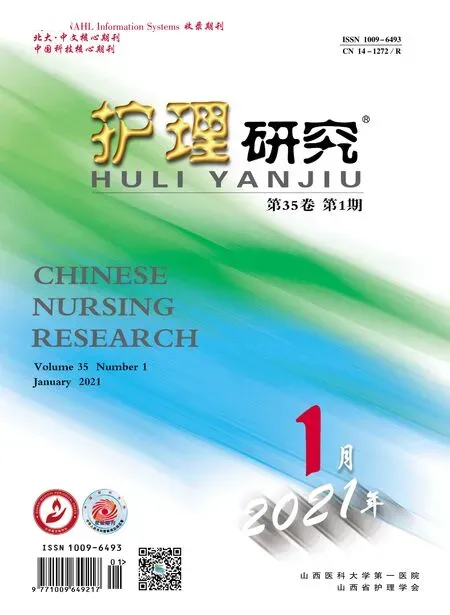老年慢性病病人久坐行為的研究進展
王慧敏,孫建萍*,吳紅霞
1.山西中醫藥大學,山西030619;2.山西省人民醫院
隨著全球老年人口的增加,預計到2050 年,全球老年人口比重占世界總人口的22%,我國老年人口總數也將超過4 億人。伴隨人口老齡化的同時,慢性病發病率快速增長。我國慢性病研究調查結果顯示,我國老年人群慢性病患病率高,75.8%的老年人患有至少1 種慢性病[1]。《中國防治慢性病中長期規劃(2017—2025 年)》中提到,慢性病是嚴重威脅我國居民健康的一類疾病,是影響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久坐行為在老年人群中很常見,被認為是慢性病的一個獨立危險因素,已成為世界范圍內的公共衛生問題,是臨床、研究和政策關注的焦點[2]。已有大量研究證實,久坐行為與老年人2 型糖尿病、肥胖、高血壓、癌癥、慢性炎癥、心血管疾病、衰老等不良健康結局有關,長時間久坐可導致老年人身體功能下降,抑郁、焦慮情緒增加,慢性病發病風險和死亡風險增加,嚴重影響老年人的生活質量[3‐4]。一項涉及全球多個國家50余萬人調查統計顯示,60%的老年人報告久坐時間>4 h/d[5]。客觀測量老年人平均每天坐著的時間為9.4 h,占清醒時間的65%~80%,并且久坐時間隨年齡增長而增多[6]。目前,國外對久坐行為的研究多集中在骨關節病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糖尿病、心臟病、腦卒中等慢性病,而國內對久坐行為相關研究較少,且多圍繞青少年和特定工作場所的久坐行為,針對老年慢性病人群久坐行為的研究不足。本研究從久坐行為的定義、危害、測量工具以及老年慢性病病人久坐行為的現狀、影響因素及干預方法進行綜述,以期為我國老年慢性病病人久坐行為的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1 久坐行為的概述
1.1 久坐行為的定義和分類 “Sedentary behavior”一詞來源于拉丁語“sedere”,意為“坐”,在文獻中可見其他表達“static behavior”“sitting”,國內翻譯主要有“久坐行為”和“靜態行為”2 種,相關研究多見于體育運動領域和健康衛生領域。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久坐行為與靜態行為二者含義相同,故本研究采用“久坐行為”這一表達方式。過去人們對久坐行為的理解是經常久坐和缺少鍛煉,久坐行為的定義在文獻中也不一致。2012 年,由來自世界各地的久坐行為研究者和對久坐行為研究感興趣的衛生專業人員組成的久坐行為研究網絡(SBRN)對久坐行為進行定義,后被頻繁引用[7]。2017 年,SBRN 進一步針對久坐行為制定了適用于所有年齡段和所有身體能力人群的久坐行為的共識定義[8],并將其與缺乏體力活動(physical inactivity)等概念區分出來,其定義指任何坐著、斜臥或躺臥姿勢時,能量消耗≤1.5 代謝當量(METs)[1 MET=耗氧量3.5 mL/(kg·min)]的清醒行為。久坐行為按照其表現形式大致可分為4 類:屏前久坐行為(玩手機、看電視、上網)、社交性久坐行為(聊天、打電話)、交通性久坐行為(乘坐交通工具)、其他類型的久坐行為(閱讀、寫作、下棋)。目前,久坐行為暫無明確分級,現有文獻中,王婭等[9]、胡樹菁等[10]、Jelsma 等[11]分別以每日久坐時間≥5 h、≥6 h、>7.5 h 為界劃分久坐行為。Vancampfort 等[12‐14]將 久 坐 時 間≥8 h/d 的 人 群 確 定 為高久坐行為人群。
1.2 久坐行為的危害 有證據表明,久坐行為對新陳代謝、骨骼礦物質含量和血管健康有直接影響[15],過多的久坐行為會加重慢性疾病的病情。久坐行為的影響之一是代謝功能紊亂,其特征表現為血漿三酰甘油水平增加,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水平降低,多器官胰島素敏感性和心肺適應性的可逆降低,同時,肝臟脂肪以及血脂異常增加,最終導致代謝紊亂和身體成分改變[16]。彭莉等[17]通過調查469 例2 型糖尿病病人的體力活動、血糖血脂代謝情況,發現2 型糖尿病病人的久坐時間與HDL 水平呈負相關,與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和三酰甘油水平呈正相關,即久坐時間明顯影響糖脂代謝,久坐時間越長,病人的脂代謝越紊亂。
久坐行為的另一個不良影響是骨密度降低。久坐行為和骨量減少之間的關系是通過骨吸收和沉積之間平衡的變化來調節的。久坐不動的行為會導致骨吸收迅速增加,而不會伴隨骨形成的改變,最終導致骨礦物質含量降低,增加骨質疏松癥的發生風險。此外,久坐不動的時間與身體機能減退、腿部血流有關,這可能會導致個體跌倒、骨質下降發生骨折。LaMonte 等[18]對77 206 名50~79 歲絕經后婦女平均隨訪14 年,發現規律的體育鍛煉(包括較輕的鍛煉)和較少的久坐時間與降低老年婦女骨折的風險有關,即使在控制了骨折危險因素和體力活動后,久坐行為與總體骨折風險之間仍存在正相關。與久坐時間最少的女性相比,每天久坐時間超過9.5 h 的女性患骨折的風險高4%。
除此之外,久坐行為還會對老年病人的心理健康產生不良影響。久坐可導致超重、肥胖、營養失調[19]、睡眠障礙[20],長時間的久坐行為可能會增加老年人的負性情緒[21]和認知障礙風險[22]。研究表明,久坐行為使得老年人的身體活動減少、生活空間縮小、自理能力下降,進而產生衰弱、跌倒等問題[23]。
1.3 久坐行為的測量 久坐行為的測量主要包括主觀測量和客觀測量2 種。客觀測量主要是借助加速度計之類的設備進行的測量,準確度相對較高,但存在研究經費大、研究對象依從性低及后期數據分析復雜等問題。主觀測量是通過面對面或電話詢問研究對象近來的久坐行為狀況完成調查問卷,以此評估其久坐水平,因其操作簡單、成本低和相對容易收集數據,已經被廣泛用作現階段久坐老年人常用的評價工具[23],但因其依賴于被研究者的認知功能和記憶能力,存在回憶偏倚和期望偏倚。久坐行為的測量問卷部分是在體力活動(PA)的評估問卷中加入久坐行為(SB),部分是專門針對久坐行為測量的問卷。
1.3.1 國際體力活動問卷(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IPAQ) IPAQ 是一種標準化的自我報告問卷,由國際體力活動測量小組編制,旨在為研究人員提供一種評估成年人體力活動和久坐行為的調查問卷,其有效性和可靠性已經在多個國家中進行 了 測 試[24]。IPAQ 有2 個 版 本,長 問 卷(31 個 項 目)和短問卷(9 個項目),短問卷版本是為人口監測和大規模體育活動研究而設計的,而長問卷版本側重于提供更詳細的信息,被推薦用于老年人的評估,便于更進一步闡明每個問題的含義[25]。2008 年我國香港學者將其漢化為中文版(IPAQ‐C),并在我國老年人中驗證其信效度良好[26]。王美鳳等[27]驗證該量表在2 型糖尿病病人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IPAQ 是較早將久坐行為納入測量內容的體力活動測量問卷,目前在體力活動和久坐時間的測量中應用較多。
1.3.2 久坐行為問卷(Sedentary Behavior Questionnaire,SBQ)[28]該問卷是一個簡短而全面的久坐行為測量問卷,適用于超重成年人久坐行為的測量。測量1 周日常生活中的9 種久坐行為類型,包括看電視、玩電腦、聽音樂、打電話、做作業、閱讀、玩樂器、做工藝品、乘坐交通工具。工作日和周末分別計算(總時長=工作日久坐×5+周末久坐×2),該問卷每個條目及整個問卷的類內相關系數為0.51~0.93,與IPAQ 和體質指數(BMI)有較強的相關性,信效度良好,目前在久坐行為研究中應用較多,已被翻譯成多國版本。在國內的研究中,多根據測量人群的實際情況,對該問卷進行適當刪減或增加后使用。
1.3.3 老年人久坐行為測量問卷(Measure of Older Adults' Sedentary Time,MOST)[29]該問卷是專門為老年人設計的久坐行為自我報告工具,測量的是老年人常見領域的久坐行為,包括看電視、用電腦、閱讀、社交、交通、愛好和其他方面,該問卷和加速度計得出的久坐時間量度均適用于對老年人的干預。該問卷專門用于非工作老年人的流行病學和健康行為干預測量,是老年人中第一個自我報告久坐時間與加速度計得出的久坐時間相比有效的研究工具,適合用于老年人久坐行為的測量。
1.3.4 加速度計 加速度計是測量久坐行為的一個重要的研究工具,是評估久坐行為最有效和最可靠的方法。加速度計是一種小型電子設備,通常佩戴在臀部,它可以將大多數運動的詳細數據下載到計算機中,供以后分析使用。加速度計不僅可以用來描述一個人的運動量,還可以用來描述運動的強度、持續時間、頻率和模式。客觀測量方法雖然較為準確,但其所需研究成本過于昂貴,不適用于大樣本研究。且該測量方式無法區分坐、躺或站著的狀態,對于久坐行為發生的環境無從得知,無法獲得特定領域的久坐時間估算。
2 老年慢性病病人久坐行為的現狀
久坐行為在老年慢性病病人中普遍存在。一項全球老齡化和成人健康研究(SAGE)調查了包括中國在內的6 個中低收入國家共34 129 例50 歲及以上的11 種慢性病(心絞痛、關節炎、哮喘、慢性背痛、慢性肺部疾病、糖尿病、聽力障礙、高血壓、腦卒中、視力障礙等)病人與久坐行為的相關性,結果發現,10.8%的慢性病病人存在高久坐行為(即≥8 h/d),在65 歲以上的人群中最為明顯[12]。一項包含精神分裂癥和雙相情感障礙在內的2 033 例精神病病人的研究發現,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每天久坐的時間為660.8 min(約11 h/d)[30]。從門診和透析部門招募的160 例糖尿病、慢性腎病(CKD)和血液透析(MHD)病人的研究發現,19%的CKD 病人和50%的MHD 病人存在久坐,久坐行為在糖尿病、CKD 和MHD 病人中非常普遍[31]。國內糖尿病病人每天久坐的平均時間多達6.1 h,2 型糖尿病病人久坐時間可占每日清醒狀態時間的70%[32]。Lee 等[33]客觀測量1 168 例49~83 歲的膝關節骨性關節炎(KOA)病人的久坐行為,研究結果顯示,KOA 病人白天2/3 的時間都處于久坐狀態。系統綜述發現,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的病人每天久坐時間為447 min(約7.5 h/d)[34]。
3 老年慢性病病人久坐行為的影響因素
3.1 個人因素 研究顯示,年齡、性別、婚姻、職業、在職狀態、收入、居住情況、體重狀況、有無子女及受教育程度與老年人久坐行為有關[35‐36]。余珍[23]的質性研究結果表明,老年人的靜態愛好、固有的習慣、對久坐行為認識和中斷久坐行為的靈感不足也會影響其久坐行為。
3.2 疾病因素 一項涉及中國、加納、印度、墨西哥、俄羅斯和南非6 個國家的研究發現,關節炎和慢性背痛的老年人,其久坐行為主要由殘疾、行動不便和疼痛引起,而認知問題、抑郁感和睡眠問題也可能起作用[12]。已有研究表明,疾病引起的疼痛會導致病人活動受限、行動不便、抑郁、睡眠障礙,最終導致沮喪感,進而導致其久坐不動。張琪[37]在心力衰竭病人久坐行為的研究中發現,心力衰竭病人的久坐時間與關節退行性病變有關,存在退行性關節疾病的病人平均每天體力活動時間更少,更容易出現久坐行為。一項癌癥病人久坐行為研究中,41%的癌癥幸存者表示身體不適(如疼痛和疲勞)是減少久坐時間的最大挑戰[38]。Compernolle 等[39]研究也強調了疲勞對老年慢性病病人站立或從事其他身體活動的重要性。除了生理上的限制,老年人還有因疾病帶來的心理上的限制,如抑郁、焦慮、缺乏自信、害怕摔倒等,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老年人的久坐行為。除此之外,重要的生活事件,如失去配偶或其他親密的朋友、離婚或跌倒事件,被認為也會影響慢性病病人的精神健康,進而導致他們久坐不動[39]。可見慢性病病人的軀體狀況以及心理情況等都是老年慢性病病人久坐行為的影響因素。
3.3 社會文化因素 社會支持嚴重影響行為變化的啟動和維持,一項研究指出如果有家人和朋友的支持,老年人會更有動力減少久坐時間[39]。另外,老年人表示,現有的社會和文化期望是減少久坐行為的重要障礙,社會普遍認為“坐”是老年人(尤其是患病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方式,因此,他們經常在某些情況下(如在公交車上)被要求“坐著”。同時,社會對衰老的態度也會導致老年人感受到坐著的壓力,例如,由于缺乏關于減少久坐行為益處的認知,家人、朋友和照顧者經常鼓勵老年人多坐,并且在許多針對老年人開展的活動中多需要坐著完成(如下棋、打牌、填字游戲)[40]。
3.4 其他因素 室內環境和社區環境是影響久坐行為的一個重要因素。一般來說,老年人大部分的久坐時間是在家里度過的,這大多是由于社區中缺乏休息的地方以及缺乏可用的設施(如商店、娛樂設施等)和社區活動,從而使以家庭為基礎的久坐活動成為可能。除此之外,交通可達性也是影響老年慢性病病人外出活動的首要因素,因為身體和疾病的緣故,他們往往難以到達較遠的目的地,公共交通不暢會導致他們坐得更多。安全、天氣和經濟約束也被認為是減少久坐行為的潛在原因,惡劣的天氣在一定程度上會限制老年人的散步能力[40]。
4 老年慢性病病人久坐行為的干預研究
目前,針對久坐行為的干預研究主要集中在青少年兒童和特定工作場所的人群,對老年人久坐行為的干預研究多圍繞健康老年人群和社區老年人群。在已有的減少久坐行為的研究中,多從增加輕度體力活動來替代久坐行為和減少久坐行為2 個角度進行干預。通過研究發現,基于減少久坐行為的干預措施比基于運動行為的干預措施對減少久坐時間的效果更好[41]。在針對減少久坐行為的干預中,又通過減少總的久坐時間和增加打斷久坐行為的頻率這2 個角度展開。已有文獻中常見的久坐行為具體干預技術有:常規的身體活動干預(如步行訓練)、基于信息網絡技術的身體活動干預、智能手機APP 干預、以家庭為基礎的個性化生活方式干預、便攜式運動設備(計步器監測)、面對面目標設定咨詢[23]、激勵會議和短信干預[42]、政策干預[3]。已有的久坐行為干預方法中常應用的理論有賦能理論、跨理論模型、社會認知理論、計劃行為理論、二元處理理論、健康行為過程理論、自我決定理論(SDT)等[43]。針對老年慢性病人群的特點及久坐行為的特點,建議從以下幾方面進行研究。
4.1 提高醫護人員對老年慢性病病人久坐行為的認知 以往的研究中,多關注于健康老年人的久坐行為,對慢性病老年人的久坐行為研究較少,且老年慢性病病人自身對久坐行為的認知不足,缺乏對減少久坐行為益處的認識。可通過增加醫護人員對久坐行為的相關認識以及對久坐行為相關知識的宣傳,提高老年慢性病病人對久坐行為的認識。
4.2 探索減少老年慢性病病人久坐行為的護理措施 ①鼓勵老年人參與一些不需要坐著即可完成的活動,如做一些整理家務等需要站立的工作。②支持老年人保持社交活動,以減少他們獨自一人坐在家里的時間,同時減少與社會的隔離。③鑒于老年人反映,他們通常下午和晚上比早上坐得更久[39],鼓勵老年人考慮如何通過分散白天不需要坐著完成的家務來打破下午或晚上的長時間久坐狀態,從而減少身體的僵硬和不適。④護理人員使用激勵策略,設定慢性病病人久坐時間的定期打擾,如可設置每久坐30 min 提醒起身步行2 min,提醒病人在電視廣告期間或在使用電話時起身站立或行走。
4.3 積極推動決策部門出臺相關政策 減少老年人久坐行為已被世界衛生組織作為一項公共衛生優先事項加以推動。近年來,美國、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亞、法國、英國等衛生部門出臺一系列政策,旨在減少久坐行為和限制久坐時間[44]。我國在結合國內外久坐行為研究的同時,需要出臺適合我國國情的久坐行為相關政策和相關體力活動指南。
5 展望
久坐行為在老年慢性病病人中普遍存在,影響病人的疾病康復和生活質量。減少久坐行為不僅可以改善病人的活動能力,還可以延緩疾病進程,提高病人的生活質量。目前,以護士為主導的久坐行為相關研究不斷增加,建議下一步的研究重點可從以下4 個方面進行:①加強對慢性病病人的健康教育,提高老年慢性病病人對久坐行為的認識;②借鑒國外久坐行為的研究經驗,完善適合我國患病人群的久坐行為評估工具;③調查老年慢性病病人久坐行為的現狀,結合質性研究分析老年慢性病病人久坐行為的影響因素;④積極探索有效減少久坐行為的干預研究,結合老年人群的特點和相關理論,制訂適合我國老年慢性病人群的久坐行為干預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