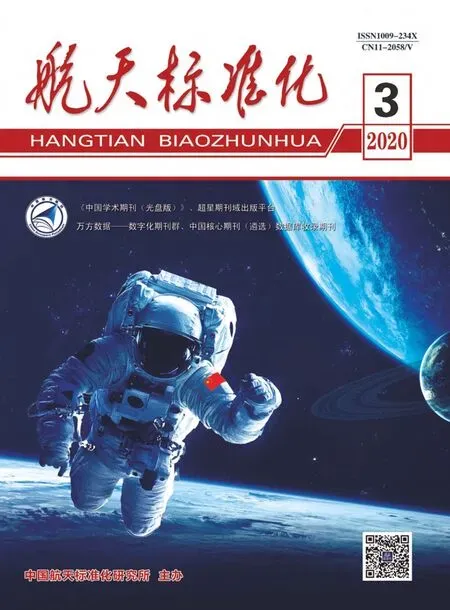航天裝備數字化設計與制造標準化的實踐與思考
黃超 梁爽 周佳臏 郁文 慕曉英
(1 上海航天信息研究所, 上海, 201109;2 上海航天技術研究院, 上海, 201109)
上海航天技術研究院 (又稱上海航天局),是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三大總體院之一,創建于1961 年, 經過50 多年發展, 已成為我國航天事業的中堅力量和重要航天產業基地。 為了貫徹落實 《中國制造2025》, 發展智能制造, 上海航天局依托企業信息化能力建設, 圍繞協同化的設計研發平臺、 面向院/所兩級管理模式的企業核心業務應用系統和高性能計算中心為基礎的仿真計算平臺等, 開展標準化頂層策劃, 不斷在裝備數字化設計和制造過程中開展標準化研究與應用, 取得了較好的成效。
1 航天企業實施數字化的必要性
1.1 國家高端裝備制造業的發展需求
伴隨著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與先進制造技術的深度融合, 全球興起了以智能制造為代表的新一輪產業變革, 數字化、 網絡化、 智能化日益成為未來制造業發展的主要趨勢[1]。 “智能制造、標準先行”, 先進的標準是智能制造實施的重要基礎和前提。 美、 德等工業強國早已認識到標準建設是重塑制造業的關鍵, 通過不同方式加大智能制造標準建設力度[2]。 我國政府也高度重視智能制造領域標準化工作, 李克強總理指出 “要打一場制造業的 ‘攻堅戰’, 實施智能制造, 用先進標準倒逼中國制造升級”。 航天裝備作為國家高端裝備制造業, 已納入 《 中國制造2025》十大重點行業。 工信部和國標委聯合制定、 發布的 《國家智能制造標準體系建設指南》 明確將航天裝備列為 “C 重點行業” 子體系中, 并開展論證規劃。
在國家層面, 由于航天裝備的特殊性, 以及長期以來軍民標準交叉使用、 信息技術快速更新等原因, 航天裝備數字化設計與制造標準的數量、 覆蓋程度均不能滿足當前 “高密度發射、 多型號并舉” 要求。 因此迫切需要開展相關標準化研究和實踐工作, 形成標準化試點示范效應, 強力支撐我國 “制造強國” 的國家戰略。
1.2 航天裝備 “離散式制造” 的轉型要求
上海航天局作為集團型軍工企業, 下轄12家軍工單位, 包含3 個總體單位、 3 個總裝單位、 6 個核心專業研究所。 其裝備研制呈現出“離散式制造” 特點, 主要是: ①集研制和批產于一體的大型軍工集團型企業; ②院/廠所兩級管理, 廠所相對獨立, 又協同設計、 生產; ③以研發為驅動的高度離散定制化生產; ④單件小批量多品種多型號研產混線; ⑤產品構型復雜, 生產周期長, 軍工質量控制嚴格等。
基于“離散式制造” 背景下, 航天裝備制造的信息化、 智能化升級轉型迫切需要實現上下游企業間的互聯、 互通, 消除“信息孤島” “數據壁壘”。同時, 大量航天智能裝備、 數字化設計、 仿真、 制造、 試驗等工業軟件以及工業大數據應用, 急需開展協同設計、 協同制造方面的數字化頂層標準研制。 為統籌利用信息數據, 形成數據共享打下基礎。 標準作為“共同語言”, 將發揮重要作用。
由此可見, 開展航天企業數字化設計與制造標準化, 必須從企業戰略高度出發, 形成標準研制的有效工作機制, 統籌規劃, 集中研制; 構建科學、 完整的標準體系, 加快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為標準, 提高標準 “含金量”; 固化、 積累 “離散式” 軍工集團裝備制造的工程實踐和寶貴經驗,進一步發揮標準牽引技術需求、 保障科研生產的作用, 助力航天裝備制造轉型升級。
2 數字化設計與制造標準化實踐
2.1 建立工作機制, 明確標準轉化提升方向
在上海航天局層面的統一部署下, 從標準化、 信息化兩條線形成了 “雙管齊下” 的工作機制, 共同推動數字化設計與制造標準化建設。 主要包括: 依托企業信息化 “兩總” 系統, 由質量技術部、 規劃計劃部歸口管理, 確保專業規劃、條線計劃、 工作經費等保障條件; 局標準化中心、 局信息化中心實施技術支撐, 各下屬廠所參與; 定期召開研討會、 協調會, 圍繞以下幾方面明確標準轉化提升方向。
a) 基礎共性標準的采標及轉化。對于航天軍工企業而言, 基礎共性的標準包括國家標準和部分軍用標準。 從標準適用性的角度來看, 一部分標準是通用的, 如術語、 參考模型、 元數據等標準; 一部分是存在交叉, 不一致的, 如功能安全、 信息安全、 標識等標準。 因此必須針對這些軍/民標準開展分析研究, 形成民標采用和軍標轉化的項目清單。 促進相關國家標準貫徹實施,服務于企業科研生產。
b) 企業數字化應用創新成果轉化。“十三五” 以來, 大量基于工業機器人、 增材制造以及工業互聯網下協同設計/制造系統互聯互通、 互操作等應用場景要求的信息化平臺、 軟件得以開發和使用。 上海航天局結合 “離散式” 制造、 軍工保密等特點, 進行了一系列數字化應用改造。當前急需將相關技術創新成果和經驗, 通過標準的形式固化下來, 用以規范指導科研生產全過程。
c) 企業數字化管理創新成果轉化。將以“科研生產管理系統” 為代表的航天數字化管理技術轉化為國家/ 行業標準。 該技術已在企業層面廣泛實施, 效果良好; 且作為產業融合技術的典范, 榮獲第十九屆工博會空間信息技術與北斗導航技術應用產品獎, 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和推廣應用價值。
2.2 健全標準體系, 推進關鍵技術標準研制
在跟蹤國內外相關標準體系的基礎上, 結合軍工企業數字化建設的特點, 確立標準體系表的框架, 如圖1 所示。 力求構建結構合理、 內容完善、 協調統一的標準體系, 牽引航天裝備數字化設計與制造標準化建設需求。
在標準體系的牽引下, 圍繞 “大設計、 大仿真、 大制造、 大測試、 大管理”, 推進關鍵技術標準研制。 具體見表1。
2.3 依托試點示范, 深化標準貫徹實施應用
依托 “國家高端裝備制造業 (高端裝備) 標準化試點” “航天器結構件智能制造新模式應用” 等國家級項目在上海航天局試點示范工作,開展了大量的數字化標準的實施應用工作。 取得以下成效。
a) 以數字化協同設計標準的實施, 實現了以數字樣機為核心, 以產品數字化定義 (MBD)為基礎, 以局數據中心為紐帶, 構建跨地域/多單位的統一型號并行協同環境, 開展型號數字化研制與過程管理。
b) 固化機加、 鑄造、 鈑金、 焊接、 裝配、電裝、 復材等專業工藝仿真瓶頸技術經驗, 通過標準在型號研制中推廣應用, 實現工藝布局、 物流仿真的全面應用。

圖1 數字化設計與制造標準體系框架

表1 數字化關鍵技術標準研制重點
c) 結合11 條數字化生產線建設, 建立航天制造單元布局、 生產線標準群。 實現航天產品研制主要環節的自動化和數字化, 達到研制效率提高, 成本降低, 質量提高的目的。
d) 建立科研生產管理系統標準群, 實現局和廠所間上下管控、 橫向協同, 廠所內的生產計劃管理精細化, 過程管理扁平化、 生產現場作業無紙化。
3 數字化設計與制造標準化思考
3.1 數字化標準研制方面
由于航天裝備種類齊全, “彈箭星船器” 各個領域、 各個型號數字化標準帶有明顯的領域/型號特色。 對于同時承擔幾個領域/型號產品的專業所而言, 在使用這些標準時難免會產生交叉重復和矛盾。 針對這一情況, 上海航天局開展了相關探索和嘗試, 后續還需要 “自頂向下” 開展設計和規劃, 通過整合、 優化等手段, 有步驟地開展這類標準的 “去型號化”。
3.2 數字化標準貫徹實施方面
對比 “波音產品標準長期戰略計劃”, 在標準數字化 (結構化)、 標準權威源、 標準應用工具等方面值得探索。 包括: 開展標準的數字化(結構化) 加工, 適應未來多源的標準數據需求;結合知識管理, 包括MBD 建模模板、 材料信息標注、 技術注釋數據庫、 標準件庫、 模型質量檢查工具等方面考慮標準嵌入, 作為數據與PDM(產品數據管理)、 PLM (產品生命周期管理)、CAPP (計算機輔助工藝過程設計) 等自動化系統實現互操作。 在互操作過程中, 還要重視標準規則的應用。 根據相應的流程, 在PDM 中定義工作流進行實施, 比如在系統中對技術文件管理規則的定義。
3.3 數字化標準實施的監督檢查
更好地發揮上海航天局 “標準化工作網絡平臺” 的 “工具” 作用, 打通與設計制造協同系統的接口, 開展結構化標準數據的使用跟蹤。 同時, 基于平臺內該標準的其他使用數據, 促進標準實施情況的監督檢查。
結合國標委、 工信部試點示范項目, 聚焦航天關鍵結構件制造工業物聯應用標準化與試驗驗證, 加快建立科技成果轉化機制, 探索以綜合標準化為核心的標準驗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