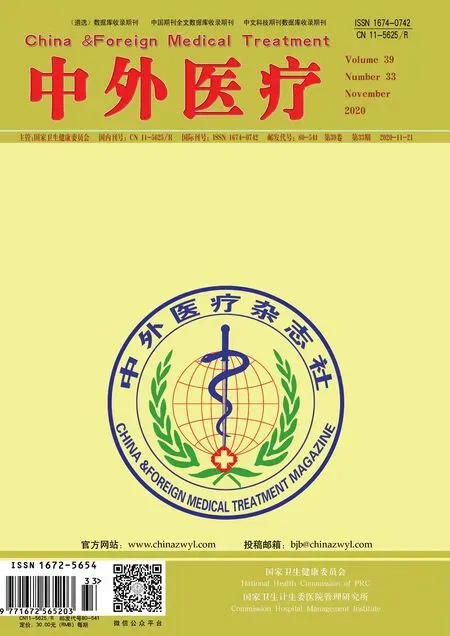經腹膜后入路腹腔鏡手術治療大體積腎癌的臨床效果評價
鄭懷穎,盧慶,林益山,周凱,陳劍暉,謝若云,江瑋
福建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泌尿外科,福建福州 350001
腎癌為臨床常見的泌尿系統惡性腫瘤, 近年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劇以及臨床診斷技術的不斷進步,腎癌患病率呈逐年升高的趨勢, 嚴重威脅患者身心健康。 在治療方面,手術是該病治療的主要手段,以往采取開放性手術,而隨著微創手術的發展與推廣,腹腔鏡手術成為腎癌治療的主流,具有創傷少、術后恢復快等優點[1]。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證實[2],腹腔鏡下手術治療腫瘤直徑>7 cm 的大體積腎癌的療效與開放性手術相當。然而,由于大體積腎癌的瘤體體積較大,血供豐富,其手術風險顯著增加,故在腹腔鏡下采用何種入路(經腹腔入路、經腹膜后入路)仍有爭議。該研究方便選擇2013年1 月—2018 年12 月該院收治的158 例大體積腎癌手術患者進行對照試驗, 以探究經腹膜后入路腹腔鏡手術治療大體積腎癌的臨床效果。 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方便選擇該院收治的158 例大體積腎癌患者進行研究,根據手術入路不同分為兩組,對照組(n=81):46例男,35 例女;年齡52~77 歲,平均年齡(63.59±6.75)歲;腫瘤直徑7.3~9.1 cm,平均(8.17±0.52)cm;病灶位置:40 例右腎,41 例左腎。 觀察組(n=77):46 例男,31例女;年齡50~79 歲,平均年齡(63.75±7.53)歲;腫瘤直徑7.1~8.8 cm,平均(8.16±0.45)cm;病灶位置:35 例右腎,42 例左腎, 兩組基線資料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該研究獲得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同意。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經影像學檢查、病理活檢確診患有腎癌,TNM 分期屬于T2a 期,腫瘤病灶直徑在7~10 cm 之間;②符合腹腔鏡腎癌根治性手術治療的指征;③患者對該研究內容知情,簽署同意書。 排除標準:①既往有腹部手術病史;②伴有嚴重新肝功能障礙,營養不良等不能耐受手術;③伴其他惡性腫瘤。
1.3 方法
兩組均接受腹腔鏡根治術治療,其中,對照組經腹腔入路,氣管插管全麻后,患者取健側斜臥位(70~80°),在臍水平腹直肌旁2 cm 做一個小切口, 建立氣腹,隨后經此孔置入10 mm Trocar 套管作為觀察孔, 并選擇患側鎖骨中線肋緣下兩橫指5 mm、髂前上棘內上2 cm處10 mm、臍水平腋前線處5 mm 切口作為操作孔。 此外,對于右側腎癌患者,還需在劍突下做5 mm 切口作為副操作孔以挑開肝臟便于手術操作。 在腹腔鏡引導下游離升(降)結腸和肝臟(脾臟),適當切開結腸外側腹膜上至結腸肝曲,離斷肝結腸韌帶(左側上至脾臟外上緣,并離斷脾腎韌帶,脾結腸韌帶),下至髂窩;將結腸(右側連同十二指腸)推到腹腔內側,顯露腎臟及腫瘤位置、形態大小;游離生殖靜脈,暴露腰大肌平面,游離并處理腎蒂血管(Hem-o-lok 結扎離斷血管),在腎上腺外側緣與腎上極內側之間游離腎臟,保留腎上腺(如果腫瘤位于腎上極, 或術前影像學檢查明確腫瘤已侵犯腎上腺,應同時切除腎上腺)。 離斷輸尿管,將患側腎臟及腫瘤切除并取出。
觀察組經腹膜后入路,氣管插管全麻后,患者取健側臥位(90°),患側十二肋緣下做長約2.0 cm 的切口至腰背筋膜,術者食指分離腹膜后空間,放置自制擴張球囊拓展空間后,在此切口置入10 mm Trocar 套管作為觀察孔,同時選腋中線髂棘上10 mm、腋前線肋下緣5 mm切口(右側10 mm)作為操作孔,在內鏡引導下清理腹膜外脂肪,在腹膜反折背側切開側錐筋膜,在腎后筋膜與腰大肌筋膜之間沿腰大肌向深面分離, 充分游離腎臟背側(上至膈下,下至髂窩),暴露腎動靜脈,Hem-olok 結扎離斷;在腎前筋膜外與腹膜之間向腹側深面游離并往上極及下極拓展, 上極處在腎上腺外緣與腎上極內側之間切開保留腎上腺(如果腫瘤位于腎上極,或術前影像學檢查明確腫瘤已侵犯腎上腺, 應同時切除腎上腺);下極在髂血管水平切除輸尿管;最終腹背側會合完整切除患側腎臟及腫瘤并取出。
1.4 觀察指標
①對比兩組治療總有效率。 療效判斷標準[3]:顯效:手術成功,病灶切除干凈,術后無并發癥發生;有效:手術成功,術后有并發癥發生,但并發癥不嚴重,未危害生命安全;無效:手術失敗,或術后有嚴重并發癥發生。②對比兩組手術時間、術后首次肛門排氣時間、下床活動時間、術后引流管留置時間、住院時間、術中出血量、術后總引流量及術后并發癥發生情況的差異。 ③對比兩組患者術前、術后1 d 炎癥指標(WBC 計數、CRP、IL-6)變化情況。 ④術后對兩組患者進行隨訪,追蹤分析患者病灶有無復發或遠處轉移。
1.5 統計方法
選用SPSS 23.0 統計學軟件分析數據,計量資料以()表示,行t 檢驗;計數資料以頻數和百分比(%)表示,行χ2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治療總有效率
觀察組治療總有效率93.51%,與對照組的93.83%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00,P=1.000),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治療總有效率對比
2.2 手術情況及術后恢復情況
觀察組患者手術時間、術后首次肛門排氣時間、下床活動時間、 術后引流管留置時間和住院時間均顯著短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觀察組患者術中出血量、術后總引流量均較對照組明顯減少,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2.3 術后并發癥發生率
觀察組術后并發癥發生率5.19%, 對照組為8.64%,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724,P=0.395),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術后并發癥發生率對比
2.4 手術前后炎癥指標變化
術前, 兩組WBC 計數、CRP、IL-6 檢測值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1 d,兩組上述3 項炎癥指標均較術前明顯升高,但觀察組較對照組明顯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2.5 隨訪結果
隨訪18~56 個月,平均(43.25±8.61)個月,兩組患者術后均每隔3~6 個月復查血生化, 胸部正側位片或胸部CT,至今無一例局部復發和遠處轉移。
3 討論
在臨床上, 腎癌治療的常見手段有手術切除、放療、化療、免疫療法等,其中,根治性腎癌切除術治療效果確切,以證實能夠有效提高患者生存率,改善生存質量。 腹腔鏡下腎癌根治術治療普通腎癌 (腫瘤直徑≤7.0 cm)的效果以獲得臨床認可[4]。 然而,對于大體積腎癌,因其病灶體積較大,與周圍組織緊密接近,若在腹腔鏡下進行手術,操作空間有限,故既往臨床通常應用開放性手術治療。 近年,隨著微創技術的不斷發展,有研究發現[5],應用開放性手術與腹腔鏡手術治療大體積腎癌均可獲得較好的效果, 而且腹腔鏡手術對機體創傷更少,術后恢復較快,其治療優勢更為突出。 腹腔鏡下腎癌根治術的入路方式有腹腔入路、 腹膜后入路2種,而對于何種入路方式手術效果更好尚有爭議。 該研究結果顯示,兩組治療總有效率、術后并發癥率對比無明顯的差異(P>0.05),但觀察組患者手術時間(113.17±6.89)min、術后首次肛門排氣時間(22.87±2.60)h、下床活動時間(26.51±2.88)h、術后引流管留置時間(3.99±0.68)d、住院時間(5.69±0.71)d、術中出血量(143.48±10.37)mL 及術后總引流量(122.03±26.54)mL 均較對照組明顯減少,與張進等[6]研究結果相似,其研究中經腹膜后組的手術時間 (120.71±10.51)min, 術中出血量(291.31±195.67)mL、 術后首次肛門排氣時間 (1.35±0.17)d、住院時間(6.95±0.11)d,與經腹腔組的手術時間(190.56±10.88)min,術中出血量(321.65±182.36)mL、術后首次肛門排氣時間(2.51±0.20)d、住院時間(10.39±0.52)d 相比(P<0.05)。這主要是因為經腹膜后入路術中操作更為簡單, 可有效減少手術操作時間和術中出血量,而且此入路方式對腹腔臟器干擾較少,利于促進術后胃腸功能康復。 而經腹腔入路術中需將十二指腸、結腸等臟器推到腹內側,并需對腹膜、后腹膜分離,故其操作時間較長,且由于術中對腸道牽拉,極易影響術后胃腸功能恢復[7]。
表2 兩組患者手術情況及術后恢復情況對比()

表2 兩組患者手術情況及術后恢復情況對比()
組別觀察組(n=77)對照組(n=81)t 值P 值手術時間(min)113.17±6.89 129.16±10.35 11.370<0.001術中出血量(mL)143.48±10.37 170.73±15.46 12.944<0.001術后首次肛門排氣時間(h)22.87±2.60 29.44±3.46 13.453<0.001下床活動時間(h)26.51±2.88 33.49±4.39 11.761<0.001術后引流管留置時間(d)3.99±0.68 4.85±0.59 8.536<0.001住院時間(d) 術后總引流量(mL)5.69±0.71 6.90±1.03 8.557<0.001 122.03±26.54 190.28±34.46 13.987<0.001
表4 兩組患者手術前后炎癥指標變化對比()

表4 兩組患者手術前后炎癥指標變化對比()
注:與組內術前對比,*P<0.05
組別WBC 計數(109/L)術前 術后1 d CRP(mg/L)術前 術后1 d觀察組(n=77)對照組(n=81)t 值P 值6.20±1.34 6.10±1.38 0.467 0.641(11.76±2.26)*(14.16±2.03)*7.023<0.001 3.45±0.91 3.66±0.75 1.548 0.124(16.03±3.83)*(23.80±5.67)*10.047<0.001 IL-6(pg/mL)術前 術后1 d 9.85±1.10 9.43±1.57 1.958 0.052(20.06±5.23)*(29.35±8.45)*8.262<0.001
手術創傷可對機體單核巨噬細胞產生一定的影響,促使中性粒細胞、內皮細胞增生,進而導致白細胞計數明顯上升。 與此同時,手術創傷還會誘導體內纖維母細胞、淋巴細胞等分泌大量細胞因子,IL-6 為生理應激反應過程中的釋放的一種細胞因子, 其可參與機體炎癥反應的病理生理過程, 反映機體組織創傷嚴重程度。 此外,CRP 為機體受傷后反映創傷情況的一種敏感的炎癥性指標。 該研究結果還顯示,術后兩組WBC 計數、CRP、IL-6 檢測值均較術前明顯升高, 但觀察組較對照組明顯降低(P<0.05),提示兩種手術入路方式均可引起炎癥反應, 但經腹膜后入路對機體炎癥反應影響較少。 這主要是因為手術為有創性操作,故可引起炎癥反應,但因經腹膜后入路對機體創傷更少,而且其手術路徑相對較淺,炎癥反應較淺[8]。
綜上所述, 經腹膜后入路腹腔鏡手術治療大體積腎癌具有療效好、創傷少、引流量少、術后恢復快等優勢,而且對機體炎癥反應影響較少,故在保證同等療效的情況下, 實施經腹膜后入路腹腔鏡手術更有利于縮短患者康復進程,值得推廣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