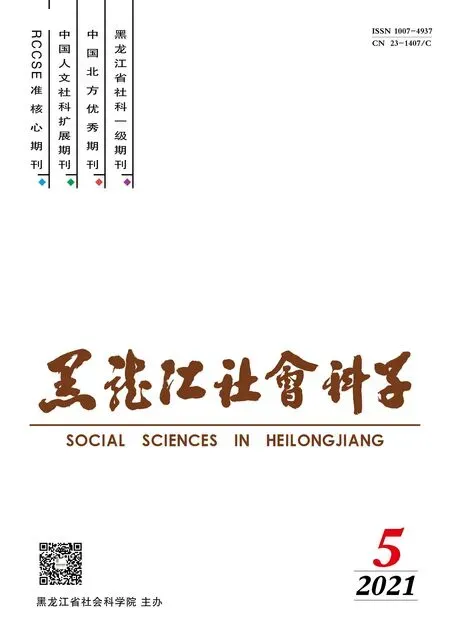儒家人性論三種形態與儒學的當代開展
正統儒家有著強烈的“道德中心主義”特質,其將道德視為人類最基本的行為規范以及人之為人的根本。而正統儒家道德哲學的構建又多以人性論為基礎,形成了關于性之善惡、先天后天、理氣、性情、未發已發等層面的思考和論述。在這種情境下,人們會自然地將人性論同人們的道德行為和道德理論等同起來,完全在道德哲學的視域內去研究儒家的人性論思想。但是,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人性和道德之間看似天然的聯姻是未經反思的,因而也是值得懷疑的。道德是否為人之為人的根本,以及道德實踐在何種程度上造就人自身,這些問題都是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如果超出單純的道德視域,便會發現正統儒家所構造出來的儒家道統其實只不過是儒家思想中的一脈,除此之外,尚有其他幾系,其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堅守和發揚了儒家的基本精神和價值訴求,但又同正統儒家表現出不一樣的思想面貌。
一
同知識相比,道德屬于實踐層面,道德思想、道德哲學以及倫理學因此都屬于實踐哲學的范疇。亞里士多德最早作出了這樣的區分,認為物理學、數學和第一哲學屬于理論知識;倫理學、經濟學(家政學)和政治學屬于實踐知識;修辭學和詩藝則屬于創制知識。后來康德也將認識歸于純粹理性,而將道德歸于實踐理性。人類實踐活動的內容非常豐富、領域非常寬廣,亞里士多德的區分雖然粗疏,但仍可被視為一個合理的區分。類似的區分我們在儒家思想中也可以發現,只是在時間上出現得比較晚。羅念庵從道德實踐的角度批判當時社會時說,今人之所求,無非道德、功名、富貴而已。道德、功名、富貴確實可以涵蓋中國古人所追求的主要目標,也涵蓋了中國人行為的主要內容。在中國傳統官僚體制下,追求功名無非是學而優則仕,以士的身份參與政治統治和管理,因此可以將其統攝于政治實踐之中。對于富貴的尋求主要通過經濟行為來實現,因此應將其歸于經濟實踐之中。這樣,個人追求的道德、功名和富貴恰好對應于道德、政治和經濟三個方面。
二
正統儒家輕視功名和富貴,高揚道德,但是對功名和富貴的自然追求,構成了人們實踐行為的主要內容。而內圣外王并重的儒家,實際上也并沒有將功名和富貴棄之不顧,而是同樣有很多的儒家學者對功名與富貴之道、對政治和經濟之學進行了探討,形成了非常豐富的思想,進而大大拓展了儒學的外延,提升了儒學的包容力和生命力。但在道德中心主義的道統意識下,這些流派的思想相對來說并未得到足夠的關注。在今天實踐哲學的視域下,倫理道德行為的限界開始顯現,道德只有同政治以及經濟聯系起來,才能構成一個較為完整的人類實踐活動。這樣,對儒家人性論的研究也只有跳出傳統的道德領域,才能拓展出人性論的完整版圖。況且,這些“非正統”的人性理論在儒家內部實際上已經有了很充分的表述,只是被主流的思潮遮蔽了而已。
道德人性論認為,道德與人性本質相關,政治和經濟是從道德理想中生發出來的。在實踐哲學視域內,政治、經濟和道德三者總是相互聯系和影響的,舉一必會牽三,需要從政治、經濟和道德三方面考察其思想的全貌,但不同思想家又各有其根本點。在三者當中,孟子、程朱理學、陸王心學等儒學正統派皆以道德為其思想之根本,而政治和經濟是從其道德理想中生發出來的。上述人性論也即道德人性論,其性善論的立場同其道德本位完全一致。道德人性論認為道德、自由和人性三者在本質上是相關的。正是在自覺的道德實踐活動中,人才能擺脫自然的動物性存在,基于自身的道德情感,在自由的道德實踐中成就人自身。若離開自由,人的活動則始終受到自然法則的限制,與動物的活動無異;而對于自由的活動,孟子認為其只能是道德實踐,因為道德情感內在于人,不假外求,在人自身之內通過自身努力即可實現,其他的實踐活動皆受外物的限制,因此無自由可言。
政治人性論不以道德之圣作為終極目標,而是通過人性的理論構建理想的政治藍圖。這里,我們主要分析的荀子、董仲舒和王安石皆有此特征。以荀子為例,荀子提出性惡并非指人本性即惡,而是指人如果任其欲望的滿足,則物質資料無法充分供給,這就勢必出現爭亂。荀子認為,禮首先為了“養人之欲,給人之求”,在欲求得到給養的基礎上,禮方以道別。在人們欲望得到合理滿足的基礎上,因禮以道別,使得尊卑有別,長幼有序,進而構建良好的社會政治秩序。荀子遵循的依然是孔子“既富之,且教之”的原則,但在孔荀時期,人們依然無法認識到物質資料生產實踐的重要性,從而將生產力的發展視為社會發展的根本。或者在荀子看來,無論物質產品如何豐富,如果每個人都追求自己欲望最大化,也必然會出現物屈于欲的狀況,爭斗和紛亂也就必不可免。在荀子的思想中,以物質資料生產為基礎的經濟活動并未受到足夠的重視,通過物質的豐富來解決欲求問題是人和自然之間的問題,在荀子看來,兩者之間的問題并非關鍵。人作為社會性的可以“群”的動物,人的社會—政治關系才是根本。荀子認為,在社會生活中,如果每個人相互平等,沒有貴賤尊卑之分,而人們又具有相同的喜好,這樣就必然會產生紛爭。這就需要“禮”和“政”來解決。以禮節用,以政富民,禮政并用,方為足國之道。需要注意的是,在荀子那里,“禮”并非指向道德的,或者說以道德作為最高之目的的,禮是政的一個重要的形式,禮指向政治而非道德。
經濟人性論的興起源于經濟在現實生活中的影響越來越大,其從儒家正統道德中心主義中走出,承認經濟的重要性,承認利益和欲望的合理性。李覯將人視為具有物質需求的現實之人,認為人們行動的基本原則是“趨利避害”,而非“克己復禮”;人們行動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實現欲求之滿足,而非成就道德之圣境。李覯將思想之重心放到實際生活領域,圍繞著物質資料的生產和交換,思考如何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而形成了與“道德人”不同的“經濟人”的人性理論。在經濟人性論中,“欲—能”成為人性的中心,人具有現實的欲求以及滿足欲求的能力,人之欲求主要是滿足生存的物質需求,人之能力則為滿足這些欲求的物質生產能力。在正統的道德儒學那里,“性—情”為人性論的中心,因為道德性的仁義禮智之性發端于相應的情感。性與情本質相關,正如欲和能本質相關一樣。雖然如此,“欲—能”和“性—情”在李覯思想中還是相互關聯的,他還是希望能夠通過“足民之用”與“節民以禮”兩種途徑,對人之欲、情進行節文,最終實現人性之善。就此而言,李覯雖然同正統儒家有著較大的差異,其于道德之外,走向經濟之途,但其思想之根本尚未脫離儒家矩矱,因而同現代經濟人性論也有差異,可以說,李覯形成了具有儒家特色的經濟人性論。而在李覯之前,《鹽鐵論》中就已有儒生和士大夫圍繞經濟問題展開的激烈論辯,當時的儒生尚未形成經濟人性論,只是在儒家立場之內表達了他們對經濟的認識。在李覯之后,葉適進一步發展了經濟人的內涵,認識到勞動實踐對于人性養成的重要性。
三
顯然,儒家人性論的三個形態亦就是儒家思想開展的三種進路,這三種進路對于儒家思想的開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既然道德人性論認為,道德與人性本質相關,政治和經濟是從道德理想中生發出來,這就意味著儒家思想的開展必以鞏固道德理念為根本,并給予經濟、政治的發展而豐富、更新道德理念和道德知識。既然政治人性論不以道德之圣作為終極目標,而是通過人性的理論構建理想的政治藍圖,這就意味著儒家思想的開展必須著力于理想政治制度的構建,并從中確立政治向度的開展方向。既然經濟人性論承認經濟的重要性,承認利益和欲望的合理性,這就意味著儒家思想的開展并不能遠離經濟利益而空談理想,而應該著眼于經濟利益與自身的關系,從中確立經濟向度的開展方向。概言之,儒家人性論的道德、政治、經濟三個路向,對于儒家思想義理的當代開展具有綱領性指示意義。面向新的時代、新的問題,儒家思想義理的開展,既要基于儒學傳統的經驗,又要與時俱進、吐故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