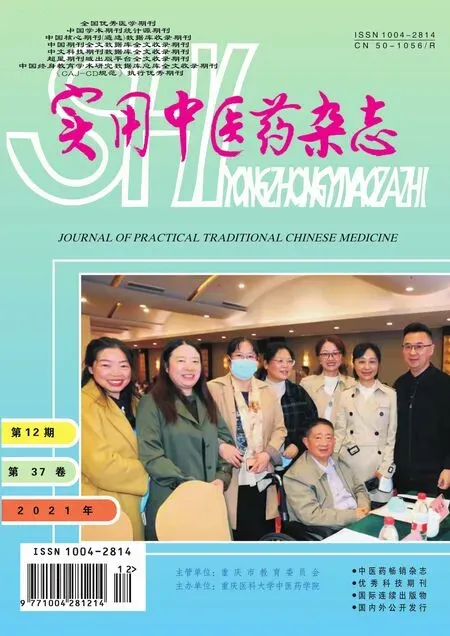醒腦開竅針法聯合焦氏頭針治療古茨曼綜合征11例
周彥含,吳 敬
(1.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2019級碩士研究生、國家中醫針灸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天津300193;2.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天津 300193)
古茨曼綜合征(Gerstmann’s syndrome)是奧地利神經學家Josef Gerstmann于1924年提出的一種由手指失認、左右失認、失寫、失算4個臨床癥狀構成的綜合征[1],其病理機制主要是優勢大腦半球的額葉角回損傷,故亦被稱為“角回綜合征”[2]。筆者用醒腦開竅針法聯合焦氏頭針針刺治療古茨曼綜合征效果較好,報道如下。
1 臨床資料
共11例,均為2019年12月至2020年9月天津中醫藥大學針灸科門診及住院患者。男7例,女4例;年齡最小35歲,最大76歲,平均(63±13)歲;病程最短0.5月,最長7月,平均(3.0±2.3)月;學歷均為中學以上,均為右利手,均為腦梗死。
納入標準:參考全國高等學校教材《神經病學》[3]古茨曼綜合征(Gerstmann’s syndrome)(以下簡稱GS)的定義及1995年中華醫學會第4次全國腦血管病學術會議修訂的《各類腦血管疾病診斷要點》[4]。診斷標準為經顱腦CT或MRI影像學檢查顯示存在頂葉角回或頂枕顳區、丘腦、島葉等部位定位損害。具有GS手指失認、左右失認、失寫、失算四主癥中至少2項。接受且能配合完成所有測驗。
排除標準:病情危重,存在嚴重神智、視聽、肢體功能及認知功能障礙無法配合評估,有嚴重出血傾向等其它不宜針灸治療的疾病等。
2 治療方法
醒腦開竅針法。主穴取內關、水溝、三陰交,配穴取極泉、尺澤、委中。患者取仰臥位,用0.25 mm×40mm一次性針灸針。雙側內關直刺1~1.5寸,捻轉提插瀉法施術1min;水溝向鼻中隔方向斜刺0.3~0.5寸,施雀啄重瀉法至眼球濕潤為度;三陰交沿脛骨內側緣與皮膚呈45°斜刺,進針1~1.5寸,施提插補法至下肢抽動3次為度;極泉沿經下移1寸,避開腋毛,直刺0.5~1寸,施提插瀉法至上肢抽動3次為度;尺澤屈肘120°,直刺1寸,施提插瀉法至患者前臂、手指抽動3次為度;委中仰臥直腿抬高取穴,直刺0.5~1寸,施提插瀉法至下肢抽動3次為度。留針30min,每天1次,每周針刺6次,1周為一療程,連續治療4周。
焦氏頭針針法。根據GS的常見損害部位及臨床癥狀選用焦氏頭針言語二區、言語三區及運用區。患者仰臥位,用0.25mm×40mm一次性針灸針,根據焦氏頭針劃線選定刺激區(患側),常規消毒后與頭皮呈30°角斜刺進針至帽狀腱膜下層(指下阻力減小),然后將針沿穴線推進1~1.5寸,得氣后行小幅度捻轉平補平瀉法2min。留針30min,每天1次,每周針刺6次,1周為一療程,連續治療4周。
3 觀察指標
采用漢語失語檢查法(Aphasia Battery of Chinese,ABC)[5-6]中的書寫和計算模塊評估失寫、失算程度;左右失認和手指失認采用簡單的代表性試驗評估[7]。檢查過程中排除因語言或肢體運動障礙導致的干擾。
手指失認檢查:①對應手指測試[7-8]:在患者無法看見自己雙手的條件下,檢查者觸摸患者一手的某個手指,要求患者活動另一手相對應的手指。②在患者無法看見自己雙手的條件下,檢查者觸摸患者某個手指,要求患者說出手指名稱,或檢查者說出手指名稱,要求患者活動相應的手指。
左右失認檢查[7,9]:要求患者按口令執行:①指出自己身體的左側或右側。②用自己的右手指出檢查者左手。③用自己的左手指出檢查者的左眼。④用自己的左手指出檢查者左肩。⑤用自己的右手指出檢查者右腳。以上檢查均確認患者能夠正確理解口令。
計算、書寫檢查:采用漢語失語檢查法(ABC)中的書寫和計算測試模塊評估失算及失寫情況。
4 療效標準
療效指數=[(治療后ABC量表評分-治療前ABC量表評分)÷ABC量表該項總分]×100%。治愈:療效指數大于等于85%。顯效:療效指數70%~84%。有效:療效指數30%~69%。無效:療效指數小于30%。
5 治療結果
治療前11例中4例存在左右失認,7例存在手指失認。11例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失寫和計算能力下降。失寫主要表現為流暢性失寫,其中3例合并有失讀。6例合并有不同程度的流利性失語,1例合并輕度命名性失語。
治療后患者左右失認及手指失認均較前改善,除1例遺留一定程度的左右失認(錯誤率≈60%)外,其余均能正確辨認手指及區分自身或周圍環境的左右方位(錯誤率<85%)。患者ABC量表書寫及計算部分測試分數均較前提高。
臨床療效痊愈3例,顯效5例,有效2例,無效1例,總有效率90.9%。
6 體 會
自提出以來,古茨曼綜合征(GS)的癥狀組成和病理機制就一直存在爭議。乃因GS在臨床中雖不罕見,但鮮有單純以四主癥為全部臨床表現者[10]。患者多合并失讀、失語或肢體功能障礙等其它更顯著的神經系統損傷表現,四主癥的嚴重程度也不盡相同。無合并癥的患者又極易被誤診為癡呆、癔癥等其它精神神經系統疾患[11],相關的臨床資料也較為匱乏,多為個案報道,缺乏大規模的系統性研究,研究結果的爭議也較大。同時GS沒有成體系的評估方式,臨床治療經驗更為罕見,因而研究較為困難。
例如GS的病變部位雖普遍被認為是優勢大腦半球的角回損害,但近年也陸續有研究指出,額、頂、顳、島葉、丘腦等部位損害亦可出現相關癥狀[12-13],故本研究納入病例時未局限于單純角回損傷的患者,且此型臨床非常罕見,研究意義較弱。同理,由于鮮有單純角回損害的患者,GS的臨床表現也常復雜化。失讀常合并出現,而失語甚至一度被認為是GS的必見合并癥[12-14],也更容易引起關注,從而掩蓋GS其它表現的存在。但GS作為一個獨立的綜合征,仍有其特定的臨床意義。
隨著更多新進檢查技術如fMRI、三維白質纖維束追蹤(DTI tractography)等的出現,近年來有學者對GS發病機理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新構想[15]。目前較為公認的一觀點認為GS的主要病理損害在于優勢大腦半球頂葉白質獨立的皮質網絡失聯[15-16],另一項較新的研究則指出GS的所有癥狀均可以被一個統一的機制概括,即患者出現了某些語言介導的空間運算能力失調[17]。在心理學層面,也有學者提出GS的發生與認知心理學中心理旋轉能力缺陷相關[10]。筆者認為,這些觀點其實并不矛盾,反而可以相互參考,并較好地解釋了GS四主癥臨床表現的變異性[10]。在了解現代醫學理論新進展的同時,從傳統祖國醫學的角度思考,發現這些相關機制的構成理念與石學敏院士所提出的中風病機“竅閉神逆,神不導氣”不謀而合。
參考各類臨床報道,除少量特殊情況外,導致GS的主要病因仍為腦血管疾病[18],患者也常合并出現一定的肢體功能障礙,故中醫治療或可參考“中風”,但GS患者畢竟不以肢體偏廢為主要臨床癥狀,而主要表現為認知功能方面的障礙,除“中風”外,或亦可劃入“癡呆”范疇,但亦不夠準確。雖然無法找到更加精確對應的中醫病名,但分析GS的臨床癥狀,是對語言文字和空間關系的處理能力降低,即“神機失用”。“靈機記性在腦不在心”,頭為諸陽之會,清陽出越于上,布達于外,而靈機為之所動。如清竅閉塞,神機逆亂,則清陽不能外達,而人為之癡鈍。
石氏醒腦開竅針法醒神開竅,梳理神機,且能滋補肝腎,充填陰精以化生榮養清陽,為治療之基本[19]。而“諸經皆歸于腦”,根據焦氏頭針理論,言語二區對應頂葉角回,主治命名性失語,言語三區主治感覺性失語,運用區則能治療失用癥。針刺頭針感應區能直達病所,醒神調神,活血通絡。雖然3個感應區未直接對應GS的四主癥,但GS患者多合并失語,或至少存在一定程度的語言運用能力下降,對語言區和運用區的刺激有利于書寫和計算能力的恢復,并改善手指失認、左右失認等癥狀[20-22]。近年也有研究表明頭針針刺能直接刺激大腦皮層,促進腦語言網絡的激活和神經重塑[23-24]。兩種針法聯合運用,相輔相成,功能醒達神機,梳理經氣,共促病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