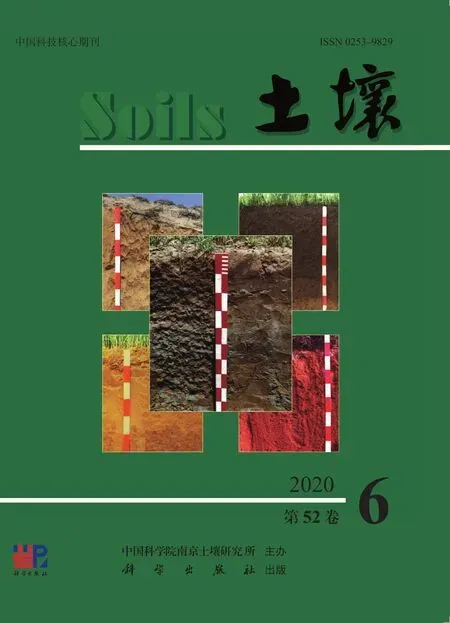基于水稻產量的江蘇省稻麥輪作區土壤質量評價①
趙 賀,王緒奎,劉紹貴,高 飛,李 鵬,李其勝,李輝信,焦加國*
基于水稻產量的江蘇省稻麥輪作區土壤質量評價①
趙 賀1,王緒奎2*,劉紹貴3,高 飛1,李 鵬1,李其勝1,李輝信1,焦加國1*
(1南京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南京 210095;2江蘇省耕地質量與農業環境保護站,南京 210036;3揚州市農業環境監測站,江蘇揚州 225101)
為明確江蘇稻麥輪作區土壤質量狀況,本研究基于2008—2015年期間江蘇省稻麥輪作區10 681個測土配方施肥樣點的數據,通過相關性和主成分分析篩選了江蘇省稻麥輪作區的最小數據集(minimum data set, MDS),并對土壤質量進行評價。結果表明:基于水稻產量分析,江蘇省稻麥輪作區的最小數據集包括有機質、有效磷、速效鉀、有效鐵和有效硼。基于最小數據集得出的江蘇省土壤質量指數(SQI-MDS)范圍在0.136 ~ 1.000之間(均值0.674),整體處于“良Ⅱ”等級,與基于全量數據集得出的土壤質量指數(SQI-TDS)之間呈極顯著正相關關系(2= 0.720),這說明最小數據集能夠較好地代替全量數據集指標。江蘇省稻麥輪作區土壤質量存在空間異質性,里下河農業區土壤質量最高,其次是太湖農業區,再者是寧鎮揚、沿江、沿海和徐淮農業區。江蘇省農業區的最小數據集存在差異性,這說明不同農業區主要的限制因素存在差異。整體來看,有機質、鉀元素和微量元素是江蘇省六大農業區主要肥力限制因子。
江蘇省;水稻;最小數據集;土壤質量評價;空間異質性
土壤質量是土壤多種功能的綜合體現,其綜合涵蓋了土壤肥力質量、土壤環境質量和土壤健康質量[1]。土壤質量不能被直接測定,但可通過間接測定指示土壤功能的指標來描述土壤質量狀態[2]。目前沒有一個統一的方法來選取土壤質量評價指標,因此,如何選取土壤指標是土壤質量評價的關鍵。Larson和Pierce[3]于1991年提出了最小數據集,即通過一定的數學方法從中篩選出具有代表性的指標,建立最小數據集,構建土壤質量指數進行土壤質量評價。最小數據集作為篩選具有代表性的評價指標的方法,在土壤質量評價中廣泛使用[4-5]。利用最小數據集方法對我國土壤質量進行評價的相關研究很多[6-8],多數使用物理指標、化學指標和生物指標。
江蘇省具有典型的地理位置、水系特點、氣候類型、地貌區域[9],轄內有徐淮、里下河、沿海、沿江、寧鎮揚和太湖六大農業區[10]。江蘇省稻麥輪作面積和水稻總產居全國前列,單產全國水平最高,在全省和全國水稻生產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11]。江蘇省耕地存在土壤養分非均衡化和耕層物理性狀變差等問題[12],明確江蘇省稻麥輪作區土壤質量狀況對全省水稻的生產有著重要的意義。關于江蘇省土壤質量評價研究多是在某個地區或者某個市(縣)范圍[13-16],而關于江蘇省稻麥輪作區土壤質量評價研究較少[17],因此,本研究以江蘇省稻麥輪作區為研究對象,從8年連續監測數據和全省空間尺度上進行土壤質量分析與評價。評價結果可為江蘇省乃至我國不同稻麥輪作區的農田管理和精準施肥提供因地制宜的科學指導。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江蘇省位于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經緯度范圍為116°18′ ~ 121°57′E和30°45′ ~ 35°20′N,總面積為10.72萬km2。全省為亞熱帶向暖溫帶過渡地帶,氣候、植被兼具南方和北方的特征,轄內有徐淮、里下河、沿海、沿江、寧鎮揚和太湖六大農業區[10]。該研究區種植制度以稻麥輪作為主,土壤類型以水稻土和潮土為主,成土母質以河流沖積物、河湖沉積物和江海相沉積物為主。
1.2 數據來源
土壤理化數據為江蘇省稻麥輪作區的測土配方施肥調查數據,數據由江蘇省耕地質量保護站提供。于2008—2015年期間每年的水稻收獲季在全省范圍內采集樣品(樣點不重復),采樣深度0 ~ 20 cm,并同時記錄樣點的水稻產量,共采集10 681個樣點(表1)。土壤樣品測定指標包括容重、pH、有機質、全氮、有效磷、速效鉀、緩效鉀、有效銅、有效鋅、有效鐵、有效錳、有效硼、有效鉬和有效硅。土壤分析測定方法均參照魯如坤[18]《土壤農化分析》。

表1 江蘇省稻麥輪作區土壤樣品信息
1.3 土壤質量評價
1.3.1 最小數據集指標篩選 首先,將各土壤指標與作物產量進行皮爾遜相關性分析,選取與作物產量有顯著相關性的指標,再對所選取的土壤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選擇特征值>1的主成分作為研究對象[19],各主成分特征值越大越能代表土壤指標體系特性。在此分析過程中,采用最大方差旋轉法加強不相關組分的解釋能力[20]。對于每組主成分而言,因子載荷變量越大對該主成分貢獻越大,高因子載荷指標即因子載荷絕對值達到該主成分中最大因子載荷90% 范圍內的指標[6]。當一個主成分中高因載荷變量只有一個時,則該指標進入最小數據集,不止一個時,對其分別做相關性分析,若相關系數低(<0.7)時,各指標均被選入最小數據集,若相關系數高(>0.7),最大的高因子載荷指標(2個指標時)或相關系數之和最大的高因子載荷指標(2個以上指標時)被選入最小數據集[21-22]。
1.3.2 指標權重值 用主成分方法確定土壤質量評價指標的權重,各指標權重值等于該指標的公因子方差與所有最小數據集指標公因子方差和的比值[22]。
1.3.3 指標評分 不同指標具有不同的單位,通過隸屬度函數可將土壤質量指標測定值標準化為0 ~ 1之間的無量綱值,主要標準化隸屬度評分函數分為3類[23]:正S型、反S型、拋物線型。
正S型:

反S型:

拋物線型:

式中:() 表示指標得分,表示指標實測值,和分別表示下限和上限臨界值。
1.3.4 土壤質量指數 土壤質量指數(SQI)采用以下公式計算[24]:

式中:表示指標個數,W表示指標權重值,S表示指標得分。
1.3.5 土壤質量評價精度驗證 利用Nash有效系數(E)和相對偏差系數(E)評價最小數據集的精確程度[25]。計算公式為:



其三,許多的“文學流派”以地域命名,有鮮明的地域色彩,如宋代的“江西詩派”、“四靈詩派(永嘉四靈)”,明代詩文的“公安派”、“竟陵派”、“茶陵派”、戲曲的“吳江派”、“臨川派”,清代的“桐城派”、“浙西詞派”、“常州詞派”等。
1.4 數據處理
數據經Excel 2016整理匯總,利用SPSS 22.0軟件進行描述性統計、相關性分析和主成分分析,ArcMap10.3作圖。
2 結果
2.1 江蘇省稻麥輪作區土壤理化性狀
江蘇省稻麥輪作區土壤理化指標統計分析結果顯示(表2):根據全國土壤養分含量分級標準[26],江蘇省稻麥輪作區土壤容重(1.26 g/cm3)處于“偏緊”等級;pH(7.23)處于“中性”級別;有機質(22.85 g/kg)、全氮(1.41 g/kg)、有效磷(18.12 mg/kg)、速效鉀(121.16 mg/kg)均值處于“中等”級別;土壤緩效鉀(600.3 mg/kg)、有效銅(3.49 mg/kg)、有效鐵(72.4 mg/kg)和有效錳(33.7 mg/kg)達到“極豐富”級別;有效鋅(1.37 mg/kg)和有效硅(185.9 mg/kg)達到“豐富”級別;有效硼(0.49 mg/kg)和有效鉬(0.12 mg/kg)處于“缺乏”級別。根據變異系數的劃分等級標準[5]:容重為不敏感指標(CV<10%);pH、有機質、全氮為低度敏感指標(CV為10% ~ 40%);有效磷、速效鉀、緩效鉀、有效銅、有效鋅、有效鐵、有效硼、有效鉬和有效硅為中度敏感指標(CV為40% ~ 100%);有效錳為高度敏感指標(CV>100%)。
2.2 土壤質量指數
2.2.1 土壤質量指標篩選 首先對10 681個監測樣點數據的水稻產量與土壤指標進行皮爾遜相關性分析,結果表明(表3):水稻產量與土壤pH、容重、有機質、全氮、有效磷、速效鉀、緩效鉀、有效銅、有效鋅、有效鐵、有效錳和有效硼指標存在顯著性相關關系,這些指標作為土壤質量評價候選指標進行下一步的主成分分析。

表2 江蘇省稻麥輪作區土壤理化性狀

表3 水稻產量與土壤屬性相關性分析
注:*表示相關性達<0.05顯著水平,**表示相關性達<0.01顯著水平,下同。
2.2.2 土壤質量最小數據集建立 對相關性分析中保留的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然后根據每個主成分中評價參數的載荷值和參數的相關性進行分析確定組成最小數據集的評價指標。采用最大方差旋轉法后的主成分分析(表4)和高因子載荷指標相關性(表5)結果顯示:特征值>1的主成分有4組,總方差的累計貢獻率達59.349%。PC1主要由有效鐵1個因子構成,因此PC1中有效鐵進入最小數據集;PC2主要由有機質和全氮2個因子構成,有機質與全氮的相關系數>0.7(0.709**),且有機質具有PC2中最高因子載荷,因此PC2中有機質進入最小數據集。PC3主要由速效鉀1個因子構成,因此PC3中速效鉀進入最小數據集;PC4主要由有效磷和有效硼2個因子構成,且有效磷與有效硼的相關系數<0.7(0.082**),因此PC4中有效磷與有效硼進入最小數據集。綜上可知,最終確定江蘇省稻麥輪作區土壤質量評價最小數據集為:有機質、有效磷、速效鉀、有效鐵和有效硼。同理篩選出江蘇省六大農業區的最小數據集,結果表明(表6):江蘇省六大農業區的最小數據集存在差異性,這說明不同農業區主要的限制因素存在差異。整體來看,有機質、鉀元素和微量元素是江蘇省稻麥輪作區主要限制因素。

表4 土壤質量指標主成分分析
注:加粗的數字所對應的指標為高因子載荷指標

表5 高因子載荷指標相關性
2.2.3 土壤質量指數 通過對與產量有顯著相關性的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獲得各個指標的公因子方差,利用指標公因子方差所占比例確定各個指標的權重值(表7)。通過隸屬度函數將土壤質量指標測定值標準化為0 ~ 1之間的無量綱值,其下限和上限臨界值[13, 23, 27]見表8。然后采用公式(4)計算SQI-MDS和SQI-TDS。江蘇省稻麥輪作區SQI-MDS介于0.136 ~ 1.000,均值為0.674。SQI-TDS介于0.247 ~ 0.955,均值為0.635。
2.2.4 最小數據集合理性驗證 驗證最小數據集的合理性是土壤質量評價的重要環節。首先將對SQI-MDS與SQI-TDS兩者進行回歸分析,然后采用公式(5)和(6)分別計算Nash有效系數和偏差系數來驗證最小數據集的合理性。結果表明:SQI-MDS與SQI-TDS呈極顯著正相關(2=0.720,圖1),Nash有效系數和偏差系數分別為 0.401和0.061,偏差系數接近0。水稻產量與SQI-MDS(=0.243**)和SQI-TDS(= 0.232**)均具有顯著相關關系。綜上所述,最小數據集能夠較好代替全量數據集指標。
2.3 基于最小數據集的江蘇省稻麥輪作區土壤質量綜合評價
根據隸屬度評分函數曲線中轉折點的相應取值,結合等距劃分法[7, 27-28],將土壤質量指數分為5個等級。基于最小數據集的江蘇省稻麥輪作區土壤質量等級頻率分布結果顯示(表9):江蘇省稻麥輪作區土壤質量19.71% 處于“優Ⅰ”等級;52.50% 處于“良Ⅱ”等級;24.28% 處于“中等Ⅲ”等級;3.40% 處于“差Ⅳ”等級,0.12% 處于“很差Ⅴ”等級。整體看來,基于最小數據集的江蘇省稻麥輪作區土壤質量指數均值為0.674,整體處于“良Ⅱ”等級。圖2和表10結果顯示:江蘇省稻麥輪作區土壤質量存在空間異質性,里下河農業區土壤質量指數最高(均值0.768),其次是太湖農業區(均值0.726),再者是沿海(均值0.654)、徐淮(均值0.649)、寧鎮揚(均值0.648)和沿江(均值0.648)農業區。

表6 江蘇省六大農業區(稻麥輪作區)最小數據集

表7 全量數據集和最小數據集的指標權重值

表8 土壤質量評價指標隸屬函數中下限和上限取值

圖1 最小數據集土壤質量指數與全量數據集土壤質量指數的相關性
3 討論
江蘇省稻麥輪作區土壤質量評價的最小數據集指標包括有機質、有效磷、速效鉀、有效鐵和有效硼。金慧芳等[5]研究總結出前人使用頻率前10的最小數據集評價指標,本研究最小數據集5個評價指標中有機質和有效磷進入最小數據集評價指標使用頻率前10位。這前10個使用頻率高的最小數據集評價指標沒有包括中微量元素指標,而本研究分析了微量元素指標。本研究中有效鐵指標與鄧紹歡等[8]對南方地區冷浸田進行土壤質量評價中pH、全氮、有效錳、有效鐵、C/N和線蟲數量進入最小數據集的結果一致。本研究中有機質、有效磷、速效鉀和有效硼4個指標與劉金山等[7]關于水旱輪作區的研究結果中有機質、堿解氮、有效磷、速效鉀、有效硼、有效鉬和有效鋅進入最小數據集的結果一致。本研究中有效鐵和有效硼2個指標與趙艷[31]對宜興市耕地質量進行的綜合評價中pH、全氮、有效鐵、有效鉬和有效硼指標進入最小數據集的結果一致。本研究中有機質和有效磷2個指標與金慧芳等[5]對紅壤坡耕地耕層土壤質量評價中耕層厚度、土壤容重、土壤貫入阻力、土壤有機質、pH 和有效磷進入最小數據集的結果一致。

圖2 基于最小數據集(A)和全量數據集(B)的江蘇省稻麥輪作區土壤質量空間分布

表9 基于最小數據集的江蘇省六大農區土壤質量指數
江蘇省地形地貌類型多樣、氣候類型多樣、農田管理也存在一定差異,所以不同自然尺度下各農業區所篩選的最小數據集指標會存在一定差異。本研究結果顯示,江蘇省六大農業區的最小數據集存在差異性,整體來看,有機質、鉀元素和微量元素是江蘇省稻麥輪作區主要限制因素,這與王緒奎等[12]提出的江蘇省耕地土壤養分主要表現在土壤速效鉀和中微量元素的虧空結果一致。
江蘇省稻麥輪作區土壤質量存在空間異質性,成土母質以河湖沉積物為主的里下河農業區、太湖農業區土壤質量最高,以黃土狀物為主的寧鎮揚農業區土壤質量次之,以河流沖積物為主的沿江、徐淮農業區以及以江海相沉積物為主的沿海農業區土壤質量最低。黃河泛濫沖積形成徐淮黃泛平原,其土壤有機質和養分含量較低[32-33],本研究徐淮黃泛平原區土壤質量較低結果與此一致。沈雨等[34]研究結果表明,里下河和太湖地區土壤有機碳含量比較高,本研究里下河和太湖農業區土壤質量較高結果與此相似。張慶利等[35]研究金壇市土壤質量結果表明,金壇市中部地區土壤質量指數相對較高,東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土壤質量指數最低,本研究金壇市的土壤質量分布結果與此完全一致。趙艷[31]關于宜興市耕地土壤質量空間特征研究以宜興市北部、西部地區耕地質量較高,而中部和西南部地區耕地質量較低,本研究宜興市的土壤質量分布結果與此一致。閏豫疆[36]研究表明湖北鐘祥市丘陵地區的土壤養分含量比平原養分含量高,本研究寧鎮揚低山丘陵的地區、沂沭低山丘陵地區和徐州市銅山區土壤質量相近且土壤質量高于周邊平原地區結果與此一致。
江蘇省稻麥輪作區SQI-MDS與SQI-TDS兩者相關系性較高(2= 0.720),Nash有效系數(0.401)接近1,偏差系數(0.061)幾乎接近0,說明評價精確度較高,這與金慧芳等[5]和鄧紹歡等[8]研究結果一致。水稻產量與SQI-MDS具有顯著相關關系,這與Qi等[13]和Liu等[30]研究中作物產量與土壤質量指數顯著相關的結果一致。
4 結論
江蘇省稻麥輪作區土壤質量評價的最小數據集指標包括有機質、有效磷、速效鉀、有效鐵和有效硼。基于最小數據集得出的江蘇省土壤質量指數(SQI-MDS)范圍為0.136 ~ 1.000(均值0.674),整體處于“良Ⅱ”等級,與基于全量數據集得出的土壤質量指數(SQI-TDS)之間呈極顯著正相關(2= 0.720),這說明最小數據集能夠較好地代替全量數據集指標。江蘇省稻麥輪作區土壤質量存在空間異質性,以里下河農業區土壤質量最高,其次是太湖農業區,再者是寧鎮揚、沿江、沿海和徐淮農業區。江蘇省六大農業區的最小數據集存在差異性,這說明不同農業區主要的限制因素存在差異。整體來看,有機質、鉀元素和微量元素是江蘇省六大農業區主要肥力限制因子。因此,江蘇省稻麥輪作區的農田管理措施中,要注重增施有機肥和微肥,平衡養分的同時進一步提高土壤質量,為糧食穩產豐產提供保障。
在本研究中,所選取指標僅為理化指標,在后續評價中應將土壤生物指標、土壤耕層指標、農田管理措施指標等納入評價范圍,這樣結果將更全面,旨在為江蘇省乃至我國不同稻麥輪作區的農田管理和耕地質量提升提供因地制宜的科學指導。
[1] 陳美軍, 段增強, 林先貴. 中國土壤質量標準研究現狀及展望[J]. 土壤學報, 2011, 48(5): 1059–1071.
[2] Karlen D L, Mausbach M J, Doran J W, et al. Soil quality: A concept, definition, and framework for evaluation (A guest editorial)[J].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 1997, 61(1): 4–10.
[3] Larson W E, Pierce F J. Conserv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soil quality[C]. Proc. of the Int. Workshop on evaluation for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International board for soil resource and management( IBSRAM). proceeding 123, 2. Bangkok, Thailand, 1991: 175-203.
[4] Govaerts B, Sayre K D, Deckers J. A minimum data set for soil quality assessment of wheat and maize cropping in the Highlands of Mexico[J]. Soil & Tillage Research, 2006, 87(2): 163–174.
[5] 金慧芳, 史東梅, 陳正發, 等. 基于聚類及PCA分析的紅壤坡耕地耕層土壤質量評價指標[J]. 農業工程學報, 2018, 34(7): 155–164.
[6] 貢璐, 張雪妮, 冉啟洋. 基于最小數據集的塔里木河上游綠洲土壤質量評價[J]. 土壤學報, 2015, 52(3): 682–689.
[7] 劉金山, 胡承孝, 孫學成, 等. 基于最小數據集和模糊數學法的水旱輪作區土壤肥力質量評價[J]. 土壤通報, 2012, 43(5): 1145–1150.
[8] 鄧紹歡, 曾令濤, 關強, 等. 基于最小數據集的南方地區冷浸田土壤質量評價[J]. 土壤學報, 2016, 53(5): 1326–1333.
[9] 趙媛, 王靜愛. 江蘇地理[M]. 北京: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1.
[10] 付光輝, 劉友兆. 江蘇省耕地保護區劃研究[J]. 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 2008, 29(1): 11–16.
[11] 佴軍. 近30年江蘇省水稻生產的時空變化與效益分析[D]. 揚州: 揚州大學, 2013.
[12] 王緒奎, 孫洋, 潘國良. 江蘇省耕地質量現狀、問題與對策[C]//江蘇土壤肥料科學與農業環境. 2004: 12–16.
[13] Qi Y B, Darilek J L, Huang B, et al. Evaluating soil quality indices in an agricultural region of Jiangsu Province, China[J]. Geoderma, 2009, 149(3): 325–334.
[14] 郭宗祥, 左其東, 李梅, 等. 江蘇省太倉市耕地地力調查與質量評價——土壤pH、有機質、全氮、有效磷、速效鉀和CEC的變化[J]. 土壤, 2007, 39(2): 318–321.
[15] 毛志剛, 谷孝鴻, 劉金娥, 等. 鹽城海濱鹽沼濕地及圍墾農田的土壤質量演變[J]. 應用生態學報, 2010, 21(8): 1986–1992.
[16] 巫建華, 許學宏, 陳斌, 等. 江蘇中部典型農區耕地環境質量評價及應用研究—— 以海安縣為例[J]. 土壤, 2003, 35(5): 387–391, 407.
[17] 王緒奎, 徐茂, 汪吉東, 等. 太湖地區典型水稻土大時間尺度下的肥力質量演變[J]. 中國生態農業學報, 2009, 17(2): 220–224.
[18] 魯如坤. 土壤農業化學分析方法[M]. 北京: 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 2000.
[19] Brejda J J, Moorman T B, Karlen D L,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regional soil quality factors and indicators I. central and southern high Plains[J].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 2000, 64(6): 2115–2124.
[20] Flury B. Riedwyl H. Multivariate Statistics. A Practical Approach. Chapman and Hall, London, Great Britain. 1988.
[21] Andrews S S, Karlen D L, Mitchell J P. A comparison of soil quality indexing methods for vegetable production systems in Northern California[J].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2002, 90(1): 25–45.
[22] Li P, Zhang T L, Wang X X, et al. Development of biological soil quality indicator system for subtropical China[J]. Soil and Tillage Research, 2013, 126: 112–118.
[23] 曹志洪, 周健民. 中國土壤質量[M].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08.
[24] Doran J W,Parkin B T. Defining and assessing soil quality. In: Doran, J W, Coleman D C, Ezdicek D F, et al, eds. Defining Soil Quality for a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Spec. Publ. 35. Madison,WI, USA, 1994, 3-21.
[25] Nash J E, Sutcliffe J V. River flow forecasting through conceptual models part I—A discussion of principles[J]. Journal of Hydrology, 1970, 10(3): 282–290.
[26] National Soil Survey Office. Surveying Techniques of Soil in China. Beijing: Agriculture Press, 1992: 87-212.
[27] 馮萬忠, 馬振朝, 張麗娟, 等. 河北平原冬小麥/夏玉米高產田土壤肥力質量最小數據集構建及其評價[J]. 江蘇農業科學, 2017, 45(15): 233–238.
[28] 張鳳榮, 安萍莉, 王軍艷, 等. 耕地分等中的土壤質量指標體系與分等方法[J]. 資源科學, 2002, 24(2): 71–75.
[29] 吳春生, 劉高煥, 黃翀, 等. 基于MDS和模糊邏輯的黃河三角洲土壤質量評估[J]. 資源科學, 2016, 38(7): 1275– 1286.
[30] Liu Z J, Zhou W, Shen J B, et al. Soil quality assessment of Albic soils with different productivities for Eastern China[J]. Soil & Tillage Research, 2014, 140: 74–81.
[31] 趙艷. 宜興市耕地土壤質量空間特征研究[D]. 南京: 南京大學, 2012.
[32] 趙明松, 張甘霖, 王德彩, 等. 徐淮黃泛平原土壤有機質空間變異特征及主控因素分析[J]. 土壤學報, 2013, 50(1): 1–11.
[33] 劉欽普, 林振山, 周勤. 華北黃泛平原潮土土壤養分與土壤粒級的關系研究[J]. 土壤肥料, 2006(2): 26–29, 51.
[34] 沈雨, 黃耀, 宗良綱, 等. 基于模型和GIS的江蘇省農田土壤有機碳變化研究[J]. 中國農業科學, 2003, 36(11): 1312–1317.
[35] 張慶利, 潘賢章, 王洪杰, 等. 中等尺度上土壤肥力質量的空間分布研究及定量評價[J]. 土壤通報, 2003, 34(6): 493–497.
[36] 閆豫疆. 縣域級平原與丘陵農田土壤養分空間差異性綜合研究[D]. 武漢: 華中農業大學, 2012.
Evaluation of Soil Quality in Rice-Wheat Rotation Regions of Jiangsu Province Based on Rice Yield
ZHAO He1,WANG Xukui2*, LIU Shaogui3, GAO Fei1,LI Peng1, LI Qisheng1,LI Huixin1,JIAO Jiaguo1*
(1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2 Jiangsu Province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Protection Station, Nanjing 210036, China; 3 Yangzhou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 Yangzhou, Jiangsu 225101, China)
This study is to clarify soil quality status of rice-wheat rotation regions in Jiangsu Province based on the data of 10 681 soil-measuring formula fertilization samples from the rice-wheat rotation regions of Jiangsu Province during 2008—2015. The minimum data set (MDS) of rice-wheat rotation region in Jiangsu Province was screened by correlation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then soil quality was evalu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ased on rice yield analysis, the minimum data set of rice-wheat rotation region in Jiangsu Province included organic matter, available phosphorus, available potassium, available iron and available boron. The variation range of soil quality index based on the minimum data set (SQI-MDS) was between 0.136 and 1.000 (mean 0.674), the average value was in the "good II" grade, and was a very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2= 0.720) with soil quality index based on the full data set (SQI-TDS). It showed that the minimum data set could better replace the full data set. There was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 soil quality of rice-wheat rotation regions in Jiangsu Province, the highest soil quality was in the Lixiahe agricultural area, followed by the Taihu agricultural area, and the Ningzhenyang, Riverside, coastal and Xuhuai agricultural areas.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minimum data sets of the six major agricultural regions in Jiangsu Province,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main limiting factors in different agricultural regions. On the whole, organic matter, potassium and trace elements are the main limiting factors for the six major agricultural regions in Jiangsu Province.
Jiangsu Province; Rice; Minimum data set; Soil quality evaluation; Spatial heterogeneity
S158
A
10.13758/j.cnki.tr.2020.06.018
趙賀, 王緒奎, 劉紹貴, 等. 基于水稻產量的江蘇省稻麥輪作區土壤質量評價. 土壤, 2020, 52(6): 1230–1238.
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2016YFD0300908)和江蘇省農業科技自主創新基金項目(CX(17)1101)資助。
(534974828@qq.com;jiaguojiao@njau.edu.cn)
趙賀(1994—),男,河南永城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土壤培肥與土壤質量評價研究。E-mail: 2016103022@nja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