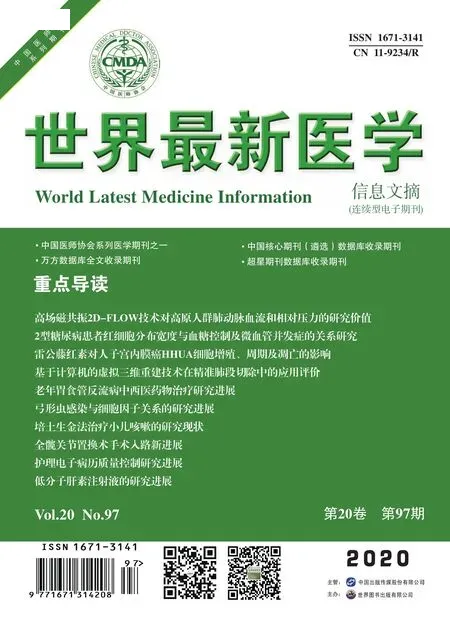接納與承諾療法對病恥感干預隨機對照試驗的系統評價
姜錦霞,喬建紅,張愛華*
(1.山東第一醫科大學(山東省醫學科學院) 護理學院,山東 泰安;2. 山東第一醫科大學(山東省醫學科學院)第一附院 護理部,山東 濟南)
0 引言
病恥感是指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因其自身屬性而受到社會詆毀的現象[1],Corrigan[2-3]將其分為公眾病恥感和自我病恥感。“公眾病恥感”是指大型社會群體對被歧視群體的刻板印象表示認可并采取行動的現象;“自我病恥感”是一種主觀過程,是個體吸收周圍社會群體認可的刻板印象并應用在自己身上的過程[2-3]。兩者相互作用,相互影響[4]。國內外數項研究表明,病恥感普遍存在于學生[5-6]衛生專業人員[5-6]患者的親屬[7-8]和患者本人[9-11]中,患病率達中高水平[12-14]。病恥感與癥狀嚴重程度增加[15]尋求幫助延遲[16]未充分利用精神衛生服務[17]及治療依從性差[15]等因素有關,它可導致自尊心低下自我排斥和社會孤立[18-20],影響個體的就業住房保險入學等社會活動[21],降低生活質量[20],因此消除病恥感對于減少心理健康問題至關重要。接納與承 諾 療 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ACT) 是第三代認知行為治療的典型代表,它通過教授個體正念相關的策略,旨在幫助其減少經驗性回避,提高心理靈活性水平[22]。研究表明[23-24],ACT 可改善個體的病恥感,促進其心理健康,提高生活質量。因此,本研究通過系統地回顧、評估和綜述現有的ACT 對病恥感的隨機對照試驗,旨在檢驗ACT 在病恥感治療中的作用,為 ACT 的臨床應用及發展提供相關循證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檢索策略
采用主題詞與自由詞相結合的方式,在中國知網、萬方、維普、PubMed、EbscoHost、Web of Science(1900-2020)、MEDLINE(1946-2020) 等數據庫進行檢索,中文檢索詞包括病恥感/ 污名/ 歧視、接納與承諾療法,英文檢索詞包括stigma/prejudice/discrimination、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ACT/acceptance、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首次檢索日期截止至 2020 年 4 月7 日,2020 年 4 月26 日再次檢索,檢索時對文獻語言類型不作限制,檢索策略會根據不同數據庫的特點作相應調整。另外,輔以“滾雪球”方法追溯納入文獻、主題相關文獻和綜述的參考文獻,以確保查全率。
1.2 文獻納入和排除標準
1.2.1 納入標準
(1)研究設計:隨機對照試驗;
(2)納入對象:存在病恥感的各種疾病患者人群或社會人群,年齡、性別不限;
(3)干預措施:接納與承諾療法;
(4)對照措施:空白對照、常規教育或其他心理干預措施;
(5)結局指標:自我病恥感及大眾對特定人群的污名化態度(即公眾病恥感)。
1.2.2 排除標準
(1)綜述類文章、會議報告;
(2)無結果或數據描述不清;
(3)ACT 治療聯合其他干預措施;
(4)沒有全文。
1.3 文獻篩選及資料提取
按照上述納入和排除標準,兩名研究者對檢索到的所有文獻進行篩查,確定最終納入文獻后,兩者分別閱讀全文并進行資料提取,過程中如遇分歧,由第三人抉擇。資料提取內容包括:作者(年份)、研究對象、例數(試驗組、對照組)、干預措施(試驗組、對照組)、測評工具及評價時間。
1.4 文獻質量評價
相同的兩名研究者按照 Cochrane 5.1.0 版系統評價手冊[25]分別對納入文獻進行質量評價,如遇分歧,由第三人抉擇。評價內容包括隨機分配、分配隱藏、對研究對象或干預實施者使用盲法、對結果測評者使用盲法、結果數據的完整性、選擇性報告偏倚和其他偏倚等 7 個項目。文獻全部滿足上述條件,質量評為A 級,發生偏倚的可能性小;部分滿足,評為B 級,發生偏倚的可能性為中度;全部不滿足,評為C 級,發生偏移的可能性大。本研究只納入質量為A、B 級的文獻,排除C 級。
2 結果
2.1 文獻檢索結果
共檢出相關文獻936 篇,中文1 篇。用NoteExpress 剔除重復文獻520 篇,得到文獻416 篇,閱讀文題和摘要刪除明顯不符合研究納入標準的文獻402 篇,剩余文獻14 篇,然后下載文獻并通讀全文,刪除非RCT 2 篇、ACT 聯合其他干預措施的文獻6 篇、無結果文獻1 篇,最終納入文獻5 篇,利用“滾雪球”方法追加文獻2 篇,最終納入7 篇文獻[24,26-31],其中1篇中文,6 篇英文。
2.2 納入研究的一般情況
本系統綜述納入的研究中檢驗ACT 對自我病恥感干預效果的3 篇[24,26-27],檢驗ACT 對公眾病恥感干預效果的4 篇[28-31],共有653 人參與。7 項研究中ACT 治療均是以團體干預的形式進行,2 項研究[26,29]的干預時長相同,2 項研究[30-31]研究對象、評估工具和隨訪時間相同,其余各研究的研究對象、預時長、評估工具和隨訪時間均不相同。納入研究的一般情況見表1。
2.3 文獻質量評價結果
納入的7項研究質量學評價等級全部為B級。3項研究[26,30-31]提到了采用隨機數字表或在線隨機數字序列進行分組,2 項研究[26,30]對結果測評者實施盲法,其余研究[24,27-29]僅提到隨機分組,未描述具體的隨機化方法和盲法的使用情況;2 項研究[24,29]中參與者知道分配條件;僅1 項研究[30]介紹了分配方案隱藏的方法;所有研究[24,26-31]中參與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失訪和退出,且3 項[24,30-31]的樣本流失率較高。文獻具體的方法學質量評價結果見表2。
2.4 ACT 對病恥感干預效果的分析結果
由于本研究納入文獻之間存在較大異質性,故采用定性的方法系統歸納和總結各納入研究的干預效果。

表1 納入研究的一般情況

表2 納入研究的方法學質量
2.4.1 ACT 對自我病恥感的干預效果
(1)肥胖患者:Lillis 等[26]在減肥診所和社區招募在過去兩年內完成過至少6 個月的任何有組織的減肥計劃的參與者87 名,其中84 名完成了所有評估程序。ACT 組中40 名參與者完成了一個為期1 天,共6 小時的研討會,其余44 名參與者被列入候補名單。利用體重病恥感問卷(WSQ),在干預前和干預后3 個月通過電子郵件、信件和電話等方式來評估參與者自我病恥感的程度。結果顯示,ACT 干預后參與者體重相關的病恥感水平顯著降低(P<0.001)。
(2)藥物使用障礙患者:Luoma 等學者[24]將133 名藥物使用障礙患者隨機分為常規教育組和常規教育+ACT 組,后者接受共3 次,2h/次,持續1 周的干預治療,干預前、后和干預后4 個月時采用內部病恥感量表(ISS)來衡量患者的自我病恥感程度。分析結果表明:ACT 患者從治療前到治療后表現出小而顯著的改善(P=0.045),在隨訪期間增加到中度且顯著改善(P=0.000)。
(3)精神分裂癥康復期患者:國內學者李莉等[27]選取 61例精神分裂癥康復期患者為研究對象,對干預組31 例患者在常規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礎上加施2 次/周,90min/次的 ACT干預,干預共 10 次,歷時5 周,在干預前、后用精神疾病患者病恥感量表中文版(SSMI-C)來測評其病恥感水平。數據分析結果顯示:干預組 SSMI-C 水平顯著低于對照組(P=0.000)。
2.4.2 ACT 對公眾病恥感的干預效果
(1) 針對精神疾病患者的公眾病恥感:Masuda 等[28]將ACT 干預與教育干預進行了比較,研究對象是85 名本科大學生,結局指標是大學生對待精神疾病患者的污名化態度,在干預前、后以及干預后1 個月的隨訪中對研究對象進行評估,評估工具采用社區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態度量表(CAMI),結果發現:ACT 組和教育干預組研究對象的污名化態度都有所減少,效應可持續到干預后1 個月,但兩種干預條件之間沒有總體差異(P>0.1)。
(2)針對酒精和藥物濫用患者的公眾病恥感:Hayes 等[29]設計了一個三臂隨機對照試驗,目的是比較ACT 組、多元文化培訓組或教育控制組3 種治療條件下酒精和藥物濫用咨詢師對其客戶的污名化態度。配對樣本t 檢驗顯示,干預后ACT 組沒有立即顯示出效果,但3 個月隨訪時態度有所改善(P=0.015;多元文化培訓組則相反,在治療剛結束時效果明顯(P=0.046),但隨訪時未見改善;教育控制組沒有明顯變化。在3 種條件下進行比較,從治療前到治療后,多元文化培訓組比教育控制組改善更多(P=0.019),但ACT 沒有;從預處理到隨訪,ACT 組參與者污名化態度的改善遠超過教育控制條件(P=0.011),但是多元文化培訓卻沒有。
(3)針對人格障礙患者的公眾病恥感:Clarke 等[30]等人比較在參加完為期2 天的ACT 干預和心理教育培訓干預后,護理服務提供者對人格障礙患者的歧視態度改變。結果表明,從基線到治療后以及從基線到6 個月隨訪,兩組參與者的污名化態度都有顯著改善,但兩組之間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此后,Clarke 等[31]又比較了ACT 和辯證行為療法的干預效果。配對比較結果顯示,與基線相比,兩組參與者對人格障礙患者的態度在干預后(P<0. 001)和隨訪中均有顯著改善(P<0.002),但兩組之間無交互作用,表明 ACT 和辯證行為療法具有相同的干預效果。
3 討論
3.1 結果歸納
綜合上述文獻評價,本研究結果顯示ACT 治療無論是對自我病恥感還是對公眾病恥感都有一定的改善作用,與Masuda 等[32]學者的系統評價結果(ACT 對減少病恥感和偏見有效)相似,這是令人欣慰的結果。但幾項研究[28,30-31]組間差異不明顯,未來需要更多研究來檢驗ACT 與其他干預措施之間的差異。
3.2 納入文獻質量
本研究符合納入標準的研究有7 篇,所有研究在隨機化、分配隱藏和盲法的使用上都存在缺陷,因此文獻質量學評價結果全部為B 級,總體質量不高,未來的研究應該采用嚴格的隨機化方法和盲法,并報告足夠的分配序列隱藏,以便更精確地調查ACT 的干預效果。
3.3 研究過程
7 項研究中的研究對象相對分散且樣本量較小,從側面反映出,ACT 在病恥感領域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其治療效果有待進一步驗證,當然也說明ACT 心理治療模型是一個跨診斷模型,也就是說ACT 適用于多類人群。各研究中ACT的干預頻次、時長差異較大,從150min 至每周多次不等,但干預都產生了類似的結果,說明ACT 治療時不存在劑量-反應關系,這提示ACT 治療師和研究人員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更加靈活地對研究對象實施ACT 治療。3 項[24,30-31]的樣本流失率較高,未來的研究可以增大樣本量來減少失訪偏倚。
3.4 干預持續效果
雖然所有與研究中ACT 干預的效果都持續到了隨訪結束,但也有一些異處,Hayes 等[29]人的研究中,ACT 組在干預后并沒有立刻顯示出效益,在隨訪時效果才顯示出統計學差異;Luoma 等[24]的研究發現,雖然干預結束時ACT 組的病恥感有所下降,但相比于隨訪時下降的幅度較低,也就是隨訪時ACT 組患者的病恥感下降幅度更為顯著;另外,Masuda 等[28]發現,盡管與基線相比,每個測評點研究對象的污名化態度都有所下降,但從干預后到隨訪期間,病恥感有所回彈。因此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闡明ACT 干預后病恥感的變化軌跡,并確定這種變化是否存在人群差異(例如Masuda[28]研究中隨訪時結果的反彈是否與大學生群體接觸病患的機會少,對病恥感的危害了解不多且感觸不深、同理能力較低等有關)。
4 局限性
本研究局限性:①本研究納入文獻質量偏低,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研究結果的可信度;②納入的各研究在研究人群、干預實施時間、測評工具、隨訪時間等方面均有些許不同,異質性大,故未對結果進行量性分析,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結論的推廣;③未檢索相關灰色文獻,這可能會導致選擇偏倚的增加。
5 結論
總而言之,雖然由于現有研究數量少、質量低和某些結果的不一致等原因,尚不能確定ACT 治療對病恥感的有效性,但本系統綜述強調了 ACT 干預是改善病恥感的一項有前景的治療措施。未來有必要在多類人群中進行更大規模、更高質量的隨機對照試驗來確認 ACT 在病恥感領域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