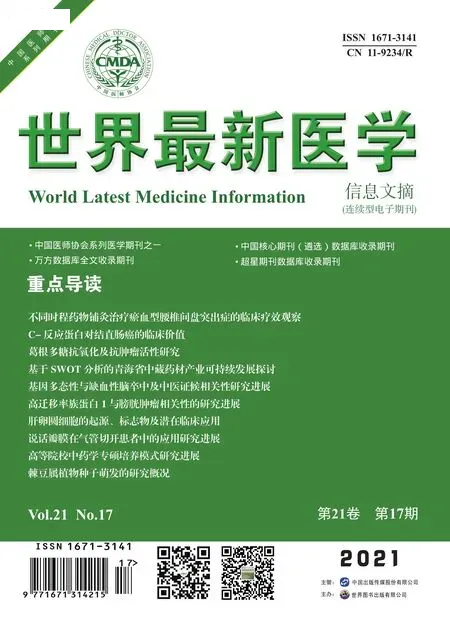從“虛瘀痰飲”論治心律失常
卞沐柳,俞興群
(1.安徽中醫藥大學,安徽 合肥 230012;2.安徽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安徽 合肥 230012)
0 引言
心律失常是指由心臟起搏和傳導功能障礙而引起的心臟激動起源部位、節律、頻率或傳導速度或者激動的次序的異常[1]。心律失常在各類人群中均有發病報道,其發病率呈逐年上升趨勢。盡管現代醫學關于心律失常的發病機制及治療等多方面取得諸多成就,但依然存在著許多難以治愈的頑固性心律失常和很多患者難以耐受的不良反應,同時抗心律失常藥的不當使用,往往也會導致心律失常。中醫學術遠源流長,在政府政策積極支持和引導下,我國中醫藥事業發展日漸成熟,歷朝歷代醫家學者關于診治心悸病證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經驗財富,通過系統整理中醫古籍臨床文獻及相關臨床研究,中醫藥對該病的治療有明顯的療效,且不良反應少,日益受到廣大患者的認可和支持。自古以來,中醫學并未提出心律失常這一具體病名,根據其臨床表現,大多歸于心悸,少數歸于胸痹、怔忡、脈結代、厥證等范疇。當代醫家普遍認為心悸的發病機制有虛實之分,虛者多為氣、血、陰、陽虧損使心失滋養;實者多由水飲、痰火、血瘀致氣血運行障礙而發此病。
1 病因病機
心悸的發生多因久病素體虛弱、飲食不節或無度、情志失和、邪氣侵犯、他病傳變、用藥不當等,以致陰陽氣血虧損,心神失養,心行血無力,或內生痰、飲、血瘀痹阻心脈,心神不安而發心悸。當今社會,人們勞動強度大,工作內容多,精神壓力高,心理承受能力弱,飲食不潔,起居無常,晝夜顛倒等均使心律失常起病顯著增加。心悸的病機常因陰陽氣血虧虛,心失所養,或外邪擾亂心神,致使心神散亂,悸動不安。其病位在心,但其發病與脾、腎、肺、肝四臟功能失調密切相關。古人的諸多著作中均有對心悸發病病因病機的相關記載。早在《陰陽十一脈灸經》中有言“心惕惕恐人將捕之”,這一描述與心悸病證頗為吻合。《素問》指出:“一陽發病,少氣,善咳,善泄,其傳為心掣,其傳為隔。”這對心悸的臨床癥狀表現做出了詳細描述,強調陽虛外感邪氣而致病;《傷寒雜病論》中有心動悸、心下悸等相關記載,分為內傷和外感兩類,其中以傷寒致心悸的描述較多;《醫宗金鑒》曰:“發汗過多,外亡其液,內虛其氣,氣液兩虛,中空無倚,故心下悸,惕惕然不能自主。”主張用桂枝甘草湯治療陽虛水飲型心悸。《千金寶要》的作者認為心悸的病因主要以氣血虛弱、風邪內擾為主;《素問玄機原病式·火類》中強調火邪可作悸,明確指出痰火在心悸中致病的重要作用。鄧鐵濤[2-4]認為,對心悸首當辨明病位,病機次之。病位雖在心,實際上是標實本虛之癥,以虛實多并存,但亦有先后緩急之分。諸臟腑間相互協調作用保證氣血的正常運行,只有脾胃功能的正常,才能保證氣血生化之長久,其功能失調則氣血乏源,運行不暢。心氣可推動血行于脈中,但其動力則源于宗氣,宗氣由自然清氣和水谷精氣相互結合而成,脾胃收納水谷其生理功能正常則宗氣足。因此脾胃為氣機運行的重要所在,若脾胃失運,可致水濕內停成飲成瘀,阻礙血之運行。故脾胃病變可連及他臟而共同引起心悸。朱良春[5]認為心、肝兩臟共同調節神志和血脈,而心悸、怔忡除自身臟器致病以外,與肝的疏泄功能關系密切。氣滯日久生瘀,心脈不暢,怔忡、驚悸作矣。趙志剛[6]認為心悸以血虛生瘀,邪氣侵犯為主要病因,心主神志,上通于腦,情志失和、煩勞過度、夜寐不安等因素均可誘發心悸。正所謂驚則氣亂,恐則氣下,驚恐而使心神外越不守于內,亦出現心悸。顧佳等[7]認為臟氣虧損,氣血不足,陰陽失和,瘀血可致心悸,病程日久者除心悸外,常兼有腎經虧虛癥狀。俞師認為心悸的病因多與外邪侵擾、情志刺激、久病或過勞體虛、治療用藥不當等相關;病位明確在心,其發病與其余四臟的功能失調密切相關,病機亦有虛實之分,既可因虛癥而發實癥,又可因實癥而發虛癥,最終致虛實夾雜的復雜病情。虛者多見于氣、陰虧損或心陽不足而發生心悸,實者多見于痰、飲、瘀血停滯于體內,致氣血運行滯澀而發心悸。《景岳全書·怔忡驚恐》認為陰虛可致宗氣生化乏源,無力推動心血運行,日久可致氣血虛衰,因此,氣陰兩虛為心悸患者疾病始終的常見證型,治療此證應善用益氣、養陰之法;在心悸患者中,氣血不足者常伴有痰濕、血瘀,正所謂“諸痰者,血脈壅塞,飲水積聚而不消散,故成痰也”,《諸病源候論》中這句話明確指出了痰與瘀在疾病發展過程當中的相關性,因此,治療心悸,當重視痰瘀的預防與治療;而水飲是人體水液代謝的病理產物,心腎陽虛,水液氣化功能異常,易生水飲,心屬火而惡水,飲停心下,則心不安,而發為悸,因此,對于陽虛水飲型患者當注重從心腎論治以溫陽化飲而治心悸。簡而言之,本病病機可概括為“虛”“瘀”“痰”“飲”四字。人體各臟腑之間在生理、病理上密切關聯,故其治療不能僅治心,還須重視整體辨證,標本兼治,方才是治療心悸的根本所在。
2 辨證分型,治療加減
氣陰兩虛:心血不足,無以濡養自身,日久全身氣血運行無力,加重陰液消耗;腎陰日漸不足,上制心火功能下降,導致水火失濟或肺氣虛損,無力輔心行血;情志失和,肝氣郁滯,氣滯則血瘀,心主神志,心脈運行不暢則心神受擾均可見心悸不寧兼神疲乏力,氣短懶言,暈眩眼花,五心煩熱,口干渴,舌紅,少苔,脈浮數。治宜益氣養陰,安神定悸,方選炙甘草湯與當歸六黃湯加減:炙甘草12g,桂枝9g,太子參10g,阿膠6g,麥門冬10g,大棗10g,當歸6g,生地黃6g,熟地黃6g,知母12g,黃芪12g;太子參益心氣,以滋氣血生化之源;知母可瀉火而不傷陰;俞師善用黃芪,自古黃芪為補氣之要藥,可補脾胃之氣,使氣血生化不絕,以滋養六腑五臟。同時也能活血逐瘀,可謂補氣之佳藥。當歸養血增液,血充以助生氣兼可制約心火。丹參既可清心火有可活血祛瘀,取其補而不留瘀之意,心血可生則悸動可止;生地、阿膠、麥冬、五味子、酸棗仁可助心陰化生,使心血充沛;俞師善用煅龍骨、煅牡蠣,取鎮心安神之效,神安則夜寐佳,精神內守,病可愈;氣虛較重可加人參、白術,益氣健脾,進一步輔助氣血生化;陰虛較重可加天冬、熟地、知母、黃柏滋陰清熱,以制心腎陰虛火旺。
陽被遏而發心悸:可見心悸頭暈,胸痞滿悶,腰膝酸軟,納呆食少,渴不多飲,小便少或下肢浮腫,舌淡胖,苔白,脈弦滑。治宜溫陽化飲,健脾利水,寧心安神,方選苓桂術甘湯合真武湯加減:附子12g,茯苓30g,桂枝5g,炒白術10g,甘草6g,澤瀉12g,黃芪10g,郁金6g,煅牡蠣30g,白茅根30g,丹參10g,豬苓15g,干姜6g;桂枝配甘草為“辛甘化陽”之法,用于振奮心陽,補其不足。俞師善用桂枝、白術配茯苓:桂枝可溫陽化氣,平沖降逆,引水飲致下焦;茯苓健脾利尿,助水液排出,可使體態輕盈,以利病情恢復;白術健脾燥濕,治生痰之源以治本,苓桂術三藥為伍則藥到飲除。附子、干姜,補火助陽,脾腎陽氣充足以利水液氣化之功,陽盛則飲可化;若兼惡心嘔吐者加砂仁、厚樸、生姜、半夏,增強降逆止嘔之功。本證急則治其標,本方以利尿( 健脾利尿) 為切入點,水飲凌心證宜快速緩解癥狀。
痰瘀互結:久病素體虛弱,飲食不節、無度,情志失和,或邪毒侵襲于內,皆可損傷心脾腎三臟,使津液輸布功能失司,津停可生痰,痰濁內阻,血之循行滯澀,致瘀血停聚,此為“由痰生瘀”;或瘀血停滯,可致氣機失和,津液輸布無力,停滯日久則結為痰,此為“由瘀生痰”。此二者終可形成“痰瘀互結”之狀況。癥見心悸不安,氣短無力,心胸刺痛,舌暗紅,苔薄膩,脈細或結代。俞師認為痰瘀互結病因各異,則治法不同。因氣陰兩虛而致痰瘀可見氣短乏力、眩暈、健忘、失眠,方選炙甘草湯和溫膽湯加減:以益氣養陰、化痰祛瘀;自汗甚者加浮小麥、煅龍骨可固表止汗。因肝腎陰虛而至痰瘀者,可見眩暈,耳鳴,面目紅赤,五心煩熱,腰膝酸軟,方選左歸丸和導痰湯加減,補肝腎,化痰瘀,瘀血較重者加川芎、桃仁、紅花,川芎重理氣,氣順則血行無阻,瘀不可留,桃仁紅花增強活血;痰癥熱象明顯者加南北沙參、膽南星、瓜蔞仁,以奏清熱化痰之功。因心脾陽虛而至痰瘀者,可見食少、腹脹、納呆、痰多,方選參苓白術散合二陳湯加減,以通陽行血、理氣化痰;兼嘔吐者可加砂仁、豆蔻、谷芽理氣消痰和胃。
3 病案舉例
患者,女性,58 歲,2019 年03 月20 日初診。患者因“心慌1 月余,眼瞼、面部水腫5 天”前來我科就診;1 月前,患者在突然出現心慌不適,未予重視及治療;3 天前患者發現眼瞼、面部水腫,遂來門診就診,病程中偶有頭暈乏力,納可,寐一般,二便調,舌淡,苔薄白,脈滑;測心率:56 次/ 分,律不齊,血壓:134/82mmHg。中醫診斷:心悸病- 水飲凌心癥,治以溫陽化飲,健脾利水,寧心安神,藥物如下:附子12g,干姜6g,茯苓30g,桂枝5g,炒白術10g,甘草6g,澤瀉12g,黃芪10g,郁金6g,煅牡蠣30g,白茅根30g,丹參10g,豬苓15g,7 劑,一日一劑,水煎服,囑平素規律起居,清淡飲食,注意控制情緒。
二診:2019 年03 月27 日,患者心悸發作頻率較前減少,眼瞼、面部水腫癥狀有所好轉。舌暗淡,苔薄白,脈滑。心率:65 次/ 分,律不齊,血壓:132/80mmHg,原方去白術、甘草、丹參,加川芎9g,茯苓、豬苓劑量改為各18g,繼服7 劑。
三診:2019 年04 月03 日,患者心悸不適癥狀明顯改善,眼瞼、面部水腫基本消失,精神狀態、睡眠較前明顯好轉,心率:72 次/ 分,律齊,血壓:128/78mmHg,納寐可,二便調,舌淡紅,苔薄白,脈沉,因患者血壓正常,遂去郁金,加丹參10g,繼服14 劑。繼觀1 月,未再發心悸,眼瞼、面部水腫已完全消失。本例病人,中醫辨證屬心悸- 水飲凌心證,治則為溫陽化飲,健脾寧心。該患者陽虛為本,水飲為標,治療隨癥靈活加減,同時也加入解郁安神藥物,標本同治,癥狀逐漸改善。俞師在治療心悸方藥中常加入龍骨、牡蠣、代赭石等沉降之性的藥物,可進一步安神定悸;同時加入丹參、川芎、桃仁等數味活血藥,使氣血運行通暢,滋養全身,以利病情恢復,常收效顯著;少量白茅根、茯苓、澤瀉等利尿之品,病人常感身體輕松,活動自如,對療效的認可度倍增。
4 現代藥理學研究
隨著國家中醫藥事業突飛猛進的發展,眾多研究者對臨床療效突出的中藥單體及復方制劑進行大量實驗研究,中醫藥治療心悸療效顯著,已受到廣泛認可,這為中藥運用于臨床實踐提供諸多理論依據。研究發現[8],黃芪注射液可緩解洋地黃引起的心律失常,其機制與改善受抑制的心肌Na+-K+-ATPase 活力有關。也有研究表明,太子參[9]中含有的有效成分太子參粗多糖,對心肌細胞有較強的保護作用。龍骨[10]中含有各種氨酸以及多種微量元素,龍骨中的Se 能夠保護細胞膜結構,豐富的Fe 則可以增強細胞的殺菌作用而提高人體免疫能力。因此黃芪、太子參、龍骨對久病氣陰兩虛型心悸患者尤為適合。文獻報道[11],從茯苓真菌中提取的茯苓素能夠促進尿液排出,這與古籍中其具有的利尿功能相吻合。又有研究表明[12]24- 乙酰澤瀉醇A、B 作為澤瀉促進尿液排出作用重要的活性成分,且其促進尿液排出的活性與所含的鉀離子的量呈正相關。藥理學研究表明[13-18],桂枝可增加冠狀動脈血液流量,對心臟的循環輔助作用明顯,故臨床很多方劑中運用桂枝治療多種心血管類疾病。實驗驗證,桂皮醛既可擴張中樞血管,又可擴張外周性血管,增強血液在脈管中的循環。因此茯苓、澤瀉、桂枝對治療水飲凌心的心悸患者效果顯著,為眾多臨床醫生治療水飲凌心證的良上佳品。鄒積隆等[19]的研究表明半夏具有促進痰液排出作用,且其祛痰作用與貯存時間呈正比。中藥川芎中的有效成分阿魏酸[20],可抑制血小板聚集,達到抗血栓的目的,對于改善血液循環作用也相當明顯。紅花[21]中含有80% 的亞油酸,能夠調整血液中膽固醇含量,對于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的治療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半夏、川芎、紅花對于生痰、瘀類疾病療效甚佳,臨床方藥中應用廣泛。
5 總結
心悸的病理特點多為本虛標實,虛實夾雜、病程日久反復。病機主要可概括為“虛”“瘀”“痰”“飲”。心悸的治療不能僅僅局限于治心病,須重視各臟腑的整體治療,堅持整體合參,標本兼治。近年來心悸病的發生呈逐年增長的趨勢,西藥治療心悸副作用較大,我國中醫藥對于心悸的治療歷史長而深遠,眾多醫家結合現代人的體質特征、生活環境制定了諸多方藥,辨證施治,效果顯著,受到廣大患者的認可和支持。在中醫治療心悸的過程中,我們既要貫通中醫藥基本理論,又要結合先進的現代科研成果與時代理念,充分調動主觀能動性去實踐、創新,促進中醫傳統理論與解決現實疾病之間的緊密配合,更好地推動中醫藥事業的全面發展。